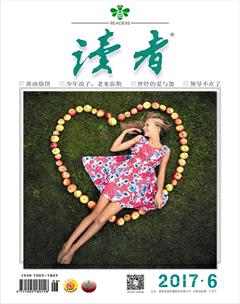紙鷂天高
2017-03-01 17:58:42鄧康延
讀者 2017年6期
鄧康延
風箏是春天的遙望,少年的向往。

一線在手,奔過曠野山丘,便在天地間活了。許多年前,我也在八百里秦川上放過風箏,“晴空一鶴排云上”,少年的心,歡喜又憂傷。在家國不安的年代,一紙風箏向天透氣。天俯視著孩子,孩子仰望著天,縹緲的事物有了牽掛。
風箏是春秋時期就有的游戲,是人類早年的“飛機”,古漢語里稱之為紙鳶或紙鷂,借代如翼的鳥兒。身形巨大者上面縛弦,風彈箏箏,猶如天琴,遂叫風箏。戶外清明,遠足踏青,可健身明目;戰時危城,傳遞信息,能振奮人心。
鏡頭拉遠了看,那飄拂的風箏不知是誰在放,也不知有誰在望,一直翻飛在東方的天空中。唐人有《紙鳶賦》:“代有游童,樂事末工。飾素紙以成鳥,像飛鳶之戾空。翻兮度,將振沙之鷺;杳兮空,先漸陸之鴻。抑之則有限,縱之則無窮,動息乎絲綸之際,行藏乎掌握之中……”史有這般形容,縱千年一線扯過,一些詞語生僻了,仍依稀得見云白風清,氣勢飛虹。
那時還有另一首學堂樂歌《紙鷂》唱道:“正二三月天氣好,功課完畢放學早。春風和暖放紙鷂,長線向我爺娘要。爺娘對我微微笑,贊我功課學得好。與我麻線有多少?放到青天一樣高。”
我可能是見過雁陣、也參與過風箏陣的最末一代。高樓、霧霾、污濁中的山河田疇,以及功課的重負和人心的躁急,都是大雁和風箏的死敵。我曾為居住城市的秋末讀書月寫過一首歌詞《云在青天書在手》,不知道在哪個環節一句詩眼被刪掉了:“長空雁過天有字,是誰佇立讀出秋。”每年歌聲響起,我會下意識地望望天,風箏還有,雁已難覓,佇立的人也被慌亂的人潮裹挾著,擁向東,擁向西。
青天一樣高的風箏、童心、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