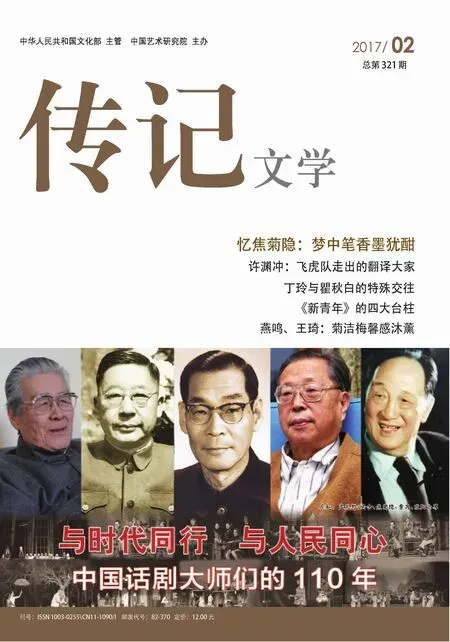丁玲與瞿秋白的特殊交往
文|林偉民
丁玲與瞿秋白的特殊交往
文|林偉民

選擇
隨著與丁玲、王劍虹兩位女性的頻繁來往,瞿秋白的個(gè)人情感波瀾迭起,沉默與憂郁也與日俱增。
后來,施存統(tǒng)老師告訴丁玲,瞿秋白承認(rèn)自己墜入愛河,但不肯吐露他愛的是誰。
猶疑不安中,丁玲跑去把此事告訴了王劍虹。而心神不寧的王劍虹要隨父親回四川老家酉陽。丁玲逼她把話講清楚,得到的卻是沉默。事后,丁玲氣得躺在床上苦苦思索:“兩年來,我們之間從不秘密我們的思想,我們總是互相同情,互相鼓勵的。她怎么能對我這樣呢?她到底有了什么變化呢?”
王劍虹的態(tài)度確如丁玲所云,是一種“變態(tài)”,這是兩年來摯友生活中未曾遇到過的。但,問題恰恰也出在這里——倘若丁玲尚處于情竇未開的年紀(jì),她可能對這類事“毫無感覺”;倘若她已經(jīng)婚配,那么作為過來人的她,也容易理解王劍虹的異常。然而,偏偏丁玲與王劍虹一樣正當(dāng)妙齡,同處于青春期階段。雖然丁玲剛到上海大學(xué)時(shí)對男女之事“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打算去想”,但情勢卻在不斷變化,況且像瞿秋白這樣一位風(fēng)骨挺拔、出類拔萃的男性突然出現(xiàn)在她面前,她怎么能做到視而不見、無動于衷呢?
丁玲對這方面的感情避而不談,在她晚年寫的那篇聲情并茂的紀(jì)念文章《我所認(rèn)識的瞿秋白同志》卻流露出蛛絲馬跡:
我正煩躁的時(shí)候,聽到一雙皮鞋聲慢慢地從室外的樓梯上響了上來,無須我分辨,這是秋白的腳步聲,不過比往常慢點(diǎn),帶點(diǎn)躊躇。而我呢,一下感到有一個(gè)機(jī)會可以發(fā)泄我?guī)讉€(gè)鐘頭來的怒火了。我站起來,猛地把門拉開,吼道:“我們不學(xué)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來!”立刻就又把門猛然關(guān)住了。他的一副驚愕而帶點(diǎn)傻氣的樣子留在我腦際,我高興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得意地聽著一雙沉重的皮鞋聲慢慢地遠(yuǎn)去。為什么我要這樣惡作劇,這完全是無意識和無知的頑皮。
我無聊地躺在床上,等著劍虹回來,我并不想找什么,卻偶然翻開墊被,真是使我大吃一驚,墊被底下放著一張布紋信紙,紙上密密地寫了一行行長短詩句。自然,從筆跡、從行文,我一下就可以認(rèn)出來是劍虹寫的詩。她平日寫詩都給我看,都放在抽屜里的,為什么這首詩卻藏在墊被底下呢?我急急地拿來看,一行行一節(jié)節(jié)啊!我懂了,我全懂了,她是變了,她對我有隱瞞,她在熱烈地愛著秋白。她是一個(gè)深刻的人,她不會表達(dá)自己的感情;她是一個(gè)自尊心極強(qiáng)的人,她可以把愛情關(guān)在心里,窒死她,她不會顯露出去來讓人議論或訕笑的。我懂得她,我不生她的氣了,我只為她難受。

瞿秋白
丁玲說的是實(shí)事真情。不過,她后來卻把自己當(dāng)時(shí)的“無聊”“惡作劇”“偶然”等情緒,歸結(jié)為一種內(nèi)心苦悶的“發(fā)泄”,“完全是無意識和無知的頑皮”之緣故。然而,正是這種“無意識”、近似“無知的頑皮”之宣泄,透露出丁玲心靈深處隱藏得很深甚至連自己一時(shí)也難以名狀的潛意識活動。
丁玲與瞿秋白相識于南京。當(dāng)時(shí)她和王劍虹剛離開令她們失望的上海平民女校,她們的老師施存統(tǒng)把正在南京代表中央?yún)⒓又袊鐣髁x青年團(tuán)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瞿秋白介紹給她們認(rèn)識。后來兩人跟隨瞿秋白進(jìn)入上海大學(xué)學(xué)習(xí)。在上海大學(xué)期間,丁玲對瞿秋白的感情趨向于雙重:既敬重又愛慕。不過,當(dāng)時(shí)她的感情變化尚處在一個(gè)量的聚集過程,因此暫時(shí)既不會令王劍虹覺察到(正如她覺察不到王劍虹一樣),又不易使她自己明確。當(dāng)秘密被施存統(tǒng)捅破,外部力量迫使她表態(tài)時(shí),雖有一瞬間的驚訝迸出,但接踵而來的則是更多的恍惚迷惘。“他到底會愛誰呢?”尋找最后的答案之過程,實(shí)際上也是丁玲的內(nèi)心由懵懂轉(zhuǎn)向清醒、由混沌轉(zhuǎn)向清晰、由潛意識轉(zhuǎn)化為意識的過程。性格樂觀、為人真率的丁玲喜歡事情明朗化,而不愿拖泥帶水。困惑中,她把消息傳遞給王劍虹,希望得到證實(shí)。她想快刀斬亂麻,誰知王劍虹卻以“沉默”應(yīng)對,這種不夠朋友的“變態(tài)”,著實(shí)讓丁玲生氣。
瞿秋白的到來也正是時(shí)候,恰好給煩躁不安的丁玲找到了一個(gè)內(nèi)心怒火的發(fā)泄口。這種移情遷怒,表面上是對王劍虹的暫時(shí)不悅,但實(shí)際上是對瞿秋白的不滿——原因似乎也只有一個(gè):瞿秋白選擇了對方而不是自己。強(qiáng)烈的失落感使她無法抑制自己,感情便不由自主地涌了出來。丁玲“并不想找什么”,恰恰說明她正“想找什么”,因而“偶然”中也蘊(yùn)含著“必然”。這無意識的舉動,折射出她對瞿秋白的愛意以及情感失落后的心理。
一旦真相呈現(xiàn),幻想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礎(chǔ)。丁玲隨即逐漸恢復(fù)常態(tài),她那樂觀豁達(dá)、熱情豪爽、俠義相助的性情也重新顯現(xiàn)。這種秉性,丁玲自己也時(shí)常能體悟到。她說:“過去我有時(shí)的確常為別人擔(dān)心而煩惱,而損害了自己,這是因?yàn)槲姨珶崆椋欢拢豢陀^,也太無辦法的原因。”其中談及的雖是他事,但丁玲的處世哲學(xué)、為人方式數(shù)十年一以貫之,她對王劍虹和對瞿秋白的感情,最后不也是采取了這種態(tài)度嗎?
接下來的故事就相當(dāng)簡單了。丁玲充當(dāng)了“紅娘”的角色,她要援救王劍虹跳出苦海,瞞著王劍虹去找了瞿秋白。然后,把王劍虹的詩交給瞿秋白,并催促他到小亭子間去找她,而自己則留在他的書房里。
等丁玲回到宿舍時(shí),一切都如她想象的那么美好,氣氛非常溫柔和諧,滿桌子散亂著瞿、王二人寫的字。丁玲知道他們是用筆談話的。瞿秋白要走了,丁玲從墻上取下王劍虹的一張全身像,送給了他……有情人終成眷屬。后來,瞿秋白為感謝丁玲,以一首詩相贈,贊她是“安琪兒”“赤子心”。

1931年2月,丁玲與母親、兒子在常德合影
“你是一個(gè)需要個(gè)展翅高飛的鳥”
1924年元月初,瞿秋白與王劍虹喜結(jié)良緣。這時(shí),正逢上海大學(xué)喬遷之喜,校舍搬至西摩路(今陜西北路)與南洋路(今南陽路)路口,于是,他們也將新居安置在附近的慕爾鳴路(今茂名北路)。那是一幢臨街的兩樓兩底的弄堂房子,施存統(tǒng)夫婦住在樓下統(tǒng)廂房,樓上正房住的是瞿秋白的二弟瞿云白。統(tǒng)廂房放著瞿秋白的幾架書,瞿秋白和王劍虹住在統(tǒng)廂房后面的一間小房里。丁玲住在過街樓上的小房里。娘姨阿董住在亭子間,施家也雇了一個(gè)阿姨,帶小孩、做雜事。丁玲與王劍虹一樣,按學(xué)校的膳宿標(biāo)準(zhǔn)每月交付十元。這樣的精心安排,丁玲知道其中也有瞿秋白對她的好意。
婚后沒有“蜜月”,瞿秋白身負(fù)使命,回廣州繼續(xù)參與籌備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大會通過了瞿秋白參與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nèi)容的宣言,確定了“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的三大政策,即著名的“新三民主義”。瞿秋白被選為候補(bǔ)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后,將暫留廣州一段時(shí)間。
瞿秋白思念著新婚的愛妻,幾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紋紙寫的信,還常夾著些詩。
沉醉于愛河里的瞿秋白和王劍虹,常常有所疏忽而把他們共同的好朋友丁玲冷落在一旁。但有時(shí)他們也怕丁玲寂寞,拉著她一起唱昆曲,瞿秋白教,丁玲和王劍虹跟著學(xué),以此打發(fā)漫漫長夜;有時(shí)他們怕丁玲冷,特地把瞿云白給他們買的一個(gè)燒煤油的烤火爐送到她房內(nèi);抑或怕丁玲孤單,到她那個(gè)小小的過街樓上去坐談。瞿秋白談鋒很健,常常幽默地談?wù)撐膲W事……惟有此時(shí),丁玲才會忘卻孤寂、冷清與憂傷。
可是生活總不能就這樣吹吹簫、吟吟詩,混將下去。即使是文學(xué),一時(shí)也難以慰藉丁玲寂寞的心。失落感、孤獨(dú)感與事業(yè)心混亂駁雜地充塞在她不安躁動的靈魂里。
一天,丁玲試探著問瞿秋白,將來究竟學(xué)什么好?干些什么?現(xiàn)在應(yīng)該怎樣做?瞿秋白不假思索地答道:“你么,按你喜歡的去學(xué),去干,飛吧,飛得越高越好,越遠(yuǎn)越好,你是一個(gè)需要展翅高飛的鳥兒……”
實(shí)際上,丁玲是一個(gè)頗有想法的姑娘,她時(shí)刻在審視著自己的前行足跡,并及時(shí)作出調(diào)整。她在詢問瞿秋白時(shí),其實(shí)早已籌劃好了自己下一站的目標(biāo):先回湖南休整,然后直接去北京。她已經(jīng)與在北京的周南女校的好友周敦祜、王佩瓊等約好,到學(xué)習(xí)氛圍濃厚的北京最高學(xué)府去繼續(xù)讀書深造。
當(dāng)丁玲把這個(gè)想法向瞿秋白、王劍虹提出時(shí),居然沒有遭到反對。這使她頗感意外和疑惑。大家俱沉默無言,仿佛都有無限的思緒。離別時(shí),瞿秋白和王劍虹誰都沒有為丁玲送行,娘姨阿董買了一簍水果,瞿云白送她上船。瞿、王二人的舉止似乎有悖常情,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興沖沖地來滬,凄慘慘地離滬,是丁玲始料不及的。來的時(shí)候,是浩浩蕩蕩的六個(gè)人;走的時(shí)候,是孤孤單單的一個(gè)人。倚著船欄,任憑風(fēng)浪吹打,往事不堪回首。丁玲想:十九年的韶華,五年來多變的學(xué)院生活,我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我只朦朧地體會到人生的艱幸,感受到心靈的創(chuàng)傷。我是無所成就的,我怎能對得起我那英雄的、深情的母親對我的殷切厚望啊!

瞿秋白書法作品
與革命失之交臂
關(guān)于人生歷程的第一個(gè)驛站——上海之行,丁玲本人曾經(jīng)如是說:“我不是突然轉(zhuǎn)變一下子跑到上海的,因?yàn)槲以缇陀袃A向革命的思想基礎(chǔ)。”
丁玲早先受母親與向警予等人的熏陶和影響,從小就確立了一個(gè)明確的意向,就是做一個(gè)革命的活動家,去探索改革中國社會之路。因此,她跟王劍虹跑到上海,進(jìn)平民女校,目的是找陳獨(dú)秀、李達(dá)干革命。但是,在這所由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親手創(chuàng)辦的培養(yǎng)婦女干部的學(xué)校里,丁玲未能像她的同學(xué)王一知那樣加入青年團(tuán)、共產(chǎn)黨;后來,又進(jìn)入由共產(chǎn)黨負(fù)責(zé)的上海大學(xué),丁玲亦未能像她比較接近的社會學(xué)系同學(xué)楊之華、張琴秋那樣加入共產(chǎn)黨。這究竟是何故呢?

1923年,丁玲(左)與王劍虹在常德
在諸多的原因中,首先是丁玲對部分共產(chǎn)黨人已經(jīng)有了一個(gè)“先入為主”的印象。1923年下半年,法國歸來的向警予曾找過丁玲談話,內(nèi)容是關(guān)于她的“孤傲”問題。顯然,共產(chǎn)黨內(nèi)外有不少人對丁玲的這種態(tài)度持有意見。丁玲回答說:“我不是對什么人都有說有笑的。” 在共產(chǎn)黨人中,丁玲相當(dāng)敬佩向警予、瞿秋白等一批實(shí)事求是、腳踏實(shí)地、無私無畏的同志,但她對某些漂浮在上層、喜歡夸夸其談的少數(shù)“時(shí)髦”的共產(chǎn)黨員(特別是女黨員)頗有意見,因此,才會對他們鄙視、看不慣甚至有意疏遠(yuǎn)。
其次,丁玲對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chǎn)黨有一個(gè)逐步認(rèn)識的過程。由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剛開始不久,中國共產(chǎn)黨還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馬克思主義尚未在國內(nèi)廣泛傳播,大量涌入的各種西方主義、思潮魚目混珠。有人在向警予面前說丁玲有無政府主義傾向,茅盾也曾明確地說過,丁玲、王劍虹“她們?nèi)泻軡夂竦臒o政府主義的傾向”。丁玲本人也直言不諱,與美國記者斯諾夫人在延安時(shí)的談話中,就詳細(xì)地談到她在上海大學(xué)時(shí)曾經(jīng)讀過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和廖抗夫的劇本《夜未央》,還讀過巴金在巴黎時(shí)寫的小說《新生》《滅亡》,也曾經(jīng)瞞著一同來滬求學(xué)的湖南同學(xué),參加北京大學(xué)學(xué)生組織的無政府主義活動。丁玲接近他們,是因?yàn)樗麄冊诙×嵫壑惺抢硐爰摇獕粝虢⒁粋€(gè)廢除政府的烏托邦新村。
如果說,丁玲對上海平民女校不像個(gè)正規(guī)學(xué)校而是個(gè)講習(xí)班而不滿意,是她離校的原因之一的話,那么她進(jìn)入上海大學(xué)后,這個(gè)原因應(yīng)該說不復(fù)存在了。然而,是什么原因促使她最后還是離開了上海大學(xué)呢?
其中,丁玲與瞿秋白關(guān)系的變化不容忽視。在上海大學(xué)讀書時(shí),丁玲不是沒有遇到過像向警予、瞿秋白這樣真正的共產(chǎn)黨員。然而,奇怪的是,近在咫尺,丁玲為什么沒有在政治上向他們靠攏,甚至連一個(gè)進(jìn)步的表示都沒有?
籠統(tǒng)地把這種情況理解為丁玲“有極端的反叛情緒”,未免顯得膚淺空泛。除了上述幾個(gè)方面的原因外,還有一個(gè)屬于私人的感情問題,即瞿秋白與王劍虹的結(jié)合,是丁玲情感的轉(zhuǎn)折點(diǎn)。她的求知欲由積極亢奮轉(zhuǎn)向消極厭煩,她的思想情緒由巔峰跌至谷底,她的心理由正常態(tài)趨向反常態(tài)。她不但沒有興趣再跟瞿秋白學(xué)俄文,而且就連對上海大學(xué)慕爾鳴路的住處都感到厭倦。丁玲與王劍虹本來是形影不離、親密無間的摯友,此時(shí)兩人的關(guān)系卻在無形之中拉開了距離。兩人沒有什么思想原則方面的分歧,“但她完全只是秋白的愛人,而這不是我理想的”,這是丁玲晚年說的一句話。從表面上看,她似乎在對王劍虹放棄理想、放棄抱負(fù)而陷于愛情之中表達(dá)自己的看法,正像剛進(jìn)平民女校時(shí)她不滿意王一知忘卻工作問題而先戀愛一樣。然而,透過表象便能窺見丁玲的情感處于失衡的狀態(tài)。王劍虹在丁玲的人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丁玲的自我形成史上具有僅次于母親的重要意義”,“是丁玲的精神保護(hù)者”。瞿、王二人的結(jié)合對于丁玲而言,似乎從她身邊奪走了摯友益友,一時(shí)難以適從,她無法面對一種姐妹加知己般的感情被活生生地剝離,她失去了一種精神支柱與依賴的力量;從另一個(gè)角度看,瞿秋白又是她見到過的最有學(xué)問、最有魅力的男人,瞿、王二人的結(jié)合最終導(dǎo)致了她心中所敬慕的青春偶像的消失,而掠走這尊偶像的卻恰恰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丁玲處于二律背反的矛盾中,一邊是她的摯友,一邊是她的導(dǎo)師,結(jié)果兩個(gè)中任何一個(gè)都攀不上,愛也不得,恨也不得。她選擇在瞿、王二人熱戀時(shí)抽身而去,離開了摯友,離開了朝思暮想的革命中心上海。丁玲心理上的失落感由此可見一斑。

1938年,丁玲在延安
王劍虹離世之謎
丁玲回到了常德母親的身邊,在幽靜、無所思慮的閑暇之中度暑假。
一天,丁玲接到王劍虹的來信,信寫得極為簡短,只說她病了。丁玲并不經(jīng)意,因?yàn)樵缇吐犝f她身體有些不適,收到信后丁玲還認(rèn)為是由于自己不在她身邊才有些身上的敏感之類的病癥而已。很快,她便被信后的附言給弄疑惑了。附言是瞿秋白加的:
你走了,我們都非常難受。我竟哭了,這是我多年沒有過的事。我好像預(yù)感到什么不幸。我們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
丁玲的離開,瞿秋白與王劍虹“非常難受”,是情理中的事情。意想不到的是,瞿秋白“竟哭了”,他為什么而哭?是為丁玲的離走,抑或是預(yù)感到什么可怕的不幸,還是兩者兼而有之?
半個(gè)月后,丁玲忽然收到上海來的電報(bào),電文寫著觸目驚心的八個(gè)字:“虹姐病危,盼速來滬!”
丁玲驚愕不已,像做夢似的難以相信。她與王劍虹分別僅一個(gè)月,怎么一下子就病情惡化了?瞿秋白哪里去了?為什么不是他而是劍虹堂妹來電?
惶然不安中,丁玲星夜兼程趕往上海。慕爾鳴路已人去樓空,王劍虹的靈柩停放在四川會館。瞿秋白去廣州參加孫中山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王劍虹的兩個(gè)堂妹只是以淚臉相迎,瞿云白也是六神無主,不知所措。
原來,丁玲離滬后,王劍虹的病突然趨于嚴(yán)重。她患的是肺病,婚后的生活加速了病情的發(fā)展。最初醫(yī)生誤診為懷孕的反應(yīng),待確認(rèn)為肺病時(shí)已非藥物所能救治了。空洞早已形成,血管開始破裂,又并發(fā)胸膜炎。
王劍虹患病期間,也是瞿秋白工作最緊張的時(shí)候。國民黨右派勢力聯(lián)名上書孫中山“彈劾”幫助國民黨改組的共產(chǎn)黨人。共產(chǎn)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奮起反擊,瞿秋白穿梭奔波于滬穗兩地。據(jù)楊之華回憶說:“王劍虹在病重的時(shí)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邊,不要離開她。秋白也很愿意多照顧她。一回到家,就坐在她的床邊,陪伴著她。在他的長方形書桌上,常常整齊地放著很多參考書,他就在那里埋頭編講義,準(zhǔn)備教材或?yàn)辄h報(bào)寫文章。從王劍虹病重到去世,我們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與平時(shí)不同。” 瞿秋白在穗期間,將延醫(yī)求藥、護(hù)理劍虹的事托付給不久前從杭州來上海大學(xué)求學(xué)的三弟瞿景白。7月間,王劍虹病情急劇惡化,不久就去世了,時(shí)年22歲。瞿秋白悲痛萬分,離滬前,用白綢布包著愛妻生前的那張定情照片,并留給丁玲。照片背后題了一首詩,開頭寫著:“你的魂兒我的心。”據(jù)丁玲生前解釋,她平時(shí)常常叫劍虹“虹”,秋白曾笑說應(yīng)該是“魂”,而秋白愛叫劍虹“夢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譯音。詩的意思丁玲只記得個(gè)大概,意思是說:丁玲送給我的是她的“魂兒”,而我的心現(xiàn)在卻死去了,我難過,我對不起劍虹,對不起我的心,也對不起丁玲。
丁玲無法接受這樣一個(gè)殘酷的結(jié)局。她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回事,為什么這么快劍虹就命歸九泉了?是誰奪去了她如花的生命?此時(shí),丁玲猛地回想起王劍虹去世前寫給她的那封信,全怪自己的疏忽,或許當(dāng)時(shí)王劍虹還要向她傾訴些什么。丁玲壓抑不住自己的情緒,用一種近乎小孩的簡單感情去尋覓王劍虹臨終前留下的感情陳述。結(jié)果,片言只語都未曾留有,劍虹就這樣默默無言地離去了。
丁玲本已受傷的心靈又被深深地劃了一刀。她與王劍虹的堂妹一同坐船到北京去了。臨走時(shí),她一個(gè)字也沒有寫給瞿秋白,雖然他離滬前曾給丁玲留下一個(gè)通信地址。
丁玲的心不斷地責(zé)怪著瞿秋白,她認(rèn)為王劍虹死于肺病,而這病源卻是從他身上傳染來的。她無法原諒瞿秋白,并下了決心,與瞿秋白的關(guān)系也終將因王劍虹的死而割斷!
即使這樣,丁玲的心里仍然懸著一個(gè)疑團(tuán):劍虹是怎樣死的?
“謎似的一束信”
在北京西城辟才胡同補(bǔ)習(xí)學(xué)校學(xué)習(xí)期間,丁玲時(shí)常收到瞿秋白的來信。這段時(shí)間并不長,但書信頻繁,收到的來信有十來封。信的內(nèi)容寫得隱晦含蓄,許多地方讓人似懂非懂,不好理解。丁玲把這些信稱之為“謎似的一束信”。
丁玲說,這些信“沒有宏言讜論,但可以看出一個(gè)偉大人物性格上的、心理上的矛盾狀態(tài)”。她恍惚地感覺到秋白有難言之苦。瞿秋白當(dāng)時(shí)處于何種矛盾狀態(tài)呢?他想要向丁玲傾吐的會是些什么呢?或許,如王劍虹之死一樣,也是一個(gè)“謎”。

丁玲
是瞿秋白挨批受委屈了,還是國共合作期間受到非議和排斥?我認(rèn)為也不完全盡然。從1923年由文學(xué)轉(zhuǎn)向政治以來,至1930年年末,瞿秋白雖然有“被另一種人生觀念的鐵律”所束縛之苦悶,雖然有與黨內(nèi)右傾機(jī)會主義作斗爭之艱難,但總的來說,最初階段他處于順境,是黨中央主要負(fù)責(zé)人和黨的政治活動家。他與丁玲通信時(shí)正擔(dān)任著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等重職,正在從事國共合作的大事業(yè)。況且,瞿秋白為人謹(jǐn)慎細(xì)致,遵守原則,從不在丁玲面前談及政治之類的事。因此,向丁玲訴說這方面苦楚的可能性很小。
值得注意的是,丁玲本人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這個(gè)情況,那就是幾乎每封信,瞿秋白都要責(zé)罵自己,說他對不起劍虹;還說任何人都不配批評他,因?yàn)樗麄儾涣私馑挥刑焐系摹皦艨伞辈庞匈Y格批評他。類似的話,瞿秋白后來也說過。他說,只有兩個(gè)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評他,一個(gè)是天上的女子王劍虹,一個(gè)是世上的女子楊之華。 瞿秋白為什么口口聲聲要譴責(zé)自己,說對不起王劍虹?他有什么事對不起王劍虹呢?后來為什么又說只有兩個(gè)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評他,又把楊之華扯了進(jìn)來?從信的意思與寫信人的口吻進(jìn)行主觀推測,似乎這“謎似的一束信”屬于個(gè)人的私事方面的可能性較大。
還有一個(gè)問題,信中瞿秋白并沒有直爽地向丁玲講出他的心里話,那他為什么還要如此頻繁地給丁玲寫信?難道像丁玲解釋的,只是把她當(dāng)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諒他的一個(gè)對象而絮絮而談嗎?
丁玲曾經(jīng)發(fā)誓要與瞿秋白斷絕關(guān)系,現(xiàn)在她忘了自己的誓言,帶著茫然而迫切的心情,重新拿起筆給他回了幾封信,談與王劍虹的真摯的感情,談她的文學(xué)上的天才,談她的可惜的早殤,談她對自己的影響以及對她的懷念。然而,丁玲憑著一種直覺,恍惚地感到,自己所談的,并非他所想的。但,她無法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為什么所苦。
這年初冬,瞿秋白來到北京,特地到辟才胡同補(bǔ)習(xí)學(xué)校來找丁玲,足足等了兩個(gè)鐘頭。瞿秋白是個(gè)大忙人,居然如此耐心地等丁玲,并留下一封信,要丁玲按信上的地址去找他。此番舉動似乎暗示著他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告訴丁玲。
于是,丁玲匆忙吃了晚飯,坐車趕到前門的一家旅館。瞿秋白偏又不在,只有瞿云白在房內(nèi)。不知是故意還是無意,瞿云白興沖沖地從他哥哥的什物中翻出一張女人的照片給丁玲看。這個(gè)女人就是楊之華。
一見到楊之華的照片,丁玲便完全明白了,她再也沒有興趣見瞿秋白了,不等他回來就告辭回校。
丁玲對瞿秋白的怨氣與日俱增,她再也沒有去前門旅舍,她不想再見到他。而瞿秋白或忙于工作或有難言之苦,也沒有再來看望丁玲。兩人同在一個(gè)北京城,而且住地相距不遠(yuǎn),卻如同陌生人不相往來。
數(shù)月來,丁玲與瞿秋白往來僅僅是因?yàn)樗庇谝私馔鮿缛ナ赖那闆r嗎?如果僅此一點(diǎn),丁玲見到楊之華的照片,為什么要如此失望沮喪地離開,再也不愿見到瞿秋白呢?丁玲曾說,楊之華與瞿秋白的戀愛,是在王劍虹死后,這是無可非議的。既然如此,丁玲為什么要這么沖動?難道這又是“一種近乎小孩的簡單感情”嗎?丁玲后來說:“我個(gè)人常常被一種無法解釋的感情支配著。”這“無法解釋的感情”又是一種什么樣的感情呢?
不久,丁玲忽然收到楊之華從上海發(fā)來的一封給瞿秋白的信,請她轉(zhuǎn)交。丁玲平時(shí)與楊之華沒有書信往來,此信為什么非要丁玲轉(zhuǎn)交不可?是楊之華不詳瞿秋白北京的住址,還是信件直接郵遞不安全?顯然這兩者都不是。楊之華是知道瞿秋白的行蹤的,否則她不會請久不見面的丁玲轉(zhuǎn)交信件。如是黨內(nèi)重要信件,既不會通過郵寄,也不可能叫非黨員的丁玲轉(zhuǎn)交。信件的內(nèi)容只能是一般的家常話和私人的事情。看來,此信的內(nèi)容并不重要,要緊的倒是其形式。丁玲說:“我本來可以不管這些事。”此話事出有因,丁玲在前門旅舍所見到的那傷感的一幕,豈能是過眼煙云,她對瞿秋白的怨氣猶在,對他感情上的疙瘩尚未解開。最終丁玲還是克制了自己,請補(bǔ)習(xí)學(xué)校同學(xué)、中共黨員夏之栩幫助她找到瞿秋白。瞿秋白當(dāng)時(shí)正在蘇聯(lián)大使館的一幢宿舍里開會。接下來的情節(jié),丁玲有一段回憶,讀起來頗有意味。她說:

1924年,瞿秋白與楊之華在上海
秋白一見我就走了出來,我把信交給他,他一言不發(fā)。他陪我到他的住處,我們一同吃了飯,他問我的同學(xué),問我的朋友們,問我對北京的感受,就是一句也不談到王劍虹,一句也不談楊之華。
不難看出,瞿秋白“一言不發(fā)”,其實(shí)是一種尷尬,顯然是一種不想讓丁玲知道更多內(nèi)情的尷尬,這就是丁玲后來感覺到的“一句也不談楊之華”的緣故。王劍虹也“已成為過去”。那么,瞿秋白在關(guān)心著誰呢?丁玲本人難道沒有察覺到嗎?非也,丁玲非但感受到了,而且多了一份靈性,多了一個(gè)心眼。她在觀察著瞿秋白的舉止,窺探著他的心事。只是兩人都在打啞謎似的,誰也不曾言明。
我好像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gè)老人,靜靜地觀察他。他對楊之華的來信一點(diǎn)也不表示驚慌,這是因?yàn)樗欢ㄓ邪盐铡?/p>
讀至此,仿佛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沒有出場的第三者楊之華在“觀察”著瞿秋白,同時(shí)也在向傳遞者丁玲“明示”著什么;而丁玲在現(xiàn)場直接地觀察著瞿秋白,希望能得到真實(shí)的回報(bào)。至于中心人物瞿秋白,他的態(tài)度是至關(guān)重要的。丁玲所看到的瞿秋白的態(tài)度連同先前他寫給丁玲那一束謎似的信一樣,都顯露出他在“性格上、心理上的矛盾狀態(tài)”。很顯然,瞿秋白在選擇,在沉思,在猶豫,在徘徊……
當(dāng)晚,瞿秋白約丁玲一同去看戲,是由梅蘭芳的老師陳德霖主演的京劇。其實(shí),看戲只是其次,無非是瞿秋白的一種姿態(tài),一種感情上的含蓄表露。那時(shí)的戲院實(shí)行男女分坐制,丁玲獨(dú)自一人坐在秋白、云白兄弟對面的包廂內(nèi)。說是看戲,此時(shí)此刻丁玲根本沒有心思看戲,她實(shí)在無法忍受這種悶葫蘆似的尷尬場面,百思不得其解。瞿秋白為什么要給她寫那一束謎似的信?丁玲心情煩躁,甚至連戲院里的嘈雜都討厭起來,不等戲演完,便寫了一張字條找茶房轉(zhuǎn)遞過去,再一次地不辭而別,獨(dú)自回校。
從此,丁玲再也沒有主動與瞿秋白聯(lián)系過。
“對不起王劍虹”
王劍虹的死,瞿秋白是抱著終生遺憾的,他不斷譴責(zé)自己也在情理之中。雖然,王劍虹患的是肺病,有家庭傳染病史可循,她的母親和姐姐都是患肺病先后過世的,但瞿秋白總認(rèn)為妻子患的病是自己傳染給她的,這是他的罪過。雖然,瞿秋白摯愛著王劍虹,很想能多些時(shí)間陪伴孤寂中的愛妻,無奈他“早已接受了另一種人生觀念的鐵律”,因而無論是新婚還是她病重階段,他都無法留在她身邊。這種苦衷又能向誰訴說,又有誰能理解呢?
看得出來,強(qiáng)烈的內(nèi)疚感、負(fù)罪感和懺悔意識折磨著瞿秋白的靈魂。然而,僅是這樣去理解心靈如此豐富、如此繁復(fù)的瞿秋白,未免簡單了點(diǎn)。我總感覺到,在瞿秋白的自我譴責(zé)里,無疑還包含著另一層意思,這也是瞿秋白最難啟齒的。
瞿秋白在王劍虹死后四個(gè)月,與他的學(xué)生楊之華結(jié)婚了。這四個(gè)月也是他與丁玲之間的書信往來最頻繁的四個(gè)月。
1924年1月,楊之華與瞿秋白在上海大學(xué)相識。其時(shí),瞿秋白剛從廣州回到上海,給上大社會學(xué)系的學(xué)生講授《社會科學(xué)概論》和《社會哲學(xué)概論》。瞿秋白給楊之華最初的印象是沉靜嚴(yán)肅、不茍言笑。后來,楊之華和同學(xué)張琴秋被一同派到國民黨上海執(zhí)行部青年婦女部協(xié)助向警予工作。由于與王一知是婦女部同事的關(guān)系,楊之華結(jié)識了王一知昔日的同窗好友、正在文學(xué)系學(xué)習(xí)的王劍虹和丁玲。此時(shí),王劍虹已是她的師母——她所敬慕的老師瞿秋白的夫人。孫中山先生的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夫婦到上海要了解上海婦女運(yùn)動的情況,向警予因事離滬去漢口,于是由楊之華代替前去匯報(bào),楊之華因此意外地遇見了瞿秋白。瞿秋白擔(dān)任他們談話的翻譯。在他的幫助下,楊之華克服了緊張情緒,順利地完成了匯報(bào)任務(wù)。
楊之華難忘這感人的情景,并對瞿秋白有了新的認(rèn)識。她說:“從這次工作接觸后,我覺得他很誠懇,很愿意幫助別人。他不但不驕傲,而是很謙虛;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熱情。他的熱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蘊(yùn)藏在內(nèi)心,只有當(dāng)人們和他在一起工作時(shí),才能深切地感覺到這種熱情的力量。”
不久,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幫助下,楊之華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她的入黨介紹人是瞿秋白。
此時(shí),王劍虹的病已經(jīng)加重。楊之華經(jīng)常抽空去看望王劍虹。王劍虹病逝后,瞿秋白與楊之華的關(guān)系也有了發(fā)展。楊之華最后走進(jìn)瞿秋白的情感世界應(yīng)該是這年的10月——這個(gè)政治上的多事之秋。雙十節(jié)“天后宮事件”發(fā)生前后,他倆的情誼很快地由師生、戰(zhàn)友升華到互相愛慕的情侶戀人。
瞿秋白和楊之華的超乎尋常的快速結(jié)合,引起了一些人包括某些自己同志的不理解,甚至非議。據(jù)黨史研究專家陳鐵健分析,瞿秋白寫給丁玲那一束謎似的信,表達(dá)了他當(dāng)時(shí)因?yàn)榇耸露a(chǎn)生的內(nèi)心煩惱和惶惑。這便是信中口口聲聲說的“對不起王劍虹”的原因。
這件事的最后結(jié)果深深地傷害了丁玲的心。丁玲對此事一直耿耿于懷,始終未能原諒瞿秋白。甚至連當(dāng)初好言相勸她要想開些、不值得為此難受的好友譚慕君(譚惕吾),也反被丁玲認(rèn)為“對世情看得真透徹”“過于理智”,而有意疏遠(yuǎn)達(dá)幾十年。
這個(gè)舉動有悖常理,遷怒于他人也令人費(fèi)解。這種被丁玲坦承為的“一種無法解釋的感情”,無疑蘊(yùn)含著極為復(fù)雜甚至永遠(yuǎn)難以破解的謎團(tuán)。正像丁玲晚年寫的那篇回憶散文《我所認(rèn)識的瞿秋白同志》一樣,總會讓人覺察到丁玲感情的復(fù)雜,有一種霧里看花的印象。
什么人也不理解她
此時(shí)的丁玲情緒極端孤寂、極端苦悶,比她離開上海告別王劍虹時(shí)有過之而無不及。關(guān)于丁玲這個(gè)時(shí)期的心態(tài),20世紀(jì)30年代初成為丁玲“左聯(lián)”同人的姚蓬子有過一段記錄,他在《我們的朋友丁玲》中寫道:

丁玲著《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書影
那一段時(shí)間,她完全沉到一種什么人也不理解的,也不愿意什么人理解的,只自己深切地痛感著的頹唐中,一直到和也頻同住。常常是這樣的:一個(gè)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夜間喝醉了酒,在黃昏的古城里茫然地躑躅著。是在一年的最后的一天罷,在朋友家里吃完年夜飯,已經(jīng)是三更天氣了,人是迷迷糊糊地醉到連站也站不住了。她掙扎著身子起來,一定要回去。不管大家竭力的攔阻和勸誘,還是要出門去。最后無法可想了,朋友決定自己伴她回家,路上也好放心些,可她也不答應(yīng)。一個(gè)人坐上洋車,也不說地方,叫車夫一直往前面拉去。等到被冷風(fēng)吹散了酒氣時(shí),睜開眼睛往四面看看,冷落的,只昏黃的電燈光霜似的凝在地面上,不知被拉到一個(gè)什么荒涼的地方了。
姚蓬子的描述是真實(shí)的,是他聽丁玲本人親口講述的。此前,丁玲曾如實(shí)地把它寫進(jìn)自己的小說《歲暮》中。
《歲暮》寫于1929年,距此事已過去了三四年,但丁玲依然難以忘懷。小說中的女主人公佩芳與魂影兩位大學(xué)生,在大年三十晚上,因遠(yuǎn)離故鄉(xiāng)親人而備覺凄涼感傷。兩人無法壓抑內(nèi)心的痛苦,佩芳上街瘋狂地購物,凡是同屋住的人,她都送了隆重的禮品,連娘姨們都送到了;魂影清早起來,第一件事就是給家里的親人和朋友接連寫了十多封信。后來魂影被友人邀請去玩,結(jié)果喝得酩酊大醉,深夜被人用車送回,又是嘔吐又是大哭大笑;昏睡時(shí)手里還拿著一張新寄來的照片,反面密密麻麻寫著她題的詩句。
書中有一個(gè)細(xì)節(jié)不容忽視。女主人公之一名叫“魂影”,而她寫信的那位上海男性友人名叫“心”,取這兩個(gè)名字,用意頗為深長。出自瞿秋白愛說的那句話“你的魂兒我的心”,只是“魂兒”(暗指王劍虹)已經(jīng)死了,“魂兒”的影子“魂影”(暗指作者本人)正在北京給上海的“心”寫信;而“心”則直接取于瞿秋白自己的昵稱“宿心”。瞿秋白曾送給丁玲兩枚自己刻的印章,一枚“夢可”,一枚“宿心”。“夢可”與“宿心”,是瞿秋白與王劍虹私下互稱的名字。書中“魂影”寫的非一般普通信而是情書,這是女友佩芳無意之中泄露的天機(jī):魂影把給“心”寫信的事瞞了好友佩芳,結(jié)果惹得佩芳生氣,“只想任性吵出來”,又怕讓房東家和娘姨們知道后笑話,“以為真的是她要管朋友,不準(zhǔn)朋友愛別人”。
至此,丁玲從離開上海去北京到與胡也頻同居前,她異常痛苦的癥結(jié),應(yīng)該說已昭然若揭了。王劍虹的死以及死之原因不明,固然是丁玲的一個(gè)心病,但不至于影響時(shí)間如此長、程度如此嚴(yán)重。到北京后,她與辟才胡同補(bǔ)習(xí)學(xué)校的女友們過著自由的生活,幾乎已經(jīng)把過去上海的痛苦忘記了,只是后來瞿秋白不時(shí)的來信才擾亂了她愉悅的時(shí)光,使她陷入更深的痛苦中。這中間,瞿秋白曾經(jīng)給過她希望與企盼,也熄滅了她的希望與企盼。

晚年丁玲
實(shí)習(xí)編輯/崔金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