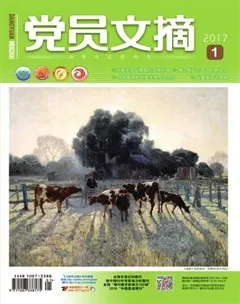年紀(jì)越大,膽子越小
馬伯庸
我比現(xiàn)在年輕十歲的時(shí)候,覺(jué)得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足以讓人膽怯,每天想的都是如何冒險(xiǎn)、如何闖蕩。我在新西蘭讀書時(shí),有一天腦子一熱,跑到當(dāng)?shù)芈眯猩缭儐?wèn)如何去伊拉克。
旅行社的人受到不小的驚嚇,問(wèn)我為什么去。我解釋說(shuō),我就是想親自去體驗(yàn)一下真實(shí)戰(zhàn)場(chǎng)的感覺(jué),說(shuō)得神采飛揚(yáng),自我感覺(jué)真是酷極了。后來(lái)這事黃了,原因很簡(jiǎn)單,我負(fù)擔(dān)不起從新西蘭飛往迪拜的機(jī)票。
回國(guó)以后,我跟我娘提了這事,結(jié)果被她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訓(xùn)斥了一頓。我沒(méi)敢還嘴,因?yàn)樗?xùn)著訓(xùn)著就哭了。我趕緊安慰她:“這不是沒(méi)去成嘛。”她抹抹眼淚說(shuō):“你以后不許干這種事聽(tīng)見(jiàn)沒(méi)有,萬(wàn)一真出了事我和你爸可怎么辦?”我唯唯諾諾,心里卻只當(dāng)它是一種親人的嘮叨。
類似的事情還有那么幾次,當(dāng)然我沒(méi)敢告訴我娘。總之,那段時(shí)間,我每天都過(guò)得特別勇敢,腦子里根本沒(méi)有危險(xiǎn)這個(gè)概念,唯一的追求就是興奮和刺激。
隨著時(shí)間推移,我的肚腩慢慢變大,膽子卻慢慢變小了。從前坐飛機(jī),一遇上顛簸,權(quán)當(dāng)是坐過(guò)山車,該看書看書,該睡覺(jué)睡覺(jué)。現(xiàn)在坐飛機(jī),只要遇到一點(diǎn)氣流,手心就開(kāi)始冒汗,腦子不斷在想各種慘狀,直到空姐解除警報(bào)開(kāi)始端茶送水,這心才算是踏實(shí)下來(lái)。
我一直對(duì)自己這個(gè)轉(zhuǎn)變迷惑不解。有時(shí)候夜深人靜,我捫心自省,把它歸咎為成年男子向世俗妥協(xié)的證明。但并非如此。
前一陣連續(xù)出了好幾個(gè)悲劇事件:某地一個(gè)年輕跑酷運(yùn)動(dòng)者從橋上跳下淹死在水里;某大學(xué)一名研究生被投毒而死;美國(guó)波士頓發(fā)生恐怖襲擊,一名中國(guó)留學(xué)生身亡。
我第一個(gè)反應(yīng)不是“這樣的年輕人死得太可惜了”,而是“他們的父母聽(tīng)到這樣的消息,該怎么辦”。我無(wú)法想象,他們的父母聽(tīng)到噩耗有多悲痛,或者說(shuō),我是不敢去想象。因?yàn)橐幌胂缶蜁?huì)無(wú)法抑制地代入到自己的情境里——如果我出了事,我的爹媽該是什么反應(yīng),他們得難過(guò)成什么樣。這么聯(lián)想下去,心情會(huì)像跳水一樣直線跌落,直到谷底。
現(xiàn)在回想起來(lái),每次我因危險(xiǎn)而害怕時(shí),腦海里冒出來(lái)的念頭,和看到那三條新聞的思路都是一樣的:“父母該怎么辦?”所以我最怕的不是自己死去,而是怕父母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一想到老爹老娘要因此而受到打擊,我的內(nèi)心就惶恐不安。
我的一個(gè)朋友也有類似感受。他告訴我,他現(xiàn)在很小心,過(guò)馬路一定會(huì)先左右看,按時(shí)鍛煉身體,盡量不熬夜。他說(shuō)他是家里的主要收入來(lái)源,如果出事,老婆、孩子還有兩邊的父母都會(huì)陷入困境。“我現(xiàn)在根本不敢死,死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太奢侈了。”他感慨。
所以,當(dāng)你發(fā)現(xiàn)死亡不僅僅只與自己有關(guān),還會(huì)對(duì)你的親人產(chǎn)生巨大影響時(shí),你就會(huì)變得膽小、謹(jǐn)慎、裹足不前,但這不該被稱為懦弱。
(摘自《讀天下》201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