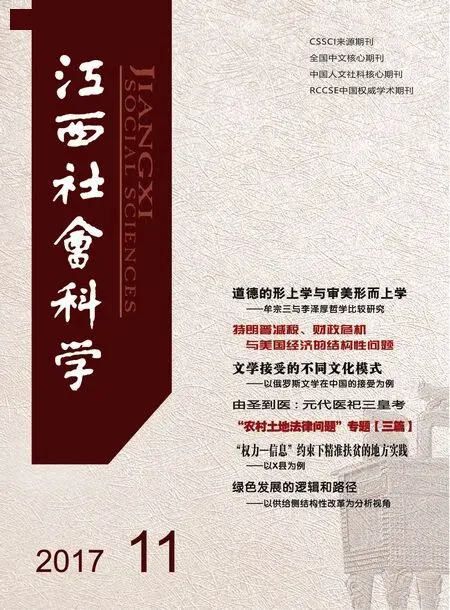朱熹思想中的經驗主義
■章 林
朱熹思想中的經驗主義
■章 林
朱熹;經驗主義;宇宙論;認識論
梁啟超說,我國在秦朝以后,“確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1](P1)。清代學術可以說是對宋明理學或道學的一次反動,在梁啟超看來,“道學派別,雖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點,是想把儒家言建設在形而上學——即玄學的基礎之上”[2](P2)。清代學術思潮作為對理學的反動,其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2](P1)。梁啟超對宋明理學和清代考據學的評斷客觀而精當,后來美國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借鑒西學的話語,把梁啟超指出的清代“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的傾向解釋為經驗主義的興起,認為黃宗羲、王夫之、李恕谷、戴震等人的思想都有經驗主義的色彩。同理學和心學不同,他們承認感性事物的實在性,承認人的感性欲望以及感性經驗的合理性。列文森認為清初的經驗主義傾向同科學精神具有一致性:
這些要求向外考察事物而非向內尋求本質的禁令如何同科學相關呢?現代科學在其發展進程中,將同反經驗主義的,或理性主義的形而上學作斗爭作為主題,二者在這點上是一致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說他們是相關的。[3](P6)
經驗主義強調對外部事物的經驗觀察,而理性主義形而上學則注重對內在本質或超驗原則的思考。列文森認為清代的經驗主義是對“理性主義”的反動,這同梁啟超認為宋明理學是一種形而上學和玄學,而清代學術正是以對客觀事物的考察代替形而上冥想的觀點如出一轍。
列文森進一步把朱熹看作宋明理學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在他看來,朱熹的理學同經驗主義不同,完全以形而上的“理”為根據去構造感性世界。他說:“理是理智能夠把握而感性無法認識的普遍性概念,是貫穿于一般和特殊,存在(Being)和個體事物的形而上秩序。”[3](P3)在這點上,梁啟超倒是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理學精神主要在于為儒學建立形而上學的根基,這是宋明理學的一般性特征和趨勢,但也有一些例外:
在“道學”的總旗幟底下,雖然有呂伯恭、朱晦庵、陳龍川各派,不專以談玄為主,然而大勢所趨,總是傾向于明心見性一路,結果自然要像陸子靜、王陽明的講法,才能徹底地成一片段。[2](P3)
在梁啟超看來,朱熹思想恰恰不與宋明儒學形而上學化的趨勢同流。
梁啟超的審慎是一種睿智。一旦具體分析朱熹的思想,我們就會發現,朱熹與列文森的不同之處在于,龐大的理學體系中實際上已經出現經驗主義的肇端。也就是說,同人們通常理解的不同,在作為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中,恰恰表現出較為明顯的經驗主義色彩,在朱子宇宙論和知識論中均可見此經驗主義的端倪。來自經驗觀察的知識有力地沖擊了當時的理學體系,迫使朱熹在理學的范圍內為其留下一席之地。雖然被視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但朱熹卻“虛心”接受由實際觀察獲得的經驗知識,并以此對理學的解釋體系做適當的調整。同樣,在認識論中朱熹也強調對外部事物感性經驗認識的重要性,強調通過對個別事物的認識逐漸上升到對真理或道的整體性認識。
一、宇宙論中的經驗主義
宋代科學的發展與理學的昌盛同步,李約瑟認為“宋代確實是中國本土上的科學最為繁榮昌盛的時期”[4](P526),并且強調得出這個結論并不牽強,“宋代理學本質上是科學性的,伴隨而來的是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本身的各種活動的史無前例的繁盛”[4](P527)。他列舉當時的一些重要的科學家,以沈括為代表,在數學、天文、地理、化學以及醫學等諸多領域都出現杰出人物,并有豐富的成果。科學的發展無疑來自于長期觀察所得的經驗材料不斷豐富,這些材料雖然沒有對儒家以氣本論為基礎的解釋范式提出挑戰,但也已與建立在傳統氣本論基礎上的一些具體的解釋原則發生沖突。在朱熹友徒中,蔡元定就具有較強的“經驗主義”傾向,其致思之領域相當開闊,尤以天文和堪輿見長,與張載相比,蔡元定更具有科學家的氣質。朱熹對宇宙現象的解釋總體是偏向張載,而對蔡元定則持保留態度,但作為一個極度審慎的思想家,朱熹同樣感受到來自經驗觀察知識的巨大壓力。有學生問蔡元定歷法究竟如何,朱熹的回答相當謹慎:
或問:“季通歷法未是?”曰:“這都未理會得。而今須是也會布算,也學得似他了,把去推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某自不曾理會得,如何說得他是與不是。”[5](P145)
歷法家同哲學家的思維方式有著很大的不同,前者傾向于就事物自身的相互關系來解釋事實,而后者則傾向于構建一個本體,然后在此基礎上解釋所有的現象。可以說天文學家同理學家分別代表兩個相互抵牾的路徑:其一是較為“科學”的解釋路徑,從觀察材料出發揭示事物自身之間的關系;其二是較為“哲學”的解釋路徑,賦予所有物理現象一個本體論的根據,從本體論層面對宇宙和物理現象作更加根本的解釋。羅家倫曾對科學同哲學各種特點做出概括,把科學稱為“描寫”,而把哲學稱為“解答”:
有一點“描寫”與“解答”根本的區別,因為在歷史上頗有混淆,也為承上啟下起見,在這里應當補足的。就是描寫僅須忠誠于各種條件,寫出他們相互的關系,則現象的表現,自然可以供我們預期。至于“解答”,則不在此地停止,而一定要去解答其所以有這種關系的緣故。譬如講行星的運行,在力學方面,僅須問星象間互引的關系,而以數學的公式表出,茍能符合,就算盡了科學的責任。至于問到“究竟為什么”有這種關系,那就不屬于科學范圍,而且科學家因為缺少一種訓練,若要強去解說,就會鬧笑話。[6](P33)
總的來說,同張載、程頤相比,朱熹在對天體運行以及其他自然現象的解釋上更具有科學的“經驗主義”的特征,只滿足于對現象的說明,而懸置現象的更加深層次的原因。
在理學家看來,天體的運行,特別是日月的運行正是“天道”“天理”的顯著表現。張載就完全從陰陽二氣相互感應作用來解釋天體的運行以及月亮的盈缺以及日食月食等現象:“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于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7](P11)而朱熹時代的歷法家至少已經能夠從太陽和月亮自身的運行軌跡來解釋這些現象了。朱熹采納了這種解釋:
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球,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于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后,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星亦是受日光,但小耳。[5](P134-135)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5](P137)
上面二段是朱熹關于月亮陰晴圓缺的認識,已經能夠充分認識到月亮本身常圓無缺,其陰晴圓缺是由于月球和太陽在運行過程中相互位置的不斷推移,人在地上看時自然會有朔望之別。
這點同樣表現在朱熹對天體運行總體規律的解釋上。朱熹根據渾天說認為,日月五星都是附天而行,而關于日月五星運行的規則大體上都是依照張載的解釋的,認為“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5](P130),在他看來日月星辰都隨天左旋: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于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5](P130)
關于天體運行的解釋,朱熹多從張載,但是如果同《正蒙》細比,就會發現朱子比張載較少“哲學”的解釋。張載的宇宙論模式大致是這樣的:陰陽二氣由于其本性不同,陰者便凝結成為地系,陽者便上升構成天系。前者包括天自身以及二十八宿恒星,后者包括地自身以及日月五星。整個宇宙都是左旋,但是有快慢之分。天及恒星最快,而地系整體都比天系要慢,在地系中,太陽的運行又是最快的,而月亮的運行則最慢。而決定宇宙運行快慢的是各自的“本性”,更進一步說,就是各自身上的陰陽元素的構成比例。因為氣運行的原則,總的來說就是“陽速而陰緩”,這是張載遵循的一個重要的氣的運行原則。所以,天以及恒星由純陽之氣形成,左旋最快。地系“七政”也因其本性,有著不同的運行速率。其中,太陽和月亮性質較為單純,所以其運動規律也較為容易解釋:
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最緩,亦不純系乎天,如恒星不動。[7](P11)月亮是“陰精”,所以左旋最慢,因此在人看來也就是右行速度最快;太陽是“陽精”,所以右行最慢,但是因為太陽尚內含陰性,所以不能像恒星那樣與天同行。
而在《朱子語類》中,相關的對話有十幾條,朱熹基本上都止步于對天體自身運行規律的說明上,也就是指明日月星辰都隨天左旋,而之所以古人一直認為日月五星右旋,其實是由于“天”運行的最快,日月五星較之都為慢,所以在人看來,反而有右行之感。在日月五星中,太陽運動最快,稍次于天,而月亮較之太陽則慢了不少。在對話中,朱熹很少從氣論出發對這些現象做進一步的解釋。其中有一處例外,朱熹附帶探討了一下月亮較之太陽運行為慢的原因,朱子給出的解釋是“月比日大,故緩”[5](P130)。雖然認為月亮比太陽大的觀點站不住腳,但是朱熹卻是試圖從太陽和月亮自身的質量出發來解釋它們的運動速度的差異。在《語類》收錄的條目中,朱熹都只是指出“天行最健,日健次之,月行遲”,以此來證明日月五星都隨天左旋的運行規律,并沒有進一步尋求超出事物本身的本體論的解釋。
二、認識論中的經驗主義
朱熹思想中的經驗主義傾向同樣表現在認識論中,朱熹關于認識的一些觀點同西方近代經驗主義奠基人培根非常接近。培根試圖從經院哲學中走出,較早提出了經驗主義原則說:
尋求和發現真理的道路只有兩條,也只能有兩條。一條是從感覺和特殊事物飛到最普遍的公理,把這些原理看成固定和不變的真理,然后從這些原理出發,來進行判斷和發現中間的公理。這條道路是現在流行的。另一條道路是從感覺與特殊事物把公理引申出來,然后不斷地逐漸上升,最后才達到普遍的公理。這是真正的道路,但是還沒有試過。[8](P10)
培根提出經驗主義原則主要針對經院哲學,而非從笛卡爾肇端的唯理主義。在培根著名的“螞蟻”“蜘蛛”和“蜜蜂”的比喻中,螞蟻比喻經驗主義者,只知道收集材料,蜘蛛則比喻理性主義者,完全從自身內部吐出蛛網,而蜜蜂則兼取二者,既從外部事物中獲取感性材料,又對這些經驗材料進行進一步的加工,上升為理性認識。在這個比喻中,螞蟻式的經驗主義者并非是現在我們理解的經驗主義者,而是指古代煉金術那樣的盲目實踐家;蜘蛛式的理性主義者也并非指后來的唯理主義者,而是指經院哲學家。經院哲學通過并不充分的經驗觀察就直接飛躍到“普遍的真理”,然后就套用這些普遍的原則去解釋所有的現象。真正的經驗主義則是在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礎上,形成“中間的公理”,最終才上升到普遍的真理。
如前文所述,在宇宙論中,朱熹面對當時日益豐富的經驗觀察知識,對建立在陰陽五行理論之上的傳統宇宙論持保留態度。這種自漢代盛行的理論,正如培根所言,在并不充分的經驗觀察的基礎上,就直接形成一套能解釋所有現象的理論體系。朱熹宇宙論中的經驗主義傾向同樣表現在認識論中,在對《大學》“格物致知”的解釋中得到集中的表述。同樣是張載,區分了見聞之知和德性之知,所謂“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行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7](P24)。見聞之知是耳目等感官獲得的關于外部事物的感性知識,但它僅僅是普通人的認知方式,若要像圣人那樣認識天道,就只能通過德性之知。與張載不同,朱熹則強調通過認識的不斷積累,最終實現認識的飛躍,所有的知識連貫起來,從而形成關于天道整體的認識: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9](P20)
只是才遇一事,即就一事究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5](P603)
二程感慨“物理最好玩”[10](P39),在他們看來,一物有一物之理,所以天下萬物都有觀察、研究的價值。二程理學把認識對象由“高高在上”的天象拉回到普通事物上,使得普通的感性事物都能成為被格的對象,朱熹繼承并深化了二程的這一思想,認為認識就應該從當下現實存在的事物開始,層層推進,不斷深入,以期有朝一日能夠“豁然貫通”。就認識的過程而言,這就非常接近于培根提出的通過經驗積累,實現由感性知識到理性知識飛躍的觀點了。
培根作為經驗主義的奠基人更多地則是批評經院哲學,到了洛克那里,經驗主義同唯理主義的矛盾才正式凸顯出來,問題的焦點開始指向認識的來源等問題。與笛卡爾“天賦觀念”說不同,洛克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說”,認為人的心靈本身一無所有,正如一塊白板,所有的知識都來源于感覺經驗,他說:“它(心靈)是從哪里得到理性和知識的全部材料的呢?我用一句話來答復這個問題:是從經驗得來。”[8](P366)在朱熹認識理論中,我們則發現一個與“白板”類似的“鏡式”比喻屢屢出現:
人心如一個鏡,先未有一個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丑。若先有一個影象在里,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5](P538)
后來,羅蒂把洛克、培根等經驗主義者和笛卡爾、康德等理性主義者關于人類心靈的理解統稱為“鏡式隱喻”:“俘獲住傳統哲學的圖畫是作為一面巨鏡的心的圖畫,它包括著各種各樣的表象(其中有些準確,有些不準確)。”[11](P9)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鏡式比喻本身并不必然同經驗主義聯系在一起,羅蒂認為笛卡爾、康德也同樣受到“鏡式比喻”的支配:“如果沒有類似于鏡子的心的觀念,作為準確再現的知識觀念就不會出現。沒有后一種觀念,笛卡爾和康德共同采用的研究策略——即通過審視、修理和磨光這面鏡子以獲得更準確的表象——就不會講得通了。”[11](P9)
有意思的是,同西方近代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同享“鏡式”比喻一樣,理學和心學也都把人的心靈比作鏡子。但是理性主義和心學強調人類心靈具有“天賦觀念”或“良知良能”,磨光鏡子是為了讓心靈自身的觀念和知識充分呈現出來,而經驗主義和理學則強調通過磨光鏡子以便更清晰地反映事物以及事物之理。所以朱熹說:“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12](P2257)可見,朱熹要求心靈之鏡不受蒙蔽,不是因為心靈具有某些天賦觀念或知識,要讓這些知識呈現出來,而是希望通過“本體自明”,實現“物來能照”,以期能夠更客觀、真實地反映外部事物。在朱熹的鏡式比喻中,心與物的關系是照與被照的關系,即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對此,陳來評論道:
朱熹關于心體虛明的思想,首先是從重視人的道德實踐出發的。如果不能正確地了解對象及對象與主體的關系,在應接和處理事物的時候就會產生失誤。但是,不可否認,以心為鏡,以認識為照物,包含了認識論的意義特別是反映論的觀點。[13](P218)
可見,朱熹作為“理學”的集大成者,在其認識論思想中,無論是關于認識的過程還是認識的來源的思想,同西方近代經驗主義確實相當接近。
三、朱熹思想中經驗主義傾向的性質
與列文森把清代學術思潮視為經驗主義的興起,把朱熹理學恰恰視為經驗主義反對的對象不同,我們發現在朱熹的宇宙論和認識論都具有經驗主義的色彩。除了宇宙論和認識論這兩個方面,這種經驗主義的色彩同樣閃耀在朱熹思想的很多其他領域。比如,同張載強調氣之“神化”作用相比,朱熹強調的是氣之絪蘊相感作用的內在之理,這就使感應關系在朱熹理學體系中逐漸失去之前的神化特色,成為對事物相互之間必然聯系的一種描述。并且,朱熹開始關注事物本身的相互作用關系,在“內感”之外提出“外感”,從而同西方科學的“因果關系”更為相近。
這種經驗主義的傾向無疑同朱熹本人兼容并包、客觀理性的治學態度密切相關,他在面對大量來自觀察的經驗材料時,并非執一既定的、普遍的“理”去強行解釋個別的“事”,而是盡量試圖從對大量的事實的觀察中總結、體悟普遍的“天理”。但是朱熹的這種經驗主義傾向畢竟是不徹底的,當遇到那些經驗觀察材料相對不足的事物和現象時,他就會同樣退回到哲學那里尋求幫助。關于日食和月食,朱熹還有另外的一些解釋:
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5](P138-139)
“遇險”,謂日月相遇,陽遇陰為險也。[5](P139)
日月食皆是陰陽氣衰。徽廟朝曾下詔書,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皆不曉歷之故。[5](P139)
同張載的解釋相比,朱熹已經非常“科學”地認識到日食和月食是由太陽、月亮以及地球的運行軌跡決定,并且星體運行有自身的規律,所以日食和月食也有其常數。在對日食和月食的解釋中,朱熹對日食的解釋較為“科學”,認為月亮在太陽之下擋住了太陽的光芒,而對月食的解釋卻又回到傳統陰陽二氣的解釋框架,認為月食是“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5](P140)。
對月食的這種解釋固然是由于受當時流行的渾天說的限制,并且當時普遍認為月亮較太陽為大,所以不能從太陽、月亮以及地球的運行位置關系來解釋月食。究其根源來說,朱熹宇宙論思想卻受其哲學體系的束縛。就其思想之全體來說,哲學傾向是要大于科學傾向的。朱熹對一些離地球較遠的星體的解釋,基本上都沿襲了傳統的陰陽二氣相互作用的解釋路徑,比如解釋五大行星的形成及性質: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卻受日光。經星卻是陽氣之余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5](P139-140)
解釋雪花的形成及其形狀: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于地,泥必濽開成棱瓣也。又,六者陰數,大陰玄精石亦六棱,蓋天地自然之數。[5](P141)解釋雨、雷、雹等現象: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郁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云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云雨之說最分曉。”[5](P141)
(雹)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棱道。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雹也。[5](P143)
可以說,在朱熹的宇宙論中,自身也包含科學路徑同哲學路徑的對抗,但總的來說,哲學路徑是朱熹的根本趨向。這點體現在朱熹對歷法性質的總體評判:“古今歷家只推算得個陰陽消長界分耳。”[5](P143)在朱熹看來,歷法推算的其實是事物背后陰陽消長的規律而已,它指涉的對象從根本上來說正是哲學思考的陰陽二氣運行之道。朱熹思想中雖然有經驗主義的隱約萌芽,但又很自然地消解在理學的體系之中。
四、結 語
從朱熹對天體運行的具體解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經驗知識同理學原則之間的沖突,只不過這種沖突被朱熹以一種平和的方式淡化,并最終消解于理學的龐大體系之中。我們借用西方哲學中的經驗主義一詞,僅是用來表述朱熹思想中較為重視經驗觀察知識的事實,這種經驗主義是不徹底的,甚或只能稱之為一種思想的“傾向”。從清代中國思想的發展來看,經驗主義逐漸發達,理學勢力逐漸衰退,但即便在清初,中國傳統思想內生的經驗主義也未能產生出科學,直到晚清民國,以一種決絕的方式推翻傳統文化,才正式引進科學。從另一角度看,如梁啟超所言,清代實學、樸學的興盛第一步源于對陽明后學空疏不實的反動,從而復歸于程朱理學。此“以復古為解放”之所以會發生,應同朱熹理學思想中蘊含的經驗主義特質有較大關系,而如果如我們前面所述,朱熹思想中的經驗主義又是經驗觀察材料不斷豐富的自然產物,那么以看似決絕的方式引進科學或許也有其內在的邏輯。
[1]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4](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科學思想史[M].何兆武,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
[5](宋)朱熹.朱子全書(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羅家倫.科學與玄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7](宋)張載.張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8.
[8]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
[9](宋)朱熹.朱子全書(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宋)程顥,程頤.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4.
[11](美)理查德·羅蒂.哲學和自然之鏡[M].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12](宋)朱熹.朱子全書(二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陳來.朱子哲學研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趙 偉】
宋代科學的發展,使經驗觀察知識不斷豐富,進而對理學的解釋體系產生了沖擊。在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中,因此出現了經驗主義的萌芽。在宇宙論中,朱熹在解釋諸如星體的運行、日食月食等現象時,試圖擺脫張載等人通過構建星體的陰陽屬性來解釋其運行規律的做法,更多從星體自身運行軌跡、質量大小等感性經驗因素來解釋;在認識論中,朱熹持有一種反映論以及通過大量個別事物的研究進而上升到普遍真理的經驗主義原則。朱子思想中的經驗主義萌芽是經驗觀察同理學玄思相碰撞的產物,最終又消解于理學體系之中。
B22;N031
A
1004-518X(2017)11-0018-07
安徽省高校優秀青年人才支持計劃重點項目(gxyqZD201619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招標項目“方東美對儒家‘生生’思想的發展”(SK2015A143)
章 林,安慶師范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安徽安慶 246133)
- 江西社會科學的其它文章
- ——評《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藝》">"茶泡"工藝對傳承民俗文化的藝術價值
——評《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藝》 - 樂理下的民間音樂鑒賞
——評《中國民族民間音樂欣賞指南》 - 虛擬現實技術在教學中的應用研究
——評《虛擬/增強現實技術及其應用》 - 論油畫創作的寫意精神
——評《油畫寫意性研究》 - 淺析蘇聯模式對新中國雕塑教學的影響
——評《蘇聯雕塑教育模式與新中國雕塑教育》 - 少數民族地區文化旅游的創新發展研究
——評《民族地區文化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