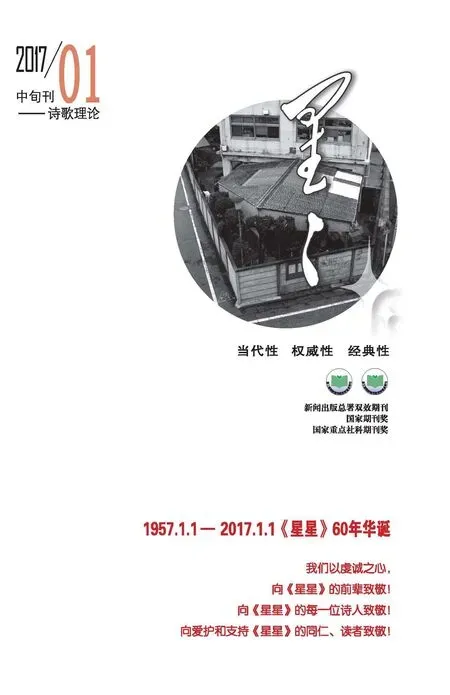驕傲的樹葉會被時間帶走
花語VS霍俊明
驕傲的樹葉會被時間帶走
花語VS霍俊明
花語:霍老師好!您是“70后”詩歌批評家中名聲最響、著述最豐、研究和批評最為勤奮、最活躍的一位,能為您做這次訪談,深感榮幸!您出過專著《尷尬的一代:中國70后先鋒詩歌》,作為一部系統、深入、全面考察中國70后先鋒詩歌的斷代史,它綜合性地呈現了與70后一代人密切相關的生活史、思想史、靈魂史和詩歌發展史。請問:當時您是出于什么考慮出這樣一部專著的?在當今詩壇,您眼中最出色的70后詩人有哪些?70后、80后的優秀詩評家有哪些?
霍俊明:謝謝花語。首先你對我的這些評價我萬萬不敢接受,近年來我也不斷反思自己的批評文字的問題。作為一個批評家或作為一個詩人,其難度在我們看來越來越大。代際研究最容易招致的是同時代人的不滿甚至非議。實際上我寫作《尷尬的一代》這本書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讓那些正在堅持詩歌寫作的70后一代人對自己的生存背景、歷史記憶、寫作狀況和精神圖景有一個初步的整體性的認識,能夠更為清醒地認識到一代人包括個體寫作的特點和差異,而且能夠拿出成色更好的文本給讀者甚至留給將來的歷史。我感謝人們對我這本不成熟的書的關注甚至是肯定,我也深知這本書因為帶有“第一次”的性質不可避免的缺憾和諸多問題,所以我更要感謝那些對這本書心懷不滿和批評我的人。關于優秀的70后詩人以及70后、80后詩評家的名單我不想在此羅列,以免掛一漏萬。另外,我越來越意識到的一個問題是包括70后在內的詩人給我們所提供的典型的、代表性的能夠引起更大面積受眾群的詩歌太少了。
花語:先有著名作家曹雪芹、張愛玲,后有詩人李瑛、李小雨,再有著名詩歌批評家霍俊明,河北豐潤這個地名,在中國文學史上也算是可圈可點。對您來說,“豐潤”是故土、是少年的成長、還是一份離別后,久久不忍割舍的牽掛?請說說您的少年成長的經歷!
霍俊明:小學一到四年級是在村里的小學讀的,校舍是簡易的北方瓦房。甚至一年級的時候和四年級同學同一個教室上課。先是給我們一年級上課然后留作業,接著給四年級的同學上課。現在想想這發生的一切都不像是真的。那時冬天特別冷,教室又沒有爐子,整個手凍得像小胡蘿卜似的。一到課間休息就和同學到操場上打鬧或者互相靠著墻根擠來擠去——這都是為了抵御寒冷。學校隔壁住著一個女瘋子,經常在我們上課的時候她就隔著矮墻痛罵——也不知道她在罵誰。她罵到興起,就把磚頭石塊什么的扔到窗玻璃上。如今校園已經不存在了,多年前已被拆除了。當年學校北面是一條河,水很深。村里的一個老人因為兒子兒媳不孝順跳河自殺了。我還記得中午放學的時候村里的人都來圍觀。這個不孝順的夫妻跪在母親的棺材前。多年后這個人成了村里的暴發戶,他的兒子子承父業經商,還當起了什么慈善家。五年級到六年級在隔壁村張莊子中心小學讀的。那時上學都是徒步,早上上學,中午放學回家吃飯,午飯后再步行上學,下午放學再回家。那時根本不知道學習,經常和同學在校園里打鬧。稀里糊涂的,1988年夏天我竟然考上縣城的重點中學——曹莊子中學。那是一個寄宿學校,第一次出門住宿我患上了嚴重的思鄉病。周五下午放學回家我就不再想上學了,每次不是說生病就說學校搞活動放假。有一個學期,我居然曠課170多課時。高中就不說了,那時整個校園都是隨處可見的暴力斗毆場面,那時喜歡聽唐朝和黑豹樂隊的歌。1996年大學中文系畢業后,我以優秀生(那時中文系168個人,一屆只有四名優秀生)的身份到老家一個鎮上高中當語文老師,期間諸多挫折辛苦就不提了。那時是實行分配,自己沒有任何選擇權,我又沒有資本去走蠅營狗茍的后門。那段經歷對我至關重要,看到了社會和人際關系最真實的一面。
還鄉河(又稱浭水、庚水、巨梁河),是我河北豐潤老家(冀東平原)一條河流的名字。而對于時下的中國詩人而言,似乎他們都宿命性地走在一條“回鄉”的路上。而這還不只是語言和文化根性層面的,而恰恰是來自于現實的命運。同時,這一條“還鄉”的路也需要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因為愈發顯豁的倫理和道德感所導致的情感優勢和批判城市化的心理正在大行其道。在此,我想到的是云南詩人雷平陽的詩“我從鄉愁中獲利/或許我也是一個罪人”。實際上幾十年來對于這條故鄉的河流我倍感陌生,盡管兒時門前的河水大雨暴漲時能夠淹沒那條并不寬闊的鄉間土路。甚至在1990年夏天的特大暴雨時,門前的河水居然上漲了兩米多到了院墻外的臺階上。那時我15歲,似乎并沒有因遭受暴雨和澇災而苦惱,而是沿著被水淹沒的道路深一腳淺一腳地去河溝里抓魚。那時的鄉村實際上已經沒有道路可言,路上的水沒過了膝蓋,巨大的白楊樹竟然被連根拔起而交錯倒在污濁的水中。在無數次回鄉的路上,我遭遇的則是當年“流放者歸來”一樣的命運。是的,很多人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成了故鄉故土的“陌生人”。多年后,為了認清故鄉的這條河流我不得不借助互聯網進行搜索,因為我無力沿著這條幾近干枯和曾經污染嚴重的河流踏踏實實地走下去。這就是我一個人的鄉下和歷史,它們遠去了但又似乎沒有遠去。它們深深扎根在我并不寬大的內心深處。它們是一個個小小的荊棘不時挑動和刺痛我。
花語:您身兼多職,工作于中國作協創研部,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臺灣屏東教育大學客座教授,站在中國詩歌的最前端,如何看待中國詩歌的邊緣化問題?有人說,與小說、散文相比,詩歌就該邊緣化,您怎么看?
霍俊明:詩歌的邊緣化是一個偽問題。如果說真的像當年的新民歌運動和小靳莊詩歌運動那樣人人寫詩、家家作詩,“村村都有王老九,鄉鄉都有李有才,縣縣都有郭沫若”這不更可笑嗎?實際上八十年代的詩歌熱潮以及詩人的明星效應是此前不幸的政治化的偏狹的詩歌傳播形態累積下來的歷史問題——實際上也是不正常的。即使在那個所謂的詩歌黃金年代,出版一本詩集多么難啊?想想當年的昌耀為了出一本詩集不得不四處托人做廣告征訂。這是詩人的不幸,還是國家的不幸,抑或是讀者和大眾的庸俗?而當下自媒體所催生出來的是大量的分行寫作者,而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詩人——文格和人格不可或缺。詩歌,因為其文體的特殊性以及對寫作者才能的極其高的要求,注定了成為詩人的永遠是少數人。這種特殊的文體也使得它的讀者少之又少。
花語:我近期斷斷續續所做的將近40人的訪談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引用了您的評論,相信得到過您評論的人都對您心懷感激。無疑,給那么多人寫評,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同時,一份好的評論,是將一些好詩或者將一個好詩人推向了歷史的前臺,為此,我得出一個結論,您的雙眼和您敲打的鍵盤,始終關注著當下執著而努力的詩人們,不論60后、70后、80后、還是90后,對此,我想問,寫了這么多的評論,您是否感到厭倦?一個好的詩歌批評家的史命,到底是什么?
霍俊明:說實在話,我曾有一段時間厭倦了詩壇,并不是說厭倦了詩歌本身。這么多年來接觸到那么多的人、事以及亂糟糟的詩歌活動和人心不古。我對于一些寫詩人的品格和文格都一度產生了懷疑。后來想到自己太熱愛詩歌,怎么也不會放下詩歌的,所以才堅持到今天。遠小人,近詩歌。這是我幾年來詩歌閱讀、批評和交往的一個標準或者底線。當年精力旺盛,也喜歡閱讀,所以在一個時期我寫下了大量的關于個人的文章(當然除了個人詩論之外,我做的一個大量的工作就是對當代新詩史的研究和寫作,以及對當代詩歌現象與問題的爬梳)。這些關于個人詩歌的評論文章,今天看來,有一部分令人汗顏。不僅自己的寫作方式和看問題的方法值得修正,而且一些詩人是不值得評論的——為一個二流詩人寫文章是不道德的。但是,我又不完全是魯迅所批評的中國的作家歷來是喜歡“悔其少作”的。對于當年的個體詩人研究的文字盡管今天看來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但是我珍惜這些不完備的文字。因為里面投入了我大量的閱讀時間和心血以及我年輕時代的激情和某種詩歌愿景。也正是得力于大量的閱讀和人生的歷練,我才能夠在今天重新反思自己批評中存在的問題,才能夠在龐雜的閱讀中不斷建立屬于自己的觀感和判斷。一個好的評論家的使命(史命),我不想說得多么的動聽和高大上,或者說一個評論家肩負著什么歷史和面對未來的詩歌史使命,我只想說的是一個評論家起碼要對自己的良心和評論對象負責。好處說好,壞處說壞,顯然后者包括我在內的很多評論家做得都不夠。
花語:在有關您的一個訪談里,曾經提到“沒有遠方的時代正在來臨,催生了詩歌的‘鄉愁化’寫作趨向”,怎么理解這段話?
霍俊明:我說這句話的背景是針對于一個城市化時代的來臨,而這一時代的到來是以鄉村和前現代性的鄉土文化的痛失為代價的。這樣說并不是說城市化時代不好,或者鄉村有多么好,而是說一種強行到來的二元對立和拆遷、清洗甚至斬草除根的城市化法則使得鄉村變了,一種連帶其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以及傳統也變了。這對每一個人都發生了近乎天翻地覆的影響,即使你一直生活在城市里你也會看到城市對鄉村的影響——比如那些移民、流民。而“遠方”則不只是地理層面上每一個地方建筑和內在結構在城市化時代的相似性和趨同性,也指涉每個人尤其是寫作者內心里的某種愿景甚至個人烏托邦式的高蹈。可惜和可悲的是,當下的每個人以及寫作者太關注于身邊和腳下的那個浮土一樣的現實表象,不僅缺乏深入的現實感而且喪失了指向更遠更深處的“遠方”的寬闊與精神的撫慰。而據此,鄉愁化的寫作并不是機械的鄉村的離亂和離鄉背井的外出群體的心理反應,而是來自于前現代和現代之間斷裂地帶的不適、尷尬、惶惑、恐懼以及深深的不安。
花語:您的專著《尷尬的一代:中國70后先鋒詩歌》這本書的書名,有三個關鍵詞:尷尬、70后、先鋒,為什么把尷尬和70后連在一起?在您眼里,何為先鋒?
霍俊明:“尷尬”一詞我不想做過多的解釋了,這本書里面已經說得夠多了。任何一代人都可能是尷尬的,身不由己的。而70后一代人和先鋒放在一起,代表了我的批評觀。一代人中如果沒有先鋒性、獨立性和創造性,那么這代人就白活了。可惜,先鋒性在當下的詩歌中幾乎越來越罕見的,相反倒是假先鋒、偽民間在大行其道。
花語:《變動、修辭與想象:當代新詩史寫作問題研究》是您關于新詩寫作方向的專著,作為一個優秀詩人,在您的眼中,什么是真正的好詩?
霍俊明:真正的好詩是多層次的——優秀的詩、重要的詩和偉大的詩,所以好詩指向這三個層面的時候側重點會有所不同。當下是有大量優秀詩作的時代,但是缺乏重要和偉大的詩,當然,這不是我個人說了算。真正的好詩起碼應該有發現力,對語言和個人以及世界的重新打開,甚至這種發現力能夠更新一代人的認知。我們看到的事實卻是同樣一首詩在不同閱讀者和評論者那里產生的觀感會截然不同,這到底是誰的原因?我希望有心人在次停留幾分鐘,多想想其背后的原因。
花語:您曾選編過《青春詩會三十年詩選》,作為曾經數屆青春詩會的輔導老師,您怎樣看待青春詩會,印象最深的是哪幾屆?
霍俊明:從第二十八屆青春詩會開始我作為指導教師,也是從此時開始詩刊社對青春詩會的評選機制進行了巨大的改革。以往的青春詩會,我認為最好的是第一屆、第六屆、第七屆,后面的就不說了。前后三十二屆(1980—2016)青春詩會,總計有466位青年詩人參加。這已然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其中有的詩人已經離世,讓我們記住他們的名字——顧城(1956~1993)、駱一禾(1961~1989)、趙偉(1947~2004)、劉希全(1962~2010)、大平(1960~2010)、劉德吾(1965~2010)……。“青春詩會”如一條自然分娩的河流,接下來的命運就得靠這些青年詩人自己來把握和完成了。有些詩人在其上不斷乘風破浪、揚帆起航、聲名遠播,有的詩人則噗通噗通游了幾下就草草上岸再也不見身影,有的則甘愿瞬間沉于水底湮沒無聞,有的則改弦更張從事小說等其他文體的寫作成為“前詩人”。36年的青春詩會歷史已經證明,其中有少數一部分極其優異的詩人成了詩壇的恒星,而有一部分成了流星——曾經璀璨耀目一時但終究黯淡、泯滅,又有一部分詩人好似閃電曾經也閃耀過,但其過程過于短暫倏忽。也有的詩人類似于茫茫暗夜里的一個小小的流螢,盡管微弱但那些光是從軀體和靈魂中生發出來的。盡管他們在詩壇上寫詩的時間不長,甚至有的參加了“青春詩會”再無好詩面世,但是當時他們寫下的詩仍能夠代表那個時代的詩歌風貌。這就足夠了。
花語:收到過您編的《天天詩歷》,是出于什么創意,編了這樣一本清新可愛、類似臺歷的詩集?
霍俊明:《天天詩歷》就是臺歷,只是比較特別而已。這一詩歷(日歷)的形式確實是開創性的。做這個詩歌日歷的初衷很明顯,一是讓更多的好詩能夠被展示出來,二是讓詩歌的閱讀常態化和日常化。2015年年底《2016天天詩歷》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響,甚至有很多人受此啟發開始編選各個省份的詩歷。我想這是好事。
花語:這個時代,每天都有人在不斷的書寫,有一些能流傳久遠,有一些渺如塵沙。在您看來,詩歌是否應該承載某種意義?您的詩寫過程,始于何年?最初喜歡的詩人有哪些?
霍俊明:詩歌自然要承載某種意義,不管這種意義具體到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詩人會多么地不同。我練習寫詩在高中就開始了,但真正的所謂詩歌寫作期則是從2000年開始的。最喜歡的詩人自然有,但說出來也無大用處,因為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屬于我個人的。
花語:著名詩人陳超的去世對我們這個時代、對于詩歌都是巨大的損失,您作為他的學生,我們曾經在微信圈目睹您長久的悲傷。請描述一下您的恩師,最令人動容的地方!
霍俊明:在詩歌界,陳超對我的影響是任何人都不能比的,至于其原因我不想在此多說了,因為我在關于陳超先生的回憶文章和研究文章中已經說得夠多了。甚至,最深的懷念是難以用語言表述的。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多看看陳超老師的詩集和詩學著作,以及我所編選的那本《在巨冰傾斜的大地上行走——陳超和他的詩歌時代》。
花語:“近五年的中國詩歌繼續在平穩中推進,在多元中發展,繁榮、多元、和諧、共生是詩歌發展的關鍵詞,以底層詩人為主體的非專業寫作成為近年的一大亮點”,這段話摘自您的某篇文章,那么,怎樣看待“以底層詩人為主體的非專業寫作”這一現象,對于我們這個時代,它意味著什么?
霍俊明:在自媒體平臺的推動下,在城市和工廠空間對底層的刺激下,以底層身份為代表的區別于傳統精英文化的非專業化寫作正在成為越來越引人注目的現象。他們的寫作帶有強烈的個人現實感,其中倫理化、疼痛式的寫作不乏其人。這樣的寫作首先是深處其中的人的發言權,他們借助詩歌來表達個人的喜怒哀樂以及對現實和周邊社會的判斷。這種詩歌(很大一部分)也許在美學上并沒有多少發現力和新的創設,但是對于人們重新認識這些人群、階層以及這個時代會有所幫助。也就是從這一時期來看,這些詩人和文本更帶有社會文化切片的意義。至于其中的詩人和詩歌能夠來自于這個時代又最終超越了這個時代,從而接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這個可能是詩歌的歷史化問題。顯然,這個問題更重要。因為以往火熱的詩歌運動、階級寫作都已經用殘酷的事實證明,能夠最終留存下來的詩人畢竟是最少數。
花語:您是詩人、又是詩歌批評家,如何平衡這二者的關系?詩人和詩歌批評家這兩個身份,您本身更喜歡哪一個?
霍俊明:詩人和評論家猶如左手和右手的關系,對我來說二者缺一不可。實際上談不上二者的平衡,因為二者的話語方式有明顯區別,但是反過來,詩歌寫作和評論寫作之間是彼此發現、相互借重、互相激活的關系。我的努力目標是做一個“詩人批評家”,盡管我知道自己的詩歌水平和評論水平還差得很遠。
花語:微信的出現,加劇了自媒體時代的催生和詩歌的傳播,您認為這是好,還是不好?如何看待一些詩人的爆紅現象?
霍俊明:這個問題我多說點,因為現實性比較強。確實,這兩年來最受關注的就是微信自媒體不斷刷屏的眾多詩歌活動、事件(比如余秀華事件、“回答——中國當代詩歌手跡拍賣會”)、獎項(各種雜七雜八的詩歌獎項達百種以上)、詩歌節、詩歌出版物(自主出版以及新近出現的眾籌出版模式)和譯介。據統計現在每天海量的集束型的詩歌產量早已經遠遠超越了《全唐詩》,而中國詩人的數量早已經躍居世界首位,中國成了名符其實的“詩歌大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每天都在激增的詩歌微信公號和微信群給詩歌生態帶來的不容忽視的影響,甚至自媒體被認為給新詩的“民主”帶來“革命性”影響。在碎片化、電子化和APP移動臨屏閱讀語境下即時、交互性的詩歌寫作、閱讀和批評都輕而易舉地實現了即時性、日常化和大眾化。由此詩歌在公眾中的地位和形象有所改變——詩歌回暖,詩歌升溫,詩歌繁榮,詩歌重新回到社會中來,詩人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被空前拉近。面對著這些被各種文化機制推動的詩歌活動,我們似乎正在迎接一個“詩歌活動”已達高峰期的時代。得出“活動多,好詩少”這樣的結論是有其依據的。然而,我們必須回應的一個近乎老生常談的話題——在談論詩歌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談論什么?這個問題會變得愈益重要和不可回避。在詩歌“活動”已達高峰期的時候研究者應對以上的詩歌判斷做出審慎分析,而不要急于下結論。自媒體平臺下的微信詩歌在提供了寫作熱潮和新聞事件的同時,也讓我們思考其現實境遇、不可靠的幻象和可能性前景。就此問題,每個人的觀感和判斷并不相同。支持者高呼雀躍認為新媒體尤其是微信給詩歌帶來了民主、進步和自由的福音。反對的聲音則認為微信平臺上的深度閱讀已經不可能。顯然,新詩與新媒體的關系已經被很多研究者提升到了“命運”這樣大是大非的程度。著名詩人北島更是認為新媒體所帶來的是新的洗腦方式和粉絲經濟,甚至成了一種“小邪教”。“傳媒話語膨脹時代”的微信平臺因為取消了審查和篩選、甄別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詩歌多元化發展,使得不同風格和形態的詩歌取得存在合法性的同時也使得各種詩歌進入到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失范狀態,隨之也降低了詩歌寫作與發表的難度。微信等自媒體并不是一個“中性”的傳播載體,正如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一文中所強調和憂慮的那樣“新的媒介不只是原封不動地傳播那內容的被動母體,它們都會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發送’的對象,把其內容改變成該媒體特有的表達。”所以一定條件下新媒體自身的“傳播法則”會對詩歌的觀念、功能、形態以及話語形式和評價標準都會產生影響。就當下詩歌來看,寫作者、評論者和傳播者的表達欲望被前所未有的激發出來,“自由寫作”“民主寫作”“泛華寫作”“非專業化寫作”正在成為新一輪的神話。“微信詩歌”作為一種新現象當然需要時間的檢驗,需要進一步觀察、辨析和衡估,但是就已經產生的現象、問題和效應來看,也需要及時予以疏導和矯正。軟綿綿甜膩膩的心靈雞湯的日常小感受、身體官能體驗的欣快癥、新聞化的現實仿寫以及膚淺煽情的“美文”寫作大有流行趨勢。一定程度上新媒體空間的詩歌正在成為一種“快感消費”,這與娛樂化的電視體驗類節目的內在機制是同構的——每個人都能夠在新媒體空間親自體驗各種詩歌訊息。微信詩歌話語的自身法則使得點擊量、轉載率的攀比心理劇增,也進一步使得粉絲和眼球經濟在微信詩歌中發揮了強大功能。這使得詩歌生態的功利化和消費性特征更為突出,而“以丑為美”“新聞效應”“標題黨”“搜奇列怪”“人身攻擊”“揭發隱私”的不良態勢呈現為不可控的泛濫,其中文化垃圾、意見怪談更是層出不窮。即時性的互動交流也使得詩歌的評價標準被混淆,寫作者和受眾的審美判斷力與鑒別力都在受到媒體趣味和法則的影響。微信這一“寫作民主”的交互性代表性平臺已經催生了“微信寫作虛榮心”,很多人認為只有擁有了微信就擁有了自己的話語權,甚至滋生出了偏執、狹隘、自大的心理。與此同時,電子化的大眾閱讀對詩歌的評價標準和尺度也起到了作用。由此引發的疑問是詩歌真正地解決“普及”和“大眾化”問題了嗎?碎片化時代的詩歌寫作是否還具備足夠引起共識和激發公信力的能力?尤其是在新媒體平臺上海量且時時更新的詩歌生產和即時性消費在制造一個個熱點詩人的同時,其產生的格雷欣法則也使得“好詩”被大量平庸和偽劣假冒的詩瞬間吞噬、淹沒。與此相應,受眾對微信新詩和新媒體詩歌的分辨力正在降低。
花語:“對于詩歌的來路、當下以及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漢語詩歌正在不斷成熟和快速發展,但是也要注意‘時間神話’和‘文學進化論’的危險,當下詩歌問題也并不比以往時代要少。盡管詩歌的交流渠道正在新媒體的狂歡中變得如此便利和快捷,但是仍有優秀的詩人可能被一擁而上的歡呼所淹沒。由此,觀察、發現、再造、冷靜、深入、沉潛,是我對當下詩人的期待。”這是您的文章《詩歌的回應“現實”與預敘“未來”》里的一段話,請問,“文學進化論”的危險是什么危險?一個詩人最可怕的迷失,是怎樣的迷失?
霍俊明:“時間神話”和“文學進化論”大抵是一個意思。在以往的文學史敘事中形成的一種共同的腔調就是相信“時間”具有進步性,即新時代的文學總是好于以往的文學,一種社會性質的文藝總是優于其他社會性質的文藝。也就是說,時間本身被賦予了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屬性。我之所以強調“時間神話”和“文學進化論”存在的危險,就是因為持這一論調的人和群體并不在少數。相反,我們倒是忽略了當下詩歌生態存在的問題,而忽略了當下和歷史的關聯。對于高呼當下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的聲音,或者相反指認這是一個最糟糕的詩歌時代的聲音,我都不以為然。因為發出這樣的判斷太容易了!一個詩人的迷失可能會有多種,比如修辭癖、技術派、自戀狂、現實幻想癥、政治傳聲筒等等。
花語:看過一個題為《詩歌是一個時代的良心》的您的訪談,我想問的是,在這個物欲橫流的年代,“時代的良心”,到底是指什么?
霍俊明:無論在任何時代,時代的良心,就詩歌而言都應該指向了對語言和內心的雙重負責,而非違心的創作和言不由衷的表達。真誠寫作是產生優秀作家的一個基本前提。最后,謝謝花語!浪費了你這么多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