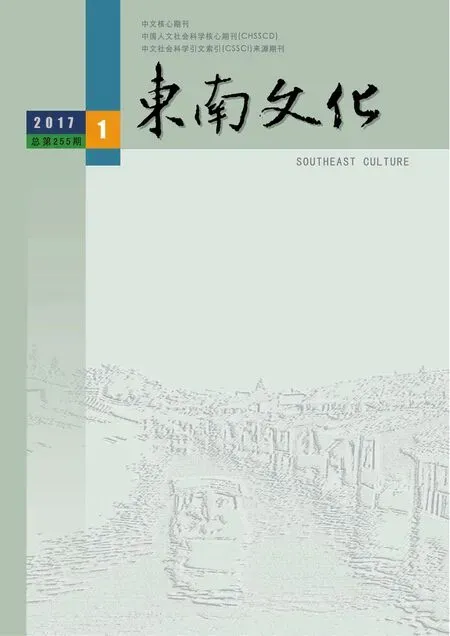論南京地區(qū)東晉南朝墓出土的明器榻
周庭熙
(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考古文物系 江蘇南京 210023)
論南京地區(qū)東晉南朝墓出土的明器榻
周庭熙
(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考古文物系 江蘇南京 210023)
考古發(fā)掘報告中,對南京地區(qū)東晉南朝墓出土的明器榻的命名經(jīng)常不一。通過對“榻”的概念的辨析、出土遺物的認(rèn)定以及榻與墓中磚砌祭臺的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墓中隨葬的明器榻與墓主的身份等級相關(guān),它在祭奠活動中與憑幾一起象征的是墓主人的靈魂所在。作為墓主生前家居的象征,墓中榻及一系列家具的布置,使墓主生前的家居生活以及應(yīng)享有的禮遇在其死后所處的墓室空間中得以延續(xù)。
南京 東晉南朝 榻 祭臺 墓葬
南京地區(qū)東晉南朝大型墓葬中常出土陶質(zhì)或石質(zhì)的坐榻模型,因其專為隨葬所制,故屬明器范疇。關(guān)于其命名、功能等問題,前人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榻與案的異同[1];第二,漢唐家具研究中榻的地位[2];第三,榻與墓葬之間的關(guān)系[3]。但以往的發(fā)掘報告及相關(guān)研究,對榻的命名及其在墓葬中的功能等問題往往意見不一,已公布的發(fā)掘材料也未經(jīng)詳細(xì)梳理。因此,本文擬在既往研究的基礎(chǔ)上,首先對南京地區(qū)東晉南朝墓葬出土的明器榻進(jìn)行認(rèn)定(據(jù)已公布的發(fā)掘資料,南京地區(qū)孫吳、西晉墓葬中尚未確認(rèn)有明器榻的存在),進(jìn)而對與之有關(guān)的墓葬等級及葬儀展開討論。
一、明器榻的認(rèn)定
東漢劉熙《釋名·釋床帳》說:“人所坐臥曰床。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長狹而卑曰榻,言其體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獨(dú)坐,主人無二,獨(dú)所坐也。枰,平也;以板作之,其體平正也。”[4]唐代徐堅《初學(xué)記》所引東漢服虔《通俗文》中記錄了漢代榻的尺寸:“床三尺五曰榻板,獨(dú)坐曰秤(枰),八尺曰床。”[5]唐代玄應(yīng)《一切經(jīng)音義》引曹魏張揖《埤蒼》稱:“枰,榻也。謂獨(dú)坐板床也。”[6]由此可見,漢晉時期的坐具與臥具可通稱為“床”,據(jù)其尺寸差異又有“床”、“榻”、“獨(dú)坐”與“枰”之分,僅容一人居坐的“獨(dú)坐”或“枰”又可視為較小的“榻”。陳增弼先生與孫機(jī)先生曾據(jù)實(shí)物資料與上述文獻(xiàn)材料,對漢晉時期榻的形制與尺寸進(jìn)行了詳細(xì)討論。陳先生更對“獨(dú)坐”一類小榻的尺寸作出了合理的推測:長75~130、寬60~100、高12~28厘米[7]。這為墓葬出土明器榻的認(rèn)定和研究提供了依據(jù)。
南京地區(qū)東晉南朝墓出土的陶質(zhì)或石質(zhì)的明器榻,在發(fā)現(xiàn)之時或簡報中常被命名為“案”或“祭臺”。盡管已有研究者提出將此類明器命名為“榻”,但此后的簡報中依然采用以往的命名方式。因此,本文首先要對南京地區(qū)東晉南朝墓出土的這類明器進(jìn)行逐一認(rèn)定。
依造型差異,墓葬出土的榻可分為無圍屏榻與圍屏榻兩類。無圍屏榻最早發(fā)現(xiàn)于1970年發(fā)掘的象山M 7。該墓出土一件陶榻,報告將其命名為“案幾”[8]。1972年發(fā)掘的南京大學(xué)北園東晉墓(以下簡稱“南大北園墓”)出土的兩件陶榻被稱為“大型陶案”[9]。1979年陳增弼先生撰文對以上三件“案”的形制、尺寸以及漢晉間案與榻的圖像與實(shí)物進(jìn)行分析,明確了案與榻區(qū)分的標(biāo)準(zhǔn),并將上述三件“案”確定為“獨(dú)坐”,糾正了以往將出土案、榻混淆的錯誤[10]。李蔚然先生亦持相同觀點(diǎn)[11]。近年江寧上坊孫吳墓出土的一件坐榻俑最能直觀地反映當(dāng)時案與榻之間的關(guān)系(圖一)[12]。人物俑坐于榻上,榻前置一案,二者的長度與高度一致,但案面相對榻面較窄。在結(jié)構(gòu)上,榻下曲尺形足與案下柵足亦顯然有別。南大北園墓中的“大型陶案”與“中型陶案”之間的尺寸關(guān)系亦與之相同,二者分別為榻與案[13]。出土這類無圍屏榻的墓葬,還包括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東晉墓[14]、隱龍山M 1與M 3[15]、郭家山M 13[16]。
最早出土的圍屏榻見于1979年發(fā)掘的堯化門老米蕩南朝梁墓,榻面已不存,僅存4件應(yīng)為榻足的“案足器”與10件用作圍屏的“小石板”。據(jù)該墓器物分布圖可知,這些“小石板”的一端均附有榫頭[17]。1988年發(fā)掘的梁桂陽王蕭象墓出土1件“祭臺”,“臺面下有5個小凹坑,另一端凹下一部分”[18]。1989年發(fā)掘的西善橋磚瓦廠南朝墓出土了形制相似的“石祭臺”,發(fā)掘者注意到“在石祭臺邊還發(fā)現(xiàn)3個凸字形小石板,將小石板插入祭臺的卯眼剛好吻合,說明這些凸字形小石板即祭臺上的插板”[19]。1991年發(fā)掘的西善橋第二磚瓦廠南朝墓出土了形制相同的石面板,面板“可與散落在旁邊的五塊圍屏石板榫卯相連”。簡報以此為依據(jù),將以往所發(fā)現(xiàn)的這類“案”或“祭臺”確認(rèn)為“石坐榻”[20]。邵磊先生也注意到以往部分考古簡報“不乏有將此種石圍屏指認(rèn)為龜趺墓志殘存志石或小石碑的誤會”,并指出白龍山南朝墓與鐵心橋馬家店村南朝墓均有圍屏石榻出土[21]。白龍山南朝墓出土的方形“墓志”與一端出榫的長方形“墓志”,應(yīng)分別為圍屏石榻的榻面與圍屏[22]。鐵心橋馬家店村南朝墓出土的“石祭臺”與“石板”同樣分別為圍屏石榻的榻面與圍屏[23]。
從上述材料中還可看出,榻除了被誤認(rèn)為“案”外,也常被稱作“祭臺”。“祭臺”一般指砌筑于棺前用以放置祭品的磚臺,通常被視為墓葬建筑的一部分而非隨葬物[24]。上述出土明器榻的各墓中均未發(fā)現(xiàn)磚砌祭臺,而其他砌有磚臺的東晉南朝墓葬中則不出土明器榻。從出土狀況來看,東晉南朝墓葬中的榻、案及其組合,與磚臺同樣發(fā)揮著承置部分隨葬器物的作用。這些器物常被認(rèn)為用于祭奠活動,因此若從實(shí)際功能的角度來看,墓葬中的榻、案及其組合與磚臺均可稱作“祭臺”[25]。然而,以上被稱作“祭臺”的陶質(zhì)和石質(zhì)明器榻,顯然模仿實(shí)用坐榻的造型制成,有別于磚砌祭臺,因此將之定名為“榻”較為合理。
南京地區(qū)東晉南朝墓出土的13件明器榻(表一),據(jù)材質(zhì)不同可分為陶榻與石榻,按造型差異可分為無圍屏榻與圍屏榻。陶榻均出于東晉墓葬,且均為無圍屏榻;石榻均出于南朝墓葬,除隱龍山M 1與M 3兩例外,其余均為圍屏榻。上述各墓除象山M 7保存完整以外,均遭擾亂破壞。但較之于墓中其他遺物,榻的體積較大,不易移動,故其出土位置應(yīng)與原始位置相差不遠(yuǎn)。象山M 7中的陶榻位于墓室內(nèi)西南方正對甬道處,即原有木棺的前方(圖二:1)。隱龍山M 1與M 3中的石榻,出土?xí)r均位于棺床之前(圖二:2)。西善橋第二磚瓦廠墓的圍屏石榻,出土?xí)r雖圍屏已散落于榻面周圍,但榻面仍位于棺床前方(圖二:3)。從各發(fā)掘簡報中的文字描述及遺物分布圖來看,除南大北園墓外,其他墓葬中榻的原始位置均在木棺前方[26]。

圖一// 江寧上坊孫吳墓坐榻俑
二、明器榻與墓葬的等級
河南省鄲城縣早年發(fā)掘的一座漢墓中曾出土一件石榻,榻面上銘刻“漢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12字[27]。“?”即榻。這件表明墓主身份的坐榻提示我們隨葬坐榻與墓主身份之間可能存在的關(guān)系,而這一點(diǎn)在前人研究中未能予以充分關(guān)注。
因此,有必要對上述墓葬的墓主身份以及包括榻在內(nèi)的隨葬明器家具的情況展開考察。如表一所示,除明器榻外,上述墓葬中還出土有陶質(zhì)或石質(zhì)的憑幾、案、帷帳座或燈座[28]。就墓主身份而言,南大北園墓被推定為晉成帝興平陵,出土明器家具類別最為豐富;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東晉墓、隱龍山M 1與M 3、白龍山南朝墓、西善橋第二磚瓦廠墓與鐵心橋馬家店村南朝墓墓主不明,但可推知其身份較高,其余各墓墓主明確,均為宗室成員或高級官僚[29]。
如上文所述,墓葬中置于棺床前方的榻、案或磚臺均有著祭臺的功能。選擇磚臺還是以榻、案作祭臺,或許與墓主人的身份有關(guān)。韋正先生將東晉墓葬分為皇帝、重臣、普通高級官員直至無官位的士族子弟、庶人四個等級,推測這一等級制度“可能只存在于帝王與重臣,而且這種差異也不一定有很強(qiáng)的強(qiáng)制性,其他社會成員的墓葬不存在明確的規(guī)定”,并指出“憑幾、床榻、帳座是一組特殊的隨葬品”,可視為帝王與重臣墓葬等級的表現(xiàn)[30]。在筑有磚砌祭臺的墓葬中,墓主均非庶人,但身份高低不一。如老虎山顏氏家族墓中,M 1墓主為安成太守顏謙的夫人劉氏,M 2墓主為州西曹騎都尉顏綝,M3墓主為零陵太守顏約[31]。象山M6墓主為衛(wèi)將軍、左仆射王彬的繼室夫人夏金虎[32],郭家山M 12墓主為散騎常侍、新建開國侯溫式之[33]。墓中筑有磚臺、墓主身份不明但推測有一定官位的墓葬則更多,如雨花臺丹寧路M 9與M 10[34]、雨花臺姚家山M 2[35]等等。所以,選擇磚砌祭臺的墓葬,墓主身份均在庶人之上,但等級參差不齊,而以榻、案作祭臺的墓葬,等級均較高,墓主應(yīng)為皇帝、宗室成員或個別重臣。
南京地區(qū)東晉南朝墓出土的明器家具中,憑幾數(shù)量最多,帷帳座或燈座次之,研究者常將二者作為推測墓主身份的依據(jù)之一[36]。通過對上述墓葬及其等級的分析可知,榻、案與憑幾、帷帳座或燈座的明器家具組合可作為南京地區(qū)東晉南朝墓葬等級判斷的依據(jù)之一。但由于多數(shù)墓葬均被盜擾,墓中原有明器家具的類型、數(shù)量與位置較難確定,因而墓葬等級的確定還應(yīng)結(jié)合墓葬形制與其他隨葬品進(jìn)行分析。

圖二// 榻在墓葬中的位置示意圖
三、榻與葬儀
《通典》所引賀循《議禮》的內(nèi)容常被用于六朝墓葬隨葬品的討論,但其中所舉的明器家具中僅談及憑幾與漆屏風(fēng)[37]。憑幾是六朝墓葬中出土數(shù)量最多的家具,漆屏風(fēng)或因不易保存,在東晉南朝墓葬中未有發(fā)現(xiàn)。雖然榻未在其所舉明器家具之列,但其他文獻(xiàn)材料中保留了墓中設(shè)榻的記錄。《晉書》提及王祥病重時對死后喪葬的安排,“勿作前堂、布幾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38],從其簡化喪葬的要求來看,墓中保留床榻比放置其他家具更為必要。石苞在生前預(yù)作的遺令中也要求:“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唅,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shè)床帳明器也。”[39]石苞強(qiáng)調(diào)墓中不必放置“床帳明器”,這從另一個側(cè)面可說明,在晉人喪葬觀念中,墓中設(shè)床榻、帷帳一類器用應(yīng)有特殊的意義。
榻作為明器用于隨葬的緣由,可從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況加以考慮。東漢陳蕃為迎接徐稺特設(shè)一榻,“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稺來特設(shè)一榻,去則縣之”[40]。宋文帝設(shè)榻以召僧人釋慧琳而為顏延之所嫉,“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xué)為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dú)榻,延之甚疾焉”[41]。由此可見,設(shè)榻待人是尊敬他人的禮儀表現(xiàn),坐榻者對主人而言應(yīng)有相當(dāng)?shù)匚唬艘嗫山忉尲墑e較低的墓葬中未隨葬坐榻的緣故。作為墓主生前家居的象征,墓中榻及一系列家具的布置,使墓主生前的家居生活以及應(yīng)享有的禮遇在其死后所處的墓室空間中得以延續(xù)。
還需注意的是,在墓門封閉前對死者的祭奠環(huán)節(jié)。《通典》在敘述葬儀時引賀循《葬禮》稱:“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先施幔屋于埏道北,南向。柩車既至,當(dāng)坐而住。遂下衣幾及奠祭。哭畢柩進(jìn),即壙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壙中。薦棺以席,緣以紺繒。植翣于墻,左右挾棺,如在道儀。”[42]柩車到達(dá)墓地后,“遂下衣幾及奠祭”,祭奠活動在墓道之北的帷帳內(nèi)進(jìn)行,將憑幾及其他祭奠器用布置好即可開始。“哭”禮結(jié)束后,先將棺置入墓中,再放置其他隨葬器物。
墓中憑幾應(yīng)有固定的擺放方式。象山M 7中陶憑幾出土?xí)r置于榻上,弧面朝外。南大北園墓雖遭多次盜擾,但發(fā)掘者據(jù)器物出土情況仍能判斷位于墓室西南角的陶榻與兩件“中型陶案”上原各置一陶憑幾。因此墓中憑幾原應(yīng)置于榻、案或磚臺上,且弧面朝外——這也是憑幾作為家具的使用方式,并可從魏晉時期墓葬壁畫中得以印證,如北京石景山魏晉墓石龕內(nèi)后壁(圖三:1)[43]、甘肅酒泉丁家閘5號墓前室西壁(圖三:2)[44]、朝鮮安岳三號墳西側(cè)室西壁[45](圖四)等墓主畫像。帷帳座或燈座則常出土于祭臺周圍或墓室四隅,用于架設(shè)帷帳或照明。墓中明器家具依照墓主生前家居布置而擺放。雖然賀循在葬儀的敘述中未提到榻或案,但在地面上帷帳中祭奠時理應(yīng)也按照同樣的布置方式,賀循所舉明器中的“憑幾”與描述葬禮中的“幾”應(yīng)包括憑幾及與之配合使用的榻、案一類家具。作為墓主靈魂所寄,墓室前部承置憑幾的榻、案或磚臺成為祭奠活動的中心。正如墓葬壁畫中的墓主畫像所示,墓主的形象以一如其生前坐榻憑幾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生者的意識中,接受祭奠。

圖三// 魏晉墓葬壁畫中的墓主畫像

圖四// 朝鮮安岳三號墳?zāi)怪鳟嬒?/p>
四、結(jié)語
“事死如生”的喪葬觀念指導(dǎo)著墓主及其家屬與工匠對墓室的營建與布置,同時也成為研究者將隨葬器物與日用器具的使用方式相關(guān)聯(lián)的前提。無疑,隨葬器物可為還原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實(shí)際使用情況提供線索,但隨葬器物在墓葬中的使用方式則常被忽視。
因此,將出土材料回歸其原本所處的環(huán)境中展開研究非常必要。雖然榻被視為漢唐時期的一種典型坐具,但通過本文的考察可知,榻的使用還受到了使用者身份與使用場合的限制,尤其是墓葬中明器榻的使用與墓主身份緊密關(guān)聯(lián)。就墓葬這一環(huán)境而言,榻與憑幾的組合發(fā)揮著祭奠活
動中表現(xiàn)墓主形象以及墓門封閉后延續(xù)墓主家居生活與生前所享禮遇的功能。

表一// 南京地區(qū)東晉南朝墓出土明器榻登記表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張學(xué)鋒老師的悉心指導(dǎo),謹(jǐn)致謝忱!)
[1]陳增弼:《漢、魏、晉獨(dú)坐式小榻初論》,《文物》1979年第9期;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第101頁。
[2]楊泓:《考古所見魏晉南北朝家具》(上、中、下),《紫禁城》2010年第10、12期,2011年第1期。
[3]蔣贊初:《南京東晉帝陵考》,《東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王志高:《南京大學(xué)北園東晉大墓的時代及墓主身份的討論——兼論東晉時期的合葬墓》,《東南文化》2003年第9期;齊東方:《中國古代喪葬中的晉制》,《考古學(xué)報》2015年第3期。
[4]東漢·劉熙撰:《釋名》卷六《釋床帳》,中華書局1985年,第93頁。
[5]唐·徐堅等著:《初學(xué)記》卷二五《床》,中華書局1962年,第601頁。
[6]徐時儀校注:《一切經(jīng)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5頁。
[7]陳增弼:《漢、魏、晉獨(dú)坐式小榻初論》,《文物》1979年第9期;孫機(jī):《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20-224頁。
[8][32]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1期。
[9]南京大學(xué)歷史系考古組:《南京大學(xué)北園東晉墓》,《文物》1973年第4期。
[10]陳增弼先生注意到南大北園墓的陶榻“器上殘留漆痕”,見其《漢、魏、晉獨(dú)坐式小榻初論》,《文物》1979年第9期。
[11]李蔚然先生亦注意到器型特大的“獨(dú)坐”明顯區(qū)別于其他案幾,見其《南京六朝墓葬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第101頁。
[12]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江寧區(qū)博物館:《南京江寧上坊孫吳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12期。
[13]南大北園墓出土“大型陶案”長125、寬100、高28厘米,“中型陶案”長126、寬35、高24厘米,二者長度與高度大致相同。
[14]簡報將所出陶榻定名為“陶案”。見南京博物院《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東晉墓》,《東南文化》1997年第1期。
[15]隱龍山M1、M2與M3各出土“石祭臺”1件及“祭臺足”4件,各墓所出“祭臺”應(yīng)均為榻。但M2所出石榻的面板已殘碎,無法推知其原貌,四件榻足均嚴(yán)重風(fēng)化,故暫不計入。見南京市博物館、江寧區(qū)博物館《南京隱龍山南朝墓》,《文物》2002年第7期。
[16]簡報將所出陶榻定名為“祭臺”。見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郭家山東晉溫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17]南京博物院:《南京堯化門南朝梁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12期。
[18]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陽王蕭象墓》,《文物》1990年第8期。
[19]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西善橋南朝墓》,《文物》1993年第11期。
[20]發(fā)掘者將其進(jìn)一步認(rèn)定為“獨(dú)坐”。見南京博物院《南京西善橋南朝墓》,《東南文化》1997年第1期。
[21]邵磊:《南京靈山梁代蕭子恪墓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南京曉莊學(xué)院學(xué)報》2012年第5期;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靈山南朝墓發(fā)掘簡報》,《考古》2012年第11期。
[22]南京市博物館、棲霞區(qū)文管會:《江蘇南京市白龍山南朝墓》,《考古》1998年第8期。
[23]南京市博物館、雨花臺區(qū)文化局:《南京鐵心橋鎮(zhèn)馬家店村南朝墓清理簡報》,南京市博物館編:《南京文物考古新發(fā)現(xiàn):南京歷史文化新探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5-111頁。
[24]考古報告及相關(guān)研究中常將祭臺作為墓葬建筑的組成部分,與鋪地磚、墓壁、封門墻、棺床、壁龕等相并列,納入到墓葬形制的描述與討論中。參見南京大學(xué)歷史系考古專業(y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編著《鄂城六朝墓》,科學(xué)出版社2007年,第16頁。
[25]齊東方先生指出:“有時置石板、案幾、陶榻,與祭臺應(yīng)該是同樣功能”,“晉墓中的祭臺是普遍現(xiàn)象,這些祭臺和案幾,以及與之組合的器物應(yīng)是祭奠用具,強(qiáng)勢延續(xù)到南朝時期。”參見齊東方《中國古代喪葬中的晉制》,《考古學(xué)報》2015年第3期。
[26]簡報推測兩件榻原分別置于主室東北角與西南角;“中型陶案”分別置于第一、二道門槽之間的甬道中與側(cè)室的甬道口。王志高先生推測,東北角的榻原應(yīng)置于棺床前而用于祭祀,其原位被附葬側(cè)室死者時所置“中型陶案”占據(jù),該榻“只能違例移置棺后的主室東北角”;位于西南角的榻則仍在原位。參見王志高《南京大學(xué)北園東晉大墓的時代及墓主身份的討論——兼論東晉時期的合葬墓》,《東南文化》2003年第9期。
[27]曹桂岑:《河南鄲城發(fā)現(xiàn)漢代石坐榻》,《考古》1965年第5期。
[28]此類器座常作饅首形或龍虎形,中部作圓孔以插桿。學(xué)界常將其認(rèn)定為“帷帳座(步障座)”或“燈座”。參見阮國林《談南京六朝墓葬中的帷帳座》(《文物》1991年第2期),羅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207-209頁),韋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學(xué)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第156-158頁)。
[29]各墓墓主身份均據(jù)發(fā)掘報告及相關(guān)研究。
[30]韋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學(xué)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第282-283頁。
[31]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老虎山晉墓》,《考古》1959年第6期。
[33]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郭家山東晉溫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34]南京市博物館、雨花臺區(qū)文化廣播電視局:《南京市雨花臺區(qū)寧丹路東晉墓發(fā)掘簡報》,《東南文化》2014年第6期。
[35]南京市博物館、雨花臺區(qū)文化廣播電視局:《南京市雨花臺區(qū)姚家山東晉墓》,《考古》2008年第6期。
[36]相關(guān)討論參見阮國林《談南京六朝墓葬中的帷帳座》(《文物》1991年第2期),羅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207-209頁),謝明良《從階級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載顏娟英主編《美術(shù)與考古》,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137-174頁)。
[37]《通典》載賀循《議禮》,詳見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diǎn)校《通典》卷八六《喪制四·薦車馬明器及棺飾》,中華書局1988年,第2325-2326頁。
[38]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三三《王祥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989頁。
[39]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三三《石苞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003頁。
[40]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卷五三《徐稺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1746頁。
[41]南朝梁·沈約撰:《宋書》卷七三《顏延之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902頁。
[42]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diǎn)校:《通典》卷八六《喪制四·葬儀》,中華書局1988年,第2346頁。
[43]石景山區(qū)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山區(qū)八角村魏晉墓》,《文物》2001年第4期。
[4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酒泉十六國墓壁畫》,文物出版社1989年。
[45]洪晴玉:《關(guān)于冬壽墓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
(責(zé)任編輯:劉興林;校對:張平鳳)
A Discussion on the BurialObject Ta Unearthed from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mbs in Nanjing Area
ZHOU Ting-xi
(DepartmentofArchaeology and Heritage,Schoolof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23)
Different names have been used in excavation reports to call the ta,the burial object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dating to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discovered in Nanjing area.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ta,examining the unearthed ta-like objects,and 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a and the brick altar from the same tomb,it is argued that the ta has a close tie with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tomb owner and was often used together with other forms of tables in ritual activities to represent the tomb owner’s soul.The ta and other tomb furniture represent the setting that the tomb owner had enjoyed before death with thewish thatsuch setting and enjoyment could be continued in his or her afterlife.
Nanjing;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a;altar;burials
K 871.42;K876
:A
2015-12-28
周庭熙(1992—),男,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考古文物系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漢唐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