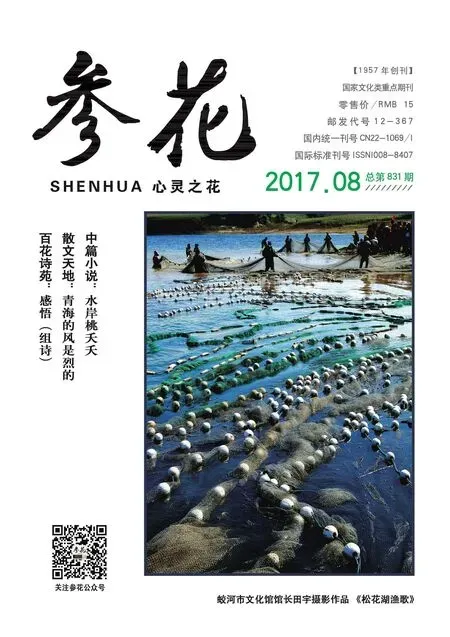“野子”之殤
◎徐醒
“野子”之殤
◎徐醒
人生是一場不斷尋求精神自足的流浪之旅。
人,為了滿足欲念,填補空洞的靈魂,心甘情愿把七尺血肉之軀放逐在精神的荒原之上,任由天命鞭撻,飽受人事戲弄,卻又樂此不疲。
欲望無盡,莽原無邊。人,骨子里高貴又卑賤,偉似古椿,亦微如草芥。
“在路上”是個體生命存在方式的普遍性展現。活法千萬種,根本動機似乎無法排除精神自足的追求。安土重遷帶來的所有心安,在這千百年來的社會動蕩、朝代更替中日漸消弭。時代飛速發展,客觀誘惑繽紛,人心日益膨脹,騷動不已。滿足,安享現在;不滿,即上征程。
人心不“安”,故鄉終“故”。
“前方是家還是無盡的曠野?”曹文軒曾經在《前方》中置此一問。是家也不是“家”,廣義上“家”的概念喻指精神歸宿。安足之地即是“家”,啟程之后“路”為“家”,心無定所,曠野也無盡頭。
人之立世,心法為軸。
束發之際,不管是隨父遠征“北上廣”,還是離家遠行奮戰學途,其悲壯程度不亞于古人參軍征戰沙場。無論是迫于無奈還是出于自愿,踏出家門的這一步源于內心難以撫平的波瀾,或攀比之下內心的惶恐,或柴米不裕時內心的焦灼,抑或是家門不興、重振無期的喟然長嘆。
在路上,為追為求,為逃為逸,多是基于某種特定的心靈需求。終于,心房因自足而通達,又因不安而促狹。
人,也許都有一勞永逸之愿,然而時世不定,人心有應,“逸”字無界。
五柳先生,徹悟明達,其精神境界庸人難臻。真隱士永久地獲得了一種精神自足,無欲無求,恬淡安適;偽隱士求得一時之足,名“隱”實“逃”,待時而起,肆機而動。南山之菊,人人可種,然而陶潛唯此一位,不可復制,只可效仿一二,稍有偏差,便得邯鄲學步之患。
人,都想成為精神貴族,卻總是淪落成荒野流浪狗。
流浪,是沒有固定方向的!人類覓食無主,趟過一條又一條或深或淺的河。縱使收獲豐碩,披金戴銀,雖解溫飽,卻仍如行尸走肉。河岸非彼岸,物豐而神空,人類悲劇性的實質恰恰在于:人,百般折騰,終被欲念所奴役!
人在精神的荒原上恰似戴著項圈的流浪狗,瘋狂地繞著“精神自足”的旗幟打轉,爭搶一塊腐臭的膝蓋骨。原始獸性的爆發性奔馳,歇斯底里,永不知倦。
人,潛意識里有些許奴性,攙雜點狗性的依賴,潛隱獸性,偶會咬人。
眾生錯集的萬古荒原上,時有瘋狗一群。毋庸置疑,人類瘋狂向前的征程拓展了人類精神之原的疆界。
人,欲壑如此深重,生命卻這般堅韌,代代相勉,誓移乾坤。
于此觀照,諸如和靖先生等隱逸之士,在這精神荒原上為自己的方寸心臺圈出三尺綠蔭,植梅養鶴,自得其樂,何嘗不是一種自欺欺人,何嘗不是一種自私自足式的微觀生存法則的體現。
蘇運瑩的《野子》唱道:“任風吹, 任它亂,毀不滅是我盡頭的展望。”
彼岸無岸,前方無方。看,那人在這荒野上盡情撒野,引頸悲吟!
(責任編輯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