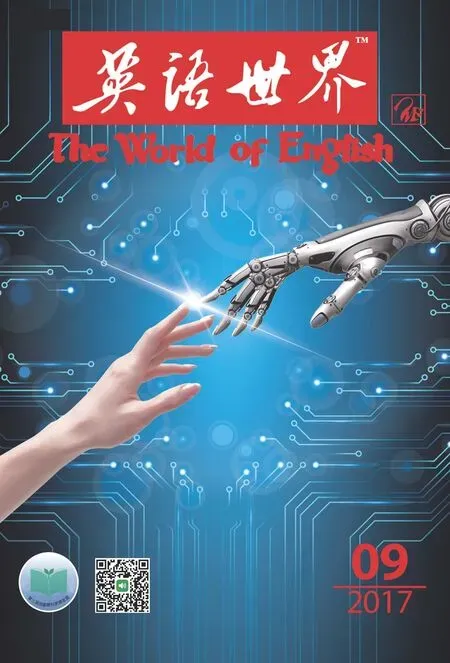一份堅持
文/金圣華
一個不是念文科的學生在講座后提問的環節里,向白先勇提出問題:“文學到底有什么用?”聽眾大概都沒有料到,白老師很干脆地回答:“文學是沒有用的!”
文學沒有用?那這么多人來聽白先勇講《紅樓夢》,把整個中文大學何善衡書院大講堂七八百個座位都占得滿滿的,聽時鴉雀無聲,全神貫注,聽后熱烈鼓掌,踴躍發問,又是所為何事?
文學有什么用?的確是個難題,是個迷思。以世俗實際的眼光來看,學文學,根本不是個飛黃騰達的途徑、青云直上的梯階;念文學作品,也算不得什么正經事。以前在美國圣路易華盛頓大學念研究院時,碩士論文以曹禺的劇作為研究對象,正當我面對大堆資料潛心苦讀、不斷尋思的時刻,兩位念理工科的室友卻在茶余飯后,把我的研究材料當消遣,隨手拈來翻閱,看得嘻嘻哈哈,不亦樂乎!她們看得明我的行當,我卻看不懂她們的專業,兩者相較,高下立判,豈不令人氣結!
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學文學,創作文學作品呢?白先勇說得好,文學不實用,但是并不表示沒有價值,因為文學是一種感情教育,在吾人生活中不可或缺。
多年前,應文壇前輩譚仲夏之邀,為一本名為《世界四百位作家談寫作》的書籍撰寫序言。那本書的來歷不小,緣起于1985年法國圖書沙龍發起的一項活動,即通過法國駐各地使館,邀請各國著名作家以“您為什么寫作”為題,撰文作答,答案由《解放》雜志專輯刊載。這本文集后來由多國翻譯成書,本港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合約簽訂,稿酬已付,只待送廠付梓,誰知突生變故,終于擱置出版計劃。但是我撰寫序文之前,卻是有機會對這本文集仔細詳讀,先睹為快的。
四百位著名作家,紛紛夫子自道,現身說法,概述自己當初入行的緣由。歸納起來,可以分為四大類:第一類冠冕堂皇,以天下為己任,為促進文化、解放人類而寫作;第二類冷靜理智,為尋求生命真諦、探索人生奧秘而創作;第三類極其感性自我,認為生也有涯,歲月匆匆,為了對個人的鞭策、對存在的肯定,而留下印記;第四類則簡潔直率,以“不明所以”“身不由己”而提筆。
無論如何,寫作始終是一種心靈的慰藉、感情的宣泄,也是一種存在的肯定、自我的鞭策。王蒙說:“寫作,為了表達,為了交流,為了建筑心靈之間的橋梁。寫作,又是為了記憶,為了挽留:當一切都煙消云散以后,還會有幾行文字留下來成為生命的見證、歷史的見證。”董橋說:“寫作是獨往獨來的事業。不怕寂寞,不求掌聲,在寧靜中認清喧嘩,在喧嘩里傾聽寧靜。”白先勇則表示,自己寫作,是“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化為文字”。即使如此,在寫作的過程中,要尋章摘句,推敲斟酌,找出一個最為適當的表達方式,則作家必須嘔心瀝血,殫精竭慮,方能成事。
林文月曾經寫道:“文字對詩人說:‘我其實是空洞的。’詩人回答文字:‘我的工作便是將空洞排列成豐沛。’”其實,要化空洞為豐沛,所需的是一份堅持,一種鍥而不舍的努力。寫作的生涯,充滿不足為人道的艱辛,就如契訶夫名劇《海鷗》中作家特里果林所言:“我接連不斷地寫,就像一個旅客馬不停蹄那樣……我放不開自己來休息休息,我覺得我是在吞噬自己的生命,是在把自己最美麗的花朵里的花粉一起用盡,再把我的花朵一起采下來,并且踐踏著花根,來向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誰的人,供奉一剎那的花蜜啊!”(焦菊隱譯)這種宗教式的奉獻,所尋求的就是心靈與知音之間的對話,而知音在不知的彼方,甚至經常是隔空隔代,超越年歲,不分畛域的。
在白先勇的身上,所看到的就是這份堅持。自從21世紀以來,他不斷努力,推廣昆曲,出版《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再于2016年出版《白先勇細說紅樓夢》,把畢生對《紅樓夢》的認識傾囊相授。正如葉嘉瑩教授所說:“《紅樓夢》是一大奇書,而此書之能得白先勇先生取而悅之,則是一大奇遇。”因此,紅書與白說的結合,白公子與怡紅公子的對話,就成為千百年難得一見之奇遇,讓滿堂聽眾涵泳其中,蒙受了畢生難忘的感情教育。
在余光中身上,也看到這份堅持。余教授自從前年底不慎摔跤后,一直在家休養。他在最近的來信中說:“雖然在家養病,成了宅男,近日卻忙于出書。《英美現代詩選》新版,在初版本出后半世紀,添譯了約80首,涉及許多‘后務’,不可開交。另外還忙于出一本評論集。所以你會收到我好幾本新書。”
就是這份堅持,也使中文大學推動的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自1998年創建迄今,仍繼續前行。19年來,我們守護著華文文學,就如西漢時蘇武牧羊一般,在天寒地凍的環境中,仍滿懷信心,堅毅不屈。
文學無用而有價,文學不死,千百年來所依靠的,也就是這一份永不停歇的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