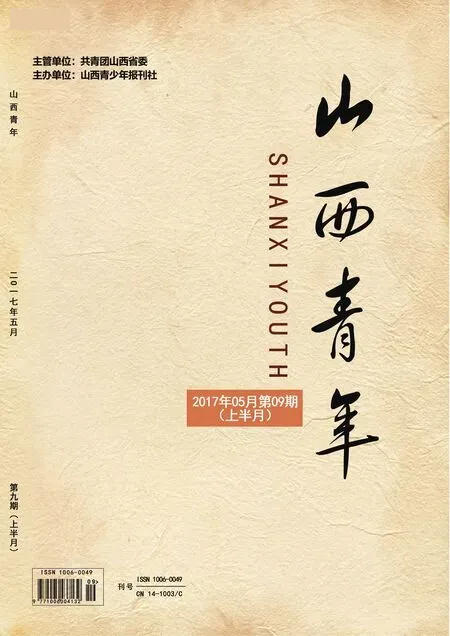論司馬遷“發憤著書說”
趙 慧
河北大學文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
論司馬遷“發憤著書說”
趙 慧
河北大學文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主張作家著書意在抒發郁結之氣,這是司馬遷對創作的概括總結,也是他文學理論精髓的體現,在文學批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本文將以“發憤著書說”為考察對象,通過對其形成背景、思想內涵和深遠影響等方面的探討,具體闡釋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
“發憤著書說”;形成背景;思想內涵;深遠影響
一、“發憤著書說”的形成背景
理論學說的誕生,是時代環境、思想氛圍與作者自身人生遭際等多種元素作用的結果。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形成主要受到司馬遷思想來源、父親遺志和李陵事件等方面的影響。
首先,司馬遷早前接受的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漢景帝延續漢文帝年間的黃老思想,崇尚無為而治,漢武帝即位后推行儒學。因此,出生于這一時期的司馬遷,其思想必將受到道家和儒家的雙重熏陶。漢武帝執政后推行改革,以儒家大一統思想取代文景時期的道家思想,司馬遷師從孔安國等大儒學習,因此司馬遷的成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司馬遷看來,“著書”旨在“發憤”,所以司馬遷的思想頗具叛逆色彩,這樣的傾向顯然已經沖破儒家思想范疇,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司馬遷雖然成長于儒家學說的氛圍,同時又受到推崇道家思想的父親的影響。因此,儒道思想為“發憤著書說”提供了理論依據。此外,司馬遷高度評價屈原的《離騷》,屈原的人格和文學精神也必定對司馬遷的文論產生影響。
其次,李陵事件的打擊和父親遺志之間的矛盾起到促進作用。李陵事件對司馬遷造成巨大影響,只因替李陵辯護便使司馬遷遭受宮刑懲罰,這不僅是對身體的傷害,更是對司馬遷人格的侮辱。但是,司馬遷的任務還沒有完成。父親司馬談年事已高,無力完成修史夙愿,因而父子洛陽相會后,司馬遷便接過了父親的心愿,立志完成修史重任。一面是奇恥大辱對身心的折磨,一面是父親殷切的期望,最終司馬遷含淚忍辱,以筆泄憤,將內心的憤懣和修史的重任融為一體,完成了史無前例的鴻篇巨作。
因此,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形成,與他的思想體系、人生際遇等因素密不可分。
二、“發憤著書說”的思想內涵
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涉及作家、作品等多個方面,是多重思想內涵相互交織的完整的思想體系。
首先,司馬遷認為著書的動機是作家個人的不幸遭際,強調作家本身對創作的動機性作用。前秦時期,文學更多是政治和社會的傳聲筒,在很大程度上被賦予政治色彩。但是司馬遷在經歷過不幸的人生遭際后,內心憤懣,逐步體會到著書的動力是心中的不平之氣。當個體極度悲苦時,其思想往往會更加深刻,并且會進一步調動情緒深入思考,作家也不例外。因此,司馬遷強調著書要從個人不幸的人生經歷出發,抒發作家自己的心聲。
其次,司馬遷認為優秀的作品大都是“發憤著書”的成果。司馬遷指出,優秀的作品需要經歷“發憤著書”的過程,要抒發作家的怨憤,只有宣泄不平哀怨的作品才能達到更高的審美規范,才能進入偉大作品之列。因此,司馬遷極力推崇屈原的《離騷》,他認為屈原被奸佞小人陷害,正直的人格遭到誣陷,使得他心中憤恨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屈原創作《離騷》,作品真摯感人,具有極高的藝術魅力。因此,《離騷》是“發憤著書”的代表,正是因為屈原憤而作《離騷》,才使得《離騷》具有永恒的價值。這也印證了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核心思想,即偉大的作品都是“發憤著書”的結果。
司馬遷將個人的人格和情緒融入到作品中,使作品不再是社會訴求的單純表達,更是作家心中郁結之氣的流露,并且強調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偉大的作品,這是“發憤著書說”最主要的內涵。
三、“發憤著書說”的深遠影響
“發憤著書說”是司馬遷對文學創作的概括和升華,不論對前人文學創作的總結,還是對后世文學理論的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首先,“發憤著書說”是司馬遷創作《史記》的精神支柱。如上文所講,司馬遷在卷入李陵事件,慘遭腐刑后開始創作《史記》。如此的屈辱使司馬遷內心幽憤抑郁,“發憤著書說”無疑為他提供了堅定的信心和不竭的動力。透過《史記》,足以體會司馬遷的“憤”,司馬遷正是在梳理史料的基礎上,通過抒發對社會歷史和個人遭際的郁結情緒而作《史記》。因此“發憤著書說”對司馬遷自身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其次,“發憤著書說”著重強調作家情感對作品創作的影響,突出作家在創作中的重要性。在司馬遷之前,作家更多是反映社會歷史的角色,因此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作家自身的意義。在司馬遷看來,《左傳》、《離騷》等作品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作家著書的動力是“發憤”,因此強調了個體在寫作中的作用。從作家自身的情感體驗到作品的敘述,司馬遷將個體人格和文學精神緊密結合,這是人文精神在其文學思想中的集中展示,更是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中的典型表現。因此,“發憤著書說”是對前人文學創作的天才概括,具有偉大的開創性。
此外,“發憤著書說”對后世文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發憤著書說”來源于作家自身對黑暗現實和不幸命運的憤慨,因此激發了后世文人的創作。同時,司馬遷強調作家在創作中的主導地位,為魏晉文論自覺意識的覺醒奠定了理論基礎。魏晉是我國古代文學走向自覺的時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到優秀的作品源于作家自身不幸的遭遇,鐘嶸在《詩品序》中也有類似觀點,他們的看法與“發憤著書說”如出一轍,因此司馬遷為魏晉自覺文論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之后,歐陽修“詩窮而后工”等文學理論都證實了個人的不幸遭遇能刺激文學創作,直到今天仍有指導意義。
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將個人內心的幽憤苦悶之情轉化為文學創作的精神動力,不僅為其自身的創作提供了不竭的動力,而且對后世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具有永恒的價值。
[1]袁濟喜.新編中國文學批評發展史(第三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2]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程世和.司馬遷精神人格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4]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5]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I
A
1006-0049-(2017)09-02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