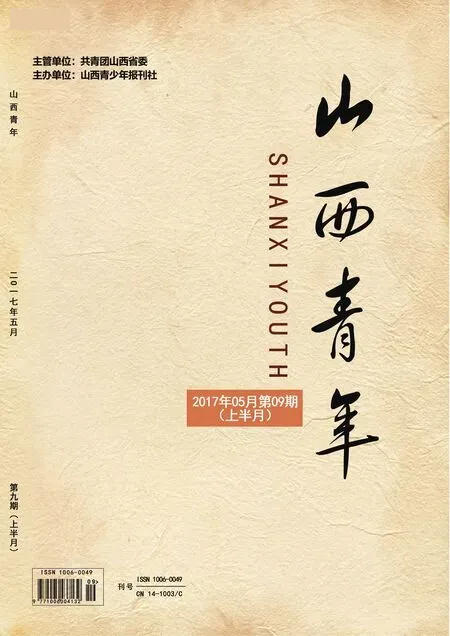《紅旗譜》中對傳統俠義小說的敘事的繼承和發展
賈鳳岐
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0
?
《紅旗譜》中對傳統俠義小說的敘事的繼承和發展
賈鳳岐*
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0
《紅旗譜》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小說通過對中國傳統俠義小說的敘事的借鑒、吸收和發展,精彩的描繪出了一部反映大革命時期農民如何由家族復仇走向階級斗爭的帶有史詩般性質的作品,并為重建“中國的敘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紅旗譜》;俠義小說的;敘事
在五六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紅旗譜》作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十七年文學的典范之作,在出版后便受到了廣大人民的喜愛和推崇。小說中復雜眾多的人物,曲折波蕩的情節,廣闊的思想內容,以及其在一定程度上的社會功利性,使其在敘事方法和敘事結構上對中國傳統俠義小說的敘事進行了相應地繼承和發展。一方面通過對傳統敘事方法傳奇性和通俗性的繼承,使小說更加充滿趣味性且淺顯易懂,從而符合廣大人民的閱讀經驗和閱讀水平,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擴大了其受眾面;另一方面,通過對傳統敘事結構(發生-發展-高潮-結局)的改變,使其由傳統的單純表現家族恩怨的傳奇演變成了具有正義性的農民革命小說。這種敘事上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分析《紅旗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紅旗譜》對傳統敘事的繼承
《紅旗譜》對傳統敘事的繼承首先表現在小說本身的敘事結構上。(1)以為父報仇作為小說的引子。在小說開頭通過一樁上輩之間的歷史糾紛事件——“朱老鞏大鬧柳樹林”,對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的身份進行了相應的介紹,并通過朱老鞏(父)的失敗及其臨終前對兒子小虎子的囑托:“要記住,你久后一日只要有一口氣,就要為我報仇”[1]作為故事的源頭,從而掀起了為父報仇的新篇章。同時,在這里朱老鞏父親的角色也與傳統俠義小說中的家族或者國家相對應,顯示出了報仇的必要性。(2)負仇出走——復仇而歸。在中國傳統的俠義通俗小說中,通常會在為父報仇的主要脈絡中穿插進一個小的離去——歸來的模式。主人公在家破人亡之后為生存背井離鄉,在外面練就一身本事之后再歸鄉為父報仇。這種大結構中套小結構的模式即推動了小說情節的發展,又增添了故事的傳奇性。同時這種模式也符合中國幾千年來流傳下來的關于“報仇”這一行為的潛意識的認知模式。因此作者梁斌在《紅旗譜》中也相應地采取了這種模式,使小說適應了人們所喜聞樂見的模式。
其次《紅旗譜》敘事手法上也借鑒了傳統俠義小說的所常有的傳奇性和通俗性。(1)小說中獨特的傳奇性。在小說中,作者從一開始便通過朱老鞏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為小說營造了一種替天行道的俠義性。隨后朱老忠的返鄉復仇以及朱,嚴兩家在報仇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忠、信、義等品格更是對傳統俠義小說的一脈相承。如在小說中朱老忠在去見被捕入獄的嚴運濤受阻時:(1)他又想起古書上說的“梁山伯的人馬,還截過法場……”。[1]這種俠義性推動了整個故事的情節發展,使小說更加生動形象,具有傳奇色彩。(2)小說中的通俗性。因傳統小說多被看做是娛樂的工具,因而文人在創作時多采用淺俗易懂的市井語言。在《紅旗譜》中,作者為了符合出農民的身份特征,增加故事的真實性,同時也為了讓文學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也延續了這一傳統的敘事方法,用通俗易懂的白描和具有北方地域色彩的民間口語作為全文的描寫手法,使語言更加直白,故事也淺顯易懂,從而滿足人們的閱讀水平和閱讀方式。如朱老忠常常掛在嘴邊“出水才看兩腿泥”
二、《紅旗譜》對傳統敘事的發展
《紅旗譜》對傳統敘事的發展與其繼承相照應,首先表現在敘事結構的轉折上——由傳統的家族復仇轉折到階級革命。梁斌在《紅旗譜》出版后曾發表多篇文章來講述《紅旗譜》的創作過程。并在《我怎樣創作了<紅旗譜>》中說道:“《紅旗譜》從短篇發展到中篇,又從中篇發展到長篇。其中,有些人物在我的腦海里生活了不下一、二十年。開始長篇創作的時候我熟讀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仔細研究了幾部中國古典文學,重新讀了蘇聯小說,時時刻刻在想念著,怎樣才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那些偉大的品質寫出來。”[2]因此,雖然《紅旗譜》以為父報仇開始,但若和傳統小說一樣以報仇成功為結局顯然不符合時代及政策所賦予它的使命性。為了使“農民復仇”與“階級斗爭”相連接,改變了傳統小說中把“返鄉復仇”作為全書的高潮和把“報仇成功”或“放下恩怨”當做結局,而是把朱、嚴兩家三代不斷與馮家兩代人之間不斷地斗爭作為小說的發展,并在斗爭中第三者——賈湘農出現后,把整部小說推向了高潮,在最后留下了一個十分具有意味的開放式結局,從而使整部小說所表達的思想內容隨著結構的變化而得到了加深。
其次,《紅旗譜》在敘事方式上也與傳統的俠義小說有所不同。雖然小說有意借鑒傳統小說的敘事方法,但為了突出“農民革命斗爭”,小說在敘述語言上做了多方面的改變,尤其是人物的對話方面,加入了許多帶有政治宣言性質的官方話語。如江濤對嚴萍講“目前的農村經濟狀況,講到農村的剝削關系”[1]以及朱老鞏和朱老忠在護鐘及報仇的時所吶喊和宣揚的始終是為了“全村四十八戶被馮家剝削和壓迫的村民的利益”[1],這樣的話語雖引起的政治功利性常常為人們所批評,但不可否認,這些話語也巧妙地使小說更好的由傳統的“農民復仇”轉化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并通過農民復仇的過程講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義性,使“家族敘事作為一種隱形結構存在于革命歷史小說。”[3]
長篇小說《紅旗譜》自出版以來,受到了不同時代褒貶不一的評價。作為十七文學中的優秀小說,雖然受政治影響出現了一些弊端,但我們不可否認它的出現對我們整個當代文學史的影響。尤其它所表現出來的在敘事方面的獨特的探索,更是為重建“中國的敘事”奠定了基礎。
[1]梁斌.紅旗譜[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2,163,239.
[2]梁斌.我怎樣創作了<紅旗譜>[J].文藝月報,1958(5).
[3]曹書文.50-70年代家族敘事的隱形書寫[J].文藝爭鳴,2008(4).
賈鳳岐(1992-),女,漢族,河南安陽人,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
I
A
1006-0049-(2017)09-01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