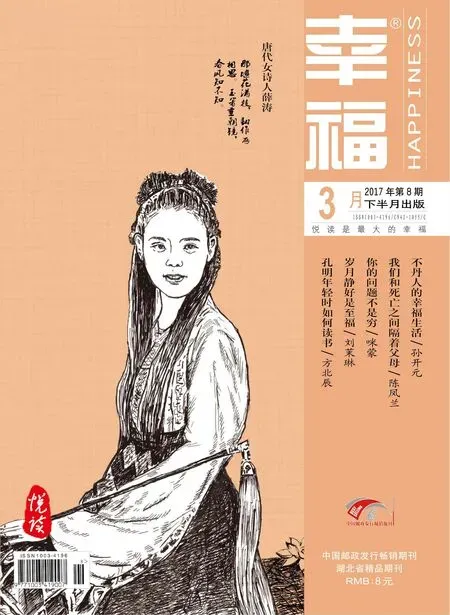爆笑
爆笑
換靴子
某人有一雙厚底靴和一雙薄底靴。一天早晨,他錯(cuò)將一只厚底靴和一只薄底靴穿在腳上。他出門去辦事走在路上只覺得一只腳高,一只腳低,非常不舒服。他詫異地說(shuō):“真奇怪,今天我的腿怎么變得一長(zhǎng)一短了?”
路上有人提醒他說(shuō):“你是穿錯(cuò)靴子啦。”
他聽了這話,急急忙忙回家去換靴子。可是,他到家一看,想了一想說(shuō):“甭?lián)Q啦,家里的也是一厚一薄。”
我叫你的兒子也挨凍
宋朝時(shí),有一個(gè)太尉很溺愛兒女。一天他回到家中,看見兒子沒穿褂子跪在雪地上。他問明原委,知道是自己的母親體罰有嚴(yán)重過(guò)失的孫子。于是他也光了脊梁,讓人把自己綁上,跪在兒子旁邊。
他母親聽說(shuō)此事,前來(lái)問他為什么這樣作賤自己?太尉回答說(shuō):
“你凍我的兒子,我也凍你的兒子!”
吃餅
有一個(gè)人餓極了,便到一家小吃店買餅吃。他吃完一個(gè)餅不飽,接著吃第二個(gè)餅。這樣一連吃了六個(gè)餅,他還不飽。直到吃完第七個(gè)餅,他才感到滿足了。可是,這時(shí)他突然懊悔起來(lái):“唉,早知道這樣,我一開始就吃第七個(gè)餅,豈不夠了,何必白白吃那六個(gè)呢!?”
剪箭桿
從前,有一個(gè)士兵在一次戰(zhàn)斗中腿部中箭,疼痛不已。長(zhǎng)官請(qǐng)了一位外科醫(yī)生來(lái)治他的箭傷。醫(yī)生看了看說(shuō):“這個(gè)不難!”便拿出一把剪刀,將露在外邊的箭桿剪掉,然后就索取手術(shù)費(fèi)要走。
士兵發(fā)急地說(shuō):“剪掉箭桿子誰(shuí)不會(huì)?我要你拔出射進(jìn)肉里的箭頭呀!”
醫(yī)生搖搖頭說(shuō):“外科的事我已做完,挖掉肉里的箭頭那是內(nèi)科的事。”
半個(gè)字
有一個(gè)粟監(jiān)(明清時(shí)期,向官府納粟買得監(jiān)生資格,稱為粟監(jiān))學(xué)識(shí)寡陋,妻子勸他好好讀書。監(jiān)生聽了不耐煩地說(shuō):你整天逼我讀書,我且問你,讀書有什么好處呢?
妻子回答說(shuō):一字值千金,難道不好嗎?監(jiān)生怏怏不樂,反問道:難道我這個(gè)身子,只值得半個(gè)字嗎?
有理
古時(shí),一官最貪。兩人打官司,原告送他五十兩銀子,被告知道了加倍送貪官銀子。上堂時(shí),貪官大喝:打原告二十大板。原告伸出手作五數(shù)說(shuō):“老爺,小的是有理的。”貪官一只手放在額頭,一手伸開作十狀,說(shuō):“他比你還有理哩。”
譏人弄乖
鳳凰壽辰,眾鳥拜賀,只有蝙蝠不到,鳳凰斥責(zé)蝙蝠說(shuō):“你位居我下,卻不來(lái)拜賀,為何如此傲慢?”蝙蝠說(shuō):“我有腳,屬于獸,為什么要拜賀你?”一天,麒麟過(guò)生日,蝙蝠也沒有到。麒麟也斥責(zé)蝙蝠。蝙蝠說(shuō):“我有翅膀,屬于禽,為什么要拜賀你?”麒麟與鳳凰相會(huì),談及蝙蝠之事,互相慨嘆說(shuō):“當(dāng)今世上惡薄,偏偏生出這樣不禽不獸的東西,真是奈何他不得。”
白嚼
有三個(gè)人坐在一起,偶然談及家里的老鼠可惡。甲說(shuō):“家里吃的,散放不得,否則一轉(zhuǎn)眼就將被它們偷去。”乙說(shuō):“家里的衣服、書籍也散放不得,時(shí)常被它們咬壞。”丙說(shuō):“唯有我家的老鼠不偷吃的、穿的,整夜吱吱叫到天明。”甲乙二人問:“那是什么原因?”丙回答說(shuō):“專靠一味白嚼。”
取笑
甲乙二人同行,甲望見一個(gè)顯者的車乘,對(duì)乙說(shuō):“這是我的好友,他見我必定下車,我應(yīng)該回避。”不想竟躲避到那個(gè)顯者的家里。顯者進(jìn)門,驚詫說(shuō):“是何人撞進(jìn)來(lái),藏在我的院子里。”于是呼喊仆人揍他并把他驅(qū)趕了出來(lái)。乙問道:“既然是好友,為什么被他毆打侮辱?”甲回答說(shuō):“他從來(lái)都是這樣,和我取笑慣了。”
認(rèn)族
有個(gè)姓王的人,一向最好聯(lián)譜,每當(dāng)遇到姓相似的人,不曰寒宗,就說(shuō)敝族。偶然遇到一個(gè)姓汪的,指給朋友說(shuō):“這是舍侄。”朋友問:“汪姓怎么會(huì)是和你同族?”回答說(shuō):“他是水窠路里王家。”遇到一個(gè)姓匡的,那人也認(rèn)做是侄孫,朋友說(shuō):“匡與王,更差得遠(yuǎn)了。”那人回答說(shuō):“他是槿墻內(nèi)王家。”那人又指一姓全的,也說(shuō)是舍弟。朋友說(shuō):“更是不相干了。”那人說(shuō):“他是從小在大人家做蔑片的王家。”那人又指姓毛的是寒家,朋友大笑其荒唐,那人說(shuō):“你不曉得他本是我王家一派,只因他生了一尾巴,弄得毛頭毛腦了。”朋友問:“王與黃同韻,為什么反而不是一家?”那人回答說(shuō):“怎么不是,那是廿一都田頭八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