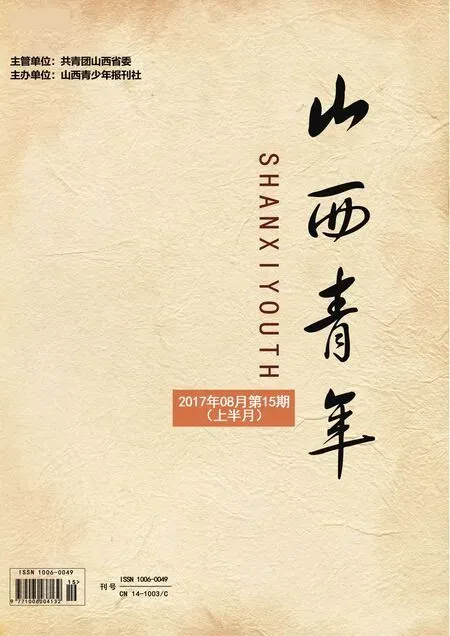馬金蓮小說《梅花樁》的底層敘事探析*
景莉莉
北方民族大學,寧夏 銀川 750021
?
馬金蓮小說《梅花樁》的底層敘事探析*
景莉莉*
北方民族大學,寧夏 銀川 750021
馬金蓮是回族優秀的著作頗豐的小說家,她的小說多取材于底層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女性甚多,這源于她的最底層的農村家庭出身和特殊的回民女性身份。她有著對平凡事物敏銳的洞察力,習慣用弱者的眼光打量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她獨特的底層敘事話語方式,在城市‘80’后寫作包圍中,點綴了最鮮亮的一筆。本文正是用底層敘事的視角來探析馬金蓮的小說《梅花樁》。
底層敘事;命運救贖;梅花樁
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飛速挺進,城鄉差距日益拉大。而農村中的年輕女性不再像母輩那樣甘愿守著貧瘠的土地和老實的莊稼漢終勞一生、終苦一生,她們背井離鄉逃離農村來到繁華的城市,沖破命運的枷鎖卻依然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層。馬金蓮的《梅花樁》正是書寫了生活在這一擠壓環境下苦苦掙扎的女性,女主人公“我”遭遇婚姻變故獨自含辛茹苦的撫養兒子,獲悉親哥哥殺人后精神上痛苦地掙扎和煎熬式的忍耐,一切的一切都像一把刀子捅向她的心窩。
一、希望到失望:城市并非命運的救贖地
從2005年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作家把眼光聚焦于底層民眾的底層生活,表現底層人民在現代化進程中思想上的變化和行為上的選擇,底層民眾重新回到了主流文學視野的關注之內。其實對底層的關注自五四以來就很興盛,但大多數底層敘述的主體并非真正的底層老百姓,他們的作品和評述往往是“作家站在啟蒙者的立場上敘述底層的故事,塑造底層人的形象”。①而這種以啟蒙者的視角審視底層老百姓的生活往往會失真,無疑會強化或弱化他們的苦難,曲解他們的情感,他們都是被任意言說的“他者”,真正的他們并未顯現。可馬金蓮不一樣,她是切切實實地生活在底層的,她對于身處底層的喜怒哀樂有更真實的感悟和體會。
反觀《梅花樁》中的女主人公“我”,生長于農村卻不想扎根于農村,農村繁重的農活粗糙的生存狀態就像一潭沒有希望的深淵驅使她離開。她驕傲她竊喜自己擁有了和農村的女伴不一樣的命運,她落腳城市打工生活,自由戀愛結婚生子。可是在吮吸掉幸運和生活表面的甜之后,也漸漸咀嚼它更深層次的苦。
來到城市卻依然過得艱辛,為了節省一塊錢,選擇步行去上班,為了省一塊錢和出租車司機磨盡嘴皮卻依然沒掏出五塊錢。為了節約錢“我”和丈夫不得不租住在超市逼仄的小出租屋內,在這個狹小的空間里孕育了兒子遭遇了離婚更見證了被生活打磨后操勞疲憊的“我”的經歷。提到婚姻,這無疑是“我”沖出農村的藩籬寄居城市的救命草,可是如今連這根草葉也沒了,“我”感慨:“這讓我禁不住一再想到自己已年過三十歲卻不能保全一份婚姻的那種蒼茫和無助”②面對破碎的婚姻“我”獨自承擔起了生活的重擔,養育兒子貼補家用,可是卻不敢將實情講給父母和兄長,因為在傳統的鄉俗觀念里離婚是不光彩的是會聯想到不夠賢惠和不守婦道的,可見傳統的封閉狹隘的倫理觀又形成了對“我”的另一種擠壓,在傳統的農村婚姻關系中,女性就像一個富有“原罪”的“他者”。婚姻家庭一切的不幸都會強加在她們身上,而往往沒有為自己辯駁的權利和機制。
未曾結婚生子的“我”把生活看成一件華袍,殊不知這件袍子在瑣碎與艱辛的生活面前不堪一擊,很快就斑駁破碎。“我”曾試著逃離鄉里女孩的悲苦命運,年少嫁為人婦,生一堆孩子辛苦撫育,撫育成人又開始為兒孫操心……但是逃離農村寄居城市的我,被生活擠壓的越來越殘酷,以至于我會在心中比較如果不掙扎著改變自己的命運,向其他女孩一樣嫁個莊稼漢守著幾畝薄田,日子會不會好一點。看來苦苦地掙扎著的貌似充滿希望的城市并非“我”的命運救贖地。
二、駭人的驚聞和哥哥的梅花樁
作者在書寫哥哥殺人經歷時采用的是一種“內心化”的敘述方式,她在她的底層敘事的寫作中始終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來講述故事,她把貌似驚悚粗暴的殺人經歷用“我”的眼睛觀察的更脆弱更平和更復雜也更無奈。這樣避免了作者作為敘述人代入上帝視角,以“我”看問題更立體更深刻。“底層敘述不是侵入,而是以一種‘內心化’的方式對文本進行滲透。他以一種平等的態度、仰視的姿態觀察他的故事人物,同時追求一種無我化的敘述效果。在這種別樣的冷漠敘述中讀者甚至會忽略掉作者的在場,從而零距離地與故事人物進行接觸,從而最大化地了解事實本身”。③
哥哥的突然到來打亂了“我”一成不變的生活,為了迎接哥哥到來,“我”精心整理房間,努力掩飾離婚的事實。平時節儉將就的“我”為了招待好自己的親哥,餐餐葷素搭配。可是母親突如其來的電話告知:“哥哥殺了四口人”,無盡的苦難又蜂擁而至。哥哥無法忍耐嫂子出軌后帶走了哥哥的三個孩子幾次三番的拒絕回家,哥哥激動之下殺了四口人。文中的“我”努力控制情緒可是竟不能自已。文中的哥哥在帖子中被描述成瘋子,惡魔,人渣。在李姐眼里是毫無人性不可理喻的。可是在“我”的眼里記憶里哥哥是良善的,在兒子阿旦眼里舅舅就像父親一樣。多元視角下哥哥的形象立體起來。
直到一天,兒子被陌生的男人接走。“我”內心焦灼如焚,原來是哥哥教兒子練習梅花樁,他希望兒子練好武功能保護“我”,而一切又重新回到記憶里:“哥哥訓練我練梅花樁,我卻因疼痛沒堅持下來”。哥哥儼然已經知道了一切,“我”的離婚,“我”的苦難,“我”的掙扎,而“梅花樁”在這里正像一種“救贖”,那是親人對飽受苦難的“我”的救贖,對辛勞孤獨的“我”的保護和愛。在底層敘述中,“馬金蓮始終以弱者的眼光打量整個世界,她敘述弱者的痛苦,既不控訴,也不反抗,而是默默地忍耐,并在痛苦中發掘溫暖的片段,發掘生活內在的尊貴。”④
[ 注 釋 ]
①王春榮,吳玉杰.女性敘事與“底層敘事”主體身份的同構性[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4).
②馬金蓮.梅花樁.朔方出版社,2017.
③邵明可.余華小說的底層敘事研究[J].安徽文學(下半月),2014(07):57-58.
④沈艷霞,馬金蓮.以弱者的眼睛打量世界.黃河文學,2011(9).
[1]王春榮,吳玉杰.女性敘事與“底層敘事”主體身份的同構性[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4).
[2]馬金蓮.梅花樁.朔方出版社,2017.
[3]邵明可.余華小說的底層敘事研究[J].安徽文學(下半月),2014(07):57-58.
[4]沈艷霞,馬金蓮.以弱者的眼睛打量世界.黃河文學,2011(9).
*寧夏區教育廳“產學研聯合培養基地建設項目”(項目編號:YDT201606)。
景莉莉(1993-),女,漢族,山西臨汾人,北方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學。
I
A
1006-0049-(2017)15-003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