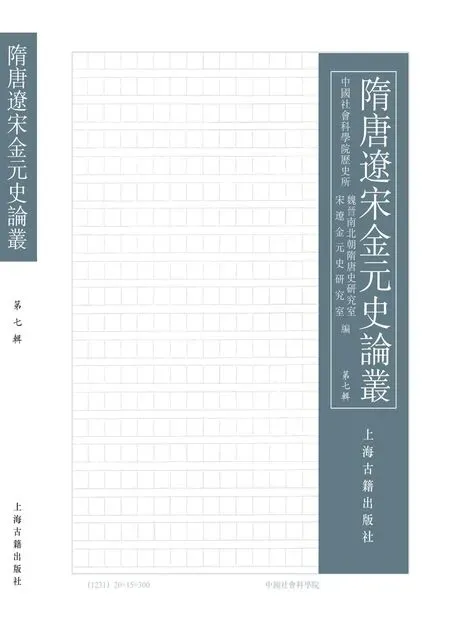魏晉至隋唐的官府部門(mén)之學(xué)
樓 勁
在我國(guó)古代教育史或?qū)W校史上,官學(xué)體系一直佔(zhàn)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這不僅是由於官學(xué)所覆蓋的知識(shí)門(mén)類(lèi)十分完整,其教學(xué)活動(dòng)的規(guī)範(fàn)化和系統(tǒng)化程度堪稱(chēng)當(dāng)時(shí)學(xué)校教學(xué)之最;更是因爲(wèi)官學(xué)代表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主流的知識(shí)觀和教育觀,並在許多方面深切影響了整個(gè)知識(shí)系統(tǒng)和人才培養(yǎng)的發(fā)展結(jié)構(gòu)和方向。從其總體發(fā)展過(guò)程來(lái)看,三代時(shí)期隱約存在的“學(xué)在官府”及“宦學(xué)事師”之制,到秦漢顯然已發(fā)生了較大變化*三代“學(xué)在官府”,乃學(xué)界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共識(shí)。《禮記·曲禮上》有“宦學(xué)事師”之語(yǔ),其大意爲(wèi)做官做事的過(guò)程即學(xué)習(xí)有關(guān)知識(shí)或技藝的過(guò)程,這種知識(shí)技藝的見(jiàn)習(xí)性傳授體制,可以概括官、私各行各業(yè)中存在的師徒關(guān)係和教學(xué)活動(dòng)。。漢武帝以來(lái)國(guó)學(xué)的出現(xiàn),略可視爲(wèi)官方意識(shí)形態(tài)和公共知識(shí)體系再次定型以後,其教學(xué)過(guò)程已有可能和必要集中進(jìn)行的産物;以儒學(xué)教學(xué)爲(wèi)中心的各地州郡縣學(xué)的逐漸建置,則是進(jìn)一步貫徹官方意識(shí)形態(tài)和強(qiáng)調(diào)公共知識(shí)培養(yǎng)的結(jié)果。而其餘各種官方所需的專(zhuān)業(yè)技術(shù)人員,除直接從社會(huì)上招攬徵選外,也仍由各主管官署通過(guò)相應(yīng)的教學(xué)設(shè)施來(lái)培養(yǎng)和訓(xùn)練,此即官府部門(mén)之學(xué)。這三個(gè)方面共同構(gòu)成了完整的官學(xué)體系,以往教育史及學(xué)校史著作卻很少涉及後一方面,其研究迄今仍相當(dāng)薄弱,以至於其基本狀況仍然多有不明之處*相比之下律學(xué)的研究要來(lái)得相對(duì)充分,其成果主要集中於法制史研究,而學(xué)校史或教育史對(duì)之關(guān)注仍頗不足。參葉煒《論魏晉至宋律學(xué)的興衰及其社會(huì)政治原因》,《史學(xué)月刊》2006年第5期;陳璽《唐代的律學(xué)教育與明法考試》,《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年第1期;呂志興《南朝律學(xué)的發(fā)展及其特點(diǎn): 兼論“中原律學(xué)衰於南而盛於北”説不能成立》,《政法論壇》2012年第1期。。有鑒於此,本文擬就魏晉至隋唐官學(xué)體系中的部門(mén)之學(xué)加以梳理、探討,以見(jiàn)其在此期的轉(zhuǎn)折、定型過(guò)程,及其不同程度地具有的官辦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校的性質(zhì)。
以下分爲(wèi)法律、方術(shù)、樂(lè)舞、工巧等專(zhuān)門(mén)知識(shí)和技藝共四類(lèi),依次考察官府部門(mén)之學(xué)的教學(xué)培訓(xùn)之況及其發(fā)展歷程,以有助於對(duì)此期教育史、學(xué)校史和相關(guān)問(wèn)題的進(jìn)一步研究。
一、 律學(xué)
專(zhuān)門(mén)教授法律、司法知識(shí)的官辦學(xué)校,一般都認(rèn)爲(wèi)創(chuàng)始於曹魏*《宋書(shū)》卷三九《百官志上》:“廷尉律博士一人,魏武初建,魏國(guó)置。”《晉書(shū)》卷三○《刑法志》述魏明帝時(shí)衛(wèi)覬“請(qǐng)置律博士,轉(zhuǎn)相教授。事遂施行”。是律博士初設(shè)於曹操封魏王後,至魏明帝時(shí)成爲(wèi)朝廷定制。又《宋書(shū)》卷四○《百官志下》述漢末以來(lái),各州或置“律令師一人,平律”。推其亦當(dāng)有一定的法律教學(xué)或吏師功能,曹魏亦當(dāng)承此,然其本非定制,各地具體設(shè)置與否當(dāng)以長(zhǎng)官意志爲(wèi)轉(zhuǎn)移。參邢義田《秦漢的律令學(xué)——兼論曹魏律博士的出現(xiàn)》,臺(tái)灣《中研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四本四分。。自此直至隋唐時(shí)期,以律博士和律生爲(wèi)主體的律學(xué)設(shè)置史不絶書(shū)。像兩晉主管刑獄的廷尉之下,均有“律博士”的編制*《晉書(shū)》卷二四《職官志》。。劉宋、蕭齊皆置廷尉律博士1人*《宋書(shū)》卷三九《百官志上》,《南齊書(shū)》卷一六《百官志》。,梁武帝天監(jiān)四年(505)改在廷尉之下設(shè)“胄子律博士”,其制爲(wèi)陳所襲*《隋書(shū)》卷二六《百官志上》載天監(jiān)四年置胄子律博士“位視員外郎”,至天監(jiān)七年定胄子律博士位三班,高於二班的太學(xué)博士、國(guó)子助教;又載陳胄子律博士與太學(xué)博士、國(guó)子助教皆第八品、秩六百石。,從其名稱(chēng)似可推測(cè)南朝後期已在貴族子弟中展開(kāi)法律教學(xué)*其名蓋取於《尚書(shū)·虞書(shū)》帝命夔教胄子之事,故此“胄子”當(dāng)非皇族之謂,而應(yīng)泛指一段時(shí)期以來(lái)不願(yuàn)習(xí)律的士族子弟。。十六國(guó)時(shí)期如後趙石勒稱(chēng)趙王後,即以“律學(xué)祭酒”與經(jīng)學(xué)祭酒、史學(xué)祭酒並置;後秦姚興亦“立律學(xué)於長(zhǎng)安”*《晉書(shū)》卷一○五《石勒載記下》、卷一一七《姚興載記上》。。北魏廷尉之下亦設(shè)律博士*《魏書(shū)》卷一一三《官氏志》載太和中官品,律博士與太學(xué)博士皆爲(wèi)第六品中階;至正始年間所頒官品,律博士已降至第九品上階,地位猶在同階的四門(mén)小學(xué)博士之下。,北齊大理寺下置律博士4員,其制當(dāng)沿自北魏*《隋書(shū)》卷二七《百官志中》。。與南朝律博士常止1員的情況相比,其律學(xué)規(guī)模顯然要大得多。隋初增大理律博士至8員,其規(guī)模又?jǐn)U大了1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dāng)時(shí)又推廣北朝以來(lái)某些成例,在州、縣設(shè)立了律博士和律生*《隋書(shū)》卷二八《百官志下》,同書(shū)卷二五《刑法志》載開(kāi)皇五年廢律學(xué)詔文,有“因襲往代,別置律官”之語(yǔ),可見(jiàn)文帝此舉乃因襲以往有關(guān)做法而來(lái)。。若按北周末年州211個(gè)、郡508個(gè)、縣1124個(gè)計(jì)算*《隋書(shū)》卷二九《地理志上》述北周大象二年(580)州、郡、縣數(shù)。,即便其州、縣律學(xué)生額皆?xún)H10人*《隋書(shū)》卷二八《百官志下》載開(kāi)皇三年(583)四月,“罷郡,以州統(tǒng)縣”。隋文帝置律學(xué)亦在開(kāi)皇三年,當(dāng)在罷郡之後,故郡一級(jí)可不計(jì)在內(nèi)。,總量也將輕易超過(guò)10000人。但實(shí)施不過(guò)數(shù)年,隋文帝就下詔停廢了大理寺和各州縣的律學(xué)*《隋書(shū)》卷二五《刑法志》載文帝開(kāi)皇三年“置律博士弟子員”,至五年詔“大理律博士、尚書(shū)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並可停廢”。六年又“敕諸州長(zhǎng)史以下,行參軍已上,並令習(xí)律,集京之日,試其通不”。同書(shū)卷二八《百官志下》述開(kāi)皇三年“罷大理寺監(jiān)、評(píng)及律博士員”。《四庫(kù)》本“罷”作“減”。疑是。。唐初重建律學(xué),將之歸屬?lài)?guó)學(xué)系統(tǒng),至高祖及高宗兩度廢置*《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述律學(xué)“武德初隸國(guó)子監(jiān),尋廢”。《舊唐書(shū)》卷三《太宗紀(jì)下》貞觀六年(632)二月戊子“初置律學(xué)”。同書(shū)卷四《高宗紀(jì)上》載顯慶三年九月,“廢書(shū)、算、律學(xué)”;龍朔二年(662)五月乙巳,“復(fù)置律、書(shū)、算三學(xué)”。,其歸屬亦有反復(fù)*《舊唐書(shū)》卷四《高宗紀(jì)上》及卷二四《禮儀志四》俱載龍朔三年以書(shū)學(xué)隸蘭臺(tái),算學(xué)隸秘閣局,律學(xué)隸詳刑寺。。到玄宗開(kāi)元年間重新確定了律學(xué)及其隸屬於國(guó)學(xué)之制,律學(xué)博士置1員,另設(shè)助教1員,典學(xué)2員,生徒爲(wèi)50人*《唐六典》卷二一《國(guó)子監(jiān)》。《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三》國(guó)子監(jiān)載律學(xué)博士3人。。
由上可見(jiàn),魏晉至隋唐的律學(xué),除後趙和唐代被歸入國(guó)學(xué)外,經(jīng)常都是直屬於主管刑獄的廷尉(大理)寺的專(zhuān)門(mén)法律學(xué)校*隋代一度設(shè)立的州、縣律學(xué),當(dāng)與地方其他官學(xué)一樣由州、縣長(zhǎng)官統(tǒng)轄,從開(kāi)皇六年命各地官吏習(xí)律而集京通試的規(guī)定看,各地律學(xué)未廢時(shí),其教學(xué)過(guò)程亦應(yīng)受大理寺指導(dǎo)並與寺屬的律學(xué)基本一致。。至於律學(xué)的教學(xué)培養(yǎng)之況,儘管記載很少,也仍有若干蹤跡可循。《三國(guó)志》卷二一《魏書(shū)·衛(wèi)覬傳》載其曹魏明帝時(shí)上書(shū)請(qǐng)立律博士有曰:
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zhǎng)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guó)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qǐng)置律博士,轉(zhuǎn)相教授。
其中所述“刑法者,國(guó)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這兩句話總體地反映了魏晉以來(lái)法律教學(xué)所處的不利環(huán)境,同時(shí)也説明律學(xué)的教學(xué)內(nèi)容在理論上固然可以包括各種法律,實(shí)際卻是以刑律爲(wèi)中心,其培養(yǎng)的也主要是執(zhí)掌刑獄的法吏。
此後如十六國(guó)時(shí)期的後秦姚興所立律學(xué),“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晉書(shū)》卷一一七《姚興載記上》。。其律學(xué)生源主要來(lái)自“郡縣散吏”,經(jīng)課試確認(rèn)其是否“通明”刑律,合格者回原地升擢爲(wèi)論決刑獄的法吏。蕭齊高帝時(shí),崔祖思上書(shū)論事,稱(chēng)“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mén)戶(hù),族非咸、弘,庭缺於訓(xùn)”云云*《南齊書(shū)》卷二八《崔祖思傳》。。可見(jiàn)此前律學(xué)生徒皆出身於社會(huì)下層,結(jié)業(yè)後則多出任朝廷機(jī)要部門(mén)的文法吏。而崔祖思則建議改善律學(xué)生源,強(qiáng)化課試和選拔環(huán)節(jié),優(yōu)其生徒出路。至永明九年(491),又有大臣奏請(qǐng)“國(guó)學(xué)置律學(xué)助教,依五經(jīng)例,國(guó)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guò)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南齊書(shū)》卷四八《孔稚珪傳》。。這是要求在國(guó)學(xué)中展開(kāi)法律教學(xué),按經(jīng)學(xué)的策試方法加以課督,以培養(yǎng)身份和知識(shí)素質(zhì)更高的國(guó)學(xué)生來(lái)出任法官。這些建議雖未落實(shí),但其與蕭梁改置“胄子律博士”升其品階的事實(shí)一樣,都代表了一種更加關(guān)注律學(xué)的趨勢(shì)。這種趨勢(shì)在北朝也有所體現(xiàn),北魏孝文帝曾親自過(guò)問(wèn)律博士人選*《魏書(shū)》卷八二《常景傳》述其少讀《論語(yǔ)》《毛詩(shī)》,長(zhǎng)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wèi)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既而用之”。《北史》卷四二《常爽傳》附《常景傳》述爲(wèi)“廷尉公孫良舉爲(wèi)協(xié)律博士”。《冊(cè)府元龜》卷七九九《總録部·強(qiáng)記》亦述常景聰敏而被公孫良舉爲(wèi)“協(xié)律博士”。而《洛陽(yáng)伽藍(lán)記》卷一《永寧寺》載常景“太和十九年?duì)?wèi)高祖所器,拔爲(wèi)律學(xué)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今案《魏書(shū)》卷一一三《官氏志》載太和中官品惟有“太樂(lè)博士”而無(wú)“協(xié)律博士”,景既由廷尉公孫良舉爲(wèi)博士,當(dāng)是律學(xué)博士。,宣武帝以來(lái)律博士常參與朝廷的立法活動(dòng)*《魏書(shū)》卷六九《袁翻傳》載正始年間詔尚書(shū)、門(mén)下於金墉中書(shū)外省考論律令時(shí),參與者有“律博士侯堅(jiān)固”;《魏書(shū)》卷一一一《刑罰志》載延昌三年議“除名之例”時(shí),與議者有“律博士劉安元”。,説明北魏律學(xué)頗有地位,律博士選擇甚精,在朝廷立法或議決涉法事務(wù)時(shí)相當(dāng)活躍。這種律學(xué)教官參與實(shí)務(wù)的精神,後來(lái)亦爲(wèi)隋代所繼承,隋初大理寺和州、縣的律學(xué)師生,都要參與本級(jí)司法過(guò)程。隋文帝廢止律學(xué),起因即是始平縣律生舞文弄法,其詔稱(chēng)“因襲往代,別置律官,報(bào)判之人,推其爲(wèi)首。殺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隋書(shū)》卷二五《刑法志》。。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各級(jí)律博士和律生身份地位依然較低而被稱(chēng)爲(wèi)“小人”,卻在論決刑獄時(shí)作用突出,其教學(xué)活動(dòng)似是與相關(guān)的司法實(shí)務(wù)密切結(jié)合的。
唐初以來(lái)律學(xué)歸屬?lài)?guó)學(xué)系統(tǒng),其生徒身份規(guī)定與書(shū)、算生相同,皆爲(wèi)文武官“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xué)者”,年齡限制在18—25歲之間,較其他官學(xué)生徒皆限14—19歲要大一些*《新唐書(shū)》卷四四《選舉志上》。。高宗時(shí)修撰《唐律疏議》,爲(wèi)的是“律學(xué)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wú)憑準(zhǔn)”*《舊唐書(shū)》卷五○《刑法志》。《唐律疏議》所附《進(jìn)律表疏》附署有“律學(xué)博士飛騎尉司馬鋭”。。故其部分用意,是要爲(wèi)律學(xué)的教學(xué)和科舉明法考試提供標(biāo)準(zhǔn)教材,説明刑律仍在其教學(xué)內(nèi)容中佔(zhàn)有中心地位。玄宗開(kāi)元時(shí)期所定律學(xué)之制,大體是律生“以《律》、《令》爲(wèi)專(zhuān)業(yè),《格》、《式》、法例亦兼習(xí)之”;課試習(xí)業(yè)管理之制與國(guó)子學(xué)相同,結(jié)業(yè)者通過(guò)科舉“明法”考試而入仕擔(dān)任法官;在學(xué)六年課試仍不合格者,罷遣出學(xué)*《唐六典》卷二一《國(guó)子監(jiān)》。。由此可以看出,律學(xué)歸屬?lài)?guó)學(xué),入學(xué)者在身份地位和知識(shí)基礎(chǔ)方面的要求都會(huì)相應(yīng)提高;其課試習(xí)業(yè)等教學(xué)環(huán)節(jié)也要按國(guó)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進(jìn)一步規(guī)範(fàn)化;而其生徒出路與科舉明法科的銜接,又有助於改善其初仕官職的級(jí)別和地位。這樣的狀況,正是循南北朝後期律學(xué)日益受到關(guān)注的趨勢(shì)發(fā)展而來(lái)的,同時(shí)也仍保留了魏晉以來(lái)律學(xué)面向平民子弟和主要培養(yǎng)涉法官吏的基本性質(zhì)。
二、 方術(shù)之學(xué)
在主管方技和術(shù)數(shù)事務(wù)的官署設(shè)置“學(xué)室”,培養(yǎng)具有天算、卜筮、醫(yī)藥等專(zhuān)業(yè)知識(shí)的官吏,秦漢時(shí)期已有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雲(yún)夢(mèng)秦簡(jiǎn)所出《秦律十八種》之《內(nèi)史雜律》有史之子就讀學(xué)室的規(guī)定,張家山漢簡(jiǎn)所出《二年律令》之《史律》有太史、太卜、太祝及各郡之史招收和課試學(xué)童的完整規(guī)定。參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之《二年律令與奏讞書(shū): 張家山二四七號(hào)漢墓出土法律文獻(xiàn)釋讀》之《二年律令釋文·史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魏晉以來(lái)則繼承和發(fā)展了這樣的做法,北朝至隋唐更多設(shè)方術(shù)博士各自教習(xí)弟子,可稱(chēng)是建立了主要爲(wèi)官府相關(guān)技術(shù)部門(mén)提供專(zhuān)業(yè)人員的學(xué)校系統(tǒng)。
魏晉時(shí)期主管醫(yī)藥的太醫(yī)令下,便有招收醫(yī)家子弟,集中教習(xí)醫(yī)藥之術(shù)的制度*《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醫(yī)署:“晉代以上手醫(yī)子弟世習(xí)者,令助教部教之。”説明魏晉時(shí)期醫(yī)藥主管部門(mén)亦招收醫(yī)家子弟集中教學(xué),當(dāng)承自秦漢各技術(shù)主管部門(mén)的“學(xué)室”之制。。五胡時(shí)期後趙石虎擴(kuò)大後宮規(guī)模時(shí):
內(nèi)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tái),仰觀災(zāi)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shí);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晉書(shū)》卷一○六《石季龍載記上》。
這套女官教習(xí)之制或者摻雜了石虎的創(chuàng)造,但也不失爲(wèi)漢魏以來(lái)太史及工、樂(lè)官教習(xí)之制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所謂“皆與外侔”,更説明其宮外整套行政系統(tǒng)中,本來(lái)就存在著星占、雜伎等方面的教學(xué)設(shè)施和相應(yīng)的培養(yǎng)活動(dòng)*《晉書(shū)》卷一○六至一○七《石季龍載記》上、下載其時(shí)有太史令趙攬,先後奏“歲星守燕”、“白雁集殿庭”、“熒惑守房”及“天文錯(cuò)亂”諸事,可見(jiàn)其“外太史”確掌星占災(zāi)祥等事,所屬應(yīng)有關(guān)於天象觀測(cè)和災(zāi)祥卜占的教學(xué)活動(dòng)。,而其顯然是承自魏晉以來(lái)的有關(guān)制度。這種存在於各技術(shù)主管部門(mén)的教學(xué)活動(dòng)和傳統(tǒng),植根於任何官署中都會(huì)出現(xiàn)的職事知識(shí)傳授過(guò)程,在有條件和必要時(shí),則可建立專(zhuān)門(mén)處所和官員,由經(jīng)驗(yàn)豐富、術(shù)業(yè)較精者向新來(lái)見(jiàn)習(xí)者集中傳授有關(guān)知識(shí)技能,卻仍可程度不同地保留其官、師合一,職、學(xué)不分的狀態(tài)。儘管相關(guān)記載留存至今者很少,但從魏晉以來(lái)私習(xí)“內(nèi)學(xué)”被明令禁止,民間相關(guān)知識(shí)的傳授已遭限制的事實(shí)看,官方星曆筮占等主管部門(mén)加強(qiáng)其所屬官吏的教學(xué)和培訓(xùn),可以説是必然的選擇。
南朝官府有關(guān)於方術(shù)的部門(mén)之學(xué),如劉宋文帝之時(shí),一度曾在太醫(yī)令下設(shè)立“醫(yī)學(xué),以廣教授”*《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醫(yī)署載醫(yī)博士之制,述“元嘉二十年,太醫(yī)令秦承祖奏置醫(yī)學(xué),以廣教授。至三十年,省”。“以廣教授”説明其本有教授之法。。這説明執(zhí)事於有關(guān)方術(shù)機(jī)構(gòu)的技術(shù)人員,平素也還是有其教習(xí)培養(yǎng)辦法的,唯史乘對(duì)之罕有記載,其詳今已不得而知。北魏的部門(mén)方術(shù)之學(xué)似乎呈現(xiàn)了新的發(fā)展態(tài)勢(shì),其標(biāo)誌是道武帝時(shí)設(shè)立了“仙人博士”之官*《魏書(shū)》卷一一三《官氏志》: 天興三年“置仙人博士官,典煮煉百藥”;同書(shū)卷一一四《釋老志》述道武帝當(dāng)時(shí)爲(wèi)仙人博士“立仙坊”,封西山以充其給,且稱(chēng)之爲(wèi)“鍊藥之官”。可見(jiàn)此官的教學(xué)活動(dòng)與履職過(guò)程仍密切相關(guān),名爲(wèi)“博士”,大概只能説明當(dāng)時(shí)“仙坊”中教學(xué)的一面已比較突出。又《通典》卷三六《秩品一·漢官秩差次》載西漢有“太常太卜博士”秩六百石。但當(dāng)時(shí)博士非必與教學(xué)相關(guān),這條記載無(wú)法説明西漢已有部門(mén)性方術(shù)學(xué)校。,太武帝時(shí)又出現(xiàn)了“算生博士”等官稱(chēng)*《魏書(shū)》卷九一《術(shù)藝殷紹傳》述其“世祖時(shí)爲(wèi)算生博士”。北朝常泛稱(chēng)教師爲(wèi)“博士”,此“算生博士”或非正式官名,但當(dāng)時(shí)設(shè)有算學(xué)則無(wú)問(wèn)題。《魏書(shū)》卷七九《范紹傳》載其“太和初,充太學(xué)生,轉(zhuǎn)算生,頗涉經(jīng)史”。此太和初年的“算生”,當(dāng)承自太武帝以來(lái)。。這類(lèi)職務(wù)既然稱(chēng)爲(wèi)“博士”,其擔(dān)任者的教育職能當(dāng)已較前突出,“算生博士”之稱(chēng)更表明教、學(xué)雙方及其所展開(kāi)的教學(xué)活動(dòng),必已有了較以往更爲(wèi)?yīng)毩⒑头€(wěn)定的形態(tài)。因而在有關(guān)官署設(shè)置博士和生徒,實(shí)際上是建立了擁有專(zhuān)職教師和學(xué)生的職業(yè)學(xué)校,部門(mén)之學(xué)至此已分化爲(wèi)較爲(wèi)原始的見(jiàn)習(xí)培訓(xùn)和相對(duì)高級(jí)的學(xué)校教學(xué)兩種形式。太武帝以來(lái),這種在官署內(nèi)部設(shè)立職業(yè)學(xué)校培養(yǎng)朝廷所需技術(shù)官員的辦法,顯然得到了迅速發(fā)展。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確定的官職序列中,僅與方術(shù)之學(xué)相關(guān)的,就有太史博士、助教和太醫(yī)博士、助教及太卜博士,以及尚書(shū)算生、諸寺算生等一批建制*《魏書(shū)》卷一一三《官氏志》。其載太和中所定官品“太史博士”兩見(jiàn),一是與太學(xué)博士和律博士皆爲(wèi)第六品中階的太史博士,一是與太卜博士和太醫(yī)博士皆爲(wèi)從七品下階的太史博士。比照尚書(shū)算生第九品中和諸寺算生第九品下的規(guī)定,這個(gè)事實(shí)似乎可以説明當(dāng)時(shí)設(shè)立的天占星曆之學(xué)不止一處。又《官氏志》後文所載景明官品中,這些官銜均已消失,然據(jù)《魏書(shū)》卷一○七下《律曆志下》載東魏興和二年(540)命李業(yè)興撰《甲子元曆》,奏上者中,有“太史博士臣胡仲和”之銜。是宣武帝以來(lái)仍有“太史博士”,此類(lèi)或已進(jìn)入視品或流外序列。《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樂(lè)署述“凡習(xí)樂(lè),立師以教”,且述“諸無(wú)品博士隨番”,是其樂(lè)舞博士已無(wú)品階。,説明當(dāng)時(shí)分別主管天曆、醫(yī)藥和卜筮等事務(wù)的機(jī)構(gòu)中,均已建立了培養(yǎng)方術(shù)官的職業(yè)學(xué)校,另又在尚書(shū)省和諸寺分別設(shè)立了若干算學(xué)。北齊尚書(shū)、門(mén)下和中書(shū)等省皆設(shè)“醫(yī)師”,似乎也反映了當(dāng)時(shí)醫(yī)學(xué)教學(xué)分頭展開(kāi)的特定狀態(tài)*《隋書(shū)》卷二七《百官志中》載北齊河清時(shí)所定官品,“尚書(shū)、門(mén)下、中書(shū)等省醫(yī)師,爲(wèi)從第九品”。。
到隋唐,部門(mén)性方術(shù)學(xué)校的設(shè)置已更爲(wèi)普遍*《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醫(yī)署述“後周醫(yī)正有醫(yī)生三百人,隋太醫(yī)有生一百二十人,皇朝置四十人”。可見(jiàn)北魏部門(mén)之學(xué)被北齊、北周不同程度地沿襲了下來(lái),構(gòu)成了隋唐部門(mén)之學(xué)的發(fā)展基礎(chǔ)。。隋初算學(xué)已與書(shū)學(xué)一起歸屬?lài)?guó)學(xué),秘書(shū)省所屬太史曹置有曆、天文、漏刻、視祲博士和生員;太常寺所屬主管醫(yī)學(xué)的太醫(yī)署,置有醫(yī)博士、助教各2人,另置按摩博士、祝禁博士各2人;太常寺所屬主管卜筮的太卜署,置有太卜博士、助教各2人和相博士、助教各1人;太僕寺又置獸醫(yī)博士120人,這就構(gòu)成了規(guī)模可觀的部門(mén)方術(shù)學(xué)體系。隋文帝開(kāi)皇五年(585)雖停廢律學(xué),晚年又大肆縮減國(guó)學(xué),但各部門(mén)的方術(shù)之學(xué)卻仍得到了重視和延續(xù)*以上俱見(jiàn)《隋書(shū)》卷二八《百官志下》,其後文又載煬帝大業(yè)三年定制,太卜署“省博士員,置太卜卜正二十人,以掌其事”。又《隋書(shū)》卷一九《天文志上》載平陳後,得善天官者周墳,任其“爲(wèi)太史令。墳博考經(jīng)書(shū),勤於教習(xí),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shí)天官”。又《隋書(shū)》卷一七《律曆志中》載開(kāi)皇十七年詔責(zé)太史造曆諸官,內(nèi)有“曆博士蘇粲、曆助教傅儁、成珍”之名。又宋代張杲《醫(yī)説》卷一《歷代名醫(yī)·巢元方》述其“大業(yè)中爲(wèi)太醫(yī)博士,奉詔撰《諸病源候論》五十卷”。以上可證開(kāi)皇五年至文帝末年裁減國(guó)學(xué)直至煬帝以來(lái),除太卜博士改爲(wèi)卜正外,各署博士大多仍照舊設(shè)置。。唐代基本沿襲此制而略有損益,據(jù)《唐六典》所載開(kāi)元之制,秘書(shū)省所屬太史局之下,設(shè)相當(dāng)於曆博士的保章正1人,曆生36人,裝書(shū)曆生5人;又設(shè)相當(dāng)於天文博士的靈臺(tái)郎2人,天文觀生90人,天文生60人;又設(shè)漏刻博士6人,漏刻生360人*見(jiàn)《唐六典》卷一○《秘書(shū)省》太史局,其載唐初沿隋設(shè)曆博士1人,“長(zhǎng)安四年省曆博士,置保章正以當(dāng)之,掌教曆生”。後文又載“天文博士掌教習(xí)天文氣色”,唐初因隋置2人,“長(zhǎng)安四年省天文博士之職,置靈臺(tái)郎以當(dāng)之”。同書(shū)卷二七《太子三寺》載太子率更寺下亦設(shè)漏刻博士2人、漏童60人。。太常寺所屬的太醫(yī)署,設(shè)醫(yī)、針博士和助教各1人、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各1人,分別教授醫(yī)生40人,針生20人,按摩生15人,咒禁生10人,另有藥園師2人,藥園生8人,藥童24人;太常寺所屬的太卜署,設(shè)卜博士和助教各2人,有卜筮生45人*《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並參《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太僕寺所屬有獸醫(yī)博士1人,學(xué)生100人*《唐六典》卷一七《太僕寺》。。更爲(wèi)重要的是,唐太宗以來(lái)開(kāi)始在各州開(kāi)辦醫(yī)學(xué)*《舊唐書(shū)》卷二《太宗紀(jì)上》貞觀三年九月癸丑,“諸州置醫(yī)學(xué)”。,玄宗開(kāi)元年間又爲(wèi)之設(shè)立了醫(yī)博士和助教,並規(guī)定府、州醫(yī)學(xué)生規(guī)模爲(wèi)京府20人、大、中都督府和上州15人,下都督府和中州12人,下州10人*《唐六典》卷三○《府州縣》述各府州醫(yī)學(xué)生“貞觀初置”,醫(yī)學(xué)博士、助教“開(kāi)元初置”。又《隋書(shū)》卷二六《百官志上》載梁初定制,“郡縣吏有書(shū)僮、有武吏、有醫(yī)……亦各因其大小而置焉”;卷二七《百官志中》又載北齊王國(guó)置“典醫(yī)丞”。唐太宗設(shè)各州醫(yī)學(xué),當(dāng)有鑒於南北朝這類(lèi)設(shè)置而來(lái)。。依此再按《通典》所載開(kāi)天時(shí)期各等府州數(shù)計(jì)算,則唐代盛時(shí)各州醫(yī)學(xué)生總數(shù)可達(dá)3000餘人。*前已引《通典》載開(kāi)元二十八年有上州109,中州29,下州189個(gè),共計(jì)327州;其中京府醫(yī)學(xué)生3×20=60人,減去京府3個(gè)後,上州醫(yī)學(xué)生爲(wèi)106×15=1590人,中州醫(yī)學(xué)生爲(wèi)29×12=348人,下州醫(yī)學(xué)生爲(wèi)189×10=1890人;以上各項(xiàng)總計(jì)3888人。然《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fù)原研究)》下冊(cè)校録本《醫(yī)疾令卷第二十六》關(guān)於各州醫(yī)學(xué)有“若州在邊遠(yuǎn)及管夷獠之處,無(wú)人堪習(xí)業(yè)者,不在置限”之條,故僅估測(cè)爲(wèi)3000餘人。天一閣博物館、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fù)原研究)》,中華書(shū)局,2006年。
部門(mén)方術(shù)之學(xué)的教學(xué)培養(yǎng)過(guò)程,可以從唐代的規(guī)定見(jiàn)其大概,史載可徵者約有下列幾端。
首先,這些學(xué)校都附設(shè)於主管有關(guān)技術(shù)的官署,都在本署長(zhǎng)官的節(jié)制之下。其教學(xué)活動(dòng)及教官的考核、生徒的選補(bǔ)、課試的組織實(shí)施和業(yè)成者擢補(bǔ)本署官吏等事,除有法律統(tǒng)一規(guī)定者外,長(zhǎng)官可以全權(quán)處理。如太醫(yī)署的藥園師爲(wèi)流外六品,由太常卿從藥園生業(yè)成者中選補(bǔ)*《通典》卷四○《職官二十二·大唐官品》、《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醫(yī)署條,並參《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fù)原研究)》下冊(cè)校録本《醫(yī)疾令卷第二十六》。;而太僕寺的獸醫(yī)博士則並無(wú)官品,地位更低,可由主管其事的太僕丞從優(yōu)秀獸醫(yī)生中選充*《唐六典》卷一七《太僕寺》。。這種分散設(shè)置、各教其事的狀態(tài),體現(xiàn)了其完全服務(wù)於各技術(shù)部門(mén)的特點(diǎn),且與專(zhuān)門(mén)教授公共知識(shí)和統(tǒng)一管理的國(guó)學(xué)形成了鮮明對(duì)照。
其次,博士、助教往往兼有部分實(shí)務(wù),本署其他官員也常參與其教學(xué)活動(dòng)。像天文博士至長(zhǎng)安四年改爲(wèi)靈臺(tái)郎後,既要“教習(xí)天文氣色”,又要“觀天文之變而占候之”。太醫(yī)署的醫(yī)師和醫(yī)工、針師和針工、按摩師和按摩工、咒禁師和咒禁工,都要佐助醫(yī)博士、助教、針博士、助教和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對(duì)生徒的教習(xí)過(guò)程。與之相應(yīng),有些生徒也仍要從事實(shí)務(wù),像太史局的天文觀生,便要“晝夜在靈臺(tái)伺候天文氣色”;漏刻生則既要“習(xí)漏刻之節(jié)”,又要“以時(shí)唱漏”。這都説明這些學(xué)校仍不同程度地具有見(jiàn)習(xí)培訓(xùn)特點(diǎn),而未全脫宦學(xué)事師時(shí)期官、師一體,職、學(xué)不分的原始性。
其三,生徒常從民間選充,有年齡限制,有的須具有一定的知識(shí)基礎(chǔ)。如太史局曆生,“取中男年十八以上解算數(shù)者爲(wèi)之”;太史局的天文生和太卜署的卜筮生,“並取中男年十六以上性識(shí)聰敏者”;太史局的漏刻生和太子率更寺的漏童,皆“取十三、十四者充”*《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fù)原研究)》下冊(cè)校録本《雜令卷第三十》。;太僕寺獸醫(yī)生“以庶人之子考試”選充。各學(xué)生徒地位最高的是天文觀生和曆生,入學(xué)後即爲(wèi)流外七品*《通典》卷四○《職官二十二·大唐官品》載太史監(jiān)曆生、天文觀生爲(wèi)流外七品。《文苑英華》卷五一二《判十·書(shū)數(shù)師學(xué)射投壺圍棋門(mén)二十七道》有《習(xí)卜算判》,即爲(wèi)卜筮生及曆生選補(bǔ)之事,可參。;其餘均爲(wèi)無(wú)品職吏。這兩類(lèi)生徒課試業(yè)成後限在本部門(mén)服務(wù)而不得轉(zhuǎn)業(yè)*《唐律疏議·名例篇》“工樂(lè)雜戶(hù)及太常音聲人犯流”條,規(guī)定天文等生徒習(xí)業(yè)已成而犯徒、流罪者,可以加杖替代徒役和遠(yuǎn)配,以便其繼續(xù)服務(wù)於有關(guān)官署。,前者可依次升補(bǔ)爲(wèi)流內(nèi)官,後者亦可逐漸上升至流外官再進(jìn)而爲(wèi)流內(nèi)官,但其最高只能做到本局本署的長(zhǎng)官,也很難再轉(zhuǎn)爲(wèi)其他部門(mén)的官吏*《唐會(huì)要》卷六七《伎術(shù)官》。。由此可見(jiàn)這些學(xué)校面向民間專(zhuān)門(mén)培養(yǎng)專(zhuān)業(yè)技術(shù)官吏的基本性質(zhì)。
其四,教學(xué)內(nèi)容以高度專(zhuān)業(yè)化爲(wèi)其特徵。如太醫(yī)署的醫(yī)生和針生,其規(guī)定是“讀《本草》者,即令識(shí)藥形而知藥性;讀《明堂》者,即令驗(yàn)圖,識(shí)其孔穴;讀《脈訣》者,即令遞相診候,使知四時(shí)浮沈澀滑之狀。讀《素問(wèn)》、《黃帝針經(jīng)》、《甲乙》、《脈經(jīng)》,皆使精熟”。其中對(duì)醫(yī)生的教學(xué),還要按體療、瘡腫、少小、耳目口齒、角法五科來(lái)“分業(yè)教習(xí)”;而針生又須兼習(xí)“《流注》、《偃側(cè)》等圖,《赤烏神針》等經(jīng)”。算學(xué)在唐初雖已歸屬?lài)?guó)學(xué),教學(xué)內(nèi)容卻仍保留了其以往作爲(wèi)部門(mén)學(xué)的專(zhuān)業(yè)特色,算學(xué)兩個(gè)專(zhuān)業(yè)的法定教材,一是“習(xí)《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yáng)》、《周髀》”,一是“習(xí)《綴術(shù)》、《緝古》”,兩者都要兼習(xí)“《記遺》、《三等數(shù)》”。此外,有些知識(shí)技能涉及禁法秘術(shù)十分敏感,只限本專(zhuān)業(yè)生徒傳習(xí)。如太卜署的三類(lèi)“式占”中,只有“六壬式”官民通用,“雷公式”和“太乙式”並禁私家所蓄,也就只有所屬卜筮生可以學(xué)習(xí)。又如太史局掌握的星曆占候知識(shí)切關(guān)天命氣數(shù),所屬各學(xué)不僅要嚴(yán)守專(zhuān)業(yè)禁止兼習(xí),而且規(guī)定天文觀生“不得讀占書(shū),所見(jiàn)徵祥災(zāi)異密封聞奏,漏泄有刑”。
其五,各部門(mén)學(xué)皆有依法課試之制,其具體辦法各專(zhuān)業(yè)有所不同。其中規(guī)範(fàn)化程度最高的是太醫(yī)署所屬醫(yī)、針、按摩、咒禁四學(xué),朝廷明令其“考試登用,如國(guó)子監(jiān)之法”,故太醫(yī)署亦如國(guó)學(xué)設(shè)有“典學(xué)”二人,專(zhuān)事課督學(xué)業(yè);而博士教授《素問(wèn)》《黃帝內(nèi)經(jīng)》《針經(jīng)》《甲乙經(jīng)》等醫(yī)典時(shí),亦“皆案文講説,如講五經(jīng)之法”。其課試問(wèn)答之式及考等高下的衡量,“並準(zhǔn)試國(guó)子監(jiān)學(xué)生例”。其中如醫(yī)、針生皆由博士每月一試,太醫(yī)令、丞每季一試,又由主管太醫(yī)署的太常寺長(zhǎng)官年終總試,凡其“業(yè)術(shù)過(guò)於見(jiàn)任官者,即聽(tīng)補(bǔ)替”;在學(xué)9年無(wú)成者,罷退出學(xué),各還本業(yè)。具體則醫(yī)生試《甲乙》4條,《本草》《脈經(jīng)》各3條;而針生則試《素問(wèn)》4條,《黃帝針經(jīng)》和《明堂》《脈訣》各2條;此外還要試其兼習(xí)的醫(yī)、針書(shū)各3條。同時(shí),各專(zhuān)業(yè)還有課試業(yè)成的不同年限規(guī)定,如醫(yī)生、針生在9年的總期限內(nèi),醫(yī)生習(xí)體療科者限7年完成學(xué)業(yè),習(xí)少小科、瘡腫科者限5年,習(xí)耳目口齒科、角法科者限2年;針生則限7年內(nèi)完成學(xué)業(yè)。其餘按摩生限3年,咒禁生限2年業(yè)成。
其六,各州醫(yī)博士、助教除教授醫(yī)學(xué)生外,均須“救療平民有疾者”,説明其教學(xué)活動(dòng)也是與履職過(guò)程相結(jié)合的,並且兼有服務(wù)於社會(huì)的功能。其博士、助教依法由州司優(yōu)先考選本地“醫(yī)術(shù)優(yōu)長(zhǎng)者爲(wèi)之”,報(bào)尚書(shū)省備案。學(xué)生的身份和年齡規(guī)定、教習(xí)課試的內(nèi)容和完成學(xué)業(yè)的年限,均比照太醫(yī)署之學(xué)執(zhí)行,允許兼習(xí)各種行之有效的“雜療”術(shù)。其生徒的課試辦法,則每季由博士、助教考試,年終由本州長(zhǎng)官與博士會(huì)同考試,皆“明立試簿,考定優(yōu)劣”,劣者有罰,“終無(wú)長(zhǎng)進(jìn)者,隨事解黜”,另補(bǔ)新生;業(yè)成者即充本州醫(yī)師,輪番巡行各地治病救人*以上除別注出處者外,皆見(jiàn)《唐六典》卷一○《秘書(shū)省》、卷一四《太常寺》、卷一七《太僕寺》、卷三○《府州縣》,其中醫(yī)學(xué)部分又見(jiàn)《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fù)原研究)》下冊(cè)校録本《醫(yī)疾令卷第二十六》。。由此看來(lái),唐代的府、州醫(yī)學(xué)既是直屬地方長(zhǎng)官的一個(gè)技術(shù)部門(mén),也是一所培養(yǎng)地方醫(yī)藥人員的學(xué)校,行政上由地方長(zhǎng)官統(tǒng)轄,業(yè)務(wù)上大體與太醫(yī)署之學(xué)一致,故可歸之爲(wèi)地方部門(mén)之學(xué)。
三、 樂(lè)舞之學(xué)
主管樂(lè)舞的官署皆須訓(xùn)練所屬音樂(lè)歌舞等藝術(shù)人員,樂(lè)舞之學(xué)也像其他部門(mén)之學(xué)一樣,程度不同地具有官、師合一,職、學(xué)不分的特點(diǎn),其主要是要解決初入官府樂(lè)署者的技藝教學(xué)和培訓(xùn)問(wèn)題,並因官方所需樂(lè)舞者數(shù)量甚大而規(guī)模可觀。
如《三國(guó)志》卷二九《魏書(shū)·方技·杜夔傳》載其東漢以知音爲(wèi)雅樂(lè)郎,後去官,奔荊州,爲(wèi)曹操所獲:
太祖以夔爲(wèi)軍謀祭酒,參太樂(lè)事,因令創(chuàng)制雅樂(lè)……時(shí)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lè),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yǎng)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tǒng)研精,遠(yuǎn)考諸經(jīng),近采故事,教習(xí)講肄,備作樂(lè)器,紹複先代古樂(lè),皆自夔始也。
這是曹魏初建其雅樂(lè)體制的過(guò)程。所謂“教習(xí)講肄”,即有一批音樂(lè)舞蹈之人集中接受杜夔主持的雅樂(lè)訓(xùn)練,而散郎鄧靜、尹齊、歌師尹胡、舞師馮肅、服養(yǎng)等,除協(xié)助杜夔創(chuàng)制雅樂(lè)外,亦當(dāng)爲(wèi)其師資*《世説新語(yǔ)》卷下《忿狷第三十一》:“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ài)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shí)俱教,少時(shí)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可見(jiàn)曹操時(shí)即有規(guī)模化的樂(lè)伎教學(xué)體制。。又《晉書(shū)》卷一六《律曆志上》載西晉欲定律管之制,校試御府所藏曹魏製造的銅竹律二十二具,問(wèn)協(xié)律中郎將列和,和曰:
昔魏明帝時(shí),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xué)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xí),依此律調(diào)。至於都合樂(lè)時(shí),但識(shí)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zhǎng)笛長(zhǎng)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調(diào)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
這就説明曹魏杜夔以來(lái)建立的樂(lè)舞之學(xué),存在著分部教習(xí)、合而排練的體制,並按統(tǒng)一的律呂系統(tǒng)來(lái)校定音準(zhǔn)。當(dāng)時(shí)“使學(xué)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xí)”,此法不僅有類(lèi)於漢來(lái)各部門(mén)所屬的“學(xué)室”之制,而且可以看作是後世“教坊”的前聲。西晉泰始十年荀勖等校正笛律,以爲(wèi)“講肆彈擊”與廟堂奏樂(lè)之準(zhǔn),説明當(dāng)時(shí)樂(lè)署“講肆”之制,大體亦應(yīng)沿襲了曹魏的這種教習(xí)體制*參《宋書(shū)》卷一九《樂(lè)志一》、《宋書(shū)》卷一一《律曆志上》。又《三國(guó)志》卷九《魏書(shū)·曹真?zhèn)鳌犯健恫芩瑐鳌肥銎漭o政時(shí)“詐作詔書(shū),發(fā)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tái),使先帝倢伃教習(xí)爲(wèi)伎”。。何晏《景福殿賦》述:
又有教坊、講肆,才士布列,新詩(shī)變聲,曲調(diào)殊別,吟清商之激哇,發(fā)角徵與折雪,音感靈以動(dòng)物,超世俗以獨(dú)絶。*《藝文類(lèi)聚》卷六二《居處部》二《殿》引。
即爲(wèi)當(dāng)時(shí)宮廷樂(lè)舞部門(mén)設(shè)立“教坊、講肆”,展開(kāi)技藝訓(xùn)練的寫(xiě)照。東晉南朝及十六國(guó)北朝屢屢在戰(zhàn)亂後重建廟堂樂(lè)舞,各朝競(jìng)相爭(zhēng)取轉(zhuǎn)輾流散的前朝伶官伎人以重建樂(lè)制*參《晉書(shū)》卷二三《樂(lè)志下》、《宋書(shū)》卷一九《樂(lè)志一》、《魏書(shū)》卷一○九《樂(lè)志》。,其背後自然也都存在著與魏晉教坊講肆相類(lèi)的規(guī)模化樂(lè)舞教學(xué)活動(dòng)。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對(duì)部門(mén)樂(lè)舞之學(xué)有所整頓、擴(kuò)展。當(dāng)時(shí)除有太樂(lè)令主管樂(lè)舞之事外*《魏書(shū)》卷一八《太武五王傳·東平王翰傳》附《元孚傳》載其孝莊帝永安末年監(jiān)作樂(lè)品,上疏述及太和中太樂(lè)令公孫崇修造金石之事,又述當(dāng)時(shí)執(zhí)掌太樂(lè)署的太樂(lè)令爲(wèi)張乾龜。,還設(shè)立了“太樂(lè)祭酒”、“太樂(lè)博士”和“太樂(lè)典録”,其制與太學(xué)設(shè)祭酒、博士和典録之況相類(lèi)*《魏書(shū)》卷一一三《官氏志》載太和中官品“太樂(lè)祭酒”從五品中,“太樂(lè)博士”第六品下,“太樂(lè)典録”從七品下。至景明所頒官品序列中,這3個(gè)官職已然消失。但從隋、唐樂(lè)舞教官仍稱(chēng)博士的事實(shí)看,太和末年以來(lái)樂(lè)舞博士當(dāng)與部分方術(shù)博士一樣進(jìn)入了視品或流外序列。。説明當(dāng)時(shí)官方樂(lè)舞之學(xué)在傳統(tǒng)見(jiàn)習(xí)培訓(xùn)的基礎(chǔ)上,也像部門(mén)方術(shù)之學(xué)一樣分化出了專(zhuān)門(mén)化的職業(yè)學(xué)校。但這個(gè)勢(shì)頭似未持續(xù)鞏固發(fā)展,只是在後世樂(lè)舞教官之制中得到了某種延續(xù)。北齊太常寺下設(shè)太樂(lè)署和鼓吹署主管樂(lè)舞*《隋書(shū)》卷二七《百官志中》。,另有直屬宮廷的“內(nèi)伎”*《北齊書(shū)》卷三九《崔季舒?zhèn)鳌份d其文襄帝時(shí)爲(wèi)中書(shū)監(jiān)而善音樂(lè),移門(mén)下機(jī)事總歸中書(shū),“內(nèi)伎亦通隸焉”。是內(nèi)伎原屬門(mén)下省,至此改屬中書(shū)省。《隋書(shū)》卷二七《百官志中》載中書(shū)省“司進(jìn)御之音樂(lè)”,包括西涼四部、龜茲四部和清商四部樂(lè)。。史稱(chēng)當(dāng)時(shí)雜樂(lè)發(fā)達(dá),吹笛、彈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傳習(xí)尤盛”*《隋書(shū)》卷一四《音樂(lè)志中》,參《北齊書(shū)》卷五○《恩倖韓寶業(yè)傳》。,但其是否專(zhuān)設(shè)教官今已不得而知。西魏、北周先由大司樂(lè)總掌樂(lè)舞及相應(yīng)的教習(xí)活動(dòng)*《隋書(shū)》卷一四《音樂(lè)志中》載北周“太祖輔魏之時(shí),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xí)以備饗宴之禮……其後帝娉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guó)、龜茲等樂(lè),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lè)習(xí)焉”。皆爲(wèi)樂(lè)舞教習(xí)之例。《周書(shū)》卷五《武帝紀(jì)上》載保定四年五月丁亥改大司樂(lè)爲(wèi)樂(lè)部。,周官改制後,教學(xué)諸務(wù)總歸樂(lè)部大夫掌管,其所屬除太學(xué)、小學(xué)博士、助教外,其餘爲(wèi)司樂(lè)、樂(lè)師、樂(lè)胥、司歌、司鐘磬、司鼓、司吹、司舞、籥章、掌散樂(lè)、典夷樂(lè)、典庸器等樂(lè)舞官*王仲犖《北周六典》卷四《春官府第九》。,其中“樂(lè)師”的執(zhí)教功能當(dāng)相對(duì)突出*《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樂(lè)署太樂(lè)令條下載“後周有司樂(lè)上士、中士”,樂(lè)正條下又載後周“置樂(lè)師上士一人,中士一人”。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司樂(lè)”與“樂(lè)師”並置,前者當(dāng)重在職事,而後者則應(yīng)如隋唐樂(lè)師(樂(lè)正)側(cè)重於教習(xí)。,整套系統(tǒng)分工甚細(xì)而規(guī)模可觀。
隋文帝時(shí),太常寺所屬太樂(lè)、清商二署分別有“樂(lè)師”8人和2人,鼓吹署又置“哄師”2人。至煬帝時(shí)改“師”爲(wèi)“正”,仍兼樂(lè)舞教學(xué)*《隋書(shū)》卷二八《百官志下》,其載煬帝大業(yè)三年“改樂(lè)師爲(wèi)樂(lè)正,置十人;太卜又省博士員,置太卜卜正二十人;以掌其事”。可見(jiàn)樂(lè)正、卜正略相當(dāng)於博士。,又大肆擴(kuò)充樂(lè)舞人員及其教學(xué)規(guī)模,朝廷禮樂(lè)宴饗所需樂(lè)舞外,各色歌舞雜伎“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隋書(shū)》卷六七《裴藴傳》。。唐代太常寺所屬太樂(lè)署和鼓吹署長(zhǎng)官皆有教習(xí)之責(zé),其下分置樂(lè)正8人和4人,皆兼教各色音樂(lè)、舞蹈,轄有專(zhuān)事傳授技藝的博士、助教*《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太樂(lè)署條載“凡習(xí)樂(lè),立師以教……業(yè)成,行修謹(jǐn)者爲(wèi)助教,博士缺,以次補(bǔ)之”。《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樂(lè)署載其教樂(lè)博士爲(wèi)“無(wú)品博士”。可見(jiàn)唐代部門(mén)樂(lè)舞之學(xué)的助教和博士皆無(wú)官品,從習(xí)樂(lè)優(yōu)秀者中隨時(shí)選補(bǔ)。。另值得注意的是,唐高祖以來(lái)又專(zhuān)門(mén)設(shè)置了直屬宮廷的教坊*《唐會(huì)要》卷三四《雜録》:“內(nèi)文學(xué)館、教坊,武德以來(lái)置在禁門(mén)內(nèi)。”又《舊唐書(shū)》卷三《太宗紀(jì)下》貞觀五年七月定死刑復(fù)奏之制,“其日尚食進(jìn)蔬食,內(nèi)教坊及太常不舉樂(lè)”。可證其時(shí)“內(nèi)教坊”與“太常”樂(lè)舞已並存。,玄宗開(kāi)元二年將之?dāng)U充爲(wèi)分擅舞蹈和歌曲的左、右教坊,專(zhuān)供御前娛樂(lè),兼事雜伎,亦有各色博士以爲(wèi)教職*《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三》述“開(kāi)元二年又置內(nèi)教坊於蓬萊宮側(cè),有音聲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此外,散在各地的大量官妓和營(yíng)妓,也各有“教頭”從事樂(lè)舞技藝的教習(xí)培訓(xùn)*《新唐書(shū)》卷一九六《隱逸·陸羽傳》載其復(fù)州竟陵人,開(kāi)天時(shí)曾“匿爲(wèi)優(yōu)人……吏署羽伶師”。《白氏長(zhǎng)慶集》卷二一《格詩(shī)歌行雜體·小童薛陽(yáng)陶吹觱栗歌》述薛陽(yáng)陶年方十二,“指點(diǎn)之下師授聲”。此樂(lè)童吹觱栗於潤(rùn)州公堂宴席間,是其必爲(wèi)官伎而指點(diǎn)之“師”當(dāng)爲(wèi)官伎教頭。又《碧雞漫志》卷五《喝馱子》條述《喝馱子》曲乃唐末“單州營(yíng)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新聲”。。
由上所述不難看出,自北魏至隋唐,部門(mén)樂(lè)舞之學(xué)的博士,已從正式官員降至無(wú)品職吏,又從獨(dú)立負(fù)責(zé)樂(lè)舞教授變而爲(wèi)輔助樂(lè)舞之官?gòu)氖卵葑嗉妓嚨膫魇凇H绻h太樂(lè)博士的設(shè)立意味著專(zhuān)職樂(lè)舞教官的出現(xiàn),那麼其地位和職能的這種下移,適足以説明部門(mén)樂(lè)舞之學(xué)中,學(xué)校教學(xué)方式已被限制在較低層次而未佔(zhàn)據(jù)主導(dǎo)地位,説明樂(lè)舞教學(xué)和履職過(guò)程的分化程度,相比於部門(mén)方術(shù)之學(xué)要來(lái)得更低。
正因如此,魏晉至隋唐的部門(mén)樂(lè)舞之學(xué),也就一直都在更大程度上保留著宦學(xué)事師的原始性。在此前提下,所有供職於朝廷的樂(lè)舞之人,幾乎均可計(jì)入其見(jiàn)習(xí)培訓(xùn)的規(guī)模。具體如魏晉至梁、陳,朝廷所屬樂(lè)舞之人的數(shù)量下限,當(dāng)是象徵正統(tǒng)所在和維持基本禮樂(lè)活動(dòng)的廟堂樂(lè)舞人員,依制爲(wèi)380餘人*《隋書(shū)》卷一五《音樂(lè)志下》:“自漢至梁陳樂(lè)工,其大數(shù)不相逾越。”這個(gè)“大數(shù)”,也就是《隋書(shū)·音樂(lè)志》序所述“漢郊廟及武樂(lè)三百八十人”。又《續(xù)漢書(shū)·百官志二》太常太予樂(lè)令條注引《漢官》,述其“樂(lè)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是爲(wèi)樂(lè)者與舞者合計(jì)之?dāng)?shù)。。但爲(wèi)之必須培訓(xùn)儲(chǔ)備者,總要超過(guò)廟堂樂(lè)舞的法定人數(shù)*如文、武舞,歷朝各八佾64人,共需128人,而《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樂(lè)署置“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原注則述“隋太樂(lè)署有舞郎三百”。,況且還有其他各色散樂(lè)雜伎,故其實(shí)際蓄有和需要訓(xùn)練的樂(lè)舞之人,往往在1000人以上*《三國(guó)志》卷三《魏書(shū)·明帝紀(jì)》載青龍三年(235)大治洛陽(yáng)宮,裴注引《魏略》述帝充實(shí)後宮,“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廷酒掃,習(xí)伎歌者,各有千數(shù)”。《南齊書(shū)》卷二八《崔祖思傳》述其太祖時(shí)奏請(qǐng)裁撤雜伎,述西漢孔光定樂(lè),“奏罷不合經(jīng)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lè)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hù)口不能百戶(hù),而太樂(lè)雅、鄭,元徽時(shí)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shù)”。又《陳書(shū)》卷七《皇后傳》末史臣述陳後主使諸貴人及女學(xué)士與狎客共賦新詩(shī),“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shù),令習(xí)而歌之,分部迭進(jìn),持以相樂(lè)”。。北魏至隋初其數(shù)不詳,隋煬帝則增廟堂樂(lè)舞者編制爲(wèi)1083人*《隋書(shū)》卷一五《音樂(lè)志下》述煬帝更造三部樂(lè),五郊樂(lè)工143人,廟庭樂(lè)工150人,饗宴樂(lè)工107人;另有文、武舞郎各二等,並132人,共有528人;又改置九部伎樂(lè),共有樂(lè)工155人。以上總計(jì)1083人,散樂(lè)雜伎不在其列。,又“總追四方散樂(lè)……自是皆于太常教習(xí)”,其總數(shù)一度竟達(dá)30000人上下*《隋書(shū)》卷一五《音樂(lè)志下》。其述煬帝時(shí)朝廷所蓄樂(lè)舞者“殆三萬(wàn)人”,《隋書(shū)》卷六七《裴藴傳》載爲(wèi)“三萬(wàn)餘”人。。另一個(gè)較大的數(shù)字出現(xiàn)在盛唐,史稱(chēng)當(dāng)時(shí)隸於太常分番接受教習(xí)的各色樂(lè)舞雜伎,總數(shù)共有“數(shù)萬(wàn)人”*《新唐書(shū)》卷二二《禮樂(lè)志十二》:“唐之盛時(shí),凡樂(lè)人、音聲人、太常雜戶(hù)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hào)音聲人,至數(shù)萬(wàn)人。”所謂“番上”,即在籍樂(lè)舞雜伎人按離京路途遠(yuǎn)近每年分成若干批,輪流赴京當(dāng)直,教習(xí)亦然。,加上左、右教坊習(xí)藝諸伎,總數(shù)當(dāng)與隋煬帝時(shí)相仿。而開(kāi)元前期的法定規(guī)模: 太常所屬有“文、武二舞郎140人,散樂(lè)382人,仗內(nèi)散樂(lè)1000人,音聲人10027人”*《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太樂(lè)署原注。又《新唐書(shū)》卷一二三《李嶠傳》載其中宗時(shí)奏“太常樂(lè)戶(hù)已多,復(fù)求散樂(lè),獨(dú)持鞀鼓者已二萬(wàn)員。願(yuàn)量留之,餘勒還籍”。《通典》卷一四六《樂(lè)六·清樂(lè)》:“國(guó)家每歲閲司農(nóng)戶(hù)容儀端正者歸太樂(lè),與前代樂(lè)戶(hù)總名音聲人,歷代滋多,至有萬(wàn)數(shù)。”可見(jiàn)一般情況,直屬太常的樂(lè)人與音聲人均在10000以上,在考慮樂(lè)舞之學(xué)規(guī)模時(shí),須注意的是其分番教習(xí)供職,並非同時(shí)在京。;此外又有處?kù)秾m中宜春院的“別教院”,亦即教坊女伎的習(xí)藝之所,其人數(shù)常在1000人上下*《舊唐書(shū)》卷二八《音樂(lè)志一》:“太常又有別教院,教供奉新曲……別教院廩食常千人,宮中居宜春院。”又據(jù)唐代崔令欽所撰《教坊記》:“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nèi)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得在教坊,謂之‘內(nèi)人家’,四季給米。”兩相對(duì)照,是“別教院”即宜春院,乃教坊女伎在宮中的教習(xí)和供奉場(chǎng)所。;以上共計(jì)12500餘人。直至晚唐宣宗大中初年,“太常樂(lè)工”仍有5000餘人,另有教坊“俗樂(lè)”1500餘人*《新唐書(shū)》卷二二《禮樂(lè)志十二》。。這還只是朝廷直屬樂(lè)舞之人的教學(xué)培訓(xùn)規(guī)模,如果再加上各地授藝培訓(xùn)的官妓和營(yíng)妓,數(shù)量當(dāng)然還要大大增加。
魏晉以來(lái)部門(mén)樂(lè)舞教學(xué)的規(guī)模之大,是因爲(wèi)其教學(xué)與履職過(guò)程的分化不充分;而這種分化之所以難以展開(kāi),又是與當(dāng)時(shí)樂(lè)舞的理論化和規(guī)範(fàn)化程度較低,與樂(lè)舞教學(xué)強(qiáng)調(diào)演奏技藝遠(yuǎn)甚於規(guī)範(fàn)化樂(lè)理舞技的狀態(tài)分不開(kāi)的。就拿北魏孝文帝時(shí)期的樂(lè)舞之學(xué)來(lái)看,當(dāng)時(shí)擔(dān)任太樂(lè)祭酒的公孫崇“徒教樂(lè)童書(shū)學(xué)而已,不恭樂(lè)事”。遂有大臣擔(dān)憂樂(lè)童曠廢音律,無(wú)法專(zhuān)精其業(yè),不符朝廷設(shè)立樂(lè)舞學(xué)校的本意,奏準(zhǔn)公孫崇參掌律呂鐘磬之事,以此促進(jìn)其樂(lè)舞教學(xué)回到正軌*《魏書(shū)》卷一○七上《律曆志上》太和十八年(494)高閭奏事。。這件事情既證明了孝文帝設(shè)立的太樂(lè)祭酒和博士,本來(lái)確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日常樂(lè)舞活動(dòng);也反映了樂(lè)舞之學(xué)重在掌握實(shí)用演奏技藝,爲(wèi)此必須限制其教官和教學(xué)過(guò)程完全脫離實(shí)務(wù)。這也就解釋了北魏以後樂(lè)舞博士、助教地位和作用的蛻變,而唐代部門(mén)樂(lè)舞之學(xué)的教學(xué)培養(yǎng)辦法,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其具體內(nèi)容除與其他部門(mén)之學(xué)相類(lèi)者外,還包括如下幾點(diǎn):
首先,習(xí)業(yè)者多從樂(lè)戶(hù)及其他官戶(hù)中選充*唐制因罪配爲(wèi)官奴婢的,一免爲(wèi)番戶(hù),二免爲(wèi)雜戶(hù),皆有專(zhuān)籍,有伎藝者配隸各司,無(wú)伎藝者割屬司農(nóng),皆稱(chēng)官戶(hù),其中包括樂(lè)戶(hù)。見(jiàn)《唐六典》卷六《刑部》都官郎中、員外郎條及《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fù)原研究)》下冊(cè)校録本《雜令卷第三十》,並參張澤咸《唐代階級(jí)結(jié)構(gòu)》第十四章《官戶(hù)、雜戶(hù)及其他》第一節(jié)《官奴婢和官戶(hù)》、第三節(jié)《樂(lè)戶(hù)與太常音聲人》。,業(yè)成者供事於本司。其具體規(guī)定是: 刑部都官司每年校閲各種配沒(méi)放免的戶(hù)口時(shí),都要從中選取“容貌端正”和符合規(guī)定年限者,充當(dāng)“太常音聲人”或“樂(lè)人”,將之列入直屬太常寺的專(zhuān)籍,核定名數(shù),依法接受太樂(lè)署和鼓吹署的“教習(xí)”*《唐六典》卷六《刑部》都官郎中、員外郎條述其年限規(guī)定是: 在京13歲以上,外州15歲以上送太樂(lè)署,16歲以上送鼓吹署。又《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fù)原研究)》下冊(cè)校録本《雜令卷第三十》:“太常寺二舞郎,取太常樂(lè)舞手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容貌端正者充,教習(xí)成訖,每行事日,追上事了,放還本色。”是舞郎從一般樂(lè)舞者中選充。。所有樂(lè)人和音聲人,凡習(xí)業(yè)已成課試合格者,即在本部門(mén)“專(zhuān)執(zhí)其事”;其中品行修謹(jǐn)者可依次選充爲(wèi)助教、博士,仍須輪番供事、執(zhí)教於官府而無(wú)官品*《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太樂(lè)署條:“其內(nèi)教博士及弟子長(zhǎng)教者,給資錢(qián)而留之。”説明樂(lè)舞博士一般仍須輪番供事執(zhí)教。;資深業(yè)優(yōu)者則可在本部門(mén)逐步升擢爲(wèi)官*《唐會(huì)要》卷六七《伎術(shù)官》。。
其次,教習(xí)或供事常分批輪番進(jìn)行,教習(xí)活動(dòng)按此展開(kāi)和調(diào)整。除太常寺自行在民間訪召的部分“長(zhǎng)上”樂(lè)人外,列入專(zhuān)籍的樂(lè)人和音聲人,均須按其居處遠(yuǎn)近,輪番赴太樂(lè)署和鼓吹署供事和接受教習(xí),因故無(wú)法前往者可以納資代替*《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太樂(lè)署條:“有故及不任供奉,則輸資錢(qián),以充伎衣樂(lè)器之用。散樂(lè),閏月人出資錢(qián)百六十,長(zhǎng)上者復(fù)徭役,音聲人納次者歲錢(qián)二千。”《唐會(huì)要》卷三三《散樂(lè)》載散樂(lè)閏月人各徵資錢(qián)爲(wèi)一百六十七文。。這説明其接受教習(xí)和供事具有服役的強(qiáng)制性。其分批輪番辦法是: 關(guān)外諸州每年分爲(wèi)6番,關(guān)內(nèi)諸州5番,京兆府4番;每次教習(xí)供事1個(gè)月,離京1500里之外的2番並上,一次性教習(xí)供事2個(gè)月;分6番的每天教習(xí)至申時(shí),分4番的每天教習(xí)至午時(shí)。
其三,“皆在本司習(xí)業(yè)”*《唐律疏議·名例篇》“工樂(lè)雜戶(hù)及太常音聲人犯流”條。。其教、學(xué)內(nèi)容爲(wèi)本部門(mén)掌管的各色樂(lè)舞,教習(xí)過(guò)程按不同樂(lè)舞分頭展開(kāi)。具體如太樂(lè)署掌朝廷禮樂(lè)燕享活動(dòng)所需的雅樂(lè)和坐、立二部伎樂(lè)及各色散樂(lè)*坐、立二部伎的構(gòu)成,參《唐會(huì)要》卷三三《讌樂(lè)》;散樂(lè)“非部伍之聲”,形式、名稱(chēng)多樣,包括各色俳優(yōu)歌舞雜奏百戲,參《唐會(huì)要》卷三三《散樂(lè)》。,其中僅雅樂(lè),唐初即定有12《和》之樂(lè),合31曲84調(diào),所用樂(lè)器包括編鐘、編磬、鼓、柷、敔、笙、竽、笛、簫、箎、塤、琴、瑟、箏、築,伴以登歌和文、武二舞,各有特定分工組合和服章儀節(jié)*參《新唐書(shū)》卷二一《禮樂(lè)志十一》、《唐會(huì)要》卷三二《雅樂(lè)上》、《樂(lè)府雜録·雅樂(lè)部》。。相關(guān)樂(lè)者、歌者和舞者的教習(xí),各須通過(guò)系統(tǒng)培養(yǎng)和訓(xùn)練,讓初學(xué)者逐步掌握其所需技藝和儀節(jié),達(dá)到能夠熟練演奏和配合的程度。
其四,“依法各有程試”*《唐律疏議·名例篇》“工樂(lè)雜戶(hù)及太常音聲人犯流”條。。即由主管部門(mén)課督所屬樂(lè)舞人的教習(xí)進(jìn)度。其分類(lèi)教習(xí)的年限規(guī)定是: 教習(xí)較難的大部伎限3年而成,次部伎2年,小部伎1年;教習(xí)樂(lè)曲的,以熟練演奏50首較難的曲子爲(wèi)業(yè)成;教習(xí)大、小橫吹者,較難的限4番而成,較易的限3番而成*《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太樂(lè)署條。。其課試辦法大體是: 教者和學(xué)者皆每年課試,每10年大校一次,按其程度分爲(wèi)上、中、下三等;教者的等級(jí)以其課督學(xué)者完成藝業(yè)的程度來(lái)定*《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太樂(lè)署條載其標(biāo)準(zhǔn)是: 教長(zhǎng)上弟子習(xí)較難和次難樂(lè)舞者各2人,四年而業(yè)成者,“進(jìn)考”。《文苑英華》卷五○八《判六·樂(lè)門(mén)十九道》首爲(wèi)《樂(lè)官樂(lè)師請(qǐng)考判》,其事由是“丙任樂(lè)司博士,教弟子雜色,五周成,請(qǐng)進(jìn)考。所司以不能發(fā)蒙,教不進(jìn)考,不伏”。其下判辭兩道反映了其教學(xué)獎(jiǎng)勸督課之況,可見(jiàn)朝廷及各地樂(lè)署的教學(xué)有五年而成者。同處所録的“樂(lè)師教舞判”,則述樂(lè)師教舞時(shí)有不受命者可加鞭撻。,並須上報(bào)禮部覆準(zhǔn),經(jīng)15年有5次課試爲(wèi)上等者,可以獲得官員身份繼續(xù)在本部門(mén)供事;若10年而藝業(yè)未成,可延長(zhǎng)5年再加校試,據(jù)其合格與否,決定其繼續(xù)供事還是退習(xí)難度較底的技藝或黜還原籍*以上除別注出處者外,皆見(jiàn)《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樂(lè)署及鼓吹署條。。
其五,教坊樂(lè)舞人直接爲(wèi)皇帝服務(wù)而性質(zhì)特殊,開(kāi)元以來(lái)改由宦官任教坊使掌管,可稱(chēng)是直屬宮廷的部門(mén)樂(lè)舞之學(xué)。供事和教習(xí)其中的樂(lè)舞人,從配沒(méi)官戶(hù)及太常樂(lè)人和音聲人中擇優(yōu)選充,也有直接從民間選取的,其中的技藝優(yōu)異者常年供職教習(xí),婦女比例較大。教坊所習(xí)皆爲(wèi)散樂(lè)雜伎*參《資治通鑑》卷二一一《唐紀(jì)二十七》開(kāi)元二年正月己卯條。,藝術(shù)形式爭(zhēng)奇鬥艷,許多膾炙人口的散樂(lè)散曲,往往都由教坊藝人創(chuàng)作或因教坊演奏而流播於世。教坊的教習(xí)課試之法,當(dāng)有類(lèi)於太常樂(lè)舞人而更爲(wèi)靈活,有興趣特長(zhǎng)的皇帝如玄宗,甚至親自主持傳授和排練某些樂(lè)舞。從其內(nèi)部按技藝高下有“內(nèi)人家”、“搊彈家”和“雲(yún)韶宮人”之別,又有第一曹、第二曹房和音聲博士等名目*白居易《琵琶行》:“自云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xué)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其顯然是平民女選入教坊第一曹房習(xí)業(yè)者。,可以推知其教習(xí)過(guò)程當(dāng)按樂(lè)舞類(lèi)別和難易程度分頭展開(kāi),亦有校試定等之制*以上除別注出處者外,皆參《教坊記》、《唐會(huì)要》卷三四《雜録》開(kāi)元二十三年勅及《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太樂(lè)署條。另參修海林《隋唐宮廷音樂(lè)機(jī)構(gòu)中的音樂(lè)教育活動(dòng)》,載《音樂(lè)藝術(shù)》1997年第一期。。至於各地官伎和營(yíng)伎的教習(xí)供事,亦當(dāng)與太常樂(lè)人相類(lèi)而有所簡(jiǎn)化。
四、 工巧之學(xué)及其他
上述律學(xué)、方術(shù)之學(xué)和樂(lè)舞之學(xué),可説是魏晉至隋唐部門(mén)之學(xué)中發(fā)展脈絡(luò)較爲(wèi)連貫的幾種。其學(xué)校形態(tài),則從律學(xué)和方術(shù)之學(xué)的相對(duì)明朗,降至樂(lè)舞之學(xué)已不甚明朗。而是否專(zhuān)設(shè)相關(guān)博士官,可説是衡量這一點(diǎn)的重要指標(biāo)。情形與樂(lè)舞之學(xué)類(lèi)似,不設(shè)專(zhuān)職博士而仍存在規(guī)模化教學(xué)體制的,還有範(fàn)圍廣及工程、製作乃至於烹調(diào)、駕馭、種植等各種工藝技能的工巧之學(xué)。
魏晉以來(lái)宮廷和官府需要的大量能工巧匠,除必要時(shí)直接從民間徵發(fā)外,正常情況下主要是由隸屬於各技術(shù)主管部門(mén)的匠戶(hù)來(lái)提供的。而匠戶(hù)身份及其服役供事的管理,向來(lái)都與樂(lè)戶(hù)類(lèi)似*參魏明孔《中國(guó)手工業(yè)經(jīng)濟(jì)通史(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第三章《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的手工業(yè)工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熊德基《六朝史考實(shí)》所收《六朝的屯、牧、官商、伎作和雜戶(hù)》,中華書(shū)局,2000年。,也就同樣應(yīng)當(dāng)存在著規(guī)模化的教習(xí)活動(dòng)。
如《宋書(shū)》卷一《武帝紀(jì)上》載東晉末劉裕北上滅南燕,獲慕容超巧匠張綱而攻克其都城廣固:
綱治攻具成,設(shè)諸奇巧,飛樓木幔之屬,莫不畢備。城上火石弓矢無(wú)所用之。
這當(dāng)然不可能是由張綱逐個(gè)教會(huì)工匠,而是利用官府作匠固有的逐層督責(zé)和集中教習(xí)之制,纔能在其設(shè)計(jì)基礎(chǔ)上大批製造出“飛樓木幔之屬”*《三國(guó)志》卷二九《魏書(shū)·杜夔傳》裴注引傅玄所序曹魏馬鈞之事,述其爲(wèi)朝廷製作攻城所用的連發(fā)拋石車(chē),亦當(dāng)如此。。《文房四譜》卷四《紙譜三》引《晉令》:
諸作紙,大紙一尺三分,長(zhǎng)一尺八分,聽(tīng)參作廣一尺四寸。小紙廣九寸五分,長(zhǎng)一尺四寸。
是爲(wèi)西晉官府造紙作坊的製紙規(guī)格,而其必定還會(huì)存在一系列相應(yīng)的技術(shù)工藝要求*參《太平御覽》卷六○五《文部二十一·墨》引韋仲將《筆墨方》述製墨之法,韋仲將即曹魏時(shí)常爲(wèi)宮中和官府書(shū)寫(xiě)匾額的著名書(shū)法家韋誕,其法應(yīng)是官府作坊製作宮廷顯貴所用好墨的技術(shù)工藝。。因而凡是官府作坊徵集的工匠,首先都要統(tǒng)一教習(xí)培訓(xùn)纔行。由於秦漢以來(lái)這方面已有相當(dāng)成熟的制度*雲(yún)夢(mèng)秦簡(jiǎn)《秦律十八種·均工律》、張家山漢簡(jiǎn)中的《複律》中,就都包含了這類(lèi)內(nèi)容。,魏晉以來(lái)其學(xué)亦當(dāng)承此繼續(xù)發(fā)展。《魏書(shū)》卷四下《世祖紀(jì)下》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庚戌詔:
自頃以來(lái),軍國(guó)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齊風(fēng)俗,示軌則於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xué)。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dāng)習(xí)其父兄所業(yè),不聽(tīng)私立學(xué)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mén)誅。
此詔隨同當(dāng)時(shí)禁毀佛教的一系列措施下達(dá),故其規(guī)定十分嚴(yán)厲。這裏的“百工伎巧”,自然包括了工藝、樂(lè)舞等各種技藝者;“騶卒”當(dāng)是車(chē)馬驛傳的駕馭和服務(wù)人員*《魏書(shū)》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傳上·廣平王洛侯傳》附《元匡傳》載其孝明帝時(shí)爲(wèi)御史中尉,尚書(shū)令任城王澄“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南齊書(shū)》卷四七《王融傳》載其嘗歎曰:“車(chē)前無(wú)八騶卒,何得稱(chēng)爲(wèi)丈夫!”是騶卒爲(wèi)車(chē)馬馭夫隨從之類(lèi)。又《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fù)原研究)》下冊(cè)校録本《雜令卷第三十》載唐令:“諸司流外非長(zhǎng)上者,總名‘番官’: 其習(xí)馭、掌閑、翼馭、執(zhí)馭、馭士、駕士、幕士、稱(chēng)長(zhǎng)、門(mén)僕、主膳、供膳、典食、主酪、獸醫(yī)、典鐘、典鼓、價(jià)人、大理問(wèn)理,總名‘庶士’……”其中“習(xí)馭”至“駕馭”六種人員皆爲(wèi)車(chē)馬之人,足見(jiàn)騶卒及所涉技術(shù)門(mén)類(lèi)之多樣。。此詔允許其世業(yè)傳習(xí)而禁止民間私學(xué)其術(shù),説明他們大都是繫籍於豪門(mén)或官方的伎術(shù)人戶(hù);“不聽(tīng)私立學(xué)校”,又説明官府建制中,百工技巧和車(chē)馬驛傳的主管部門(mén)有其相應(yīng)的技藝教習(xí)體制。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所定官品中出現(xiàn)的“方驛博士”,應(yīng)當(dāng)就是與此詔所述“騶卒”相關(guān),教授車(chē)馬驛傳相關(guān)技術(shù)的專(zhuān)職教官*《魏書(shū)》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十六年官品的從九品中階,惟有“方驛博士”一個(gè)職務(wù),其位次於第九中階的“太醫(yī)、太史助教”。至景明所頒官品中,此類(lèi)皆已消失。。這個(gè)職務(wù)到景明時(shí)頒佈的官品中業(yè)已消失,似乎也不應(yīng)是徹底裁撤,而是與太史、太醫(yī)、太樂(lè)等博士、助教一樣變成了流外或無(wú)品職吏。晚唐敦煌官、私工匠在繪畫(huà)、雕塑、建造、搟氈、金銀器等領(lǐng)域手藝高超者皆稱(chēng)“博士”*參馬德《敦煌工匠史料》研究篇之《敦煌工匠的技術(shù)級(jí)別》、史料篇下篇《工匠技術(shù)級(jí)別》二《博士》,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便從一個(gè)側(cè)面反映了北朝以來(lái)工藝技術(shù)領(lǐng)域的授徒傳業(yè)者地位不斷下降,但也仍像其他領(lǐng)域的教師一樣稱(chēng)爲(wèi)博士的事實(shí)。
從唐代各技術(shù)部門(mén)所隸匠戶(hù)的教學(xué)體制來(lái)看,爲(wèi)適應(yīng)官方建築和器物、製品的特殊標(biāo)準(zhǔn)和要求*參《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fù)原研究)》下冊(cè)校録本《營(yíng)繕令卷第二十八》。,除按宦學(xué)事師的傳統(tǒng)方式見(jiàn)習(xí)和提高技藝外,匠戶(hù)在番上供事服役時(shí),恐亦不免要由本司集中進(jìn)行一定程度的專(zhuān)門(mén)訓(xùn)練*《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fù)原研究)》下冊(cè)校録本《雜令卷第三十》載唐令: 無(wú)官之人“有技能者,各隨其所能配諸司”。此外,每年十月都官案比官戶(hù)中男送少府監(jiān)教習(xí)工藝技能,“其父兄先有技業(yè),堪傳習(xí)者,不在簡(jiǎn)例”。可以推知匠戶(hù)子弟可由父兄自行教習(xí),然其番上供事時(shí)仍當(dāng)有針對(duì)相關(guān)工程或製作的集中訓(xùn)練。。特別是爲(wèi)維持各部門(mén)所需匠戶(hù)的數(shù)量,朝廷每年都要像樂(lè)舞之人的培養(yǎng)和訓(xùn)練那樣,從官戶(hù)中選取聰敏少年分隸主管部門(mén),輪番赴京接受教習(xí)以掌握相應(yīng)的工藝技能。其具體規(guī)定是: 刑部都官司每年核定配沒(méi)官戶(hù)時(shí),除部分中男容貌端正者被隸籍太樂(lè)、鼓吹署外,也要選取十六歲以上符合規(guī)定者隸籍少府監(jiān),分番接受“教習(xí),使有工能”*《唐六典》卷六《刑部》都官郎中、員外郎條及《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fù)原研究)》下冊(cè)校録本《雜令卷第三十》。令文中只提到少府監(jiān)而未及內(nèi)侍省、殿中省、將作監(jiān)、軍器監(jiān)等同樣隸有大批專(zhuān)業(yè)技術(shù)人員的部門(mén)。據(jù)同書(shū)下冊(cè)校録本《廄牧令卷第三十》載唐令: 飼養(yǎng)馬、駝、騾、牛、驢處各給獸醫(yī),“其牧戶(hù)、奴中男,亦令於牧所分番教習(xí),並使能解”。可以推知選取聰敏少年隸籍主管部門(mén)分番教習(xí)的,並非止是少府監(jiān)一個(gè)部門(mén)。。《唐律》規(guī)定: 諸工、樂(lè)、雜戶(hù)及太常音聲人,“皆取在本司習(xí)業(yè),依法各有程試”*《唐律疏議·名例篇》“工樂(lè)雜戶(hù)及太常音聲人犯流”條。。這條法律中的“工戶(hù)”,專(zhuān)指隸籍於少府監(jiān)從事器物製作和織造、冶煉的工藝技術(shù)人員;“雜戶(hù)”則包括了配沒(méi)於各主管部門(mén)的各色技術(shù)者。其程試之法,如《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監(jiān)》載監(jiān)中教習(xí)各種工藝技巧之法:
金、銀、銅、鐵、鑄、蔞、鑿、鏤、錯(cuò)、鏃,所謂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平慢者,限二年成;諸雜作,有一年半者,有一年者,有九月者,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吐魯番阿斯塔那一五四號(hào)墓所出文書(shū),包括了多件“高昌作人名籍”,即高昌官作坊工匠之籍。
這樣的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也適用於其他各部門(mén)的技術(shù)教學(xué)。其顯然是一種規(guī)模化的定向培養(yǎng)和訓(xùn)練,並與樂(lè)舞之學(xué)一樣具有某種學(xué)校教學(xué)的性質(zhì)。
除以上所述之外,魏晉以來(lái)還零星出現(xiàn)過(guò)其他一些教習(xí)專(zhuān)業(yè)技藝的部門(mén)性教學(xué)設(shè)施。由於記載較少,對(duì)此只能綴其一零半爪略作介紹。
如書(shū)法之學(xué): 西晉曾在秘書(shū)監(jiān)下設(shè)立“書(shū)博士,置弟子教習(xí),以鍾、胡爲(wèi)法”*《晉書(shū)》卷三九《荀勖傳》。。這裏鍾爲(wèi)鍾繇,胡即胡昭,爲(wèi)漢魏間書(shū)法名家*《晉書(shū)》卷三六《衛(wèi)瓘傳》附《衛(wèi)恒傳》載其《四體書(shū)勢(shì)序》有曰:“魏初有鍾、胡二家,爲(wèi)行書(shū),法俱學(xué)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參《三國(guó)志》卷一一《魏書(shū)·管寧傳》附《胡昭傳》、卷一三《魏書(shū)·鍾繇傳》。《法書(shū)要録》卷一録王僧虔《論書(shū)》:“鍾公之書(shū),謂之盡妙。鍾有三體: 一曰銘石書(shū),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shū),世傳秘書(shū),教小學(xué)者也;三曰行押書(shū),行書(shū)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卷八張懷瓘《書(shū)斷》中《妙品》述:“胡昭……甚能史書(shū),真、行又妙。”,可見(jiàn)這是一所專(zhuān)門(mén)教習(xí)書(shū)法的學(xué)校。十六國(guó)、北朝的國(guó)學(xué)都很重視識(shí)字與書(shū)法,至隋唐國(guó)學(xué)包括書(shū)、算學(xué),其中書(shū)學(xué)以識(shí)字爲(wèi)主,性質(zhì)與西晉秘書(shū)監(jiān)所屬“書(shū)學(xué)”不同。倒是北齊設(shè)有“八書(shū)博士”2人*《隋書(shū)》卷二七《百官志中》。,顧名思義當(dāng)以教習(xí)八種字體爲(wèi)主*《晉書(shū)》卷六○《索靖?jìng)鳌份d其作《草書(shū)狀》,述當(dāng)時(shí)字體“觸類(lèi)生變,離析八體”。《魏書(shū)》卷九一《術(shù)藝江式傳》述其延昌三年上表奏準(zhǔn)編集字書(shū),“兼教八書(shū)史”,以學(xué)士五人助之,又置書(shū)生五人專(zhuān)事抄寫(xiě)。其表前文述其祖上六代俱習(xí)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chóng)書(shū),五曰摹印,六曰署書(shū),七曰殳書(shū),八曰隸書(shū)”。《北齊書(shū)》卷四四《儒林張景仁傳》載其以書(shū)法封王,“自蒼頡以來(lái),八體取進(jìn),一人而已”。《唐六典》卷二一《國(guó)子監(jiān)》稱(chēng)書(shū)學(xué)亦教“古文八體”。又可見(jiàn)“八體”爲(wèi)魏晉以來(lái)書(shū)家所重,而北魏江式編書(shū)之時(shí),八書(shū)教學(xué)已具雛形。,性質(zhì)似與西晉秘書(shū)監(jiān)所屬的書(shū)博士相類(lèi)。
再如禮儀之學(xué): 除各種官學(xué)教習(xí)的博士外,曹魏文帝另設(shè)太常博士專(zhuān)掌禮儀,其制爲(wèi)後世沿襲損益*《晉書(shū)》卷二四《職官志》並參《通典》卷二五《職官七·太常博士》。。魏晉以來(lái),朝廷禮制不斷系統(tǒng)和規(guī)範(fàn)化,士族門(mén)閥對(duì)之強(qiáng)調(diào)不一而足,但一般官民對(duì)繁複的禮儀典章卻已日漸生疏,操辦各種儀式和掌握相關(guān)的典章故事,成了一項(xiàng)專(zhuān)門(mén)化和技術(shù)性較強(qiáng)的工作,遂有必要加強(qiáng)對(duì)有關(guān)禮儀人員的培養(yǎng)和訓(xùn)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頒佈的官品序列中,出現(xiàn)了“禮官博士”之職*《魏書(shū)》卷一一三《官氏志》載太和中官品,無(wú)“太常博士”而有“禮官博士”,與太學(xué)博士、太史博士、律博士皆爲(wèi)第六品中階;景明中官品則無(wú)“禮官博士”而有“太常博士”,與太學(xué)博士同爲(wèi)從七品下階。又《魏書(shū)》卷四八《高允傳》載其作《徵士頌》,內(nèi)有“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同書(shū)卷一○八之一《禮志一》載泰常三年(418)八月明元帝祭白登廟時(shí),有“太廟博士許鐘”;又載太武帝神妤二年(429)九月立密太后廟於鄴,“置祀官太常博士、齋郎三十餘人”。可見(jiàn)北魏明元帝時(shí)有“太廟博士”,太武帝時(shí)有“太常博士”,俱爲(wèi)祀官。,從其與太學(xué)博士、太史博士和律博士地位相同,以及當(dāng)時(shí)所設(shè)各類(lèi)博士皆爲(wèi)教官的情況來(lái)看,“禮官博士”的設(shè)立,似乎也應(yīng)標(biāo)誌當(dāng)時(shí)建立了某種形式的部門(mén)禮儀之學(xué)。到唐代,太常寺和太常博士主持的禮院之下,各設(shè)置有行政地位類(lèi)似吏員的“禮生”35人*《新唐書(shū)》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條。“禮院”統(tǒng)管朝廷一應(yīng)禮事禮制的諮詢(xún)顧問(wèn),與太常寺相對(duì)獨(dú)立,由太常博士主持。《舊唐書(shū)》卷八《玄宗紀(jì)》載其正式設(shè)立於開(kāi)元十九年四月壬午。。且其既要在儀式活動(dòng)中充當(dāng)引導(dǎo)等輔助性角色*《通典·禮典》多處引《大唐元陵儀注》規(guī)定了禮生在相關(guān)儀式扮演執(zhí)紼引導(dǎo)等角色,故《唐大詔令集》載諸禮事制策或德音,常包括了賜參與儀式的禮生以勳級(jí)或優(yōu)予出身的條款。,也就必須接受相應(yīng)的教習(xí)和訓(xùn)練*參《舊唐書(shū)》卷一六二《陸亙傳》、《新唐書(shū)》卷一七七《高釴傳》附《高銖傳》,並參《唐會(huì)要》卷六五《太常寺》貞元八年(792)四月太常寺奏。。此外,唐代秘書(shū)省太史局的五官正之下,另有“五官禮生”15人,似乎是供事和教習(xí)節(jié)氣時(shí)令之儀的人員*《舊唐書(shū)》卷四三《職官志二》載秘書(shū)省司天臺(tái)有“五官禮生十五人”。所謂“五官”指春、夏、秋、冬、中官。又《唐會(huì)要》卷六五《太常寺》載長(zhǎng)慶二年(822)太常寺奏稱(chēng)“兩院禮生,元額三十五人”。。大體説來(lái),唐代這兩種禮生,都只是見(jiàn)習(xí)和供事於朝廷禮儀活動(dòng)的人員,因而與之相關(guān)的教習(xí)過(guò)程和設(shè)施,在性質(zhì)上與部門(mén)方術(shù)或樂(lè)舞之學(xué)並無(wú)不同。
再如宮人之學(xué): 內(nèi)廷宮人動(dòng)輒成千上萬(wàn),其教習(xí)培訓(xùn)向來(lái)自成系統(tǒng)*《後漢書(shū)》卷一○《皇后紀(jì)》序:“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可見(jiàn)漢代宮人自有教習(xí)之制。。魏晉以來(lái)見(jiàn)於記載者,如前引後趙石虎“內(nèi)置女官十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晉書(shū)》卷一○六《石季龍載記上》。。所置的“女官十八等”,顯然擴(kuò)充了魏晉宮官之制;其教宮人以“星占及馬步射”,也應(yīng)是在以往宮人教習(xí)的基礎(chǔ)上增加的新內(nèi)容*《唐六典》卷一二《宮官》引《晉令》述晉宮官有二千石的銀章艾綬、千石的銅印墨綬和千石以下的碧綸綬三等,包括大監(jiān)、食監(jiān)、都監(jiān)、上監(jiān)以及女史、賢人、恭人、中使、大使等不等級(jí)別的職務(wù)。其中女史如《周禮·天官塚宰》篇鄭注謂其“如太史之於王也”;《後漢書(shū)》卷一○《皇后紀(jì)》序稱(chēng)古來(lái)女史“記功書(shū)過(guò)”。魏晉女史亦然,故顧愷之《女史箴圖》繪女史執(zhí)筆記事,而《藝文類(lèi)聚》卷一五《后妃部·后妃》載西晉張華及裴頠所撰《女史箴》文,大抵亦皆規(guī)諫之語(yǔ)。這説明內(nèi)廷存在著一套由宮人組成的文書(shū)簿記系統(tǒng),也就意味著宮人不僅須在禮儀起居上,也須在書(shū)算知識(shí)上接受必要的教習(xí)。而石季龍?jiān)鲋门偈说戎械摹芭贰保@然就是在魏晉內(nèi)廷女史的基礎(chǔ)上增置出來(lái)的。。前秦苻堅(jiān)“課後宮,置典學(xué),立內(nèi)司,以授於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shí)者署博士以授經(jīng)”*《晉書(shū)》卷一一三《苻堅(jiān)載記上》。。這似乎是歷史上首次在宮中設(shè)置了專(zhuān)門(mén)教授宮人的經(jīng)學(xué)學(xué)校,其制包括了典學(xué)及相應(yīng)的官署和從宦官和宮人中選任的博士。南北朝以來(lái)的宮人之學(xué),如南朝劉宋文帝時(shí),曾以嫻於文辭的宮人韓蘭英爲(wèi)博士,“教六宮書(shū)學(xué)”*《南齊書(shū)》卷二○《皇后列傳》武穆裴皇后傳附韓蘭英事蹟。。北齊長(zhǎng)秋寺所屬掖廷和晉陽(yáng)、中山的別宮“各置宮教博士二人”*《隋書(shū)》卷二七《百官志中》。。隋初內(nèi)侍省置宮教博士13人,唐開(kāi)元年間則置2人,“掌教習(xí)宮人書(shū)、算衆(zhòng)藝”*《唐六典》卷一二《內(nèi)侍省》掖庭局條。其載唐代宮教博士從九品下,《隋書(shū)》卷二八《百官志下》載隋宮教博士從九品。又《舊唐書(shū)》卷一九○上《文苑蔡允恭傳》述其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煬帝“嘗遣教宮女,允恭深以爲(wèi)恥,因稱(chēng)氣疾,不時(shí)應(yīng)召。煬帝又許授以?xún)?nèi)史舍人,更令入內(nèi)教宮人,允恭固辭不就,以是稍被疏絶”。。但唐太宗以來(lái)也曾在宮人中展開(kāi)過(guò)經(jīng)學(xué)教學(xué)*《舊唐書(shū)》卷一八九上《儒學(xué)傳》序。,具體則設(shè)立了“內(nèi)文學(xué)館”,選宮人有儒學(xué)者一人爲(wèi)學(xué)士,“掌教宮人”。武則天以來(lái)改“內(nèi)文學(xué)館”爲(wèi)“習(xí)藝館”(一度亦稱(chēng)“翰林內(nèi)教坊”),其規(guī)模則大爲(wèi)擴(kuò)充,置有內(nèi)教博士18人,其中包括經(jīng)學(xué)5人,史、子、集、綴文3人,楷書(shū)2人,《莊》《老》、太一、篆書(shū)、律令、吟詠、飛白書(shū)、棋各1人*《新唐書(shū)》卷四七《百官志二》內(nèi)侍省掖庭局條及《舊唐書(shū)》卷四三《職官志二》中書(shū)省習(xí)藝館條。。這種盛況,當(dāng)然是武則天身爲(wèi)女主時(shí)發(fā)生的特殊現(xiàn)象,此後宮人學(xué)規(guī)模當(dāng)已減縮。不過(guò)內(nèi)廷習(xí)藝館中唐以來(lái)仍然存在,其教習(xí)活動(dòng)與宮教博士並行不悖*《新唐書(shū)》卷四七《百官志二》內(nèi)侍省掖庭局述習(xí)藝館“開(kāi)元末館廢,以?xún)?nèi)教博士以下隸內(nèi)侍省,中官爲(wèi)之”。然據(jù)《新唐書(shū)》卷七七《后妃傳下》尚宮宋若昭傳,其父庭芬德宗時(shí)擢爲(wèi)?zhàn)堉菟抉R、習(xí)藝館內(nèi)教。可見(jiàn)中唐以來(lái)內(nèi)廷仍有習(xí)藝館。又《唐會(huì)要》卷九一《內(nèi)外官料錢(qián)上》載大曆十二年(777)定百官料錢(qián),宮教博士與按摩、咒禁、卜筮博士各1917文。是宮教博士安史亂後仍在正常履職。。
綜上所述,魏晉至隋唐的官方部門(mén)之學(xué),特別是經(jīng)北魏轉(zhuǎn)折變遷而發(fā)展至隋唐的這類(lèi)專(zhuān)業(yè)技術(shù)知識(shí)、技能的教學(xué)體制,其總體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完備性和規(guī)範(fàn)性,不僅達(dá)到了空前的程度,也在當(dāng)時(shí)整個(gè)官學(xué)體系和各種教育設(shè)施中佔(zhàn)有重要地位。當(dāng)時(shí)官學(xué)體系各組成部分的功能區(qū)分,大體是由國(guó)學(xué)各學(xué)和州郡縣學(xué)針對(duì)身份較高的社會(huì)成員,培養(yǎng)可以成爲(wèi)各種重要官吏的文儒之士和文書(shū)之人,以體現(xiàn)和鞏固經(jīng)學(xué)的官方意識(shí)形態(tài)地位和經(jīng)史子文等主流公共知識(shí)的影響;又由各種部門(mén)之學(xué)針對(duì)身份較低的社會(huì)成員,培養(yǎng)在官府中不佔(zhàn)重要地位,卻仍不可或缺的各種技術(shù)官吏和專(zhuān)業(yè)服務(wù)人員,同時(shí)也可通過(guò)一定的課程設(shè)置,展開(kāi)不同程度的公共知識(shí)教學(xué)。若從各種專(zhuān)業(yè)技術(shù)知識(shí)、技能對(duì)於整個(gè)文明發(fā)展和社會(huì)生活品質(zhì)的重要性,從官府部門(mén)之學(xué)幾乎包括各專(zhuān)業(yè)門(mén)類(lèi)而培養(yǎng)規(guī)模可觀,切關(guān)乎官府施政又兼有一定的公共服務(wù)功能,並在推進(jìn)相關(guān)知識(shí)技能本身發(fā)展時(shí)佔(zhàn)有重要地位的角度來(lái)看,加強(qiáng)對(duì)之的關(guān)注和研究應(yīng)是今後教育史和學(xué)校史亟待補(bǔ)足、改進(jìn)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