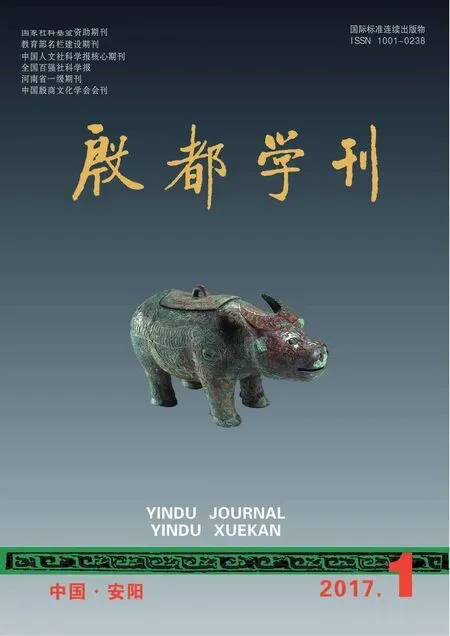宋玉辭賦“微諷”之風考辨
舒 鵬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宋玉辭賦“微諷”之風考辨
舒 鵬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宋玉與屈原并為中國文學之祖,而史書對二人評價差距頗大,《史記》評宋玉“終莫敢直諫”引發后人對其人格的質疑。本文從宋玉辭賦“微諷”風格進行分析,認為司馬遷對宋玉的評價并無人格貶抑之意。而宋玉本身際遇與屈原差相仿佛,空有滿腹才情,在上不得君上親任見察,在同僚中招嫉蒙謗,在下則“不譽之甚”,宋玉雖有拳拳之心卻難申其志,而選擇“放游志乎云中”,由此形成了宋玉辭賦的微諷風格。同時,宋玉辭賦在文學疆域中有意“鋪彩摛文”,開“夸飾淫麗”賦風傳統。
宋玉;辭賦;直諫;微諷;文采
宋玉,字子淵,戰國楚人,屈原后學,約生于楚頃襄王元年(BC289),卒于楚亡之時(BC222)[1],生平好為辭賦,與屈原并為中國文學之祖[2],后人多稱“屈宋”。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盛贊宋玉的文學造詣,并首以“屈宋”并稱,曰“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云”(《時序》),“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辨騷》),“宋玉含才,頗亦負俗”(《雜文》)。著名詩人李白則以詩句“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感遇四首》其四)高譽宋玉品質之純;杜甫亦作詩“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戲為六絕句之五》)、“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詠懷古跡五首》其二)表達對宋玉的景仰之情。
宋玉生平事跡極少見載于籍,司馬遷作《屈原列傳》略提及宋玉,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3]盡管太史公并未對宋玉有苛責之意,而“終莫敢直諫”之論終使得宋玉蒙被人格上的污玷,并不斷被放大,以至于在近代,宋玉在文學作品中成為諂媚權貴、欺師滅祖的代名,并一度作為政治揶揄的對象而被丑化扭曲。對于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言,蒙受如此不白之冤是不可漠視的。既然這段公案由“莫敢直諫”為肇端,本文試從宋玉“莫敢直諫”的因由論起。
一
司馬遷說宋玉“好辭而以賦見稱”,《漢書·藝文志》載“宋玉賦十六篇”,而后人網羅署名宋玉者的辭賦共計有十九篇:《九辯》、《招魂》兩篇最早見于東漢王逸《楚辭章句》;《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五篇最早見于南朝梁蕭統《文選》;《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六篇最早見于唐人章樵所編《古文苑》;《微詠賦》最早見于南宋陳仁子編《文選補遺》;《高唐對》、《郢中對》兩篇最早見于明劉節《廣文選》;《對友人問》、《對或人問》兩篇最早見于南宮邢氏藏本明人輯《宋玉集》;《報友人書》一篇則最早見于明梅鼎祚編《皇霸文集》。這些篇章真偽雜陳,隨著近年來楚辭研究和宋玉研究的深入,對宋玉辭賦的界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當前主要觀點認為《九辯》、《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共10篇賦可確認為宋玉的作品;至于《高唐對》、《郢中對》疑分別為《高唐賦》、《對楚王問》之異文;作者尚有爭議的是《招魂》、《笛賦》、《舞賦》(疑為漢傅毅《舞賦》之摘錄)、《微詠賦》、及臨沂銀雀山竹簡中《御賦》等篇。而《對友人問》、《對或人問》、《報友人書》三篇則為偽作。[1]、[4]
從已確認的宋作諸篇可見,《大言賦》、《小言賦》為應制之作,內容前后承接,敘楚襄王君臣游陽云之臺,召唐、景、宋作賦以定高下,結果“宋玉受賞”。兩篇基本屬于取悅于君王而作,窮形盡相地描寫大小物象,無諷喻之意。《高唐賦》、《神女賦》二篇同樣內容前后有所勾連,敘述楚襄王與神女交歡之事,《高唐賦》主要筆墨描繪巫山地區山水風物;《神女賦》則著意塑造巫山神女絕代風華。賦作之中暗借遇合神女之事批評襄王昏庸無能和無所作為。《風賦》、《釣賦》兩篇則全篇諷諭君王,前者以“大王之雄風”和“庶人之雌風”的對比描寫,使大王豪奢和庶人悲慘形成鮮明比照,言辭瑰麗而暗諷辛辣;后者則以釣術寓治國之術,警示君王不應耽于小道而怠于治國。至于《登徒子好色賦》、《諷賦》、《對楚王問》三篇均以自我辯解為務,發心中憤懣,指斥世俗而無賢,實則暗指君王為君不明,昏聵偏聽,其諷諫意味頗濃。《九辯》則以抒情擅場,相較于其他篇章的含蓄,該篇言辭直接,一承屈原《離騷》之風。單就其諷諫方式而言,與屈作的熱烈直達,犯言直諫相比,宋作中除《九辯》諷諭較為直白外,其他作品諷諫之意皆迂曲委婉,蓄勢不發。故司馬遷說宋玉“莫敢直諫”,極是。
然,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是以史學家眼光觀照千古人物的,對于敢言直諫的歷史人物,司馬遷往往帶有明顯的肯定傾向。在《滑稽列傳》中他將齊之淳于髡,楚之優孟,秦之優旃等一眾社會地位極低的倡優列入傳記中,極力凸寫他們面對君王敢于直諫,善于智諫的事跡,并認為其符合六藝之旨,評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豈不亦偉哉!”[5]這無疑是對他們敢于進言,面諫君過行為的認可褒揚。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司馬遷對屈原的追求美政、直言敢諫、上下求索、九死不悔、以死相諫,賈誼的上書勸政、無辜被貶、才高蓋世、英年早逝的事跡表現出高度崇拜。尤其是對屈原,不同于其后班固、楊雄對屈原“露才揚己”而不知明哲保身的看法,司馬遷認為屈原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6]屈、賈二人都以犯言直諫立身而終以悲劇告終,聯系司馬遷本身也因直諫而遭難的際遇,其惺惺相惜,物傷其類自然在情理之中。因此在《史記》中司馬遷同情悲劇人物,鐘情敢諫之士的例子所在皆是,也形成了他衡量歷史人物的一個標準。宋玉同為楚國顯名者,卻未能如屈原一般直諫君王,未能毫無保留地為楚國盡力,以太史公史學家眼光衡量,他在政治上的表現自然是略遜屈賈一籌的。惟其如此,說明司馬遷對宋玉并未有人格上的貶斥,而是比之前輩屈原,宋玉終究能達到“直諫”的程度是值得遺憾的。
屈、宋雖同為楚人,且均一度為楚王近臣,然氣性畢竟不一,時勢也各異,所以后人用屈原的標準來衡量宋玉,未必中正。
二
后人指責宋玉的罪名中有一條是“諂媚權貴”,認為宋玉憑獻媚邀買高位,方成為楚王近臣。而事實卻非如此。宋玉生平無明確史料可考,《史記》但言其在屈原之后,與唐勒、景差并時,筆者從散見于籍的一些語焉不詳的資料里試勾勒宋玉生平。
王逸《楚辭章句·九辯序》“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7]與《隋書·經籍志》“《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8]均認為宋玉為屈原弟子,學界對于屈宋生卒年歲研究的結果證明此說恐不可信,而宋玉作為屈原后進,仰慕屈原道德文章則確實無疑。《韓詩外傳》記“宋玉因其友而見楚相”,劉向《新序》說“宋玉因其友以見楚襄王”,晉代習鑿齒《襄陽耆舊傳》亦載“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者,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9]可知宋玉起于微賤,大約受朋友——楚王族同姓景差所薦方與楚頃襄王交接,頃襄王欣賞其文才,引為近臣,宋玉方得以隨侍左右。此情在宋玉辭賦中多有反映,《風賦》云:“楚襄王游于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大言賦》云:“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陽云之臺。”《釣賦》云:“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于玄洲,止而并見于楚襄王。”出土文獻《御賦》亦云:“唐勒與宋玉言御襄王前。”這段時期大約是宋玉生平里最為得意的時候,《小言賦》云:“楚襄王既登陽云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隨侍楚頃襄王左右的文學之臣還有唐勒、景差等人,而宋玉文才高妙,勝出同儕一籌,故而宋玉最受楚頃襄王青睞,單獨陪侍楚頃襄王左右的機會多于他人,《高唐賦》記“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于云夢之臺”,《神女賦》記“楚襄王與宋玉游于云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或正因為宋玉的才氣高絕,不知藏鋒,以致招人嫉恨,加之其“體貌閑麗”“身體容冶”而行止放達不拘,以致貽人口實,《諷賦》記“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于王曰……玉休還,王謂玉曰……”,《登徒子好色賦》記“大夫登徒子侍于楚頃襄王,短宋玉曰……”,《對楚王問》更記“楚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自詡圣人,瑰意琦行,而世人嫉誹,其處境與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漢·班固《離騷序》)一般無二。
世人蒙昧嫉妒,宋玉自可不以為意,而作為倚仗的對象,楚頃襄王對其態度又如何?從《高唐賦》《神女賦》《風賦》《大言賦》《小言賦》《釣賦》的描述可見,楚頃襄王是一個游宴無度,貪淫好色的君王。《戰國策·楚策四》中借莊辛之口說楚頃襄王在郢都時“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10]《漢書·古今人表》將其列入下上之品,也可略知楚頃襄王并非一個合格的君上。頃襄王為楚懷王長子,即楚王位之初便聽信令尹子蘭與上官大夫讒屈原之言,“怒而遷之”。而宋玉平素“口多微詞”,意有諷刺,劉勰《文心雕龍·諧隱》云:“楚襄宴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五臣《文選注·風賦解題》云:“時襄王驕奢,故宋玉作此賦以諷之。”李善《文選注》論《高唐賦》:“蓋假設其事,風諫淫惑也。”《登徒子好色賦》表面寫登徒子好色,實則諷諫楚襄王不要迷女色而誤國政。可見宋玉在君王之側,見王耽于淫樂,時時有所誡喻,可見其拳拳之心。然這并非楚王所喜聞樂見,也不符合楚王心目中對宋玉的身份定位。《襄陽耆舊傳》卷一云:“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 宋玉為楚頃襄王近臣確然無疑,而其在楚國朝中所任官職又或是否有所職位都不得而知,比之屈原的“左徒”“三閭大夫”遠有不及。
從上述資料大致可知,宋玉生于屈原之后,且出身寒微,一度入仕,而并不得志。與其在《九辯》中“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所反映的仕途不暢是相吻合的。宋玉空有滿腹才情,在上不得君上親任見察,在同僚中招嫉蒙謗,在下則“不譽之甚”,其煩惱苦悶于《九辯》體現得極為明顯,曰:
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生而貧困窘頓,無師無友,寂寥一人,空任歲月蹉跎,年過中途而一事無成,秋涼似水,孑孓一身,顧影自憐,徒然悲嘆而已。又曰:
豈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云而永嘆!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郄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11]
君王在上而聽之不聰,饞諂之徒在下阻斷視聽,舉朝之中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宋玉懷抱利器卻難以見察于君王,與屈原“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離騷》)如出一轍。不同的是,屈原“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而決絕選擇“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宋玉則“愿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云中”(《九辯》)。宋玉選擇超越塵俗,放志云外,雖無三閭大夫為國為民九死不悔那般令人感佩,卻為貧士選擇了一條超越之路。放懷寥廓,對于困頓難行的文士未嘗不是一種合理選擇。
此外,宋玉一生主要生活在楚頃襄王、考烈王時期,這段時期正值楚國風雨飄搖之際。楚頃襄王元年(BC298年)秦昭王發兵楚武關,大敗楚軍,斬殺楚軍五萬人,奪取楚國析邑等十六座城池而歸;十九年,秦攻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之地;二十年,秦將白起攻楚,奪楚西陵;二十一年,白起再攻楚,奪楚都城郢,焚毀楚國先王墓地夷陵,楚遷都于陳;二十二年,秦取楚巫郡和黔中郡。同年頃襄王死,楚太子熊完即位,是為考烈王,令尹黃歇奉行其“親秦附秦”路線,秦兵鋒芒東指三晉,楚國暫得茍喘,而其時楚國已被秦蠶食鯨吞,日趨衰弱,再無力與秦爭雄。考烈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而無功,返而遷都壽春。
宋玉在家國江河日下,仕途又蹭蹬難行情況之下,選擇與莊子同樣“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莊子·天下》)而為辭賦,“極聲貌以窮文”(《文心雕龍》),于極聲色中暗寓諷刺,形成宋玉式的微諷文風,開后世大賦“勸百諷一”之先聲。
三
《漢志·詩賦略》對從戰國到西漢的文風遷變有精到概括,曰:
春秋之后,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云,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12]
周之文脈本出于《詩三百》,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詩》有治國化民之效,“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至于春秋之后,人心尚戰,法勢當權,禮崩樂壞之勢已積重難返,《詩》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詩大序》)的傳統日漸消弭,宋玉前輩如荀子、屈原之輩在家國遭隳,身世浮沉之時作辭賦以諷,尚能得《詩》之三昧,至于宋玉時,身處末世,一變辭章不尚浮華則例,“競為侈儷閎衍之詞”,后世仿效者比比皆是,馳騁文才,而諷諫意味大為消減。
《詩》因承擔著正國安家、移風易俗的使命而具備諷諫的現實意義,這也是荀卿、屈原辭賦作品的根柢所在。孔子輯《詩》,荀、屈作賦都對作品寄予強大變風易俗的期望,故而孔、荀、屈都以政治家身份躋身歷史。至于宋玉,“放游志乎云中”的志向選擇決定了其作品社會功能的相對弱化。宋玉更關注自己作品的文學藝術性,所以在喪失部分社會功效的宋玉辭賦中,文學作品的文學特性卻得到放大和張揚。
以《對楚王問》為例,曰:
楚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有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征,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云霓,負蒼天,足亂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昆侖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13]
對于世俗之人的讒毀,宋玉云淡風輕,先以曲高和寡為喻,又以高飛之鳳與蕃籬之鷃,縱橫四海之鯤與尺澤寸水之鯢作比,形象地說明自身與世俗之人境界上高下之別,自身高行志節自然難為眾人理解。宋玉以圣人自況,超然獨處,孤高自安,充分刻畫了自命清高、孤芳自賞的高潔形象,成為后世孤高負俗、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形象的先聲。《文心雕龍·雜文》云:“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文。”金圣嘆《才子必讀古文》卷五《宋玉<對楚王問>解題》云:“此文腴之甚,人亦知,煉之至,人亦知。卻是不知其意思之傲睨,神態之閑暢。”何焯《義門讀書記》評“宋玉《對楚王問》……氣焰自非小才可及。”此篇所展現的鋪張揚厲,氣勢沛然,詞巧句麗的氣質正是后世大賦的雛形。
宋玉另有散體賦兩篇與《對楚王問》同一基調。其一《登徒子好色賦》曰:“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愿王勿與出入后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賦中寫登徒子詆毀宋玉生性好色,恐淫亂王宮,令楚王心生疑慮,轉詰問宋玉,宋玉則以東家鄰女至美而其不動心為例以示其并不好色,又以登徒子妻其丑無比,登徒子卻與之孕生了五個孩子,反責登徒子才是好色之輩。同時借章華大夫“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之說來闡述自己的“發乎情,止乎禮”的愛情觀。其二《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于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同僚唐勒在楚王面前進讒說宋玉容貌英俊,口善言辭而行止不端,調戲主人之女。楚王由此見責于宋玉,宋玉描述當時至主人家中情況,主人之女先是將宋玉引入暗示男女交歡的蘭房之室以示愛慕之意;又以華麗的著裝示美,以精致的飲食示好,以掛釵的動作示愛,以由衷的情歌坦白心扉;最后徑直以死明志,以殉情相脅迫希望與宋玉歡好。面對主人之女三番挑逗,宋玉均無動于衷,且予以拒絕,最后甚至說出“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來斷絕女子的求愛之心。宋玉的辯白讓讒言不攻自破,楚王感服。兩篇文章都窮形盡態地刻畫出“宋玉”的立身高潔的正人君子形象,同時留給文學世界以“鄰家之女”“好色登徒子”“主人之女”等一眾經典文學形象。
在文學疆域中盡力施展其才氣是宋玉辭賦的重要特點,諷諫意味則藏而不顯,正所謂“意在微諷”。上述三篇散體賦均有宋玉受讒——楚王詰問——宋玉自我辯白這一行文模式,文辭絕艷,令人目不暇接,而其諷諫意味藏而不顯,細細深究,各有深意。《對楚王問》文中楚王表現的與世俗之人一般,用世俗之人的“不譽”詰難宋玉,不知好歹,不分賢愚,偏聽不明,其為君不明可知。宋玉于文中并未對楚王所責之“遺行”進行辯解,但以曲高和寡,燕雀尺鯢不知鳳凰鯤魚之喻使得“遺行”之誣不攻自破。宋玉的孤高絕塵,自然顯現,楚王及世俗之人的昏昧昭然若揭。《登徒子好色賦》、《諷賦》取屈原“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離騷》)之意。登徒子、唐勒之輩對宋玉心生嫉妒,抓住宋玉“體貌閑麗”“口多微辭”而捏造事端,以“淫”極力誹謗之。宋玉在楚王問責之下,極夸張之能事,描寫自身在美色當前,百般挑逗之下尚能義正詞嚴,不事淫亂。相較之下登徒子好色無度,主人之女多情大膽才是真正的“淫”。面對宋玉的辯白,《登徒子好色賦》中楚王信之如初,而《諷賦》中楚王的反應則頗耐人尋味,“王曰:‘止止。寡人于此時,亦何能已也!’”楚王的此番慨嘆至少有四層意思,一則楚王自詡有非常之操守,不會為一般的女性示愛所動;二則即便如楚王,直面主人之女示愛攻勢,也難保無動于衷;三則是接受宋玉的辯白,消除了對宋玉“不亦薄乎”的質疑;四則認同宋玉做法,接受宋玉的諷諫。此篇賦也是宋玉作品中明確表示楚王受諫的一篇。《諷賦》的主旨可參見宋章樵的解題:“楚襄王好女色,宋玉以此賦之,之詞麗以淫,謂之勸可也。”由此觀之,《登徒子好色賦》與《諷賦》均是諷諫楚襄王勿貪女色而誤國。
與屈原的“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卜居》)、“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直言世之丑惡、王聽不聰不同,宋玉雖同樣以高潔不俗自況,“竊慕詩人之遺風”卻不熱烈直達地表達對君王的指摘、對庸俗諂媚制備的厭惡,而是縱筆于文,重彩華色,逞才使氣,以一個文人身份在文學疆域中大展拳腳,以瑰麗炫彩的色調和玄幻無垠的想象將屈原開辟的瑰奇世界進一步拓展。面對與屈原一樣偉大的文學肇始者,自然不當以單一的諷喻為唯一評價標準。漢人文章事即家國事,故漢代學者對賦的褒貶,都是以有無“風諭之義”為尺度進行肯定或否定。如楊雄早年學相如作大賦,晚來悔之,以為“沒其風諭之義”,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對賦“勸百諷一”頗為不滿。至于文學自覺時代,南北朝劉勰作《文心雕龍》,認為賦體興起于戰國,造極于漢,是一個由粗樸到精致的歷史過程,而正是“宋發夸談,實始淫麗”。劉勰對宋玉作品雖有“無貴風軌,莫益勸戒”之語,認為其諷喻不夠強烈,同時卻認為“楚襄宴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諧隱》)并未完全否定宋玉作品中諷諫意味的存在。宋玉與屈原生平境遇差相仿佛,而以賦見稱,“原夫茲文之設,乃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于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雜文》),劉勰認為夸飾淫麗正是賦的“立體大要”。宋玉以其出類拔萃的賦作和魅力四射的藝術風采,為兩漢魏晉以來千百年的賦家開辟了無限可能。也由此劉勰將宋玉與屈原相提并論,認為其“雖取镕經意,亦自鑄偉辭”,充分肯定了宋玉在文學史上的拓宇之功。
盡管在史學家的眼中,宋玉終究不登大雅之堂;而作為文學家,“鋪彩摛文”的宋玉之名足以鐫銘千古。
[1]吳廣平.宋玉研究[M].長沙:岳麓書社,2004.
[2]陸侃如.屈原和宋玉[M].商務印書館,1930.
[3]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傳二十四)[M].中華書局,1982.
[4]湯漳平.出土文獻對宋玉研究的影響[J].中州學刊,2012.
[5]史記·滑稽列傳(傳第六十六)[M].中華書局,1982.
[6]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傳二十四)[M].中華書局,1982.
[7]洪興祖.楚辭補注[M].引王逸.楚辭章句·九辯序[M].中華書局,1985.
[8]魏征.隋書·經籍志[M].中華書局,1982.
[9]吳廣平.宋玉研究[M].轉引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卷一)[M].長沙:岳麓書社,2004.32.
[10]劉向.戰國策·楚策四[M].中華書局,2012.
[11]洪興祖.楚辭補注·九辯[M].中華書局,1985.
[12]班固.漢書·藝文志[M].中華書局,1962.
[13]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對問·對楚王問[M].中華書局,1977.
[責任編輯:邦顯]
2017-01-10
舒鵬,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學文獻。
I207.223
A
1001-0238(2017)01-008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