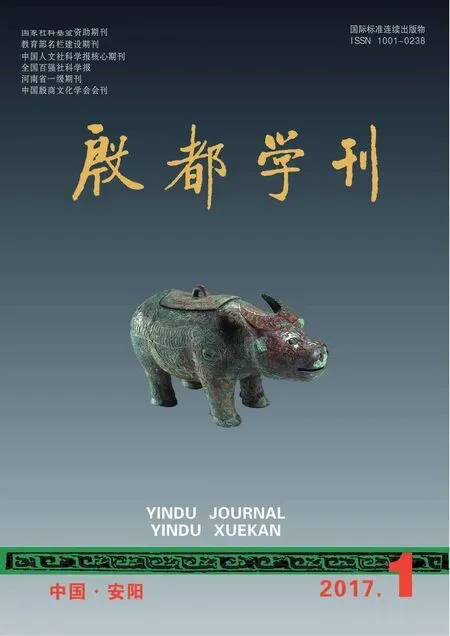從小林形象塑造看劉震云的胸襟與氣度
焦會生
(安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安陽 455000)
從小林形象塑造看劉震云的胸襟與氣度
焦會生
(安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安陽 455000)
劉震云通過小林形象的塑造,充分表現出他藝術創作的胸襟與氣度,即同情并理解小林之異化,“反諷”并“抗議”造成小林異化的現實環境。這種胸襟與氣度和現代啟蒙者“狂人”與古代士大夫精神相比,還遠不夠雄遠和高逸,還有極大提升空間。
小林;劉震云;胸襟;氣度
小林是著名河南籍作家劉震云奉獻給當代文壇的為環境壓抑而異化的知識精英典型形象。它誕生二十多年來,一直受到廣大讀者深切的關注,尤其是被著名導演馮小剛以“一地雞毛”為名搬上銀幕以后,更是引起廣泛的重視。深入研究其形象特征并由此探究作者藝術創作的胸襟與氣度,對于研究當代作家的責任與使命不無裨益。
一、小林形象特征
小林是劉震云在中篇小說《單位》和《一地雞毛》中精心塑造的知識精英典型形象,是一個被惡劣的現實處境所異化而走向平庸的墮落者和妥協者,是一個喪失知識分子責任與擔當而遁入俗世的隨波逐流者和混世者,是一個為日常瑣事磨蝕而日漸變得心靈沙漠化的薄情者與冷漠者。
首先,小林是一個屈從于現實環境而逐步放棄自我個性而走向平庸的墮落者和妥協者。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為了入黨,為了升官,他被迫放棄自己的自由個性,而違心地融入以“官本位”為中心的現實環境,以期達到自己改善生存處境的目的。
在《單位》里,小林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某國家機關做了一名小公務員,成了國家體制內的一分子。他原本是一個孩子氣十足,自由慣了的人,以說話隨意、行為不拘而著稱。然而,在“單位”里一切都是以“官”或者說“權力”為本位的。個人生存條件的優劣,人生的榮辱浮沉,均圍繞著“官位”和“權力”而旋轉,“錢、房子、吃飯、睡覺、撒尿拉屎,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在單位混得如何,升官成為人們竭力追求的價值目標。因此為了升官,人們在這里使盡各種招數,什么巴結奉迎,什么爾虞我詐,什么投其所好,什么投機鉆營……應有盡有。在這種環境里,小林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適應并學習這里的一切。“從此小林像換了一個人。上班準時,不再穿拖鞋,穿平底布鞋,不與人開玩笑,積極打掃衛生,打開水,尊敬老同志;單位分梨時,主動抬梨、分梨,別人吃完梨收拾梨皮,單位會餐,主動收拾桌子。”他雖然十分討厭女老喬,但女老喬是黨小組長,掌管著他入黨的事情,為了入黨,為了升官,他“得重新認識女老喬和她的狐臭,夏天再也不能嫌女老喬狐臭,得一日一次挨著她的身子和她談心”;他雖然極不情愿幫剛升為副局長的老張搬家,但還是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他甚至還積極主動地為張副局長家刷馬桶、倒垃圾桶。這一切都是為了達到提級、升官、改善生存條件的目的。正如他對老婆所說:“我何嘗想幫這些王八蛋搬家?可為了咱們早搬家,就得去給人家搬家!” 可見,他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主動地克制自己的個性而違心地去適應現實環境,成了一個墮落者和妥協者。
其次,小林是一個迫于生活重負逐步放棄知識分子的社會理想而日漸融化于庸俗不堪的塵世的混世者。如果說《單位》側重描寫“單位”這一特殊的當代社會機制對人所產生的磨損與銷蝕力量,那么,《一地雞毛》則著重描寫小林在家庭生活中所經歷的精神磨礪與變化;如果說《單位》著重表現工作環境對小林自我個性的侵蝕,那么《一地雞毛》則著重表現家庭生活環境對他個性的磨損。這種磨損更滲透進他的私人生存空間,使他在更本己的層面上徹底擯棄自我意識。[1]
“小林家一斤豆腐變餿了。”這是小說開頭的第一句話,也是小說描述的第一個故事。這當然是一件微不足道、再平凡不過的日常瑣事,但正是諸如此類的“雞毛小事”構成了小林的全部生活內容:房子、孩子、蜂窩煤、保姆、老家來人、愛國菜等等。對所有這些瑣事的敘寫就構成了這篇小說的全部情節。“一地雞毛”由此成為這篇小說最為突出最具特征性的審美意象。“一地雞毛”這個意象深刻揭示了20世紀后期中國社會現實的某些本質方面:人為無數日常生活瑣事所拖累,所異化,形成令人無可奈何的“煩惱人生”。這些生活瑣事造成了對人的最大磨損。正如作者所說:“生活是嚴峻的,那嚴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嚴峻。嚴峻的是那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瑣事。”[2]這些一地雞毛一樣的日常生活瑣事,無不滲透著某種社會權力關系,無不證明著小林的“沒有本事”,無不磨蝕著知識分子公務員小林的個性。
小林與無數大學畢業生一樣,“大家都奮斗過,發憤過,挑燈夜讀過,有過一番宏偉的理想,單位的處長局長,社會上的大大小小的機關,都不放在眼里”。但參加工作步入社會之后,每天奔波在單位、家庭兩點一線之間,上班下班,洗衣做飯弄孩子,對付保姆,還有為房子發愁,為滴水偷水臉紅,為孩子入托求人,為老婆調工作送禮……他置身于生存的沉重壓力之下,在無數的摸爬滾打中,難以有機會從容地聽從于內心,而不得不墜入到無邊的生存網絡之中,聽任自己的精神世界愈加滑向平庸和貧瘠。1因而書也不想看了,世界杯足球賽也不能看了,理想抱負也化為泡影,故而“很快就淹沒在黑壓壓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從而認同了大學同學“小李白”“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的觀點,“什么宏圖大志,什么事業理想,狗屁,那是年輕時候的事,大家都這么混,不也活了一輩子”,最終得出結論:“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過下去,也滿舒服。舒服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可見,小林的精神發展軌跡,就是他的精神世界逐漸被抽空、個性逐漸消退的過程。[1]
再次,小林是一個為日常瑣事磨蝕而日漸變得心靈沙漠化的薄情者與冷漠者。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瑣事的磨損之下,心靈日漸沙漠化,精神世界日漸萎縮,變得冷漠而無情。當看到曾經有恩于自己的小學老師的死訊時,他難受了一天,可等一坐上班車,想著家里的大白菜,就把老師給忘了。當查水表的瘸老頭央求他辦批文時,“小林已不是過去的小林”,如果放在過去,只要能幫忙,他會立即滿口答應,但那是幼稚;“能幫忙先說不能幫忙,好辦先說不好辦,這才是成熟”。最終,隨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在收受了查水表老頭的賄賂后,就把批文給辦了。小林由此得到啟示,看來改變生活也不是沒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加入其中”就是不僅認可了原先自己所不恥的行為,而且放棄了自己的操守和理想。“小林感到就好象是娼妓,頭一次接客總是害怕,害臊,時間一長,態度就大方了,接誰都一樣。”物質生活生存空間狹窄,物質資源貧乏,無法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因此人們渴望改善生存狀態,而在這種“渴望”之中致使小林這個典型人物由一個思想單純,意氣風發的大學生轉變為失去理想和操守,心靈日漸沙漠化的小市民。
總之,小林是一個為外在環境所擠壓、所剝奪、所磨損、所銷蝕的知識分子公務員形象。其成長過程,是一個蛻變的過程,變異的過程。隨著他的成長,他逐漸喪失獨立個性和遠大理想,喪失知識分子應有的使命與擔當,喪失公務員所應有的表率示范作用,而一步步混入小市民之間并成為平庸世俗的混世者。由此形成了小林的悲劇命運。
二、作者敘述立場
那么,對于小林這樣一個悲劇命運,作者劉震云是持什么態度呢?或者說他的敘述立場是什么呢?
首先,作者對小林的悲劇命運充滿了同情與悲憫。無論是《單位》還是《一地雞毛》,字里行間都充滿了作者對小林悲劇命運的同情與悲憫。小林是從農村考上大學進到城里并進入國家機關的小公務員,由于沒有什么政治背景且無權無勢,所以生活狀態十分拮據。從在單位里“打水掃地”的地位,到日常生活中的“二等公民”的感覺,從“分房難”,到“調動難”、“入托難”,無不體現出作者對小林生活艱難的同情、理解與悲憫。
作者之所以這樣,我們應該從他的人生經驗和體驗中去尋找原因。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社會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清代學者王夫之也說,任何作家創作都有一個“身之所歷,目之所見”的“鐵門限”,[3]郁達夫認為“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有自傳的色彩的”。[4]這些論斷說明,任何作家的創作都是以其所熟悉的生活為藍本的。劉震云這位來自河南民間的著名作家,“對中國鄉土社會的苦難有著極其深刻的體驗”,[5]對權力給人造成的壓抑與傷害深惡痛絕。這一點在他的《塔鋪》、《新兵連》、《頭人》、《故鄉相處流傳》等作品中多有表現。在這一點上他與其他河南籍作家,如周大新(《向上的臺階》)、閻連科(《瑤溝人的夢》、《黑豬毛白豬毛》)、劉慶邦(《新房》)等一樣,感受深重。就《單位》和《一地雞毛》來說,也是這樣,劉震云與小林一樣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和體驗。劉震云和小林都成長生活在20世紀后期的中國社會,從農村考上大學,留在京城,且進入體制內工作。因此,他真切地描寫了小林的奮斗史,掙扎史,并聲稱小林的“見識相當了不起,我是把他當做一個英雄來寫的”[6]。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從小林身上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影子,看到作者對小林的同情、理解與悲憫。
其次,作者對造成小林悲劇的社會環境給予無情的揭露與“抗議”。[7]在作者筆下,小林雖為大學畢業生,雖為小公務員,但其物質生活條件或說滿足生存需要的基本條件與普通市民一樣窘迫。在《單位》中小林由于住房逼仄、工資微薄、人微言輕,幾乎舉步維艱,由此意識到生活本身的沉重分量,為此他不得不謀求在單位里提級長工資,不得不改變從前大學生的自由脾性,向過去深惡痛絕的世俗關系下的人與事低頭,進而變成一個規規矩矩的、毫無自我特點的小市民。《一地雞毛》基本上承續了這個思路。只不過“單位”里的生存壓力擴展到整個生活中去。為了老婆工作調動得去送禮,為了孩子入托得去求人,為了孩子上幼兒園得給阿姨送炭火……老婆單位通班車是沾了人家單位頭頭小姨子的光,孩子入托是沾了“對門‘印度女人’的丈夫”的光,自己像個“二等公民”,心里像吃了馬糞一樣齷齪……所有這些,都說明社會權力體系對人的壓抑與制約。小林就是在如此的摸爬滾打中,不得已而墜入到無邊的生存網絡中,從而聽任自己的精神世界滑向平庸和貧瘠,生存的過程也就意味著喪失自己的過程。
劉震云運用冷靜客觀的敘述,活生生地勾畫出人對現實無可奈何的處境,揭示出這處境的荒謬。小林的淪落是當時那個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小林的生存狀態和命運反映了那時大多數中國知識精英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困窘的生存狀態。生存空間逼仄,物質資源匱乏,人們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除了權力體制的壓抑之外,人們還要受到諸如吃穿住行的羈絆,因而人們對改善生存環境提出了強烈要求。劉震云讓讀者感受到了這一切,從而揭露并抗議了現實環境的惡劣。這種揭露與抗議“來自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對自己所賴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原則的絕望”[8],由此也就意味著作者對于知識分子立場的艱難的保持。
總之,劉震云對小林的悲劇命運給予了深切的同情與理解,對造成其悲劇命運的現實環境給予了深刻的揭露與抗議,體現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
三、由小林看劉震云的胸襟與氣度
胸襟指志趣、抱負等;氣度指氣魄風度。在這里是指作家進行文學創作時所表現出來的理想追求和人格境界。劉震云通過小林形象的塑造,充分表現出他藝術創作的胸襟與氣度,即同情并理解小林之異化,“反諷”[9]并“抗議”造成小林異化的現實環境。
小林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公務員,其胸襟與氣度怎么樣呢?概括地講,小林既沒有現代啟蒙知識分子的啟蒙精神,更沒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士大夫精神,是缺少雄遠高逸的胸襟與氣度的。
首先,小林作為生活于二十世紀后期的知識精英,與生活于二十世紀初期的“狂人”(魯迅《狂人日記》)相比,在胸襟與氣度上不僅沒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狂人”作為“人國”理想的先驅者和啟蒙者,以其歷史使命感、自我犧牲精神、深刻的虛無感和痛苦而清醒的罪人意識,完成了“五四”時期奮發揚厲而又蒼涼絕望的中國式啟蒙者的角色定位。由于其思想的超前性,使得普通民眾視之為“狂人”;而小林則在“官本位”和“金錢”本位的雙重圍困中,放棄理想,一步步把自己混同于普通民眾,丟失“啟蒙精神”,最終“加入其中”,成為蕓蕓眾生中的一員。[10]當代著名作家方方曾經描寫了三代知識分子形象,第一代有節操,有氣節,有擔當,正義凜然;第二代屈服于外在壓力而放棄理想,被迫喪失個性與操守,變得渾渾噩噩;第三代在經濟大潮沖擊下,自動放棄理想,擁抱現實,成了地地道道的小市民。魯迅筆下的“狂人”與劉震云筆下的小林不正是這第一代和第三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嗎?因此,與“狂人”相比,小林是一種蛻變,是一種地地道道的退步。
其次,小林作為知識精英與中國古代的士大夫相比,缺少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所謂士大夫精神,是大丈夫精神與治理天下之志的融合。孟子曾經強調,“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11]也就是說普通人的志向與其物質產業相匹配,只有那些德行修煉達到一定高度的士,才能不依賴于產業支撐而成為社會中堅。范仲淹則把這種思想推演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以天下為己任,不僅僅是一種職責,更重要的是一種人生使命。憂國愛民,心懷天下,“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12]可見,像孔子、孟子那樣胸懷家國,寄情天下,像顏回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才是大胸襟,大氣度。在小林身上我們看不到這種胸襟與氣度。
對小林寄予深切的同情與理解的作者的胸襟與氣度自然與小林相近。正如他七十多歲的小學老師對他所說的,你寫的書不如孔子寫的書,“差在胸襟氣度”。[13]
如上所述,作者精心描繪了知識精英小林被異化的悲劇,同時把小林異化的原因歸結于現實生存環境,并過分強調了知識精英異化的被迫性,過分強調了外在環境對人性的擠壓與塑造,從而忽略了人的主體性和自主性。環境對人的制約固然重要,但人自身的選擇與追求更為重要。正如文藝復興時哲學家喬萬尼·比科·米蘭多拉在《人類尊嚴論》中所說,上帝給予人類的恩賜就是選擇的自由與獨立的意志。下至禽獸,上至圣人,人無所不能。[14]關鍵在你怎么選擇。我們不能因為外部環境而放松對人自身內在修為的重視。對作家來講,要塑造人心,創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15]“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16]養德和修藝是分不開的。劉震云曾說道:“我不是那種要堅持什么,不妥協的人,我也不是那種幫別人指出道路的作家……”。[17]他還說:“中國知識分子歷來就是一個社會的附庸”。[17]這些自白可以看出他的胸襟與氣度還有提升的空間。
有許多評論家在評價劉震云時都充分肯定他對現實的反諷和抗議。比如:“劉震云是一位把中國文學傳統中以《儒林外史》為代表的諷刺藝術和以《官場現形記》為代表的暴露藝術發揮到極致,同時又兼具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和哲學的反諷意味的小說家。”[18]又如:“劉震云的作品反映了知識分子面對世俗沖擊的各種變化,表現了當代知識分子面對世俗壓力從抗拒、掙扎到屈從、沉淪的姿態變化,從而揭示出他們身上傳統人格理想的消隱與消解,呼喚著知識分子崇高人格理想的重建。”[19]再比如:“他對物質至上和權力至上的抗議,意圖即在構建人的精神的存在”。[7]反諷、抗議和呼喚并不是引領與重建。“放棄了對知識分子崇高的心路歷程的追述,只是著力于刻畫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態度”,[19]只能是作家精神的迷失與消隱。
作家不僅要揭示與抗議,更要引領與構建。魯迅曾說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20]習近平同志殷切希望文藝工作者要“做到胸中有大義、心里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時代呼聲、展現人民奮斗、振奮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優秀作品,為我們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為我們的民族描繪更加光明的未來。”[21]劉震云自己也說:“我覺得知識分子最大的作用不僅是過去和現在,更應該是未來,他們的目光應該像探照燈一樣,共同聚焦,照亮這個民族的未來。”[22]我們相信作者能夠提升自己的胸襟與氣度,把這個創作理念落實到他的創作中去。
[1]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313-317.
[2]劉震云.磨損與喪失[J].中篇小說選刊,1991,(2):88.
[3]王夫之 戴鴻森.姜齋詩話箋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55.
[4]郁達夫.達夫日記集·日記文學[Z].上海:北新書局,民國二十四年版. 1.
[5]姚曉雷.劉震云論[J].文藝爭鳴,2007,(12):122-132.
[6]劉震云.從《手機》到《一句頂一萬句》[J].名作欣賞,2011,(5):92-98.
[7]摩羅.劉震云:中國生活的批評家[J].當代作家評論,1997,(4):44-56.
[8]陳思和,李振聲,郜元寶,張新穎.劉震云:當代小說中的諷刺精神到底能堅持多久?[J].作家,1994,(10):69-74.
[9]陳曉明.漫評劉震云的小說[J].文藝爭鳴,1992,(1):69-72.
[10]杜玉梅.生存思考中沉重的突圍——《狂人日記》與《一地雞毛》知識分子主體形象比較[J].東岳論叢,2006,(5):193-194.
[11]孟子.孟子·梁惠王上[Z].北京:中華書局,2010. 11.
[12]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潤州謝上表[Z].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390.
[13]劉震云.從《手機》到《一句頂一萬句》[J].名作欣賞,2011,(5):92-96.
[14]麥吉爾 王志遠.世界名著鑒賞大辭典·散文[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0. 1453.
[15]李漁.閑情偶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1.
[16]王充.論衡·別通[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122.
[17]張英.劉震云:“廢話”說完,“手機”響起[N].南方周末,2004/02/05.
[18]於可訓.小說家檔案[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 346.
[19]苗祎.傳統人格理想的消隱與重建——論劉震云小說中的當代知識分子形象[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07,(4):147-149.
[20]魯迅.魯迅大全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159.
[21]習近平.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2016年11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130/c64094-28915395.html 2016年12月20日訪問.
[22]劉震云.文學夢與知識分子[J].甘肅社會科學,2013,(5):9-12.
[責任編輯:舟舵]
2016-12-01
焦會生(1961- ),男,河南林州人,安陽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文藝理論教學與研究。
I206
A
1001-0238(2017)01-003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