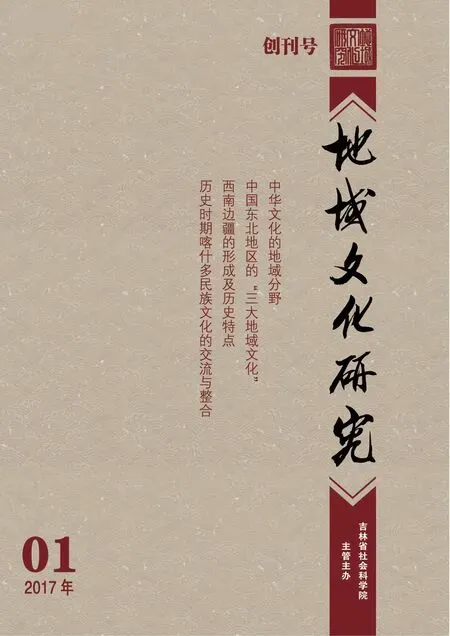中國東北地區的“三大地域文化”
王綿厚
中國東北地區的“三大地域文化”
王綿厚
東北地域文化是中國地域文化和東北亞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論題之一。有必要對中國東北地域文化的“泛流域文明”等文化命題進行重新思考。科學地界定中國東北地域文化的學術意義,是可以在宏觀上正確把握中國東北乃至東北亞區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分布,闡明中國東北地區“三大地域文化”的成因及其基本特征。
中國 東北 地域文化“泛流域文明”
一、中國東北地區“三大地域文化”的提出及其根據
對中國東北地域文化的分布、命名的研究,早在20世紀初葉就已經開始,其中“遼海文化”“關東文化”和“東北文化”為最初對東北地域文化的表述。在20世紀90年代,李治亭先生主持編著《關東文化大辭典》時已經提出過“東北文化區”的概念①李治亭:《關東文化大辭典》前言,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實際上是對近百年以來,東北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譜系的小結。而對其次文化區的命名,則始于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地域文化熱”研究的興起,并在以“遼河文明”“長白山文化”“草原文化”等正式提出以后。以2006年黑龍江省《多維視野中的黑龍江流域文明》編著的為例②潘春良、艾書琴主編:《多維視野中的黑龍江流域文明》,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頁。,關于東北地域文化內部的分區命名,就有“多流域文明”假說,如遼河文明、松花江文明、黑龍江文明、鴨綠江文明等。此書的兩次編寫會議和討論,我都是親歷者,因此萌生了對“東北地域文化”的不同看法,并主要針對“多流域文明”的“泛流域文明論”,提出以下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
對這一至今有爭議問題的思考,我并不是一時靈機而動,而是有其研學基礎。至少從1994年出版《秦漢東北史》時,就已深入思考“東北文化圈”問題。諸如上述的“多流域文明論”,看起來比較容易劃定文化范圍,其實并不完全合理。比如長白山區系,其東、南、西、北發源諸多水系,難道每個河流都應命名為獨立文化?所以“泛流域文明”的要害,是只重視了“水系”因素,而忽略了其他綜合社會因素,會產生無法科學界定的“泛流域文明”。而在我看來,命名或界定一個大的“地域文化”,盡管因素很多(包括水系),但最主要的應至少有以下不可或缺的三點:其一,有相對獨立的自然地理基礎和生態環境(如長白山區系);其二,應有相對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如草原群牧);其三,應有相對獨立的、不間斷的民族譜系和考古學文化(如遼河流域)。從這三點綜合看,如“黑龍江流域文明”,盡管也有較長的歷史和較寬闊的領域,但在“經濟形態”上,卻一直處在“混合類型”中;其在人文意義上的考古文化譜系中,與“遼河文明區”相比,也有斷裂和缺環。因此我把它作為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中的“子文化系列”——即黑龍江流域的古代文明,在上、中、下游三個地區,分別表現出“草原文化”“(江河)漁獵文化”“(山林)采集文化”等混合特征。
這樣來界定“東北地域文化”,毫無貶低某一區域文化地位的意愿。它的學術意義在于,可以在宏觀上正確把握中國東北包括東北亞區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分布。故如我在2015年5月1日《中國文物報》上著所《中國長白山文化“考古編”書后》所說,在近期出版的《中國長白山文化》這樣一部專門的地域文化著作中,對“東北地域文化”也沒有統一分區,有的章節引用了“遼海文化”“長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區等,有的章節又分為“遼河流域文明”“松花江流域文明”“鴨綠江流域文明”“黑龍江流域文明”等“四大流域文明說”或“五大流域文明說”。可見討論中國東北地域文化,應是中國乃至東北亞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論題之一。筆者在以下各部分,就此分別逐一解說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的成因及其基本文化特征。
二、遼河文明
遼河文明,又稱“遼海文化”和“遼河文化”。20世紀80年代,它在中華文明和中國地域文化中的地位,是隨著遼西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等重要發現,不斷引起世人關注。筆者關注遼海文化研究始于2002年,為紀念母校北京大學考古系創建50周年,曾撰有《遼河文明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歷史地位》一文。其后在2006年,又應邀撰寫遼寧省重點文化工程《遼寧文化通史》秦漢卷。在對秦漢遼寧地域文化源頭的歷史追述中,曾提出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以“遼河文明”為中脊,以“長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為東、西兩翼①王綿厚:《遼寧文化通史》秦漢卷第十章,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9年。,指出應當從東北亞的大區域來看待遼海文化。
(一)遼河文明的地理概念和“遼海文化”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基礎
“遼海文化”“遼河文明”或“遼河文化”,應是從不同的學科角度和學科內涵,對遼河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社會文化的命名。三者不存在如有些學者認為的主次的問題,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如同“齊魯文化”與“黃河文明”一樣,前者是地域文化命題;后者是考古文化和“文明起源”的術語。這二者具有共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基礎和歷史的必然性。概括地說,主要有三條。
其一,在宏觀自然地理上,遼海文化或遼河文明,是面向太平洋的東北亞前沿的區域文化。在“流域文明”上,它是黃渤海北岸和“遼河流域片”等大的地理區系。因此審視它的眼界,不能僅放在遼寧省的行政區劃內,而應投放在中國東北和東北亞的大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范圍內。即“遼河文明”作為一個大區域的文明單元,它的基本區域地理應以黃渤海北岸為腹地。其東界與遼東山地的“長白山文化”南緣接壤和交叉;其西界應以燕山以北、遼西努魯兒虎山以西至大興安嶺以南,在上遼河地區與“草原文化區”銜接;其北界則至松遼分水嶺。
其二,在東北亞大區域的文化地理視野上看,遼海地區應地處黃渤海北岸的東亞前沿內陸。它的廣義區位優勢,是橫跨東亞太平洋北緣黃、渤海北岸的南北相連的三個半島: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的中脊和前沿地帶。
其三,從“區域文明”的角度,看待遼河文化的區域特征。它的東緣有“長白山文化”;西緣有“草原文化”,是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的“中脊”和“橋梁”。如果從“海洋文明”與內河“流域文明”兼容的角度,看待歷史上的“遼海”稱謂,至少在東漢時曹植給其父曹操的《諫伐遼東表》中已提出,“遼東負阻之國,襟帶遼海”①曹植:《諫伐遼東表》,《陳思王集》,清光緒十八年《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而不是過去許多人引證的《魏書》等,認為“遼海”的地名稱謂,出現在南北朝時期,比過去應至少提前200年。我們應用更深遠的文化視角來審視遼河文明。
(二)遼河文明具有深厚的歷史文脈基礎
遼海文化或遼河文明的基礎是依托遼河水系。遼河古稱“大遼水”,是最早見于先秦文獻的中華名川。在《禹貢》和《呂氏春秋》“有始覽”等已記載:“何為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②《呂氏春秋》卷13《有始覽》,引自東郭士編《東北古史資料叢編》,沈陽:遼沈書社,1989年,第113頁。《呂覽》記載的“六川”,與《尚書》“禹貢”等一樣,是大禹平定中華“九州”后,最早確認的九州水系。如同“五岳”“五鎮”一樣,是代表當時中國九州方域的地標。《呂氏春秋》中的“黑水”,并不是指今天的黑龍江,而是甘陜交界和內蒙古居延地區的“黑水河”。所以“遼水”在戰國以前,已是中國東北乃至東北亞地區唯一載入正史的中華名川。《尚書》“禹貢”的名句“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正是指先秦由遼東和朝鮮半島,經黃渤海北岸的遼河腹地和遼西走廊,經過今山海關內外的遼寧省綏中縣“右碣石”,進入中原黃河的最早文化與民族通道。③其古代交通地理和文化地理、民族地理的深厚根源,可詳見筆者所著《中國東北與東北亞古代交通史》,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6年。自先秦以后,它的深厚歷史文脈基礎,更傳承了數千年。
(三)遼河文明的區位優勢和地域文化內涵
我認為從宏觀的角度,評價遼海文化和遼河文明的區位優勢,至少可以概括為如下六個方面。
其一,依托遼河水系形成的多元生態資源。遼河流域的自然生態的多元性和生態保護,是遼海文化多元兼容的自然基礎。這是我們在21世紀研究“遼河文化”首先應當具有的科學文化觀。遼河文化的生態保護和文化傳承,是當代研究遼河文化的“一車雙輪”。從歷史上追述,遼河文明從沿黃渤海北岸的橫向分布看,其東部為“長白山文化”,其西部為“草原文化”。從縱向地理的分布看,它又是中國北方北緯41度—42度之間,以“長城地帶”劃分的南北文化的不同分區,即遼河腹地的農耕文化和北緣游獵文化的中沖地帶。這一生態資源是歷史上長期形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它的“多元性”決定了遼海地區地域文化和考古文化的多樣性。
其二,由多元生態資源決定的綜合性經濟文化形態。上述多元自然生態資源條件,是決定遼海文化本質特征的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基礎。遼海地區這種多元、綜合性的經濟文化特征,數千年來隨著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在開發的深度和廣度上不斷攀升,但其本質特征并沒有根本改變。如遼河腹地,以東西遼河交匯的遼吉兩省銜接的松遼平原南部,向來就是以農業為主兼營漁牧的農業區,自戰國以來就是“漢郡文化”的傳布地區。東臨以東遼河和渾河、太子河上游為中心的遼東地區,歷史上就是山林、川澤地區。具有“長白山南系”依托山林資源的狩獵、捕撈、采集等經濟特征的文化區,歷史上亦是“穢貊”族系的遼東古代民族的母體(南貊)發源地。而上遼河流域的西部,努魯兒虎山以西,歷史上就是以“游牧”和“群牧”為特征的“草原文化”區,并形成了“燕亳”“東胡”“鮮卑”“契丹”等土著民族文化。遼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的經濟文化區,有一個內在聯系,就是在自然和人文地理上,都是以遼河干流為中脊,連接和帶動兩翼文化的發展。而今遼河下游的鞍山、盤錦、營口等地,更具有遼河平原農業生態的特殊性。
其三,在人文歷史上的遼河文明,是中國北方文明起源的中心。這在進入21世紀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已經被確認,“遼河文明”是與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并列的中華文明起源之一。從遼河下游的“早期智人”營口金牛山人開始,遼河流域就是與北京“周口店猿人”先后發展在黃渤海沿岸的最早的古人類,是東北亞地區人類起源和文明發端的重要地區之一。其后從紅山遼河文化的“古國文明”,到遼西“夏家店下層文化”(我認為應是先秦燕山以北“燕亳”族團)的“方國文明”,直至秦漢以后“漢郡文化”的帝國文明,遼河流域文明有幾千年不間斷的傳承發展。
其四,遼海文化區域在歷史上是北方“長城地帶”和“絲綢之路”的東端,自古為連接東北亞的橋梁和紐帶,在現代仍是東北亞大區域連接黃渤海北岸以及跨國經濟、文化區的東西走廊和重要前沿地帶,因此被列為國家級經濟區。環“長城地帶”南緣在歷史上,已經形成了軍事上的區域障塞區,變成了南北民族文化交融的“文化熔爐”和歷史平臺。而“草原絲綢之路”的東段,已達今遼河上游(以今遼寧朝陽古“龍城”為中心),并東傳朝鮮、日本,這使遼河文明的影響具有世界意義。
其五,遼海文化在社會人文意義上,應具有獨特的“關東文化”的多元人文特色。在歷史上,以遼河流域為中心的東北南部地域文化,依托農業為主形成的具有獨特地域文化的“長城地帶”,匯聚了“漢郡文化”“薩滿文化”“騎射文化”“流人文化”等獨特的關東地域文化,從而使“遼海文化”同黃河文明、長江文明等一樣,毫無置疑地躋身于我國幾大區域文明之林,成為相對獨立的文化區。
其六,遼河文明從其最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形態”上看,雖然其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也有過興衰,但始終地處“長城地帶”以內的沿黃渤海北岸的農業生產區,具有兩翼“長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不可比擬的自然生態優勢。既使歷史上有短期游獵民族進入遼河流域,如晚明時期“建州女真”進入遼海,也在不久實行了“計丁授田”制度。這是不以人(民族)的意志為轉移的深刻的“自然法則”,它決定了“遼河文明區”在以農業為主導的中國歷史上,一直處于“東北亞前沿”的地理、經濟、人文優勢,也是“遼河文明”具有獨立性、先導性、多元性、兼容性的內在動因①參見劉厚生主編《中國長白山文化》第二編,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
三、長白山文化
20世紀中葉隨著“長白山叢書”的出版,長白山文化逐漸為人們所認同。2014年出版的《中國長白山文化》一書,這樣來定義“長白山文化”:“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的、以長白山地區為地理空間范圍,以東夷文化為先導,漸以華夏—漢文化為主體的、東北各民族共同鑄就的,具有鮮明歷史、民族、地域特點的地域文化。”①劉厚生主編:《中國長白山文化》第二編,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第234頁。盡管在對這一文化的認知概念上,可能會有局部的差異。但從其基本文化的定義上看,“長白山地區(或區系)”“東夷(東北夷)文化先導”“華夏(漢)文化為主體”“多元民族內涵”“地域文化”,應當是構成“長白山文化”的基本內涵。筆者以下擬圍繞上述幾個方面,對“長白山文化”進行解讀。
(一)長白山文化的區系地理界定
筆者在解讀“長白山文化”中,之所以用“區系”,而不用“地區”,是因為自然地理概念上的“長白山”及其余脈,存在著不確定性和交叉性;而“區系”作為文化地理概念,可以兼顧山川、民族、疆域等多元涵蓋性,可相對準確地界定其文化覆蓋區。從這一視角界定“長白山文化”,它應是以長白山主峰為地標,以相關山系、水系交織組成的特定文化區。即南含遼東半島千山山脈,北延張廣才嶺東西;東括狼林山脈和蓋馬高原;西至醫巫閭山和大興安嶺以東的松遼分水嶺。在這一“山系”與“水系”并重的地區內,就是“中國長白山文化”的基本文化地理區域。
(二)長白山區系的山系和水系
長白山文化的“山系”分布,上已指出,可分為四個延伸方向。其南支,包括今遼吉兩省交界的龍崗山脈和遼東腹地的千山山脈,基本以東北—西南走向,一直延脈到旅順老鐵山。其北支,應包括張廣才嶺、牡丹嶺和完達山脈,即東流松花江和烏蘇里江之間的縱向山地。其東支,以老嶺以東、今朝鮮半島的狼林山脈和蓋馬高原山地為主干。而其西支,以吉林哈達嶺以北的松遼分水嶺為限,逐漸過渡到松遼平原區。與上述“山系”對應,長白山區系的“水系”,亦由以下幾大水系構成:其南系為“鴨綠江水系”,包括渾江、靉河等水域。其北系為圖們江、烏蘇里江水系,包括牡丹江等水域。其東系,為清川江、大同江水系。其西系(西北)為松花江水系。包括東遼河和伊通河等發源哈達嶺的諸水系。在上述諸“山系”和“水系”中,一個重要的區域特點是“縱橫交錯”,共同交織成“長白山區系”的地域文化格局。
(三)長白山區系的古代民族譜系
長白山區系的古代民族分布和構成,與“山系、水系”相比,是一個具有動態分布的民族譜系。這里介紹的是在漢民族外,在這一區域的土著族團。從東北地區已普遍認同的族系劃分看,主要可分為三系:“穢貊系、肅慎系、沃沮(東穢)系”。如以東、南、西、北的山系和水系的自然分區看,這“三系”的大體分布是:南系:為穢貊族系的“南貊”——包括歷史時期的“高句麗(高夷)”和“青丘”;北系:以縱向張廣才嶺分界;其東屬“肅慎”,其西為“槖離”——包括其后的“靺鞨”和“渤海”等;其東系:為“沃沮”和“東穢”——包括“古朝鮮”等;其西系:為穢貊族系的“北穢”和“夫余”——包括由“槖離”南下松花江中游的遺民。與這一基本族系分布的相關考古學文化考察,是這一區域進入青銅時代以后,人文歷史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
(四)“長白山區系”已發現的重要考古學文化與民族譜系
上述與長白山區系的“族系相關的考古學文化考察”,是“進入青銅時代以后人文歷史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涵蓋三方面含義:其一,考古文化的主述重點是“青銅文化以后”。這主要考慮石器時代以前尚缺乏民族構成的基本因素和社會條件,在考古學和民族學中一般不納入“族系”考察階段。其二,“青銅文化以后”的考古文化的考察也不是無限延長,而是終止在“早期鐵器文化”的兩漢之際。主要是“長白山區系”的民族和考古文化的“奠基期”①劉厚生主編:《中國長白山文化》第二編,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其三,與地域文化分區相比,考古學文化由于受考古發現的階段性、偶然性和認識程度的局限,其界定和譜系的認知更復雜,所以本文對“長白山區系考古學文化”的分區介紹,區別于各類“考古文化類型學”的分布,是以“長白山文化”的自然地理分區“四系”為基礎,從宏觀的考古學與族系對應的角度分析,所持的研究方法是地域文化的方法,而不是考古學的方法。以下試分區簡介:
1.長白山南系
長白山南系的考古文化,如我在《中國長白山文化》“考古編”中所說,指龍岡山脈以南以遼東山地為主的考古文化。②劉厚生主編:《中國長白山文化》第二編,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這一文化的局部分區,是以千山山脈為標志。在千山山脈以南的遼東半島沿海區,早期有營口“金牛山人”等舊石器文化和“小珠山”“后洼”等新石器時代文化;進入青銅時代,則以大連地區為主的“雙坨子文化”為代表。這一地域文化的最大特點,是發生在半島本地的土著文化,但受山東半島的“岳石文化”等影響顯著。從古代遼東半島南部曾屬“海岱曰青州”地域看,這一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文化,可對應為古“青丘文化”。③劉厚生主編:《中國長白山文化》第二編“青丘”條,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第53頁。
在千山山脈以北和龍岡山脈之間的遼東腹地,稱為遼東“二江”(鴨綠江、渾江)和“二河”(太子河、蘇子河)流域的“大石蓋墓文化區”。它是典型的遼東“南貊”土著文化區,漢代以后則是遼東“高句麗文化”起源和早期高句麗“五部”的核心地區。
2.長白山北系
該地區考古文化應以縱向張廣才嶺為界分為東西兩區。其東區牡丹江流域和烏蘇里江以西地區,在進入新石器晚期和青銅時代以后,雖然部族分散、復雜,但其主體文化,當以20世紀60年代發現確認的“鶯歌嶺文化”——“肅慎系”為主的考古文化為主。其文化延續至后來的“挹婁”和盛唐“渤海”時期。在張廣才嶺以西的東流松花江南北,其進入青銅時代以后的代表性考古文化,應是黑龍江省“索離溝文化”,即北夷“槖離國文化”。這一文化遺跡發現較早,但對其文化和性質的較深認識應在進入21世紀以后。
3.長白山東系
這一區域考古文化的分布,多涉及圖們江以東和朝鮮半島北部。在《中國長白山文化》“考古編”中稱為“東穢地區”。其在青銅時代以后實際上的族系問題,還應包括南部的“古朝鮮”和北部“沃沮”等濱日本海地區,故統稱“東穢”。在高句麗《好太王碑文》中或稱“韓穢”④參見耿鐵華《通化師范學院藏好太王碑拓本——紀念好太王碑建立1600年》,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4頁。。這一區域文化,應統屬東北亞“穢貊”文化系統的“北方式支石墓”文化。關于“長白山東系”主要分布于朝鮮半島北部的“支石墓文化”的淵源,韓國考古學家李亨求是這樣總結的:“大凌河流域的積石墓,經遼東半島(石蓋墓)傳到朝鮮半島,在朝鮮半島從新石器時代后期至青銅時期相繼出現……(支石墓)是在渤海沿岸地區發生并發展起來的。”①李亨求:《關于東北亞的石墓文化——以渤海沿岸北部、東臨及朝鮮半島為中心》,《東北亞歷史與考古信息》1995年第1期。應當指出的是,這一文化在具有遼東“石蓋墓文化”影響和東傳因素的同時,亦有日本海沿岸的海洋文化因素。
4.長白山西系
長白山西系的考古文化,在地域上屬于長白山脈向西南和西北兩個方向延伸的張廣才嶺和威虎嶺以西、吉林哈達嶺以北的松花江中游。在進入晚期新石器和青銅時代后,其公認的代表性文化,為20世紀50年代發現確認的“西團山文化”。董學增先生在《西團山文化研究》中,這樣來界定西團山文化的范圍:“東界在張廣才嶺南端威虎嶺以西;西界在伊通河和東遼河流域;南界在輝發河、飲馬河、伊通河上游;北界在拉林河中、上游左岸。”②董學增:《西團山文化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51頁。據20世紀80年代以來,筆者與李健才和王俠等兩次實地調查,夫余先世西團山文化的分布區,在西漢以后,正是以今松花江中游吉林市為中心,以吉林東團山、南城子和龍潭山為核心區域的“夫余”文化中心區。③董學增:《西團山文化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51頁。在吉林市龍潭區的“土城子遺址”等地,明確發現了在“西團山文化”的上層,疊壓著西漢時期的“夫余文化”遺存。所以“西團山文化”在考古學和民族學上,普遍認同為“夫余先世文化”,即歷史文獻中記載的以“鹿山”和“穢城”為中心的“北穢”系統的“夫余王國”④(晉)陳壽:《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夫余》,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41-842頁。。從西團山文化(夫余先世)的北界在拉林河南岸看,在夫余立國以前,確有一支東流松花江的“北夷槖離國”(索離溝文化)部族,南渡拉林河(古掩淲水)進至松花江中游的夫余故地建國。
四、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與上述“遼河文明”和“長白山文化”,在地域和文化形態上對應的東北地域文化之一,是個具有更廣闊覆蓋面的文化區。在中國東北(含東蒙古草原)地區,其基本地域范圍,應接續上述“遼河文化”的西緣,燕山以北、努魯兒虎山以西、至大興安嶺南北,西連貝加爾湖以南的蒙古草原。從整個北方“草原文化區”看,東北區域的草原文化,應屬于其東緣地帶。在燕山和太行山以北一線,基本以歷代的古長城南北為分界,即草原文化區,基本在長城線以北的草原游牧區。由于草原文化橫跨亞歐大陸的廣闊覆蓋面,其文化的傳布和影響亦具有世界意義。
余對“草原文化”的涉獵,起步在21世紀初。由于2002年起參與《中國長白山文化》的編寫。因為全方位審視“長白山文化”,特別是區系考古、民族學,離不開東北亞大陸的另外兩個文明——“遼河文明”和“草原文化”的比較。所以在2004年,應內蒙古社會科學院邀請,參加呼和浩特市首屆“草原文化”學術會議。2006年,應呼倫貝爾市博物館邀請,研討“草原文化”展覽,又考察過近年發現的細石器文化重要遺物——“哈克文化”玉器與陶器。在呼和浩特市的“草原文化”討論會上就“草原文化的三個主要標志”的主題發言,后扼要發表于2005年1月28日的《光明日報》①王綿厚:《論草原文明形成的三個標志》,《光明日報》2005年1月25日理論版。。其后在完成《中國長白山文化》“考古篇”的過程中,又進一步思考了“草原文化”的特質。
其一,從社會生產方式、經濟形態或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草原文化具有三個特征:“群牧業態”的確立、“細石器文化遺產”傳承、“騎射文化傳統”。其二,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神文化層面上,具有“以自然為本”的人文精神。以下擬按這幾個方面對“草原文化”略予闡述。
(一)草原文化的“群牧業態”
我認為,這一經濟形態是“草原文化”確立的基礎,是草原文化有別于“大河文明”孕育的農業文明、山林文化孕育的“漁獵采集”文化的特質。草原文化作為具有世界意義的人類社會文明形態的載體之一,產生和存在的經濟基礎,主要是牧業文明特別是以“群牧”形態為主的生產方式。這種群牧經濟形態也有一個長期發展過程,從最初的狩獵到野生動物的馴養,從個別家畜的馴化、儲養到規模化的“群牧”,最后形成了具有獨立業態形式的生產方式。從中國歷史的發展看,在北方真正形成具有聚落式“草原群牧”的民族文化進程,應至少經歷了三個大的歷史階段:一是開始于戰國、漢魏時期的匈奴、東胡、鮮卑等長城以外草原民族的“帳幕式群牧”,即《三國志》烏丸鮮卑傳所說:“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②(晉)陳壽:《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烏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32頁。二是公元10世紀前后,草原帝國契丹遼王朝,把“帳幕式群牧”上升為國家專門管理的群牧機構,從國家級的“總典群牧司”,到各府州的“群牧林牙司”,把“群牧”的管理納入了國家的根本管理體制。這是“草原文化”從民間生態文化,上升到國家“國體文化”的里程碑。三是舉世公認的蒙元帝國初期。在“草原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的同時,“群牧”作為支撐蒙古汗國興起的最初“國本”生業,得到了空前發展。至此“群牧”經濟形態,可以說發展到了歷史高峰。這種群牧業態的確立和發展,為草原民族從狩獵、采集文明走向蓄牧文明,提供了新的生產手段和智慧。所以從“草原文化”的發展看,契丹族的遼朝和蒙古族的蒙元時期,應是“草原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二)“細石器文化”載體
草原文化在當代考古學上的重要載體和表現形式,是“細石器文化”傳統。包括它的非物質文化形態“巖畫藝術”和“自然崇拜”等。限于“巖畫藝術”和“自然崇拜”的專門性和復雜性,這里只單獨談考古學上“草原文化”本體的“細石器文化傳統”。著名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裴文中先生,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在《中國細石器時代略說》中,對依托“草原文化”的“細石器時代”已有明確界說。盡管對到底存在不存在“細石器時代”,學術界尚有爭論,但歷史上確實存在“細石器文化”,應當是不爭的事實。這種保留著草原文化原生態特征的石器工藝,蘊含著草原文化的多元生態和生產手段的內涵。諸如:以打制、琢制、磨制結合的“細石器工藝”,表現了草原民族對“畜牧經濟”生產加工和狩獵活動的必要手段;而伴隨“細石器”的“復合式”工具,如復合式刮削器、骨角器和弓箭等,也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特征。這其中要特別提到“草原文化”和草原民族的最先進的復合式工具(同時為武器)的弓箭。弓箭的發明,是草原文化和草原射獵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它的發明,連同“騎射文化”,甚至不亞于金屬工具的發明。所以細石器文化傳統和以弓箭代表的“復合式工具”的出現和發展,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巨大影響,應是凸顯“草原文化”歷史地位的重要文化表征之一。應當指出的是,“細石器文化傳統”不僅在“草原文明”中特色突出,而且在人類文明發展中,也對其他文明(如農業文明)發生過影響。如公認的以原始農業為主的、距今7000年前的下遼河流域的沈陽“新樂文化”,其早期“細石器工藝”和工具,亦曾經是其發展的重要階段性特色。
在當代考古學上,進入21世紀的呼倫貝爾“哈克文化”的發現,如我在2005年《光明日報》著文中指出,是草原“細石器文化”的凸起異軍。該文化因首次發現在內蒙古海拉爾市哈克鎮得名,2002年被正式命名為“哈克文化”。這一文化遺址,僅在呼倫貝爾地區已發現300余處。“哈克文化”發現的區域文化意義在于,這一地區自古是歐亞大陸“草原文化”和“草原民族”的核心發源地之一。從秦漢以前的“丁靈”,魏晉南北朝的鮮卑、烏洛侯,隋唐時的“室韋”,到遼金元的契丹、蒙古,均崛起在呼倫貝爾草原南北。所以呼倫貝爾地區這一文化的新發現,應當是“草原文化”特別是“細石器文化”應引起世界矚目的重要發現。筆者2004年在呼倫貝爾博物館原館長趙越陪同下,曾親自考察其出土文物,觀其玉器和陶器,特別是玉器獨具特色。而這一距今6000年以上的“哈克文化”,其細石器和玉器的加工工藝水平,可令同時期的內地新石器文化見拙。由此我認為,應當使人們重新審視北方“草原文化”,特別是“細石器文化”的歷史內涵和歷史地位。
(三)“騎射文化傳統”和馬具的發展
草原文化的另一個突出文化特征是“騎射文化傳統”,這也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課題。在中國北方和東北地區,草原“騎射文化”總是離不開馬具和馬匹馴養,所以筆者在這將騎射文化傳統和馬具的發展一并考察。騎射文化是人類依托“群牧”的經濟形態而產生的“草原文化傳統”。至少從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起,由游獵發展到牧獵的結合,并由此產生了野馬馴養。在東北亞地區,它的起源主要在中國北方。最早的見于文獻是“土方”和“山戎、東胡、匈奴”等部族。如戰國時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即針對北方“胡人”,是戍邊戰略的改革。考古發現證明,東北亞最早的馬具,出現在距今3500年至春秋時期的燕山以北、上遼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東胡族)。考古發現,在其墓葬的骨板上刻有“髠發”的游獵部族形象。在寧城南山根等“東胡人”的墓葬中,發現有最早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車具、馬具等。
從青銅時代開始發展來的馬具和“馬具文化”,是“草原文化”發展進程的又一劃時代進步。馬具連同早期車具的出現,不僅具有新的“生態文化”意義,同時具有“軍事文化”和“交通文化”的意義。①王綿厚、樸文英:《中國東北與東北亞古代交通史》第五章第八節“騎射文化與馬具”,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年。英國著名科技專家懷特曾經說過:“很少有發明像馬蹬那樣簡單,而又很少有發明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者、英國另一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也指出:“(在中國)只有極少數的發明像馬蹬這樣,在歷史上發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響。”這一“催化影響”,改變了草原民族從一般的“游獵文化”生態,發展到對交通、騎兵、騎戰等深刻變革。盡管對馬具、馬蹬的發現,最早在游牧民族還是農耕民族產生,還存有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草原民族是最早接觸和經歷馬具使用和改革的民族。上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史記》匈奴列傳中明確記載“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一個“變俗”,一個“習騎射”。說明當時草原民族的騎射必精于長城內的民族。這就是戰國時期及其以前農耕民族順應和學習草原“騎射文化”的歷史明證。至少證明當時“草原民族”是普遍精于“騎射”的民族。不僅如此,從考古學上看,在中國北方,騎射文化和馬具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應是東晉十六國時期的草原民族的鮮卑“三燕”。
三燕時期是繼先秦兩漢北方東胡、匈奴的“草原文化傳統”,在草原文化和馬具發展的新時期。所以“三燕”的騎射文化和馬具,可稱公元3-4世紀最早使用馬具,并把馬具傳播至朝鮮半島和日本的先行者。①田立坤:《朝陽發現的三燕文化遺物及相關問題》,《文物》1994年第11期。其后又經歷了契丹遼王朝和蒙元時期,草原文化的代表性標志“群牧”和“騎射”均發展到最高峰,“草原文化”也達到了歷史意義上的頂峰。而這一切,均與燕山以北至大興安嶺的東西部的“草原文化區”有著歷史淵源。
(四)以“自然為本”的人文精神
當代“草原文化”最具有現實社會意義的,是它的生態理念——“以自然為本的人文精神”。這一生態理念的產生,不是后社會形態的人文意義上的哲學理念,而是與“草原文化”與生俱來的自然生態長期發展、演化的必然結果。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生成的自然和社會基礎,而草原文化的“以自然為本”的人文精神,更有其獨特性、原生性、永恒性。
所謂獨特性,是指草原民族和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相比,更具有依托自然資源的直接性和依賴性。這是在特定的生活環境中形成的“生態文化”。在世界范圍內,與“農業文明”和“漁獵文明”相比,它更具有連續幾千年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幾乎沒有根本變化的特殊性和穩定性。“草原文明”的連續性,是其生態文明的歷史表征。
所謂原生性,是指草原文化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始終保持著“以原生態為載體”——直接將自然的草場、水、土地、陽光,利用和轉化為畜牧、肉乳、皮毛等生活品。特別是對草場、水、土地的利用,較少農業文明對上述自然資源的改造和破壞。用現代的經濟學說法,可稱原生態經濟。而越是古代這種現象越突出——草原民族的“衣”,以動物的皮毛及其加工的毛織品為主,其物質資源和工藝均具有原生性;草原民族的“食”,以肉、乳和加工品為主,早期并伴隨狩獵和采集;草原民族的“住”,素以“氈帳穹廬”為家,這是傳統草原民族適應游牧和狩獵生活的居行方式;草原民族的“行”,前在“騎射文化傳統”中已經指出,主要是利用馬、牛等及配套的畜力車。
所謂永恒性,是一個既伴隨著現實生活又具有歷史深度,并超出現實生活的文化生態理念,即指草原文化“以自然為本”的人文理念的永恒性。需要指出的是,這里講的“以自然為本”,與一般民族學意義上的“自然崇拜”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指在長期社會實踐中,人類自覺或不自覺產生的對自然的“理性尊重”;后者“崇拜”則是多在對自然無知或朦朧中的“宗教盲從”。在當今世界上,應有兩種不因意識形態差別和社會制度不同而存在的“永恒理念”,即“以人為本”和“以自然為本”,這是兩個具有自然和人文雙重價值的社會價值觀和哲學觀。但這一生態理論,本身就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理論問題,不可能在這篇討論地域文化的文章中盡述。所以,最后筆者只想指出,由“草原文化”及其衍生出來的“以自然為本”的人文精神的“永恒價值”,具有深刻的當代社會文化意義。
G127
A
2096-434X(2017)01-0011-10
王綿厚,遼寧省博物館研究員,研究方向:東北歷史、考古與文物;遼寧,沈陽,110167。
劉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