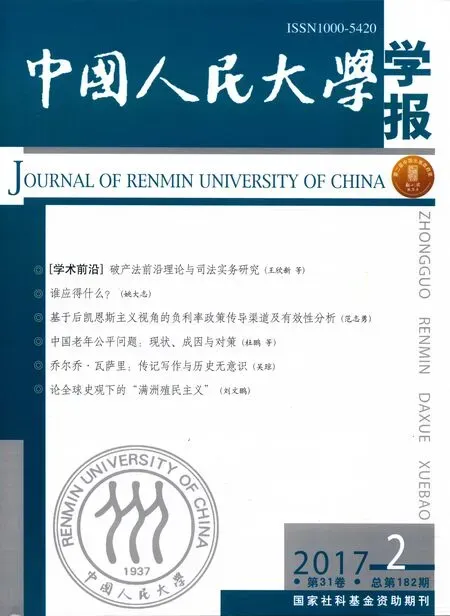論公司債權人的體系保護
許德風
論公司債權人的體系保護
許德風
公司債權人首先享有其他個人債權人所能獲得的全部法律保護。除此以外,公司法上還有很多特殊規則圍繞保護公司債權人這一任務展開,如注冊資本制度、出資及資本維持制度、董事高管對債權人的責任制度、股東對債權人的連帶責任制度(刺破公司面紗)等。在理解這些制度時,一個體系化的思考框架至為重要。事實上,在上述公司法規則之外,合同、侵權和破產制度也承擔著重要的債權人保護功能,在對公司法上的傳統規則進行規劃與解釋時,須認真對待這些相互關聯的制度安排。
公司債權人保護;侵權法保護;刺破公司面紗;公司資本;資本維持原則
目前,盡管作為私法基礎的民法是商法中相關制度的重要參照,但對民法規則是否適合被用于商法(尤其是公司法)爭議的解決,很多學者持謹慎的態度。*我國有學者批評現行立法及司法實踐過度強調用民法的思維處理公司法問題。以《公司法司法解釋三》(法釋[2014]2號)為例,其主要的問題在于該理論來源上的錯誤,進而導致其“恪守僵化的法定資本制,用靜態集合財產的觀念去對待公司,從股東出資的角度去界定股東和公司的關系,用物權方法去界定股東間的財產共有關系,用集合財產作為擔保去向債權人提供保護”。參見鄧峰:《物權式的股東間糾紛解決方案》,載《法律科學》2015(1)。還有學者指出,在公司股權轉讓的問題上僅適用民法的一般財產轉讓規則是不夠的,這樣做“忽視了股權和股權轉讓的團體法特性……將股權轉讓視為轉讓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公司只是股權轉讓的效果承受者,而失去了主動干預股權轉讓的能力,不僅無法反映公司介入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也無法說明股權轉讓關系的復合性”。參見葉林:《公司在股權轉讓中的法律地位》,載《當代法學》,2013(2)。無獨有偶,德國也有學者反對過度擴張民法的適用范圍。Grigoleit.Gesellschafterhaftung für interne Einflussnahme im Recht der GmbH.München: C.H.Beck, 2006, S.203.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一百余年來,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與經濟的全球化,公司法經歷了重大變遷,而民法總體上仍沿襲著羅馬法的基本原理,其能否滿足解決具有特殊性的公司法爭議的需求值得商榷。以侵權法在公司債權人保護中的作用為例,相比公司法上的細致規則,侵權法通常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一般條款”的方式,要件模糊[1](P1014-1015)且缺乏可預見性[2](P174-175),故不適合作為公司債權人保護的依據。這一觀點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民法規范和商法/公司法的內在關聯及民法本身的演進及發展。
從成本收益的角度觀察,公司這一法律形式的功能在于降低獲取資本、勞動力、原材料及消費者等要素的市場交易成本。*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如果一個企業完全由與其沒有任何業務往來的人所有,則該企業所有涉及投入產出的交易都要通過市場合約來完成。這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在實踐中卻可能導致無效率的結果。”亨利·漢斯曼:《企業所有權論》,27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實現這一功能的內在機制則是公司通過法律所確立的在組織、人格、財產及責任方面的獨立性及相關制度。但是,與物質世界的建筑不同,法律“架構”的有效性,要么系于當事人的守約,要么系于違約或侵權時執法的強制力及其他外部監管,因此,在分析討論有關公司法問題時,不能將其孤立起來而忽略其他相關的制度。具體而言,除了公司資本制度外,(有調節能力的合同)債權人還可通過利息、擔保等制度安排尋求保護(公司債權人的合同保護),可通過侵權法主張公司股東及董事高管等實際運營者承擔責任(公司債權人的侵權法保護),也可通過破產法的制度安排實現債務人財產的統一管理與債權的統一清償(公司債權人破產法保護)。另外,從公司法的發展歷史來看,人們從公司制度存在之初就意識到以補償損害為中心的民事責任的局限,并就濫用公司形式的問題規定了周全的刑法規范(公司債權人的刑法保護)。
公司債權人的法律保護應通過一套相互協作的制度體系來實現。在這一過程中,公司法固然要發揮作用,但其他法律,包括合同法、侵權法乃至刑法,也都有發揮作用的空間。實際上,相當多寫在公司法中的債權人保護規范在性質上并不屬于公司法,不過是民法(合同、侵權)、行政法和刑法的規定而已,或者即便被定性為公司法上的特殊規定,其法理基礎也依然植根于其他法律部門。在這一背景下,體系化的分析有助于澄清公司債權人保護的內在原理,同時使具體的債權人保護制度各得其所,與各自的制度本源建立起聯系,最終促成法律的體系化與科學化。只有了解這些制度間的相互關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每一項具體制度的運轉機制及其邊界;只有整體看待這些制度,才能讓每一項制度的定位更為精準。以下從私法層面討論公司債權人的體系保護問題。
一、公司債權人的合同保護
借債(債權融資)和發行股票(股權融資)是公司獲取資本的兩種基本形式。對于有調節能力的債權人[3](P124)[4](P52)而言,利息、債的擔保、債的保全(代位權與撤銷權)等合同安排或合同救濟都是可用于自我保護的制度:利息的保險功能有助于分散債權人所面臨的個別債務人破產的風險;擔保可確保債權(在債務人破產時)的優先受償,降低債權的實現成本與執行成本;代位權、撤銷權等債的保全措施則可以在破產程序之外保障債權的實現。*如果把公司的本質看做是合同束,則債權人也是這個合同體系中的一類重要成員,包括銀行、公司職工、供貨商等等。在這種情境下,若可以通過合同規則保護債權人,則無須公司法介入。Armen Alchian et al.“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62).除此之外,債權人還可以通過控制債務人實現自我保護,如在銀行借貸和債券市場中普遍應用的“限制性條款”(covenants)。運用這些限制性條款,債權人可以控制債務人企業的財務政策、管理策略、股利發放和進一步負債等事項,并在企業違反這些條款時提前終止合同,收取債權。[5]
當然,并不能因為存在公司債權人的合同保護,便完全將保護債權人的“責任”推給債權人自己。的確,任何債權人在與公司交易時都應預見到公司因破產而不能償債的可能性,但這種預期的前提是公司合理地使用了有關借款而未從事投機或其他轉移財產行為。然而,在長期而復雜的公司經營實踐中,這一前提常常被破壞。如股東本應如實繳納出資而未能履行該義務,又如股東侵占公司財產(或將個人的侵占和浪費包裝成公司的正常虧損)而獲得非法利益。股東從事上述行為的動因,一方面在于借款合同雙方存在“委托—代理”式的利益沖突,另一方面也在于有限責任制度在技術上對股東個人責任的阻隔。*如果不對股東的這些行為進行限制,會產生對各方均不利的后果:投資者不敢向公司放貸,公司經營者無法獲得債權融資,社會經濟的整體活力降低。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律保護公司債權人,一方面是出于正義理念,另一方面也是社會經濟有效率發展的客觀需要。Hertig et al.“Creditor Protection”. In R.Kraakman et.al.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A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Apporac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71-99.也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現實中并不存在100%債權融資的公司。[6](P192)在這個意義上,在合同法之外規定強制性的公司債權人保護規則,有助于約束股東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債權人和股東之間的“委托—代理”成本,彌補公司債權人合同保護制度的不足:其一,某些債權人與公司所進行的交易規模太小,額外進行協商的成本與收益不成比例。其二,某些債權人太“幼稚”,缺乏必要的協商能力或協商經驗;某些債權人甚至對債權的發生與否都完全沒有選擇的余地。[7]其三,在公司有多個債權人時,會出現所謂“搭便車”的現象:大家都沒有動力去推動與債務人達成那些有利于所有債權人的條款,如強制要求債務人公開必要信息的條款或者登記/披露某些大宗公司債權的條款。[8]下文所述的關于公司資本制度的法律規定,便是此類規則。
二、保護債權人的公司資本制度
法律上,債權人與股東之間顯然并無直接關聯:債權人不過是和公司進行交易,而股東只是公司的成員,并未與債權人訂立合同。不過,鑒于公司不過是擬制而成的法律實體,在一些特殊場合,有必要透過交易形式來探究其實質。對這一問題,本文持如下觀點:債權融資不過是企業所有者融資的方式之一,雖然在法律上、交易形式上體現為債權人將有關款項出借給公司,但其經濟實質還是出借給企業所有者,在債權人與所有者的關系上,除了借款合同條款以外,還包括與有限責任有關的“交易”內容。具體而言,有限責任可以被理解為是企業所有者與債權人之間的(默示)合同約定,債權人“自愿”放棄要求企業所有者承擔相應債務的權利,“賦予”股東有限責任保護;股東則承諾遵守公司資本制度,放棄(企業清算時的)優先受償權,確保個人財產與公司財產的區分,維護公司財產的獨立性,即所謂“分離原則”(Trennungsprinzip)。股東任何背離公司資本制度的行為都構成對債權人的“違約”,也足以正當化債權人對股東的直接追責。*“商法起源于無限責任,除非法律有特別的規定。因此,當事人在享有有限責任的同時,必須同時付出相應的代價,遵守有關的資本管制規則。”BGHZ 117, 323, 331 = BGH WM 1992, 870; BGH WM 2003, 348 (349); Wiedemann, Gesellschaftsrecht I, 1980, S.515; BGHZ 142, 315, 319, 322 = BGH WM 1999, 2071.換言之,如實出資原則(Grundsatz der realen Kapitalaufbringgung)和資本維持原則(Grundsatz der Kapitalerhaltung)[9]是股東享有有限責任的“對價”。*“Permitting individuals to organize their enterprise as distinct legal entities, thereby separating assets devoted to particular businesses from the shareholders’ personal assets or assets devoted to other business, and shielding these personal or other business assets from the risk of the enterprise.” “The separate personality of the corporation will be disregarded or the corporate veil pierced whenever the separateness of the corporate form is employed to evade an existing obligation, circumvent a statute, perpetrate fraud or crime or generally commit an injustice or gain an unfair advantage.” O’Neal and Thompson’s Close Corporation and LLCs, Volume 1, § 1:11.高旭軍:《論“公司人格否認制度”中之“法人人格否認”》,載《比較法研究》,2012(6)。類似地,英國Rickford報告中將保護債權人看做是對公司享有有限責任的“合理平衡或協調分配的問題”(a question of reasonable balance, or proportionality),在論理上也是基于一種公平或常識的觀念。“Rickford Report”. European Business Law Review, 2004(15):919-967.
對于出資制度,與1993年和2005年的《公司法》相比,2014年《公司法》進行了重大調整,采“認繳登記制”:公司發起人或創始股東可以自由設定出資額、出資期限、出資比例,在認繳(而非實繳)全部出資后即可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設立公司,并取消了法定最低注冊資本的要求。這一改革的目的在于放松管制、促進創業[10](P51),同時也暗合了世界公司法放松注冊資本管制的潮流。[11]對于這一寬松的注冊資本制度,有學者擔憂公司債權人保護的問題。[12](P509-510)本文認為,如果能準確、嚴格適用既有的法律規范,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一方面,我國《企業破產法》第35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債務人的出資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資義務的,管理人應當要求該出資人繳納所認繳的出資,而不受出資期限的限制;另一方面,若將《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3條的規定(股東在未出資本息范圍內對公司債務不能清償的部分承擔補充責任)理解為不要求履行期限屆至,則對公司債權人的保護很可能是加強了。[13](P35)
對于資本維持制度,《公司法》第36條以及此后的《公司法司法解釋三》規定了以限制“抽逃出資”為中心的具體規則。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抽逃出資”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概念,其既包括股東侵奪公司財產的行為,也包括公司向股東輸送利益而使股本受侵蝕的行為。[14][15][16]具體而言,依據《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2條的規定和學者的總結,“抽逃出資”是一種源自股東視角的概念(股東為主體,公司為相對方或客體),包括減少公司資產和增加公司負債兩種形式,有直接抽逃和間接抽逃兩種類型。直接抽逃多指“賬實不符”,如公司賬面記載不完全或公司捏造債權掩蓋股東抽逃出資的事實(第2項規定的“通過虛構債權債務關系將其出資轉出”);而間接抽逃則借助股東與公司間商業交易來實現公司向股東返還出資的效果(第3項規定的“利用關聯交易將出資轉出”)。[17]如果從公司的視角看待抽逃出資(公司為主體,股東為相對方),抽逃出資也可以理解為是導致公司財產無對價流向股東的一種“分配”。[18]
對于“抽逃出資”的定性,較有影響力的觀點認為,“侵權責任路徑已經失去了法理基礎與現實支撐”。理由是“侵權責任作為民事責任的基本類型之一,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在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所應承擔的具體責任形式可能是不同的,這些由專門立法規定的民事責任與侵權責任法之間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應優先適用”。[19](P190-192)這是值得商榷的。從文義上看,《公司法司法解釋三》恰恰是有意回避了對債權人追究股東抽逃出資責任的定性。退一步講,將規則定性為“公司法的專門規定”僅僅是第一步,只有將其與私法的其他規范相對接,該規則才真正與既有的法教義學建立起關聯,進而獲得更強的解釋力和確定性。
三、公司債權人的侵權法保護
通說認為,在以下情況中,公司(在股東、董事高管控制之下)從事不當行為,進而損害債權人利益的可能性較大,此時法律強行規定債權人保護制度的收益通常要大于其成本:其一,公司接近破產時,此時股東更容易選擇無效率的投資(主要是高風險的投機性項目)或者更有動力非法轉移公司財產;其二,債務人是從屬于某個公司集團的子公司時,因受到總公司的直接控制,在經營和財務上缺乏獨立性,更容易從事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行為;其三,債權人是非自愿債權人時,此類債權人完全沒有選擇權,更容易受到損害。[20](P52-60)
針對上述情形,各國通常都在公司法或相關法律(如破產法)中制定保護債權人的特殊規則,既包括特定的行為規范,也包括具體的事后救濟規則。前者如公司董事高管在公司陷入困境時的破產申請義務制度[21],公司在破產前特定時間內不得無償轉移財產或偏頗清償個別債權人的制度(我國《破產法》第31條、32條);后者主要是在已經造成債權人的損害時,債權人如何尋求救濟的制度。對此,在比較法上,侵權法的適用并未被簡單地排除。以下結合德國法及我國現行法對相關制度的解釋與選擇做出分析。
(一)類推適用公司法上的實質合并規則
就公司債權人保護的機制選擇而言,德國1993年裁判的TBB案(BGH NJW 1993, 1200)非常具有典型性:被告與其妻子是A有限責任公司(GmbH)的股東,同時也是B兩合公司(KG)的無限責任股東。被告的妻子同時還是TBB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被告是以上三家公司的執行董事即“經營人”(Gesch?ftsführer)。因經營不善,所有三家公司都陷入破產境地,其中前兩家先后于1986年、1987年被注銷。原告對TBB等公司享有總額為166 000馬克的債權,但因TBB公司的資產幾近為零,故要求被告以個人財產承擔責任。本案中的焦點問題是:原告與TBB公司訂有合同,但TBB公司的唯一股東是被告的妻子,而原告不僅要求TBB公司及其股東承擔責任,也試圖要求公司經營人及其所控制的其他公司共同承擔責任。原告的主張在公平觀念下雖然不無道理,但從公司法理上看,被告并不是TBB公司的股東,要求其個人及其所控股的其他公司承擔責任顯然超越了傳統“穿透”制度的適用范圍(足見德國法對該制度的保守態度,未考慮諸如“反向刺破”的可能性)。于是,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其判決中認為原告的損害雖應給予救濟,但在具體規則上選擇了類推適用的解釋路徑:在企業以公司集團的形式運作時,實際控制人最終利益的實現并不取決于個別子公司的收益,而是公司集團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個別子公司的利益有可能被忽視或被放棄。基于此種考慮,德國《股份公司法》(AktG)第302條、303條規定,母公司在行使其控制與管理公司集團的權力時,應對子公司的利益給予關注,并對給子公司造成的損害負責。類比這一規范,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推理認為:自然人控股多家公司與公司控股多家公司的情形并無本質區別,當某一自然人同時控制多家公司時,完全可能為了其個人的最大利益而在不同公司間進行取舍,因此,可以類比適用上述規定。在本案中,被告及其妻子作為一個整體客觀上共同控制了多家公司,因此,應共同對利用子公司給債權人造成的損失負責。
在本案中,如何證明TBB公司被被告所控制并因此損害了公司債權人的利益,是原告訴訟請求能夠被支持的關鍵。原告提出了這樣一項證據:被告曾以其所控制的其中一家公司的名義向銀行借款,在借款合同中約定,各公司均對該筆借款的償還承擔連帶責任,并同時在TBB公司的機器設備等動產、應收賬款等債權上為該銀行設定了擔保。對此,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即使有上述這些行為,如果TBB公司的利益在這些安排下并未遭受損害,也仍不足以要求被告及其控股的公司向TBB公司的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而且,即使被告及其所控股的公司應當向TBB的債權人承擔責任,如果TBB與被告及其他公司之間的資金往來有清晰明了的會計記載,原告也不應整體性地要求被告及其所控股的公司承擔連帶責任。從本案的現有證據來看,被告公司集團內部并無清晰的財務記載,因此,要求其承擔整體性的連帶責任是合理的。至于責任的具體范圍,原則上應當由原告舉證,但是,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強調(BGHZ 122,123):“不應忽視的是,對于外部債權人而言,其通常無法準確了解公司集團內部的運作情況,要求其就公司應當承擔的責任提供全面的證據是非常苛刻的,因此,應減輕其舉證責任上的負擔。在原告提出請求后,如果被告確實了解有關的事實并且舉證對其而言不構成過分的負擔,應該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被告無法滿足該項舉證責任的要求,則應在原告請求的范圍內賠償原告的損失。”[22](P11)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本案中原告符合該項原則的要求,而被告能否完成證明責任仍是有待查明的問題,因此將該案發回前審法院重新審理。此案的裁判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肯定,有學者對該案評論說,在涉及有限責任公司的法律關系中,適用德國《股份公司法》第302條、303條關于公司集團的規定是合理的。另外,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要求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公司承擔整體性責任的前提是集團內部缺乏清晰具體的資金往來記錄,也讓公司集團責任不至于過分擴張。[23](P1204-1205)比較而言,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導案例15(徐工集團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訴成都川交工貿有限責任公司等買賣合同糾紛案)的裁判思路與本案相似。
(二)內部責任與外部責任
在此后的KBV案(BGHZ 151, 181)中,原告是K公司的債權人,被告有三位,分別是K公司的兩位股東甲(持有40%的股份)、乙(持有60%的股份)以及股東甲所控股的公司丙。原告對K公司享有8萬馬克的債權,在原告主張權利時,K公司陷入不能履行債務的境地,原告根據缺席判決進行強制執行,未果。后K公司進入破產程序,但破產程序因破產財產不足以清償破產費用而被終止。經查,在K公司進入破產程序前,曾將價值21.5萬馬克的存貨和價值99萬馬克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丙,丙為此承擔了K公司82.3萬馬克的債務,而原告的債務不在該范圍之內。在該交易中,K公司的代表人為甲,丙公司的代表人為乙。
在這個案件中,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債權人獲得救濟的基礎有兩個。其一,內部責任,即股東行為減損公司財產,毀滅公司之存在,成立“毀滅公司責任”。其二,外部責任,即鑒于股東計劃性地造成了債務人一般財產的減少,損害了債權人利益(純粹經濟損失),構成基于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而損害他人的侵權責任(BGH NJW 2002, 3024, 3025)。就本案而言,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論證是,從現有證據看,兩位被告的確從事了有計劃地從公司中轉移財產的行為,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正如被告乙的陳述——甲是主要的執行者,但乙作為持有多數股份的股東,有糾正和阻止甲從事此種行為的義務,而其對此持放任的態度,違背善良風俗和故意這兩個要素都難謂不成立(BGH NJW 2002, 3024, 3026)。這是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在這類案件中提及適用《民法典》第826條保護債權人的可能性,即允許債權人直接向股東或公司董事提起訴訟。當然,鑒于案件還有一些事實問題未被澄清,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未在裁判中做出選擇。
正如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的權衡中所觸及的,在相當長時間內,內部責任與外部責任一直是公司債權人保護制度構建中的困難選擇。兩者在保護債權人的效果上或許類似,但在制度理念上有重大差異。關于內部責任,英國法上的相關規定可為一例。根據英國1986年《破產法》的規定,在企業蓄意欺詐而進行交易時,相關的管理人員要負損害賠償責任。具體而言,“在對公司進行清算的過程中,如果發現公司的任何一項交易是帶有蓄意違約的目的(with intent to default),或為了任何欺詐目的,經清算人申請,在認為合適的情況下,法院可以要求以前述方式進行交易的任何知情人對公司做出充實資產的支付”[24](P95)。與此后確立的不當交易[25](P369)制度類似,在法律后果上,如果董事從事了不當交易或欺詐交易,則應負補充公司資產的責任(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any’s assets)。與此種內部責任不同,在董事高管違反德國《破產法》第15a條所確立的破產申請義務時,將構成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2款所稱的因“違反保護性法律”而產生的侵權行為,即德國《破產法》第15a條所保護的債權人可以對董事高管提起侵權損害賠償之訴。這是一種外部責任安排。概言之,內部責任將其規范的邏輯建立在董事高管與公司之間的關系上,即這是董事高管對公司而不是對債權人所承擔的責任,在理論上仍堅持公司的獨立人格,堅持由公司而不是債權人向有關董事主張損害賠償。而外部責任則“穿透”了債權人與公司內部經營管理人員之間的隔離,賦予債權人請求直接救濟的權利。
(三)毀滅公司責任
就公司債權人保護問題,真正確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外部責任立場的是在Trihotel案中的裁判。在該案中,原告是A有限責任公司的破產管理人,被告是該公司的股東。原告認為被告的一系列經營管理行為導致了公司的毀滅(公司最后僅存55歐元的資產),要求賠償總額約714 000歐元的損失。A公司成立于1991年,當時的注冊資本是30萬馬克。1993年9月1日,A公司與被告簽訂了長期土地租賃合同(Pachtvertrag)。此時,被告持有公司52%的股份,其妻子持有公司48%的股份,直到1999年以前,被告是公司唯一的執行董事即經營人,另一股東即其妻子于1996年給予他總括的代理授權。1996年,被告的母親取得了控股公司J有限責任公司的全部股權,同時任命被告為J公司的唯一執行董事即經營人。被告此后又收回了長期出租給A公司的土地,利用自己或其母親成立的J公司和W公司,與A公司簽訂了酒店管理合同(簽約時兩家公司都由被告代理),約定了高額管理費。至1998年度結束時,A公司有累計25萬馬克的虧損。1999年,A公司虧損67萬馬克。后來A公司于2000年4月25日提出破產申請并于5月15日被啟動破產程序。本案一審判決被告對公司的損失承擔個人責任,二審判決駁回了被告的上訴。三審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經過審理支持了被告的上訴主張,并將案件發回二審法院重組合議庭審理。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首先承認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第30條、31條在保護債權人利益方面存在漏洞,僅限于要求股東如實出資或返還其所撤回的出資(“維持股本所必要的公司財產,不得支付給股東”,“違背該規定給付的款項須歸還給公司”),該規則在內容上與我國《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3條第2款類似,認為對于因撤回出資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而造成的公司財產損失以及進而造成的債權人的損失,《有限責任公司法》并未提供任何救濟,因此,有必要確立一項新制度以保護債權人的相應權利。在權衡了公司法規范與民法上的其他制度后,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用侵權法上的相關規則(《民法典》第826條)進行調整在法理上更為合適。
總的來看,2007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Trihotel一案中論證了“毀滅公司責任”(Existenzvernichtungshaftung)的法理基礎,用侵權法的相關規范為公司債權人提供救濟,結束了多年來在外部責任與內部責任之間取舍不定的狀態,明晰了公司債權人保護的法律體系。這項制度強調公司的股東因毀滅公司的行為致公司破產時,應當對公司(而不是直接對公司的債權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在請求權的基礎上,重新回到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上;在規則的理念上,尊重了既有法律制度與教義框架,避免過分擴張的“刺破公司面紗”責任破壞有限責任制度的基礎,使有限責任公司徹底喪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德國法上的這項安排,沒有采用英美法上的刺破公司面紗責任的單一救濟方式,在教義基礎上相當牢固,具有良好的可預見性,同時也維護了有限責任的基本制度價值。
(四)毀滅責任的構成要件
根據學者的總結,毀滅公司責任在構成上應滿足以下要件:
在行為要件上,公司的股東應從事了侵奪公司財產的行為,并導致或加速了公司的破產,如忽視對公司償債能力的維持、追求與公司經營無關的目的、損害公司用于償債之必要財產的價值、從公司中攫取現金流或侵奪公司機會等。在此,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特別強調,責任的構成無須股東從其侵權行為中直接獲益(BGH NJW 2007, 2689, 2691)。但是,經理人的經營管理失誤,如忽視或放棄特定的贏利機會,并不構成毀滅公司的行為,因為這種管理失誤并不是追求與公司經營無關的目的,這使得毀滅公司責任與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第43條第2款規定的經理人責任區別開來。此外,該責任類型與出資不足時股東的補繳責任也是不同的,后者仍可通過第30條、31條救濟。
在主觀構成要件上,股東毀滅公司須出于故意,即在行為時明知公司的財產會因其行為或附和投票而遭受損害。根據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分庭的意見,對于該故意,權利人無須直接加以證明,而只需證明有能夠反映該故意客觀存在的事實即可,如股東應當了解有關行為將導致對債權人的持續性損害而仍然繼續行為或放棄減少損害的措施。總體而言,在毀滅公司責任被長期的司法實踐類型化以后,學界所擔心的故意難以被證明的問題在實踐中并不突出。[26](P492)在Trihotel案件中,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假如在長期土地租賃合同解除的同時,股東對A公司進行了適當的補償,便不應認為構成毀滅公司的行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這里特別強調,不能認為任何沒有對價的行為都會導致毀滅公司責任。在確定是否存在毀滅公司的行為時,法官的任務并不在于判斷某一經營行為是否妥當(即通過商業判斷規則加以檢驗),而主要在于判斷某一行為是否超出了公司經營管理所必要的限度。另外,毀滅公司行為是違反商業判斷規則中較為嚴重的類型,若某一行為不違反商業判斷規則,通常也就不會構成毀滅公司的行為。
就否定要件而言,毀滅公司責任的成立要求有關損害無法通過適用《有限責任公司法》第30條、31條關于公司資本保護的規定獲得補償(BGH NZG 2005, 177)。也就是說,毀滅公司責任只是這些規定的有益補充,并非用來取代這些規則。
毀滅公司行為的直接受害人是公司本身,因此,應由公司而不是債權人提出相應的救濟請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毀滅公司行為所引發的是前文所述的內部責任。也就是說,債權人無法直接對股東提起毀滅公司責任之訴。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這樣的安排并不會對債權人的利益造成本質上的影響,因為在適用毀滅公司責任時,公司通常都已陷入破產境地,破產管理人雖然名義上是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對股東提起訴訟,但因其在客觀上主要代表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因而債權人的利益仍然可以得到充分保障。當然,在公司資產不足以清償破產費用而導致無法開始破產程序時,債權人還可以通過訴訟取得強制執行的名義,進而取得代替公司起訴公司股東與經理人的資格代位權。[27]鑒于現行法上對公司現有資產不足以至于無法支付破產費用的情形還有關于(債權人乃至破產管理人)墊付破產費用的規定,因此,若破產法制度能夠周全地與公司法共同作用,將不存在明顯的債權人保護不足的問題。[28](P906)
最后,在舉證責任問題上,雖然對于是否實行舉證責任轉移,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仍未最終下定論,但是從證據規則上看,只要破產管理人證明股東有毀滅公司的行為和公司陷入破產的情形即可,至于其間的因果關系,則應由掌握更多信息的公司經營者或股東承擔舉證責任。*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GH NJW 1999, 2887, 2888)駁回了前審法院的裁判意見并將案件發回前審法院的另一個民事分庭重新審理,提出了以下三項理由:首先,在借款和讓與擔保的過程中,僅僅借款合同的簽訂和讓與擔保的設定并不必然導致公司陷入破產的境地,因為讓與擔保權可能并未被行使,公司仍可繼續使用有關擔保物。當然,擔保可能會導致公司借款能力的下降,但是對于有限責任公司而言,這種借款能力的降低造成多少損害也是很難證明的。本案中,A公司在設置了讓與擔保后,仍然通過股東保證的方式獲得了借款,可以證明該讓與擔保并未達到毀滅公司的程度。其次,前審法院認為提前解除長期土地租賃合同構成了毀滅公司的行為,也是錯誤的。該合同本來也應于8月31日到期,提前5個月并不會對公司造成毀滅性的損害。即便在終止了土地租賃合同以后,A公司仍然在該土地上繼續經營活動,其經營基礎并未受到該合同的影響被剝奪。第三,在最高法院看來,如果該管理費過高的話,本案中的管理合同可能對公司利益帶來毀滅性的侵害。但是,前審法院并未提出程序法上毫無爭議的證據——有權威性的專家意見。因此,最高法院決定將該案發回重審,要求二審法院進一步查明有關事實,確定有關管理費在多大程度上超出了正常的范圍和導致了公司的破產。
(五)侵權法與公司法關系的一般法理
以上的分析表明,從Trihotel案開始,德國法院正式開始運用侵權責任來處理(部分類型的)公司債權人保護問題。不過,這種做法也還是難以跳出構成要件模糊的困境。那么,為什么會選擇適用侵權法來解決問題?或許是覺得既然公司法的論理也不過是模糊權衡,索性不如直接適用模糊推理制度之王——侵權法上的一般條款?但侵權法與公司法相比有何優勢?從德國的情況來看,法官和支持適用侵權法解決公司法問題的學者從來沒有試圖用侵權法取代公司法。在他們看來,侵權法的規范,尤其是一般條款色彩最為濃厚的第826條,主要被用作公司法特別規則的補充,被作為“兜底條款”,在公司法規則欠缺或不完全時,為當事人提供救濟。[29](P302-303)[30](P26)實際上,在人們將公司法標識為“特別法”的同時,就不得不接受這樣的判斷:越是具體的規范,其調整范圍越是有限,越可能不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相對靈活的侵權法“一般條款”恰恰具有在具體規則不充分情況下彌補現行法不足的功能。
以侵權法還是公司法解決債權人保護問題,在具體性或可預見性上并無差異。但用侵權法保護債權人,有一些其他制度無法替代的好處。其一,維護了公司法的體系完整。任何保護債權人的制度都是有成本的:若公司法自身的債權人保護制度過于復雜,會損害公司法的清晰性及其保護股東的效率,降低公司這種投資形式的吸引力。與“毀滅公司”侵權責任不同,“刺破公司面紗”或“穿透責任”制度意味著股東要對公司債權人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很可能失之過嚴,而侵權責任強調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聯,強調責任與損害的相當性,故可以更好地確定責任的范圍,維護公司制度,尤其是有限責任制度的可預期性。其二,為股東、董事高管等公司經營者提供了明確而簡明的指引。無論采取怎樣的形式,只要是通過濫用公司的組織形式造成債權人損害的,均要承擔相應責任。
四、公司債權人的破產法保護
從文義上看,“公司債權人的保護”所關注的主要是要求債權的受益人(相對人)承擔義務,包括直接受益人公司,也包括其他間接的、經濟意義上的受益人(如股東、董事高管等主體),以實現債權的受償。相比較而言,破產法所“針對”的并不是交易相對人,而是其他債權人。這也意味著破產法債權人保護機制的重心更多地在于利益趨同的多方協調,而不在于利益對立的雙邊博弈。破產法對“集體清償”和“平等保護”原則的強調,就產生于這一背景之下。
(一)從股東控制到債權人控制的轉換
債權的實現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需要債權人主張權利及債務人的配合履行。若債務人不認可債權人的主張,債權人還需要提起訴訟并憑生效判決申請強制執行。這一過程短則數月,長可經年,并且在整個過程中,債務人都掌握著有關財產的控制權,債權人除了要承擔債權得不到裁判支持的風險外,還要承受債務人財產變動的風險。比較而言,破產則是在肯定債務人存在破產原因后,先指定破產管理人接管或監督(在債務人自我管理的情況下)債務人的財產,之后再確定債權的具體數額與財產的變現方式及分配安排。其與債權實現一般過程的一個關鍵差別,便是財產控制權的移轉:法院做出破產開始裁定的時點(有些國家甚至是當事人提出申請的時點),是股東在法律上喪失控制權,管理人(主要代表債權人利益,同時兼顧股東利益)取得控制權的轉換時點。盡管控制權的轉換并不意味著財產權的變動,但與債權人相比,就債務人企業的財產,股東原本便處于后順位,在控制權轉換之后,股東財產權的實現自然也要受到限制。
(二)交易的撤銷與組織的撤銷
破產法強調債權人的整體保護,但其制度設計與公司法上的組織安排仍有所不同。以破產撤銷為例,其與公司法上其他的債權人保護制度如“刺破公司面紗”和“實質合并”(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等的區別是:前者強調通過撤銷權的行使,制約債務人個別的危害債權行為而維持債務人的責任財產;“刺破公司面紗”則是將債務人(公司)與其股東的財產視為一體;“實質合并”是將債務人與其股東(母公司)及其股東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商事組織的財產視為一體,將公司、股東、股東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之間全部的財產移轉乃至整個組織“一攬子”地“撤銷”。*在一些國家(如美國)的破產法理論中,也將“刺破面紗”與實質合并等制度納入到破產撤銷制度(欺詐性轉讓)之中。比較而言,破產撤銷所影響的仍是單項交易的效力,而“刺破公司面紗”與實質合并則產生組織法上的效果。另外,破產撤銷的潛在對象及于債務人所有的交易當事人,而公司法上的債權人保護制度所涉及的主體范圍則限制在公司股東、實際控制人、公司股東所控制的其他公司等特定的交易主體上。
(三)債權統一行使
“債權統一行使”也充分體現了破產中債權平等與集體清償的特征。破產程序開始后,對于本應由破產債務人向第三人主張的債權,交由破產管理人行使也較為妥當。首先,破產管理人可代表全體債權人的利益,由其行使債權有助于避免債權人之間的協調難題,如個別債權人可能在針對第三人的代位權訴訟中采取妥協政策,寬待第三人而損害破產債務人即全體債權人的利益。其次,由破產管理人統一行使債務人對第三人的債權,有助于保障債權人平等受償,避免個別清償,如向債務人的債務人請求返還財產,或要求股東補繳出資或返還抽逃的出資等。第三,在債務人董事高管、發起人、公司股東等的行為構成對債權人個人的侵權時,對于這類直接債權,參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第22條規定交由破產管理人統一行使,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債務人董事高管、發起人、公司股東等的侵權行為所損害的對象,不是個別債權人,而是全體債權人;另一方面,這些人之所以要對債權人承擔責任,根源還在于其侵吞公司財產或未能妥善保管公司財產,法律即便賦予債權人以直接請求權,也不能改變行為人損害破產企業利益的性質。*類似地,德國《破產法》第92條規定,債權人因在破產程序開始之前或之后由于屬于破產財產的財產減少而共同遭受損害(共同損害,Gesamtschaden)所產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在破產程序進行期間,只能由破產管理人主張。請求權系針對破產管理人的,只能由新任命的破產管理人主張。上述理由不僅在擁有有限責任保護的公司制企業中適用,對普通合伙、有限合伙等合伙企業的破產,也都有適用的余地。例如,對于合伙債權人向普通合伙人的追償權,由破產管理人統一行使也很必要。[31](P1021)
公司債權人的保護課題歷久彌新,本文綜述了各種可能的債權人保護制度,主要有以下結論:(1)放貸也是一種投資方式,債權人尤其是有調節能力的債權人要承受因此可能遭遇的破產風險,因此,合同保護是債權人首先應考慮到的救濟手段;(2)從公司法層面言,應當從有限責任與公司資本制度內在的“對價”關系角度理解在股東一方違約時債權人的追索權;(3)就債權人保護而言,侵權法亦有用武之地,這一制度一方面可以維系公司財產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又有助于更好地實現債權人的集體與平等受償;(4)破產法是私法中債權人的最后保障,這一制度強調債權平等、整體受償和債權統一行使,以期實現破產財產的最大化和對全體債權人的最優保護。
[1] Z?llner.Gl?ubigerschutz durch Gesellschafterhaftung bei der GmbH.In Barbara Dauner-Lieb et al.(Hrsg.).FestschriftfürHorstKonzenzumsiebzigstenGeburtstag. 2006.
[2] Mertens.Zur Bankenhaftung wegen Gl?ubigerbenachteiligung, ZHR 143 (1979).
[3] 萊納·克拉克曼、亨利·漢斯曼等:《公司法剖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4][20] 弗蘭克·伊斯特布魯克、丹尼爾·費希爾:《公司法的經濟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5] Smith et al. “On Financial Contracting: An Analysis of Bond Covenant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79(7).
[6] 羅曼諾:《公司法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7] LoPucki.“The Politics of Article 9: The Unsecured Creditor’s Bargain”.VirginiaLawReview, 1994(8).
[8] Armour.“Share Capital and Creditor Protection: Efficient Rules for a Modern Company Law”.ModernLawReview,2000(63).
[9] 白江:《論資本維持原則和公司資產的保護》,載《社會科學》,2007(12)。
[10] 劉燕:《公司法資本制度改革的邏輯與路徑》,載《法學研究》,2014(5)。
[11] 高旭軍、白江:《論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改革法〉》,載《環球法律評論》,2009(1)。
[12] 甘培忠:《論公司資本制度顛覆性改革的環境與邏輯缺陷及制度補救》,載《科技與法律》,2014(3)。
[13] 馮果、南玉梅:《論股東補充賠償責任及發起人的資本充實責任》,載《人民司法·應用》,2016(4)。
[14] 馬勝軍:《股東抽逃出資的民事法律后果》,載《人民司法》,2013(2)。
[15] 樊云慧:《從“抽逃出資”到“侵占公司財產”》,載《法商研究》,2014(1)。
[16][18] 張保華:《分配概念解析》,載《政治與法律》,2011(8)。
[17][19] 劉燕:《重構“禁止抽逃出資”規則的公司法理基礎》,載《中國法學》,2015(4)。
[21] 張學文:《公司破產邊緣董事不當激勵的法律規制》,載《現代法學》,2012(6)。
[22] Sarah R?ck.DieRechtsfolgenderExistenzvernichtungshaftung.Tübingen:Mohr Siebeck, 2011.
[23] Kübler.Anmerkung zu TBB-Fall, NJW 1993, 1204.
[24] PaulDavies.AnIntroductiontoCompanyLa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 費奧娜·托米:《英國公司與個人破產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6] Wagner.Existenzvernichtungs als Deliktstatbestand.In Heldrich et al.(Hrsg.), FS Canaris, Bd.2, 2007, 473.
[27] Christian F?rster.Der Schwarze Ritter-§826 BGB im Gesellschaftsrecht, AcP 209, 398.
[28] Theiselmann.Die Existenzvernichtunshaftung im Wandel.GmbHR 2007, 904.
[29] Kleindiek.Ordnungswidrige Liquidation durch organisierte “Firmenbestattung”, ZGR 2007, 276.
[30] Kort.Die Haftungses Einflussnehmers auf Kapitalgesellschaften in ausl?ndischen Rechtsordnungen, AG 2005, 21.
[31] Bork.“Gesamt(schadens)liquidation im Insolvenzverfahren”.InK?lnerSchriftzurInsolvenzordnung. K?ln: ZAP Verlag, 2010.
(責任編輯 李 理)
Protection of Corporate Creditors: A Systematic Approach
XU De-feng
(School of Law,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The corporate creditor has primarily all of the safeguards provided by law for creditor of individual.In addition to these “general” rules, there are also a great number of “special” provisions in corporate law dealing with corporate creditor protection, such as rules concerning legal capital, permanent capital, fiduciary duty of directors and corporate officer and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towards creditors(piercing corporate veil).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mechanisms, a systematic framework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part from the traditional mechanism of creditor protection in corporate law,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d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creditor protection by contract, tort and bankruptcy, and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mechanism.
protection of corporate creditor;tort liability;piercing corporate veil;legal capital; maintenance of share capital
許德風: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