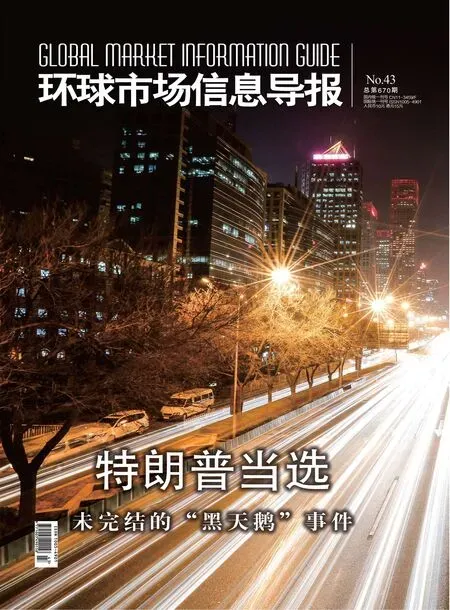《紐約時(shí)報(bào)》,或許就是媒體轉(zhuǎn)型的最佳樣本
《紐約時(shí)報(bào)》,或許就是媒體轉(zhuǎn)型的最佳樣本
Point
盡管我們尚無法評判,傳承到第五代的這份“家族報(bào)紙”能否轉(zhuǎn)型成功,但起碼它曾經(jīng)或仍然在定義著一個(gè)成功的媒體所應(yīng)具備和承擔(dān)的職能。

今年稍早時(shí)候,《紐約時(shí)報(bào)》迎來了它的第五代“領(lǐng)導(dǎo)人”——亞瑟·格雷格·蘇茲貝格。這意味著這份傳承了120年的媒體巨頭迎來了它的新時(shí)代。
事實(shí)上,隨著近年來全球媒體掀起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浪潮,《紐約時(shí)報(bào)》早在前兩年就開始了“轉(zhuǎn)型之路”。2014年上半年,《紐約時(shí)報(bào)》那份96頁的內(nèi)部研究報(bào)告在呈送到其高層后,就傳遍了海內(nèi)外媒體圈。在我的記憶中,當(dāng)時(shí)正值國內(nèi)媒體圈對有關(guān)媒體轉(zhuǎn)型的話題討論得甚囂塵上之時(shí),幾乎所有國內(nèi)媒體人都想方設(shè)法地搞到了這份報(bào)告:管理者以期從中尋找到轉(zhuǎn)型的靈感,記者、編輯希望看到自己在未來可能擔(dān)任的角色,其他八卦好事之徒則好奇多年后媒體會變成什么模樣。
遺憾的是,不知道是否由于這份報(bào)告過于冗長,它并沒給國內(nèi)媒體在轉(zhuǎn)型的道路上帶來太多共識,至今,我們的媒體轉(zhuǎn)型仍然只是在各說各話——每個(gè)人在自己認(rèn)定的道路上艱難前行,留下一地雞毛。
在數(shù)字化時(shí)代,作為一份有著120年歷史的傳統(tǒng)媒體,它依舊是全球的行業(yè)標(biāo)桿。盡管我們尚無法評判,傳承到第五代的這份“家族報(bào)紙”能否轉(zhuǎn)型成功,但起碼它曾經(jīng)或仍然在定義著一個(gè)成功的媒體所應(yīng)具備和承擔(dān)的職能。
有意思的是,從上世紀(jì)初起,在《紐約時(shí)報(bào)》就職的記者、編輯和管理人員就十分清楚這個(gè)名字所意味著的巨大榮耀,并且他們并不會刻意去對其表示出謙虛和保留,即使他們偶爾也會對其發(fā)出批評,但從未懷疑過這四個(gè)字所擁有的巨大能量。曾經(jīng)在《紐約時(shí)報(bào)》任職了十余年的蓋伊·特立斯就是一個(gè)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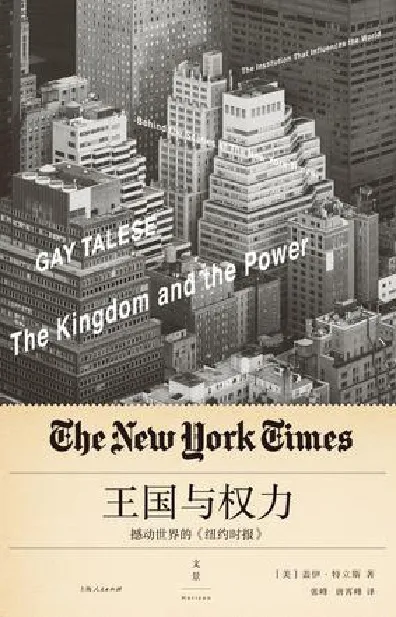
這位被后世稱為“新新聞主義之父”的作者,最初不過是《紐約時(shí)報(bào)》的一個(gè)送稿生:也就是給編輯跑腿兒送報(bào)紙文章,給記者買三明治、咖啡,為臨時(shí)出席活動(dòng)的部門主任買皮鞋、皮帶、領(lǐng)帶……他們也有可能寫一些無關(guān)緊要的小稿子,運(yùn)氣好甚至可能登到《紐約時(shí)報(bào)》,但不會有署名。
不過,他在上班第二個(gè)星期里,就在報(bào)紙上發(fā)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寫的是時(shí)報(bào)大廈外的滾動(dòng)廣告牌(用燈泡組成,只顯示新聞標(biāo)題,類似于今天液晶顯示的跑馬燈),以及操作這個(gè)廣告牌的“燈泡男”。在升為記者后,特立斯長期跑的是體育條線。正是有了這個(gè)職業(yè)生涯的“伏筆”,在離開時(shí)報(bào)多年之后,特立斯依舊出于職業(yè)敏感而關(guān)注到了中國女子足球隊(duì)。
在離開《紐約時(shí)報(bào)》不久,特立斯便開始回顧自己在《紐約時(shí)報(bào)》的經(jīng)歷。他在寫了一篇有關(guān)當(dāng)時(shí)《紐約時(shí)報(bào)》的主編克利夫頓·丹尼爾(1964-1969年擔(dān)任主編)的文章后,又繼續(xù)挖掘克利夫頓與管理層其他人員的關(guān)系,在這其中他采訪了在或曾在時(shí)報(bào)供職的上百位人士,最終碰觸到了這份偉大報(bào)紙的歷史,并將其還原在紙張之間,這就是《王國與權(quán)力:撼動(dòng)世界的〈紐約時(shí)報(bào)〉》。
這也就是為什么,在特立斯的這本書里,克利夫頓會經(jīng)常穿插出現(xiàn),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這本傳記作品是在克利夫頓的采訪基礎(chǔ)上衍生而成的衍生品。所以,我們也能看到,《王國與權(quán)力》的敘述并不是按照時(shí)間順序來展開,而是按照人物角色來展開。很顯然,特立斯認(rèn)為,這些“重要角色”是帶領(lǐng)時(shí)報(bào)取得偉大成就的原因,也同樣是這些“重要角色”給時(shí)報(bào)帶來了曾經(jīng)經(jīng)歷的那些挑戰(zhàn)、矛盾、困惑和迷惘。
如果把克利夫頓看成是特立斯這個(gè)“宏大故事”的引子的話,我們想要了解時(shí)報(bào)的精神品質(zhì),就不得不去追溯它的“奠基者”阿道夫·奧克斯。之所以我們在這里將奧克斯稱為“奠基者”,而非創(chuàng)辦者,是因?yàn)椤都~約時(shí)報(bào)》是由亨利·賈維斯·雷蒙德和喬治·瓊斯在1851年9月18日創(chuàng)辦的,最初的名字是《紐約每日時(shí)報(bào)》,到6年后才正式改為今天的名字——《紐約時(shí)報(bào)》。
不過,半個(gè)世紀(jì)不到,《紐約時(shí)報(bào)》就陷于瀕臨破產(chǎn)的境地。這時(shí)候作為南方報(bào)紙《查塔努加時(shí)報(bào)》的老板,奧克斯以75000美元收購了《紐約時(shí)報(bào)》,正式開啟了《紐約時(shí)報(bào)》的王國。奧克斯上任后,就開始對《紐約時(shí)報(bào)》進(jìn)行了大刀闊斧地改革,三年內(nèi)就將時(shí)報(bào)的發(fā)行量從9000份提升到了75000份,其廣告量也出現(xiàn)大幅增長。特立斯如此評價(jià)奧克斯:他的“天才不僅在于他創(chuàng)造的報(bào)紙的類型,而且在于他使這個(gè)報(bào)紙賺了錢”。
對此,我們可能會意識到,這個(gè)“對報(bào)紙有著特殊熱情的小個(gè)子”在媒體經(jīng)營上所具有的平衡觀念:他希望報(bào)紙能夠盈利,同樣又希望能夠杜絕利潤的誘惑;他希望“不僅僅是為了利潤而經(jīng)營《紐約時(shí)報(bào)》,而且多少要遵循偉大教會的經(jīng)營路線,靠美德來給財(cái)富鍍金”。
除去經(jīng)營,奧克斯的“平衡觀念”還體現(xiàn)在新聞報(bào)道上。1897年,奧克斯就為《紐約時(shí)報(bào)》確定了報(bào)道原則:報(bào)道“所有值得印刷的新聞”。這一原則直到今天仍然是時(shí)報(bào)的圭臬。同時(shí),奧克斯還認(rèn)為,新聞報(bào)道應(yīng)該“力求真實(shí),無畏無懼,不偏不倚,并不分黨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
正是有了這些原則的存在,《紐約時(shí)報(bào)》誕生之初似乎更像是個(gè)“怪物”,尤其是與當(dāng)時(shí)那些偏好報(bào)道小道消息和亂發(fā)評論的媒體相比,《紐約時(shí)報(bào)》卻不斷地?cái)U(kuò)張版面來為讀者提供新聞信息;同時(shí),時(shí)報(bào)還十分注重抑制發(fā)表自己的觀點(diǎn),而只把評論的版面圈囿在有限的欄目里,盡管它在歷史上并不缺少犀利的評論。這樣的辦報(bào)理念,可以說直到今天對大部分媒體來說都極為另類。
當(dāng)然,隨著時(shí)報(bào)的成功和擴(kuò)張,它在上世紀(jì)三四十年代,起碼在外觀上來看,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巨大的“新聞工廠”。
“它是一個(gè)巨大的功能性的大屋子,從第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據(jù)著《紐約時(shí)報(bào)》14層大樓的第三層,內(nèi)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屬桌子、打字機(jī)和電話連接起來,幾百個(gè)人手里握著筆坐著,或者敲擊打字機(jī),寫作、編輯或閱讀著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看起來,每五分鐘就有一次災(zāi)難的報(bào)道到達(dá)這里——仰光的暴亂,坦桑尼亞的騷動(dòng),某國的軍事政變或者地震。但所有這一切似乎不會給這個(gè)房間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這么多的壞消息早就滲透了這個(gè)地方的氣氛,以致這里的任何人都對它產(chǎn)生了免疫力。這些消息像是一種無害的病毒,漂流進(jìn)這座大樓,通過這個(gè)系統(tǒng)流傳,在打字機(jī)上進(jìn)出,經(jīng)過筆下加工,進(jìn)入旋轉(zhuǎn)的金屬機(jī)器,被印在報(bào)紙上,裝進(jìn)卡車,分發(fā)到報(bào)攤,銷售給容易煩惱的讀者,在世界上引起反應(yīng)和反行動(dòng)。”
特立斯的這段速寫,為我們鮮活地呈現(xiàn)出了時(shí)報(bào)編輯部的表面模樣。或許,第一次看到這種壯觀景象的“觀眾”都會感嘆這個(gè)龐大的“新聞流水線”——這是現(xiàn)代新聞工業(yè)的巔峰。
正是基于這種“新聞生產(chǎn)”的理念,奧克斯雖然并不否認(rèn)個(gè)人才能在新聞報(bào)道中的作用,但他更希望自己的雇員能有鮮明的團(tuán)隊(duì)精神,能夠尊重時(shí)報(bào)的價(jià)值觀。所以,“應(yīng)該雇傭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有才能卻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在《紐約時(shí)報(bào)》沒有哪個(gè)人是不可或缺的”。這樣的用人標(biāo)準(zhǔn),使得時(shí)報(bào)在一個(gè)世紀(jì)以來的運(yùn)作過程中,得以將奧克斯確立的報(bào)道標(biāo)準(zhǔn)和經(jīng)營原則一以貫之。有趣的是,這種限制性的用人原則并沒擋住《紐約時(shí)報(bào)》不斷涌現(xiàn)出“新聞明星”。
更有意思的是,《紐約時(shí)報(bào)》這么多年來都嚴(yán)苛地保持著家族經(jīng)營的模式。奧克斯曾要求“自己去世后,《紐約時(shí)報(bào)》應(yīng)只由他的家庭中的直系親屬來掌管,進(jìn)而再由他們的家庭成員來控制,他們?nèi)加胸?zé)任以他所具有的那種奉獻(xiàn)精神在一生中進(jìn)行管理。”這個(gè)看似傳統(tǒng)保守的經(jīng)營原則,竟然不可置信地被保留至今。我們很難判定,這個(gè)傳統(tǒng)的人事原則在《紐約時(shí)報(bào)》的成功過程中起到了何種作用,但它確實(shí)保證了在過去一個(gè)多世紀(jì)里,時(shí)報(bào)領(lǐng)導(dǎo)層的相對穩(wěn)定。
當(dāng)然,同一切大機(jī)構(gòu)一樣,《紐約時(shí)報(bào)》也不可避免地遭遇過內(nèi)部糾紛和權(quán)力斗爭。尤其是紐約總部和華盛頓分社的矛盾,特立斯將其穿插于整部作品的始終。在特立斯的筆下,這兩個(gè)機(jī)構(gòu)之間的斗爭之激烈,并不亞于其他大企業(yè)里的高層權(quán)斗。可以想象,特立斯通過這樣的描寫也是在提醒我們,《紐約時(shí)報(bào)》的歷史同樣面臨著挑戰(zhàn)和分裂,“《紐約時(shí)報(bào)》是人的組織,龐大而脆弱”。
誠然,曾經(jīng)作為記者的特立斯,在寫作過程中無法拋開新聞報(bào)道的風(fēng)格影響,也因此我們可能無法直接從這部作品中獲得《紐約時(shí)報(bào)》的成功經(jīng)驗(yàn)。更何況,在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gè)全新的時(shí)代,數(shù)字技術(shù)的迅猛發(fā)展,讓我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應(yīng)對技術(shù)手段的沖擊上。這也使得特立斯在上個(gè)世紀(jì)70年代所寫的有關(guān)《紐約時(shí)報(bào)》的故事,似乎多少就有些不合時(shí)宜了。
然而,我們每個(gè)人都忽略了這樣一個(gè)根本問題:作為一個(gè)19世紀(jì)末成長起來的媒體,《紐約時(shí)報(bào)》經(jīng)歷了廣播技術(shù)、電視技術(shù)、數(shù)字技術(shù)這三個(gè)媒體史上的大轉(zhuǎn)折,但它在今天依舊傲然卓立于世。從這一點(diǎn)來看,《紐約時(shí)報(bào)》就可以被看作是媒體轉(zhuǎn)型成功的最佳樣本和案例。
所以,讀它的歷史和故事,我們就一定能從中有所體悟:對于今天的媒體來說,哪些法則和習(xí)慣應(yīng)該被拋棄,哪些觀念和原則又值得珍視和保留。就像特立斯在結(jié)尾處寫道,“就要像一棵根深蒂固然而又靈活的大樹,每天從左到右、從右到左搖擺,在搖掉了它的衰老的舊葉子后進(jìn)行調(diào)整,保持四季茂盛。”
(文/嚴(yán)杰夫 來源/經(jīng)濟(jì)觀察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