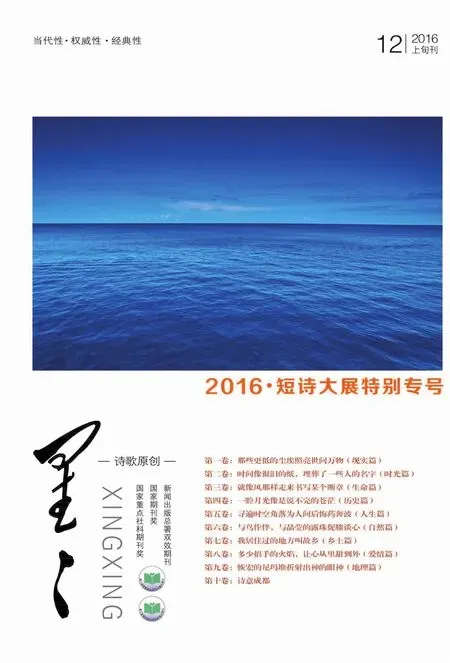詩性的日常化歷史書寫
——一腔月光像是說不完的蒼茫(歷史篇)評論
干天全
詩性的日常化歷史書寫
——一腔月光像是說不完的蒼茫(歷史篇)評論
干天全
如果不是從社會學的意義看,天地間過去的一切都可以稱為歷史。大自然萬物的進化構成了歷史,人類的進化過程構成了歷史,社會的演變發展構成了歷史。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和認識也會構成自己的歷史。詩人用詩行所表達的歷史既可是對國事、天下事的感慨,也可是對家事或個人經歷的感悟。本卷詩集名為“歷史篇”,其內容并非如司馬遷、班固之類史家對歷朝歷代帝王將相事非功過和社會變遷的依據記載,而是對歷史現象和人物的主觀透視,借歷史遺跡和陳年舊事來表達人世滄桑的感受。這些詩中鮮有涉及國事天下事的宏大抒寫,多為對日常生活歷史感受的碎片似呈現。然而,本卷中十多位詩人的短作卻能小中見大,平中見深地表達出各自對過去的歷史情懷。
本卷中采用社會歷史題材的那些詩都是可圈可點的。陸子的三首小詩頗具代表性。他的《秦兵馬俑》寫的僅僅是出土文物的局部,而讓我們想象到的是“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的威風氣勢。詩人以高超的聚焦本領,省略了七雄爭霸的慘烈戰爭場面,也撇下了始皇帝的雄才大略和一統天下的豐功偉績,甚至于連宏大的兵馬俑陣容也視而不見,只凸顯了秦軍將士臉上自豪與勝利的微笑,讓人們“不敢相信這就是當年的虎狼之師/每一個士兵,甚至連每一匹馬/都在微笑呵——/他們把六國吞進了肚里”。詩里的特寫鏡頭畫面有限,但卻給我們留下了壯闊的想象空間,讓人們對兵馬俑的象征意義有了深刻的印象和理解。他的《乾陵無字碑》為武則天的無字碑做了一個小注。“立一塊豐碑/卻不著一字碑文/留下的一方空白/也許是那個女人/給大唐,也給天下的男人/留個面子”。正如魯迅所說“武則天當皇帝,誰敢說男尊女卑”。武則天的無字碑之意也許是一種大度,該受的屈辱受了,該權傾天下傾了,該風流的風流了,是非功過由人說去,你愛怎么評價就怎么評價。這點氣度是西方女權主義者波伏娃望塵莫及的,就是天下包括做皇帝、做圣人、做英雄的男人們也會羨慕嫉妒恨的。但是武則天卻給男人們“留了個面子”,也讓男人們想想,是不是不要有太重的男權意識,也不要希望為自己樹碑立傳就可以留下身后名。《法門寺》這首詩雖然沒有像韓愈《諫迎佛骨》那樣鮮明地表達了對皇帝勞民傷財、禍國殃民行為的不滿與勸誡,但也含蓄地表達了對現代愚昧的不屑。“造三千畝廟宇/忘了佛祖就住在心靈一隅/種田人一邊嘴上念經/一邊心上疼著土地/釋迦牟尼翹在這兒的大拇指/永遠都是骨頭,舍利”。詩人說得對,舍利就是骨頭,永遠都是骨頭。骨頭是不會顯靈的,是不值能夠養活民眾的三千畝土地的。小詩的寥寥數語卻耐人尋味,發人深思。
詩人小語借《殘碑》表達了對家鄉歷史的斷想。“戰馬、桐油、嘶鳴/野百合、殺人溝,提著燈籠輪番過來/舔干土碗”這一切象征著歷史上曾有的戰爭、反抗、屠殺都隨云煙散盡。而面對現實,詩人心里有著自己的殘碑,記載著自己感受到的苦痛歷史。“酒,攪紅顏成禍水/燒毀我的整個王宮”。發思古之幽情是為了現在,作者“死死抱住那塊殘碑”,也許是在思考歷史興衰的教訓。萬有文的《烽火臺》從歷史遺留的戰爭遺址,描繪了歷史的“孤與冷”,讓人們想起了唐代的邊塞詩。在遍地砂礫石頭上長滿駱駝刺的大漠孤煙中,戍邊將士們的辛苦可想而知。遍地酒壇也未必能療治鄉愁,何況荒涼的邊塞并沒有許多酒可借酒澆愁。更多的時候,思鄉的人,只能喝下清冷的月光。游子至此,看到的只能是風化的歷史,引起的同樣是難以揮去的鄉愁。望秦的《古城墻》對“虛無主義捏造的繁榮”表示了質疑。“急于重建信仰的人/在城市中央圈出一片區域/標上警示牌,幾塊石頭就充當了歷史的/解說員,青草爬到這里的時候/只剩幾盞霓虹燈在草叢里尋找蟋蟀”。這樣的古城墻,是否就能充當歷史,現實中的官員與百姓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商業潮流涌動的現代社會中,歷史往往并不重要,它只是像流行的說法:歷史是被人們任意打扮的小姑娘。王祥文的《釣魚臺》借歷代高人隱士釣魚之故,感嘆“釣魚”是釣江山,而江山依在,釣魚的人卻隨逝去的流水而去。釣魚留給詩人的感受,還是閑適的本意,人在自然中自尊獨立為精神之王,獨享自由自在。
卷中的其它詩,則是以詠物詩來表現對日常生活史的感嘆。朱勝國的《樹木辭》借樹木立詩人之言。中國遠古有“有巢氏”之說,可見我們的祖先與樹木的生死依存關系。先人高居樹上,避免毒蛇猛獸的侵害,以獲安全感。而詩人卻從現代人的意識,看到人的生命與樹的關系,“從木頭里挖出犁鏵,桌椅,床,棺材/挖出愛或恨,祈禱或詛咒,刻骨銘心或心如死水/前世或今生”。從古至今,生命輪回的人們并不比歷史的“樹木”恒久,只不過是在“樹木”上留下了悲歡離合的年輪。“樹木”記載著人們的歷史,睹其形象便可想到人的生命歷程與命運。蔣明的《朽木》同樣寫樹,但寫的是生命已然終結的朽木。詩人有意忽略了樹的生機勃勃和參天而立的形象,也未表現其轟然倒地的悲壯,只將它的朽木價值展示給了人們。“朽木不雕,/才是朽木的價值。//微小的菌種給大地裝上/一只只黑色的耳朵,/命運,/就會聽見失語者的哭泣!”。朽木如各類弱者,沒有話語權,甚至沒有生存權,豈能不悲而泣之。華秀明的《三棵樹》仍然寫樹,寫的卻是苗地鄉里歷史的象征。不管是擋過“土匪子彈的傳說”還是舊時代的烏啼,抑或是踏碎遍地梨花的馬幫,一起都隨 “三棵樹”象征的舊日歷史消失而消失了,古老山野的歷史讓人在懷舊中感到了失落。他的《皮影戲》則是對人生的另一種 洞穿。在他看來,人與牲畜、與草木同靠一張皮在黑與白的生活舞臺上亮相,“鑼鼓一經停歇,皮依舊是皮/為蟲為獸,為畜為人,并無分別”。其實人與獸、靈與肉還是有區別的,只是面對人生舞臺上的皮影似的虛幻表演,作者提醒人們,皮只是表象。
李達飛的《張思古民居》、白象小魚的《正午帖》、白紅雪的《青銅的玫瑰》、《那些細密針線的吻》、帕男的《那個在純白旗袍里 翩然行走著的女人》、洪波的《變臉》和《隱身之術》都從生活歷史的角度,借物、借景或托人表達了自己獨到的人生感悟和愛憎之情。他們的詩和前邊談及的詩作在藝術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詩歌語言具有突出的現代性和象征暗示的藝術性。整卷詩,無論是稍長一點的短詩或是只言片語的小詩,都讓人感到了未曾相見的語言陌生化。意象的創意、語言的張力都帶給人較大的想象空間和美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