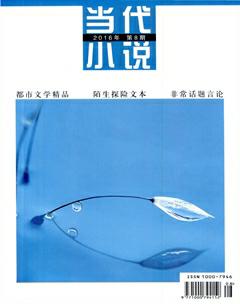鍋鏟
趙廣建
貴堂上小學時就在鍋頭棚里幫娘做飯,抱柴火、拉風箱,啥活都干。鍋頭棚里有個大鍋臺,鍋臺左側是風箱,右側靠墻是鍋蓋,鍋蓋旁有餾干糧的木杈、箅子,和一把磨沒了棱角的鐵鍋鏟。鍋鏟多數時候炒菜用,表面發黑,整體帶有錘打的痕跡,鐵把上有兩個相同的圓環,看上去滿精致。
貴堂對鍋鏟并無癖好,偶爾隨手拾起來拿到院里玩耍,不小心被娘瞅見,定會聽到一聲突如其來的喝喊,放回去,找挨打啊!貴堂就莫名其妙地乖乖把鍋鏟放回到原處,然后換來燒火用的煤鏟繼續玩耍,心里卻一再嘀咕,不都一樣的鐵鏟啊,煤鏟能玩,鍋鏟咋就不行!
貴堂一直膽小,這與娘的喝喊有關。他家鍋頭棚與堂屋之間有個磚砌的雞窩,天黑后,雞婆們鉆了窩,娘用石板把雞窩擋上,反復查看無誤后才進屋歇息,即使如此,無論冬夏,家里依然每年出現幾次意想不到的突發事件,一到深更半夜熟睡時,突然聽到雞窩里發出嘎嘎的雞叫聲,其慘烈的哀鳴駭人毛骨悚然。爹無言,甚至鼾聲不誤,娘卻驚叫不停,嗷——哧!嗷——哧!嚇得貴堂驚魂四散,捂頭蒙被往娘被窩里一陣亂鉆,縮成一團抱緊娘身,娘邊喊邊扒拉開貴堂出屋去了。
第二天,必有一只老母雞失去。娘說黃鼠狼子又來了!爹說房后支了大鐵夾子,夾死它個畜生!貴堂知道大鐵夾子能把黃鼠狼夾死,可每次都是房頂上或房間過道里一堆雞毛,血肉模糊帶來的腥味令人作嘔,駭人怯步。
貴堂極恨黃鼠狼偷雞,少了雞,奢侈一回雞蛋比登天還難,等待新雞下蛋解饞時節,又輪到猴年馬月了!
令貴堂對鍋鏟生懼的誘因是有一天晚上,娘突然嗷哧嗷哧地狂喊了好幾聲,貴堂蜷縮在被窩里聽到的不是嘎嘎的雞叫聲,而是娘在問爹,你聽,鍋頭棚里鍋臺上,鍋鏟響了!貴堂爹說夢話般怒斥,胡扯!接著翻身又睡。貴堂娘身披上衣呆坐在被窩里像了木頭,不躺,也不起身外出,嚇得貴堂不敢再睡。他好像也聽到了鍋臺上“當啷”一響,聲音像是鍋鏟碰了鍋沿,娘猜不準聲響的源頭,也許還在等那黃鼠狼出現,爹不讓多嘴,白天干活太累了,貴堂內心突然對鍋鏟產生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懼,此恐懼并非被窩里空穴來風,而是腦海深處另有因由,一個無法解釋的奇怪現象是,他聯想起了娘對鍋鏟的異樣目光。如果說過去他無意中拿鍋鏟玩耍引起娘怒吼,現在回想起來,每當娘在炒菜時,那鍋鏟好像嶄新如初,既壓手,又珍貴,握在手上死不松開,拿到的瞬間,眼睛分明一亮,恨不得猛然摟在懷里,像有一種暗來的沖動涌至心頭,手握鍋鏟的同時,伴隨著極目遠望的暢想,一并往鍋里慢慢地攪啊,攪啊,攪得鍋里的熱氣一冒再冒升為無有,攪得人心有一款心潮起伏的味道,那味道分明是一陣暖流在涌動……
貴堂忽然悟到了什么,地里的活計那么忙,整天累死累活地顧不上吃穿,娘惟一的幸福是看一眼鍋鏟,他忽然內心一怔。
貴堂還注意到,炒好菜后,娘手握鍋鏟深吸一口氣,然后又長長吐出來,像有心事堵在胸口,緊握鍋鏟的表情顯示出生怕鍋鏟會無端飛走,盡管有時把炒好的菜一下下鏟出來,有時把木杈、箅子和干糧重新拾回到鍋里蓋上鍋蓋,她都是手握鍋鏟不撒手,甚至把菜端進堂屋的地桌上也要手握鍋鏟來回出入。
回到鍋頭棚,娘拿抹布把鏟頭擦洗干凈,深情地呆望一會兒,然后才依依不舍地放回到鍋臺上,望著鍋臺直直發呆。貴堂狐疑多端地有些緊張,娘干活就那么幾件家什,針線板、大木盆、菜刀、飯勺,惟獨鍋鏟被另眼相待,這不會是娘的腦子有毛病吧?貴堂開始對鍋鏟產生疑問,更對娘看重鍋鏟多了疑心。
貴堂在小飯桌前對爹說,夜里我也聽見了,咱家鍋頭棚里鍋鏟響了。
爹說,胡吣!
娘說,做夢吧?我也夢見鍋鏟響了。
自那,娘在夜里很少再出現嗷哧嗷哧的狂叫。但貴堂還是膽小了,黑夜不敢出門,上樹不敢爬高,下地干活不敢靠近牲口,更沒有偷雞摸狗、惹事生非的賊膽劣跡。但他內心深處最為驚懼的還是那個黑黑的鍋鏟。在他腦際間,印象最深的是娘看鍋鏟那癡迷的眼神和面對鍋鏟久久發呆的樣子,極嚇人,嚇得屏息呼吸一再令人多慮,夜間減少出門也無濟于事,出門躲著鍋頭棚繞走也無法釋懷,那棚里的鍋鏟似乎總在耳畔當當響,像是娘的身影變黑了一樣,凝視鍋鏟發呆的影像令人日夜不安。
爹常年下地不見笑容,有生產隊時在隊里使牲口,打起來牲口咬牙切齒。分田到戶后,爹帶一家人種自家的承包地,干啥活都是一副怒相,不見顏笑的舉止,像是娘和孩子欠了他一輩子情分,話不多,話狠,雖然無從打罵過誰,但瞪一眼,嚇得娘和貴堂半晌不敢吱聲。
日子這樣過了多年,貴堂深切感受到,娘和自己一樣,同樣伴有內心驚懼,很顯然,娘的驚懼另有起因。
再一次引起貴堂對鍋鏟產生驚懼的是,在他初中畢業那年秋天的一個下后晌,娘讓他到街西環子家街門口看看那一堆人在圍觀啥事?似乎有心示意他,你去看過學舌給我就是,不必再去說給你爹。剛出街門,東關街的二杰娘手持一把鐵鍋鏟緩緩走來,一晃一晃在貴堂家門口站下了。當時的街上夕陽斜照,紅紅的墻上格外柔和,而且近前并無他人,貴堂明明看到二杰娘的鍋鏟就在手里攥著,合眼、睜眼的工夫,恍惚又聽到鍋鏟在當當聲響,貴堂娘像是得到了什么旨意,順著響聲追了過去,一臉少有的笑容遞向對方說,哎呀他嬸子,這是去哪了呀,稀罕哩。好似二杰娘是多年不見的娘家姊妹,面前的天空頓時亮開,萬里晴空碩展無比。貴堂就站在娘的身后,真切地看到了娘的異常興奮,就像鍋鏟有著巨大引力一樣,一下就把娘的身心吸過去了,那喜出望外的神情令貴堂后脊梁直冒冷氣。
貴堂娘搶上鍋鏟仔細巴望,好似在查找鍋鏟上的什么記號,渾身跟著有些顫抖,心思不再他顧,翻看鍋鏟目不轉睛,似乎把貴堂叫出來的目的也丟擲了腦后,至于是否在認定這鍋鏟像她那把當年新到手的鍋鏟,還是在查找鍋鏟上的什么記號,無法猜測,但這鍋鏟的鏟把上確實也打有兩個同樣的圓環。
剛才,貴堂娘叫貴堂去看街西邊環子家門口停來的那輛銀灰色小汽車附近鬧啥動靜時,向他交待得比較細致,遠處那場面模糊不清,看看車上下來的那灰頭發老人到底是誰,是不是在向人們打問啥事?這會兒,她神情專注地又不說讓過去了。
二杰娘說,我也稀罕,多年集上沒見賣過,雜貨攤上有現貨,剛買了一個。這如今哪還有鐵鍋鏟呀,不好找哩。
貴堂娘恍惚說,是哩,不好找,我光找它找了多年,找不見哩!眼含淚花反復巴望,似乎在與自家的鍋鏟反復比對,生怕那鏟飛了似的,握在手上如獲至寶,觀望的神情走火入魔。
這是貴堂驚恐鍋鏟的又一次震撼。
何以一個鍋鏟擾心到如此地步呢?而且在反復巴望的同時,只字不提自家也有同樣的一把。貴堂想說,雜貨攤上有的是,俺家早就有一把。可娘卻一問再問,從哪買,從哪買哩?不知為啥也說非要找去買。那鍋鏟似乎在貴堂耳畔當當亂響個不停了,甚至有敲后腦勺的感覺,敲得他近乎暈頭轉向。
二杰娘說,集上雜貨攤上有賣哩,好多人都在挑揀呢。
貴堂娘說,炒菜能補鐵哩。哪家呀?
二杰娘說,大爪子家二閨女那雜貨攤上。
噢,貴堂娘失落地噢了一聲,笑容頓失。多年里,貴堂多次見娘往那雜貨攤上去過多回,那里的鍋鏟是從省城土產批發部躉來,出處在哪,款式、樣式她一清二楚。貴堂心生驚懼,娘那神不守舍的樣子像是腦子突發了奇想,拿著鍋鏟突然失望得令人多疑不安。
貴堂忽然想到,娘讓他去看環子家的門口處,少不了也是為了問這鍋鏟吧!
貴堂對鍋鏟的響聲簡直要揮之不去了。
二杰娘原以為停下來能和貴堂娘多嘮叨幾句,見她神不守舍地扭頭向西巴望,言不由衷客套了幾句,慢慢悠悠走開了。貴堂娘轉即像忘掉了二杰娘,站在原地一心巴望街西邊的異常景象。她好像又在猶豫不決,是否叫貴堂快去擠到環子家門口圍看那里的真相,對那車上下來的老人問個仔細,該不是在尋找一把打著圓環的鐵鍋鏟吧?貴堂好像進入了娘的幻覺中,以為看到的那是個老工匠,那人手里也捏了把同樣的鍋鏟,說是要找當年同樣鍋鏟的一個女人……甚至眼里還滿含了淚花……
貴堂娘醒過神來,扭頭見二杰娘已經走遠,又回頭向西瞥去了不舍的一望。她沒言語,也沒動身,木木的呆望動作一定是想到了二杰娘手里那把打有圓環的鍋鏟,肯定和自家的鍋鏟有所區別,不免又想起了什么,木然發呆。她沒想回家去拿出來自家的鍋鏟和誰比對,也沒流露出更多的遺憾表情,而是轉身回望二杰娘遠去的背影,目送她緩緩消逝在黯然失色的夕陽里。
貴堂細心認真地觀察到了娘的這一切,娘沒讓他再向街西那邊走過去,好像習慣了這多年不抱希望的場景,無助地嘆了口氣。
街西邊,環子家門口還殘存著熱鬧場面。汽車旁邊好多人還在圍著那人問長問短。至于那場面是環子爹從外鄉回來了,還是環子家有人來走親戚抑或真的有人來打問鍋鏟,絲毫無法得以判斷。
貴堂娘扯扯貴堂衣角,示意讓兒子隨娘回家,失望地轉身回過神來往家走。回到家,她拭去臉上的淚跡,又讓貴堂去后院里抱柴火,天又到了該做晚飯的時候。
一天又這樣過去了,貴堂更多看到了娘的無奈和焦慮。
后來,他家拆舊房蓋上了小二樓,蓋街門洞時,整條街上家家都是方門洞,惟獨他家蓋成了上邊半圓的弧形式樣,像個倒過來的鍋鏟一樣好是別致。貴堂爹陰臉沒反對,貴堂卻對鉆門洞忐忑不安,來回進進出出疑似有鍋鏟在當當碰頭。搬家時,大部分舊物棄失了,惟炒菜的鐵鍋鏟還在隨手使用。
這讓貴堂心事重重,五味更雜。
貴堂娶了媳婦之后,貴堂娘曾專門對兒媳說過,一定要用家里這把鍋鏟炒菜,大人孩子都能補鐵。說得貴堂直冒冷汗。
貴堂娘死前,讓貴堂拿給她鍋鏟再巴望一眼,貴堂拿起來鍋鏟覺得和往常很不同,似乎很重、很實,比市場上的不銹鋼鍋鏟沉多了,而且整體漆黑,油光光的還有麻子點,好像永遠也擦洗不凈。
娘是望著鍋鏟去世的,死后沒有瞑目。貴堂爹當場把鍋鏟扔到了屋門外,過后貴堂又偷偷撿了回來。
埋了娘,貴堂把娘的照片和鍋鏟一并壓進了箱底里,本意是不想再從鍋鏟上望見娘那傷感的神情,因為常作噩夢,夢見鍋鏟當當響,因而不想再把鍋鏟擺出來攪擾自己安靜的日子。
樓房里沒有鍋頭棚,廚房灶具架上的刀、鏟、叉、勺一概是不銹鋼新品,盡管貴堂娘丟下的鍋鏟在灶具架上無處擺放,貴堂媳婦仍然不同意貴堂把鍋鏟壓進箱底不許再用,說是婆婆多次交待過,炒菜一定要用自家的鍋鏟,具體為啥沒有多說,應該是為了孩子補鐵。
貴堂說,一見鍋鏟我就發蒙,總在不斷聽到聲響,為此害得我經常失眠,一宿一宿翻來覆去,而且對鍋鏟的驚懼完全成了對娘的思念,只要一想娘,就會有鍋鏟伴隨在腦海亂響,不得安寧的日子折磨得神魂快要顛倒了!我對你說,自我記事就沒去過姥姥家,娘說她娘家早沒人了,她也從沒回去過,說她是從臨村的舅舅家嫁來的東門里。她叫韓二妮,那韓大妮呢,她上頭總還有個姐姐吧!那里還有沒有其他人,誰能證實娘的過去?不行,我得到姥姥村里走一趟,打聽打聽到底有啥事,鍋鏟響得我腦袋快暈菜了!
貴堂就帶上鍋鏟來到姥姥家的村子里。
村子不大,幾十里路讓他騎車騎了小半天,頭晌午才到了村口。
一進村,貴堂看天全是陰云,云下籠來一股霧氣,家家半圓形街門像一個個倒著的鍋鏟,死眼盯看霧中人,盯得他誠惶誠恐,六神無主,他忽然明白了娘讓蓋半圓形街門的用意。
貴堂定神壯膽快速往前行了一段,見路邊全是陌生人,想打問情況無處下嘴,便直奔有人值班的村委會來。
在村委會門口,貴堂遇見了一位看門的老漢,那老漢坐在門口老遠盯他,好似早在專門等他過來一樣,聽到打問,隨口就答,韓姓人家?啊,村西那邊全都是,半個村子都姓韓,誰家呀?
韓二妮家。
韓二妮?老漢突然若有所思沉默了一下,低頭之后又抬頭,那可是多年前的老人兒了,咱這村里有過一個。你是她啥人?
兒子。
是嗎?老漢又一次感到意外,將信將疑地猶豫說,那,韓小國是你舅舅了?韓小國多年打聽他姐,一直沒有得到音信。
你認識?
認識。從小一塊堆兒長大,能不認識!韓小國比我小兩歲,他姐和我是同歲,找得韓家好苦啊。如今她在哪?
沒了。
是嗎?俺倆一樣大。老漢又是一驚,啥時沒了?
剛沒。
沒了還有啥話可說?沒了就沒啥可說了。老漢臉色沉了下來,眼里像是含了淚花,你娘年輕時候長得那才叫俊,可憐了哩。說著,掃了一眼貴堂手里那把鍋鏟。
我娘回過村不?
回過不就找見啦!多年沒見回來過,回來還不炸了鍋……見自己說走嘴,慌忙又改口,誰都找不見,啊……老人又問非所答自言自語,沒了就安生了,仨鐵匠都沒了。倆徒弟剛沒。
那是誰,哪仨鐵匠?
早年你姥爺家街對門打鐵的。
是打這樣的鐵鏟嗎?貴堂抬起手里的鍋鏟。
老漢有些心不在焉,好像說過又后悔,不情愿接過來鍋鏟仔細巴望,猶豫說,很像是,你瞅瞅,鏟把上有明顯標記,雙環中間有個三角,倆徒弟都拿同樣一把鍋鏟打聽,咋會在你手里?這可能,三把鍋鏟全齊了,莫非……
貴堂聽得莫名其妙,拿回鍋鏟小心巴望,果真看到雙環中間有個三角,覺得鍋鏟像條活蛇在手中蠕動起來,甚至發出當當聲響。遂小心問,誰找鍋鏟?
沒誰找,沒……和你舅舅找人不一碼事。老漢吞吞吐吐問非所答。
那是誰?
不是誰。早年在你姥爺家門口的鐵貨鋪好是熱鬧,一師二徒,手藝那才叫高超,腰上都圍黃雨布,那家伙,師傅的小鐵錘敲到哪,徒弟的大鐵錘砸到哪,師傅的小鐵錘在鐵砧上原地輕碰,徒弟的大鐵錘就在燒紅的火鐵上,一對一地不停地跳啊,跳啊,一直跳到火鐵發暗或小鐵錘停叫為止,那家伙……老漢忽然賊一眼貴堂臉色,突然話鋒一轉,那年你娘最多也不過十幾歲,爹娘放她隨便出門時,街門口正是那個打鐵爐子。
老漢恍惚又思索到什么,自言自語說,后來添得麻煩,那也是個秋后少有的陰天,出門頭一眼肯定是看到了。
陌生小伙兒拉風箱,身材魁梧,肌腱豐碩,是個新來的外鄉人。
你娘摳弄辮梢,挪不開眼,多少回拿家里的破舊家什讓鐵貨鋪鍛打。
倆徒弟為鍋鏟打得頭破血流。
你大舅被鍋鏟鑿得滿處是傷。
日本人夜里進村那回,外鄉小伙兒拿鍋鏟鑿死過日本兵。
你娘是被你姥爺求人綁走離開的村子。
你姥爺后來也后悔了,像個瘋子四處打聽閨女的下落。你舅舅也找了多年。
倆徒弟逃走后又都回來,多年在村西住著,互相摽著,一輩子都沒娶,當年誰介紹對象也不應……年輕時候可帥氣了……
說到這里,老漢眼里的淚花落下來,別問了,你娘可憐哩……沒了,都沒了……嘆口氣,難受得幾乎不想再說,沒了安生了……
還有誰?
沒誰了。
都死了?
都死了。
埋哪了?
村東老槐樹旁邊。
貴堂沒再多問,鍋鏟似乎又在腦里當當亂響。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