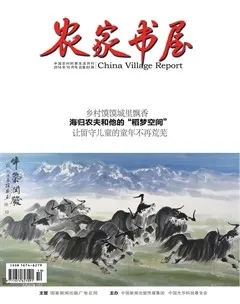三代教書人 一脈家國情

這是一部家族史書,記述了湯氏祖孫三代的身世經歷;這是一部學術史書,濃縮了作者在百年動蕩變遷中的學術操守及其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守望;這是一部自傳,作者以平實、中性的筆法還原了許多歷史真相,講述了個人的悲歡得失及學術生涯。讀完湯一介遺著《我們三代人》之后,筆者心潮起伏,難以平靜。感嘆湯一介先生的真誠和自我解剖精神。
我的父親湯用彤
如人們所知,作者的父親湯用彤先生是蜚聲中外的哲學家、佛教史家、教育家,也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少數幾位“會通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
在作者眼中,湯用彤是位慈父,“父親從未對家人發過脾氣,為人一團和氣”。據錢穆在《憶錫予》(湯用彤,字錫予)一文中說:“錫予之奉長慈幼,家庭雍睦,飲食起居,進退作息,固儼然一純儒之典型。”在湯一介的印象中,父親與當時的學者大都相處得很好,與朋友相聚論證、論學,從不喜爭論,亦無門戶之見。“錢穆與傅斯年有隙,而我父親為兩人之好友;熊十力與呂溦澂佛學意見相左,但均為我父親的相知好友;我父親為‘學衡’成員,而又和胡適相處頗善。” 故朋友們給湯用彤起了個“湯菩薩”的綽號。
湯一介認為,湯用彤治學之嚴謹世或少見。“父親做學問非常嚴肅、認真,不趨時不守舊,時創新意,對自己認定的學術見解是頗堅持的。”故其代表性作品《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已成為研究中國佛教史的經典性著作。據胡適在其《胡適日記》中記載:“此書極好。錫予的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最權威之作。”1944年,當時的教育部授予湯用彤這本書最高獎,父親得知此消息后很不高興。“多少年來一向是我給學生分數,我要誰給我的書評獎!”湯用彤對自己的學問頗為自信,但對金錢卻全不放心上。湯一介記得,1946年,傅斯年請父親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父親全數退回說:“我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拿另一份。”1949年后,湯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被征用,政府付給了八千元,夫人頗不高興,但湯用彤卻說:“北大給我們房子住就行了,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湯用彤在解放前一直教書,先后在東南大學、南京中央大學等高校任教,1931年應胡適之邀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多年。“父親平時主要只管兩件事,一是‘聘教授’,二是學生選課。”季羨林在世時,對我國這種評職稱的辦法頗為不滿,多次對人道:“過去用彤先生掌文學院,聘教授,他提出來就決定了,無人有異議。”學生選課時,他總是要看每個學生的選課單,指導學生選課,然后簽字。湯用彤的學生鄭昕于1956年接任北大哲學系主任時說:“湯先生任系主任時行無為而治,我希望能做到有為而不亂。”
湯一介先生評價祖父湯霖時說:“祖父對父親影響最大的題詞是:‘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樂’。”湯用彤一生確實遵照父親湯霖的教訓,傳繼家風,為人為學,立身處事,憂國憂民。這也成為湯一介立身行事的座右銘。書中,湯一介謙虛地評價自己說:“我雖無力傳‘家風’,作為父親的兒子和學生,也有志于中國哲學史之研究,但學識、功力與父親相差之遠不可以道里計。”
父輩們的友誼與追求
在《我們三代人》的第二部分“我父親”中,作者用了很多筆墨記敘了父親與胡適、吳宓、熊十力、錢穆、傅斯年等著名學者的交往故事。
在湯一介印象中,父親不善交際,因此朋友并不多。“但吳宓伯父卻是父親最相知的親密朋友之一。”吳宓是我國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早年曾留學哈佛大學,與湯用彤、陳寅恪交往甚密,人稱“哈佛三杰”。書中作者回憶,1919年6月,湯用彤從美國漢姆林大學轉到哈佛大學研究院,師從白璧德,曾選修了白氏的《比較文學》,吳宓先期至該校,“父親隨之亦去,我想這是受到吳宓伯父的影響所致。”留學哈佛期間,湯用彤、陳寅恪與吳宓三人常聚而談讀書及學問,吳宓在其《日記》中說:“此中樂,不足為外人道也。”正因為三人志在“讀書學問”,而遠離“功名權利之爭”,為當時在哈佛留學生中的佼佼者,故有“哈佛三杰”之稱。
在吳宓之子女吳學昭的《吳宓與湯用彤》一文中,詳細記載了兩位大師的交往。“我父親吳宓與湯用彤伯父相知相交,長達半個世紀以上。”“兩人都極愛好文學,并以文學的根在于思想為共識。父親常說,非有真性情、真懷抱者不能作詩。用彤伯父則更加明確:‘無道德者不能工文章。無道德之文章,或可期于典雅,而終為靡靡之音。無卓識者不能工文章。無識力之文章,或可眩其華麗,而難免堆砌之譏。無懷抱郁積之知識,非有天生之性情,不能得之。’”
“像老一輩學者能保持半個多世紀的友誼,并在學術上相互支持,是不多見的。”湯一介記得,小時候,吳宓常來家里,“每次總要抱抱我和妹妹,并用他的胡子刺我們的臉玩,我們非常喜歡他,叫他‘大胡子伯伯’。”“吳宓伯父是一位非常有個性的學者,他情感豐富、為人正直,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對中外經典無所不讀”“我們的父輩學者都已故去,他們的為人為學有許多方面我們是學不來的。”“我們這一輩子無論在‘國學’或‘西學’上都遠遠不及上輩。”“我們的后輩,看來問題更多,是否能比我們在學術上的造詣更強也很難說。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中華民族何時才能真正復興而對人類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我們等待著。”
湯氏三代的文化情結
在湯一介先生的墓地上,一塊長20多米、高約3米的墓碑矗立在蒼松翠柏間,碑文上醒目地刻著“湯氏三代論學碑”:確立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性,使中國文化在二十一世紀的返本開新中會通中西古今之學,重新燃起思想火焰,這是當代中國哲學家的責任……
湯一介生前時刻牢記“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祖訓,并以“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樂”為行事立身的座右銘。在筆者與湯先生的接觸中,也深感先生為人為學之儒者風范。
他生活很樸素,對吃穿不太講究,冬天總是帶著一頂毛線帽,跟學生在一起,是先生最開心的時刻,他總是面帶微笑,并勉勵學生抓緊時間做學問。如其父親湯用彤一樣,先生不喜交際,不愛應酬,除了看書寫書,幾乎沒什么其他愛好。
在筆者印象中,湯一介一直不承認自己是一位哲學家,而稱自己是“哲學工作者”。“我們這批人在學術根底上不如老一代。”“在做學問上不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調。”湯一介在書中認真剖析自己“沒有成為哲學家”的原因。在北大哲學系讀書期間,他也曾夢想過成為一位哲學家,但是到1949年后,“我想當哲學家的夢破滅了,甚至對哲學做點真正研究的可能也因政治原因喪失了。”“我父親自回國后,在20世紀20年代初至40年代的二十余年中,正是他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這應該是人生最有思想活力的時間,他得以全心地做研究,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加之他此時常常研究到深夜兩三點,其書數易其稿,才得以成為權威性之著作,至今為海內外學者所重視。”湯一介記得,父親在寫《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時,至少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
雖然歷經政治動蕩,湯一介曾經有過心灰意冷,想扎在故紙堆中做些學術研究打發余生。但其內心對現實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和希望中國早日富強的愿望從來沒有熄滅過。因此,在80年代中期開始的“文化熱”中,湯一介并未超身事外,憑著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他先后寫了許多文章,滿懷熱情地投入到“中國文化問題”的大討論中,并在大家的推舉下,擔任了“中國文化書院”首任院長,終身致力于中國文化研究全面走向世界前列的努力中。
最后兩年,湯先生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了儒藏及其相關事務上,日程表排得滿滿的。雖然經常被疾病所困擾,身體越來越虛弱,但只要精神好一些,他就要去工作。因為“這是他最大的夢想,最后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