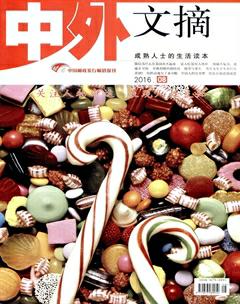虛榮心
介子平
1912年,農林總長宋教仁為調和南北事,拜見袁世凱。袁見其西服敝垢,問曰:“君著此服已幾年?”對曰:“留學日本時買的,已穿十年了。”袁感嘆良久,贈以銀:“錢不多,可為君置新衣。”宋婉辭不受:“貧者士之常。今驟然富貴,哪能忘其本?衣服雖襤褸,但尚可蔽體,沒必要太華麗。”以宋教仁的孤注使命感,其旱已不在乎華服帶來的虛榮。《阿甘正傳》里有句臺詞:“一個人真正需要的財富就那么一點點,其余的都是用來炫耀的。”若沒有了炫耀,宋教仁真的無需銀摺扣。
黃興做了一輩子副手,他說:“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一代人的愿望,為此前仆后繼,在所不辭,哪里在意副手還是主帥。無欺我自安.九天涼月凈初心,白云森天外,人到無求品自高。金庸所言“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用在天性曠達、不作疑吝的黃興身上,十分貼切。
柏格森說:“虛榮心很難說是一種罪行,然而一切惡行都圍繞虛榮而生,都不過是滿足虛榮心的手段。”多數人一輩子只做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而虛榮心屬自欺。多數時候,虛榮心源自內心。是心靈的動機,蕭伯納說人生的苦悶有二:“一是欲望沒有被滿足。二是它得到了滿足。”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了錯誤的東西。有些時候,則源自外界。
沈從文被貶歷史博物館作講解員,汪曾祺曾親見他非常熱情興奮地向普通觀眾講解。“一個大學教授當講解員,沈先生自己不覺有什么‘丟份,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里總不免凄然。”沈從文學立道通,自然貞素,是個認真得有些天真的人,他的不在意,不染心,本性使然,反使作為學生的汪曾祺等糾纏不已。
虛榮心還會從自我心理,蔓延為集體意識。魯迅在《外國也有》一文中說:“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競發現了就更好。”
國有虛榮病,地方上也有虛榮癥。魯迅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又說:“我們中國的許多人……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志,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十景病”“八景病”,為舊癥,大廣場、寬馬路、五大工程、十大建筑等等,乃新癥。
林散之的“浮名乃虛花浪蕊。毫無用處”,說來容易,然能徑其道、自明自凈者,獨為其難。張愛玲說:“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人間.沒有誰可以將日子過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終相信,走過平湖煙雨,歲月山河,那些歷盡劫數、嘗遍百味的人,會更加生動而干凈。時間永遠是旁觀者,所有的過程和結果.都需要我們自己承擔。”
單就個人而言,學生時比分數的多少,俞敏洪說得好:“在大學里的學習,不能再以成績為驕傲,應該驕傲的是你在大學學會思想上的成熟、個人獨立人格的發展、獨立的思考能力或者推動社會前進的責任感,這些東西比你的成績重要很多。在大學,要把自己從一個吃奶的孩子變成一個獨立的頂天立地的人。”比文憑的高低,錢鐘書為此玩笑道:“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工作后比單位的好壞,比工資的多寡;退休后比子女的長短,比身體的優劣。心聲者,終日營營。暗自較勁,言語者,六根不倦,饒舌無休。
生者不過百,太匆匆,寂對河山,沽取對君酌,何不金樽飲?歡樂苦短,鏡里朱顏改,何不放歌行?西哲盧梭靜坐常思己過,其《懺悔錄》云:“把一個人真實的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這個人就是我。”魯迅也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從別國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而惟有將虛榮心剔除后,方可有此境地,脫離虛榮,即在凈土。
摘自《梅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