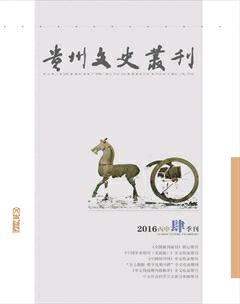論中華文化的樞紐蛻變:由商朝的鬼神信仰到周朝的人文精神
摘 要:從人類四大文明的角度來檢視,不難發現中華文化最早由鬼神信仰發展出人文精神,這個樞紐蛻變來自夷夏兩大部族文化的長期沖突與融合。夷夏兩種文化自新石器時期即可看出不同的發展傾向,并常通過激烈的軍事沖突確立彼此共主與賓服的關系。商朝的族裔源頭與文化傳承都承接于東夷部族,鬼神信仰對東夷人生活具有主導性的意義,其最崇敬的至高神就是上帝。商朝統治階層深信自身天命來自上帝的授權,而周王朝通過不懈的奮斗滅亡商朝的事實裂解了長年被普遍認同的“血統天命觀”,開啟了特有的“德性天命觀”。周建國初期,統治階層對于天命的確保就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使得從商朝的亡國到周朝的立國,不止是王朝的更迭交替,更反映出中華文化的樞紐蛻變。周文化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源頭,其表現就在人們盡管依然有天命的信仰,卻不再迷信鬼神,更相信人自身的奮勉與否,才是任何事情成敗的關鍵因素,中華文化的理性化歷程由此展開。
關鍵詞:人文精神 鬼神信仰 德性天命觀 血統天命觀 理性化歷程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6)04-32-40
一、前言:夷夏文化的沖突與融合
在秦滅六國前,整個中國的格局是夷夏作為東西兩大文化正在激烈沖突與融合的格局,在秦滅六國后,這個格局才開始轉向成南北兩大文化格局,然而不論是東西格局或南北格局,基本架構就是生活在中國的各部族,長年從事著農業與畜牧(或漁獵)這兩種不同的生活型態的資源爭奪,并最終在不同時間點獲致和解共生。我們從神話與考古的對照得知,夷與夏這兩種文化自新石器時期即有不同的發展傾向,彼此亦常會爆發激烈的軍事沖突,夷夏間的關系其實并不難理解,就是藉由戰爭確立誰是共主與誰得賓服。不過,目前尚屬傳說時期(并未有精確的文字紀錄)的夏朝,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其統治過山東的東夷族,然而我們卻在山東發現大量的商王朝曾在這里活動的痕跡,商人與東夷人頗有深厚的淵源,尤其各種文獻都顯示商人與東夷人有直接的血緣關系。商朝始祖契最早居于山東,商族應該確由少皞部落發展出去,其后蔚為大族,由獨立建國到獨立改朝,而少皞部落就是東夷族里最有名的“鳥夷”,且一直世居于山東1。我們由后來周人對商人常稱做“夷”,同樣可看出商人出自東夷人的系統。譬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記說:“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1。”《逸周書·明堂》則說:“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2。”顯然由“紂有億兆夷人”與“紂夷”的混同使用可知商人與夷人確有直接關系,故被當日時人視作一體來指稱。
商人與東夷人彼此緊密的關系,不只體現在他們有著相同的生活風俗(如游牧漁獵或殺人殉葬),更體現在長期生活范圍的重迭性,這包括商王室的子孫在現在山東省建立約七個國家,其間同時住著東夷人。但,商人既已由東夷族獨立擴充發展出去,其與東夷的關系不論就部落對部落或宗主對臣屬的角色,都不可能會完全處于和諧毫無矛盾的狀態。傳至第十任商王仲丁,東夷里的藍夷部落叛變,王朝未能有效弭平,此后夷人對商王朝就叛服不一,如此持續三百余年的光景,當商朝最后一任(第三十任)商王帝辛(紂王)因統治失措且無當,招致東夷的徹底叛離,帝辛率兵消弭東夷叛變,但,因消耗過巨,國內空虛且民怨沸騰不已,這就給周武王偷襲進取的機會,因此,商朝的滅亡與其說是滅于外面的周人,不如說是滅于自家的夷人3。
周族屬于黃帝民族因聚落擴大而獨立劃分出的支部落,黃帝民族即是夏族的前身,有文獻顯示夏朝的創立者禹為黃帝玄孫,如《史記·夏本紀》說:“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4。”意即夏族亦屬于因聚落擴大獨立劃出的支部落,甚至逐漸取替黃帝,成為西方農業民族的新領導者,故而周族屬于諸夏部落集團的成員,周族自稱出自于夏,可能經過“文化改宗”的歷程,這個現象甚至包括黃帝部落本身原本都不是農業民族,由于夏族獨立出去且改為農耕,政治統治能量越來越強大,大部的黃帝部落就開始歸順于夏,成為諸夏部落,剩余的某些黃帝部落則繼續過著游牧生活,這就是“戎”與“狄”的源頭。因此,同樣是游牧民族,蠻與夷是一個系統(姑且稱作甲系統),戎與狄是一個系統(姑且稱作乙系統),這是最早在中國生活的兩大類游牧民族,本來乙系統里的黃帝部落打敗炎帝部落(這是最早期的農業民族),并打敗蠻夷系統里的蚩尤部落,成為全部農牧民族的共主,由于統治得當,因此包括甲系統的東夷人都忠誠歸順,長期視作游牧民族的領袖,“黃帝”這個名號甚至成為東夷人的精神象征,后來乙系統里率先出現開始過農業生活的夏族,致使黃帝部落式微,文化就逐漸轉型成夷夏沖突與融合的格局。
夏族與周族有著相同的文化背景,周人常自稱為“夏”,把自己視為夏文化的繼承者,譬如《尚書·康誥》說:“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5。”而《尚書·君奭》則說:“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6。”最后,還有《尚書·立政》說:“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7。”都可看出周族自承文化出自于夏,其滅商具有“恢復正統”的意蘊8。周人同大部的黃帝部落共同向夏族學習,轉型成過農業生活的民族,而本來血緣相通的戎人則不愿意向夏族學習,繼續過著游牧生活,這是早年周人與戎人生活范圍犬牙交錯的主因。周族因農業發達而著稱于世,該族創始者后稷開始就敏于農事,如《史記·周本紀》說:“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1。”后稷死后三傳至公劉,周族雖然與戎狄雜處,依然不廢農事(由此可知夏與非夏的差異并不在血緣,而在生活型態,這種差異有著文化自主的選擇性,地理環境并不是影響生活型態的絕對因素),周族很懂得因地制宜,善用地利來取得資源并擴大發展,使得百姓能蓄積財富,《史記·周本紀》有這段紀錄:“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由“周道之興自此始”可看出農業奠立周國的立國基石,這是周文化首先從生活型態層面突顯出來的文化特征。
公劉是周族能興起的關鍵領導人,他帶領部族由漆水流域南渡至渭水流域生活,其子慶節則開始立國于豳,公劉九傳至古公亶父,《史記·周本紀》說:“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2。”他依然靠著農業起家與富國。周族在遷至岐山前,有個長期累積的大問題,就是該族長年與戎狄雜處生活,彼此常有爭執,古公亶父發現忍讓無法換取和平,只得帶領子民由豳移至岐山下,《史記·周本紀》說:“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己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面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古公亶父遷族至岐山下,并不意味著該地沒有戎狄3,但,或許空間較廣闊,周人與戎狄不至于完全混居,使他能開始確立周人本身該有的風俗,而與戎狄的文化做出明顯區隔,包括營建城廓、宮室與房屋,設立各階層政府制度,使周族更擴張立國的規模,讓百姓獲得安居樂業,《史記·周本紀》說:“于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筑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這是周文化接著開始在風俗制度層面突顯出來的文化特征。
二、認識商朝鬼神信仰的形態與內容
商朝的國風就屬于東夷文化系統,這使得商文化有著濃厚的鬼神信仰,其信仰的對象本來包含大自然現象的各層面,例如河神、山神、石神、樹神或日月星辰這些對象都包括在內,呈現萬物有靈論的薩滿教(shamanism)性質,其中居各種鬼神最高的位置就是“上帝”,這是他們最崇敬的至高神,商人的祖先死后就與上帝相伴,《禮記·表記》就曾經對商文化有如此總括性的描寫:“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4。”這表示其整個王朝禮儀的架構,都奠立在對鬼神的崇敬上,這是個率領百姓來事奉鬼神,將神權與王權完全結合,藉此來解釋各種自然與社會現象的國度。早在商朝的開國君主商湯在征討夏桀的時候,就已經反映出他對上帝降給他天命來滅掉夏朝的強烈自信,《尚書·湯誓》記當成湯要準備宣誓征夏,成湯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他還說:“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再說:“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1。”商朝王室相信自己是上帝授權在人間的實踐集團,其依據上帝的旨意,順承天命來統治萬民,上帝會恒久保護商王室,對圍繞在商民族外面的其它全部民族,則都呈現出不仁慈與不庇佑的態度,因為其它全部民族都不是“上帝選中的子民”(the chosen people of God),這使得商人對于“異族”的殘忍變得理所當然2。
這種“血統天命觀”,由商湯開始,就是商王室長期的信仰,這是商文化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可能同樣來自對上帝眷顧著自己的強烈自信,第二十四任商王祖甲后,歷任商王就開始耽溺于享樂,他們不再能體會百姓維持各種生計的艱難,對他們(商王室)來說,反正上帝會保護他們,他們對于百姓的苦痛毫不在意,甚至覺得那就是這些未被選中的子民該承擔的宿命,《尚書·無逸》說:“自時(祖甲)厥后,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3。”傳至第二十七任商王武乙,商朝更加衰敗,再度基于對上帝無條件眷顧的強烈自信,武乙竟然命令做個偶人,戲稱做天神,還命人操作偶人與其打斗,甚至竟然給偶人裝個盛血的革囊,將其仰天而拿箭射破,任其血流不止,并稱此行徑為“射天”,《史記·殷本紀》記載此事說:“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4。”仰賴神權統治的商王朝,其敬天畏神,獲得天命來統治萬民的思想本來甚濃厚,現在卻同樣基于對獲得天命來統治萬民的傲慢,進而發展出對上帝(天神)本身的傲慢,還膽敢“射天”,這種辯證思維卻形同泯滅自己的傳統,當商王室把持血統天命觀無限上綱到極致,“天命”的思維變成“命天”的思維,很難不轉而變成血統天命觀本身歸于崩解,這就引發諸侯各國與其子民的疑慮,該點最主要體現在同個時期,本來是商王室母族的東夷人開始離心離德,轉往淮河與岱山這些中土的地點開枝散葉的經營,政治能量越來越旺盛,因此,《后漢書·東夷列傳》記載:“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5。”反過來看,這就表示武乙時期商王室統御節制的能量越來越衰微,我們從商朝滅亡于夷人叛離的外在原因外,還可進而看出商朝滅亡于思想崩解的內部原因,這是目前可經由文獻考證得知最早有關中華思想發展的紀錄。
據說當周文王打敗黎國,商臣祖伊奔告于商紂王,表示老天已經終止商朝的天命,會告訴人吉兇禍福的大烏龜,現在都不靈驗了,人民沒有不想商王早點死掉,而商紂王卻依舊認為自己生來就有天命,因此不信周文王能奈何商朝,《尚書·西伯戡黎》說:“西伯既堪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何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臺?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6。”商紂王“我生不有命在天”就反映出其血統天命觀的思維,然而商臣祖伊已經看出商朝的滅亡是紂王淫戲人間的結果,老天竟然會放棄一個長期蒙天眷顧的王朝,只因它不被人民接納信賴,可見人事的奮勉才是興衰的關鍵因素,這種理性啟蒙思潮已經是商末社會普遍的共識,并不僅流傳于周國境內,雖然周朝自認能滅掉商朝而得統治萬民是老天對新朝的“受命”(授與天命),但,他們開始體認這個天命沒有德性不會恒常永在,統治者必須要不斷體察民意,否則國脈會重蹈商朝斷滅的后果。《尚書·康誥》說:“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1。”周公還藉成王的命令告誡負責帶領殷民后裔被封至衛國的康叔說:“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2。”杜正勝先生對此表示可見周朝承襲商朝的天命思想,殷人取替夏族而做共主的天命,至此重回周朝的手里3,我們應該能看出周文化在承襲商文化的影響的同時,時人的意識層面已經發生新的巨大變化,由“我生不有命”到“惟命不于常”,這種思潮變化,就可讓我們得見德性天命觀獲得醞釀的源頭。
三、周朝如何架構與發展人文精神
周朝的領導者在剿滅商朝的過程中,就已經在反思商朝滅亡的癥結因素,《史記·齊太公世家》曾經如此記載:“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4。”姜太公相信盡人事不需仰賴天啟,因此強烈建議周武王按照原訂的計劃出征。杜佑《通典》一百六十二征引《六韜》而對此事有更具體的描寫:“周武王伐紂,師至泛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恐而死。太公曰:‘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迎太歲,龜灼言兇,卜筮不吉,星變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眾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5。”這段文字顯示出在面對兇兆,周國大臣間曾經有歧異的意見,姜太公認為重點是周國能尊敬且善用賢人,獲得天下百姓的愛戴,征商的戰爭是順應客觀條件的義舉,不需要再看時日,或假手于卜筮,或跟上天祈禱,自然就會有福蔭相伴;周公旦則認為目前犯太歲,卜筮不吉,這顯示未來會有災難,他希望武王能還師,這卻引發姜太公的憤怒,他覺得商紂王包括對自己的親族大臣都不惜殘害(刳比干與囚箕子),更不要說我們可估計從周文王到周武王,這場戰爭已經籌備與等待多年,對姜太公而言,經由長年經營,檢驗成敗就在此一舉,征商究竟有何不可?干枯的蓍草與腐壞的龜骨如何能測得出這些事實,姜太公因此把它們焚燒摧毀,自己率先帶領軍隊渡河,藉此強化大家征商的意志。這時期的人其實并沒有很豐富的“前人歷史教訓”可作為參考依據(更不要說他們對商朝采取否定的態度),周朝君臣就是真正在“開創歷史”的人,他們的爭論完全可理解,但他們最終能依憑的完全是自身的判斷。
對于文獻記載商周時期人物的歷史,由于文獻本身的晚出,我們應該著重于其人物深層意識的刻畫,而不見得能有效考證其歷史細節真實到如何程度,因為我們的重點在藉由觀看該時期的人物文化與心靈的合理變化,來探索當日社會思潮演變的脈絡。武王是個慎謀能斷的君主,因此能認清商朝已經衰敗的事實,不會因卜筮不吉而讓自己心里就深受影響,漠視自己長期累積的奮勉。然而,重點更在這里描寫出姜太公與周公旦兩人的差異,在于如拿天道與人道做光譜的兩極,周公旦更偏向天道,而姜太公更偏向人道,周公旦深信上天告誡人事的消息,深恐人的不慎受到天的譴責,而重蹈商朝覆亡的結局,寧愿采取更仔細謹慎的態度,觀察每個事情變化的征兆;姜太公則不能被簡化說是站在天道的對立面,他只是相信人的自覺與奮勉才是能否成事的主因,上天果真明察秋毫,就會幫忙更愿意修德納賢的君王,而不會只因卜筮不順,或不賴卜筮指引,就此不幫忙該君王來解救蒼生倒懸的苦。不過,值得注意者:周公旦與姜太公兩人的觀念差異并不是對德性天命觀的認同差異,或該理解為德性天命觀在型塑過程中,針對天如何影響人事的內部差異(這種差異后來影響到兩人各自建立的魯國與齊國的國風,并各自醞釀出魯學與齊學1),再者,盡管周公剛開始采取較傾向于保守主義的態度,后來更因為經歷各種人事的歷練,進而對德性與天命的關系有更深刻的體認,這種個人精神的蛻變實屬不易2。筆者曾覺得姜太公如打開周文化的幅度;周公則保持周文化的純度,然而如果身歷其境展開整體思考,周公旦后來的思維轉變歷程,并不僅在保持著周文化的純度,更同樣打開周文化的幅度。
周武王克商不到兩年就去世,由于去世得太快且猛,周公旦恐怕天下都會對周王室是否擁有天命產生質疑,因此立即替尚在童年的周成王攝政當國,《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說:“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這可看出周王室內部發生裂解,王室成員自己都有人懷疑周朝擁有天命,周公旦為此還特意跟姜太公與召公奭解釋自己暫行攝政的用意,爭取兩位開國功臣的支持,《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說:“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這反映出他對祖先累積的基業有著強烈的責任感,他希望自己臨危授命承擔大任最終能無愧于祖先;就敵對陣營來說,周公旦此舉無異于謀反,立刻給予其“撥亂反正”的機會,《史記·魯周公世家》還記載說:“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3。”會由商紂王的兒子武庚來帶領周王室成員管叔與蔡叔,聯合東夷諸國來對抗周公,就意味著這確實是個“商周誰擁有天命”的對決,如果我們不站在后世的角度來回看當時的政局,純粹由兩大陣營的人馬來觀察,就會發現這的確是個勢均力敵的斗爭,兩大陣營都各自有其“自圓其說”的合法性,就武庚來說,他象征著商的天命,帶領著整個東夷來復商,還有周王室的成員愿意“幡然悔改”來順應天命,這樣的陣容營造的聲威,絕對會給剛創國的周朝帶來極大的心理威脅。就周公旦來說,盡管他有姜太公與召公奭的支持,確立自己暫行攝國的合法性,然而周朝是個根基并不穩固的新興政權,其尚未藉由實際的作為,跟天下子民證實自己擁有天命,天下子民盡管對于商紂王的暴虐心有余悸,然而商紂王畢竟已死,如果其兒子武庚能表現出擁有天命的自信,并且對外宣示自己會表現出相較于商紂王完全不同的作風,天下子民未嘗不可能動搖意志,轉而相信天命依舊在商朝,并轉視周王室為“叛亂集團”,因此,在周朝的國祚正搖搖欲墜的時刻,周公旦如果沒有發掘出有關于天命的嶄新論點并付諸實踐,周朝極可能就會在轉瞬間歸于覆滅。這就是周公旦要提倡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外在現實背景。
面對著“武庚復商”,商王室的后裔高舉著天命在商的主張來大舉復辟;再面對著“卜龜失靈”,周王室對無法正確跟上天溝通深感憂慮,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周公旦處在進退維谷的僵局里。或許是患難使人成長,周公旦能不顧時人的猜忌,緊急宣布接替尚在稚齡的侄子成王攝政,這固然反映出他決策的果斷,他的兩個弟弟管叔與蔡叔,本來是負責監管殷遺民,卻聯合商紂王的兒子武庚叛亂,不論他們是害怕如同兄長般遭到“天譴”短命而亡,或出自個人私利的意念(不滿周公旦掌握大權),他們跟著武庚在東土興風作浪,其行徑自有合法性與號召性,這使得周公旦不得不率師東征,出兵掃平內亂。《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衛,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4。”這應該是中國歷史里空前未有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周公旦不僅親自帶著部隊出征,還帶著大量的周族人民前往拓墾,每平定一個區域,就由周人帶著殷遺民共同實施農耕,冀圖徹底改變善于游牧的商人的漂泊性格,這種拓墾工作顯示出周公旦想從生活型態徹底轉變商文化的態度。這個大規模的戰爭與拓墾工程極為辛苦,周公花費近三年時間才完全穩住局面1,他殺掉武庚與管叔,流放蔡叔,設立東都雒邑,再立商王室的后裔微子啟與衛康叔,命其帶領剩余的殷遺民,前者建立宋國,后者建立衛國,讓他們保存對商朝祖先的祭祀,而不是將遺民變成奴隸。該仁政固然反映出周公對商周共同擁有的祖先信仰的尊重,更反映出周公體察出這個道理:他不能只是征服人的國,卻沒有征服人的心!往更深層來看,周公沒有那種基于血統的傳承來獲得天命的自信,又無法依循本來的靈性路徑來探索上天的真實意旨,長期都處在既有的內外層面都瀕臨絕境的關頭,他最堅固的精神信靠,就是自己含藏不滅的良知(盡管當時還沒有這個詞匯來稱呼),這意味著他只能往自己生命的內在挖掘,確認并落實自己的誠意,來摸索出上天可能會有的指引,身為統治階層的首腦,最重要的工作莫過于構思創國藍圖,將其落實社會,帶給天下諸侯與子民美好的生活,由此開拓出德性的傳承,這就是他能確認自己把握住天命最踏實的辦法,如此才會設計出“治禮作樂”的各種制度。周公率先引領出的天命型態,已經跟過去完全不同,因為生于憂患,使得周人開始發展出“天命靡常”的道理2,他們相信只有蓄積與擴張統治者的德性,并藉由這德性開啟的智慧,施加善政于百姓,統治階層才能確認恒常蒙受天命的眷顧,經歷長年的激烈斗爭,“德性天命觀”最終取替“血統天命觀”,指引中華文化邁往新的里程碑。
四、中華文化的理性化歷程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在其撰寫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中指出,在公元前800~200年間(相當于西周宣王十八年至劉邦稱帝(202 B.C.)前二年),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心時期”(axial period),在此期間,世界有四個互不相干的區域——歐洲、中東、印度與中國共同邁往哲學的黃金時期,這些地區產生蘇格拉底、耶穌、佛陀與孔子四位圣哲,直至今天我們思考的基本范圍依然在他們闡發與確立的思想體系內,人類精神仰賴存活的世界宗教,其源頭同樣在該時期獲得創立(主要是指基督信仰與佛教信仰)。雅斯培指出軸心時期最大的特點就在神話時期從此消失,人類學會用理性思考與闡明問題,尤其懂得學會理性來反對神話的虛構性。這個時期的人開始思考“自身和世界”的關系,他們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與自身的限度,更意識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他們想知道這些事物存在的原因,于是開始探究根本性的問題,使得哲學家首度出現在軸心時期,人類意識到精神的能量,讓他們敢于依靠自身,衡量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人在理論思辨中空前意識到自我的可貴,這種體驗宛如在上帝體內的蘇醒,透過思辨領悟到上帝的旨意,這使得人開始有后世理解的那種個性。軸心時期對人類來說最重要的在于精神能量從此在人類社會中具有重要的影響,軸心時期文明與此前的古文明最大不同點莫過于其象征人類意識的覺醒,人類在這一時期架構新的歷史秩序,并長期靠著軸心時期產生、思考、創造的資產而獲得存在3。
雅斯培的看法固然自有其道理,然而征橥史實,中國的軸心時期或許可謂由孔子發揚光大,并引發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思潮,然而其樞紐轉變并不在東周時期,而在西周時期,尤其在商末周初的草創階段,中華文化的理性化源頭實可謂來自西周由文王到武王,最終因周公旦獲得確立的人文精神,周公旦與孔子對比,顯然前者置身的政治位置與開啟的文化意義,比后者更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商末周初在面對至高的神圣信仰,商朝與周朝已有著細微的不同,這反映出華人靈性思想的深刻變化。原本商王室特別看重“禘”(就是上帝),在周王室則轉而特別看重“天”(就是上天),由上帝轉至上天,同樣都是宇宙終極的存有,人對其賦予的含意卻大有不同。上天相較于上帝,其意思反而變得較模糊,但范圍卻變得更寬廣,這就來自前面指出周王室面對“卜龜失靈”產生的挫折感,他們并沒有徹底否認天意的存在,只是如同后世鄭國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1,天道難測,只能藉由把握住人道來體察天道,因此,周朝推翻商朝,不僅是政權的改換交替而已,“轉禘成天”作為樞紐蛻變,更意味著中華文化從此由“鬼神的信仰”邁往“人文的信仰”,意即對人文精神有著如信仰般的堅持,征諸商王室凡事都要靠卜筮問上帝才能做決策,他們相信上帝只保護同樣血緣的商人,結果卻依然不能免于亡國,周王室已自覺不能再如此盲目信仰鬼神,而得要更真實去面對上天含藏的義理,他們感知出的上天會保護全部的子民(不僅是王室與貴族這些統治階層),尤其會假手于人自身的奮斗,來間接照顧人現實的幸福,這使得殺人殉葬的習俗逐漸消失,象征著中華文化首度破除蒙昧,展開理性化歷程,才能有后世孔子開啟的儒家思想,這個歷程帶來最劇烈的影響,莫過于使中華子民變得更務實于人事經營,不再懷想輕易獲得上帝無條件的救贖,雅斯培有關軸心時期的說法,顯然受限于文化隔閡,無法涵蓋與理解由“上帝”轉至“上天”這層轉折的重大意義。
或許我們還可換個角度來理解:周人在克商后,要給周朝取替商朝的事實得到政治的合法性與宗教的合理性,逐漸將上帝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具有道德判斷意志的上天,由該最高仲裁者來決斷人間世事,因而會有所謂“天命靡常”的說法,上天不再是無條件的降災賜福,反而是有選擇彰顯其強大的能量,因此,這不見得是削弱天的意義,反而是更深層的強化2。人文的信仰雖然把上帝的無上人格拉往凡間,卻否認上天的存在,而是承認人間的問題最終得靠人自己運用智慧去解決,只靠卜筮或賄賂的辦法乞靈于鬼神,自身不實際正視問題并奮勉于人事,則鬼神依然不會保護人得享天命。《中庸》第十四章說:“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3。”這個“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鋪陳在這里就特別有意思,人文精神雖然產生于探索天意的挫折感,卻不是要人對天產生怨懟,更不需要對經營人事的困難有任何指責,重點就在這個“居易”,安于自己的位置或情境,踏實去奮勉,則天命最終會自然降臨人身。周公領悟這層義理,設計出“制禮作樂”的人文建設大工程,讓人透過在社會知禮習樂而通天意,這個作法長期影響華人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他把奮勉的對象由天轉至人,而且奮勉的過程來自誠意面對政事,招徠各類賢人共同輔政,架構出具有文化視野的盛世,《史記·魯周公世家》記當周公先派其子伯禽就封于魯國,周公并特別叮嚀伯禽:“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無以國驕人4。”沐浴會三度散發,吃飯則會三度吐食,在在顯見周公流露著求賢若渴的情懷,唯恐沒有賢人來支持國政,“賢人佐國”從此成為中華王朝系統獲得確立的核心支柱,這點同樣影響后世會特別看重政治良窳對社會風俗的意義,使得人文精神常藉由士人參與政治的程度來獲得彰顯與體現,并構成支撐中華文化的“士人倫理”。雅斯培研究四大文明的重要思想家后,選出蘇格拉底、耶穌、佛陀與孔子四位圣哲作為人類的典范,他覺得這四人的偉大正在于見證人類精神的豐富潛能,并覺悟人類存在的尊嚴,然而殊不知當我們置身在不同宗教信仰引發文明劇烈沖突的當前時空背景里,周公旦離開濃郁的鬼神信仰,替中華文化開啟人文精神,更彰顯著人類精神的豐富潛能,引領著世人覺悟存在的尊嚴。因此,筆者總結指出:中華文化共經歷三回具關鍵意義的理性化歷程,第一回理性化歷程就是前面由周公開其端到孔子總其成的理性化歷程,這是人文精神的萌芽階段;第二回理性化歷程則是在宋明儒學發展時期,由周敦頤開其端到王陽明總其成的理性化歷程,這是人文精神的深化階段;第三回理性化歷程則可由這百年來中國正經歷未曾有的千古巨變來檢視,如何將傳統中華學問轉型出適合于當前環境的本土社會科學,實屬我們從事學術工作的關鍵課題。當前社會正受到資本主義帶來物質主義(materialism)的劇烈牽引,人被異化成創發各種產能的螺絲釘,人的生命價值低落,人文精神沈淪不彰,如欲恢復人文精神,則應該首先對由商朝的鬼神信仰如何轉型出周朝的人文精神有清晰認識,對照當前人類文明正因不同宗教信仰引發無窮戰爭與人禍,緬懷前人創業維艱,或能體會中華文化特有的人文精神背后深藏的理想與意義。
Survey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re Changing -from Shan Dynastys Ghoast Believe to Zhou Dynastys Human Spirits
Chen fu
Abstract:From the view of four civilization,it is easy to find that form the earlier time,Chinese culture developed from ghoast belief to humanity ones.This key changing is coming from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mbining between Yi and Xia clans long ago. From Xin Si Qi period,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ways are quite obvious.It always goes through heated military conflict to decide who are the rul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Shang Dynasty,the resourse of clans and cultural keeping is from Dongyi Clans.Ghoast belief is the main meaning of Dongyi clans,whose main belief is the God,The ruler of Shang firmly believed that their power was coming from the authority of God. Inspite of the uncomfortable treating towards their People later on,a lot of clans continued to do rebellion against Shang,King Wu Zhou led his army to defeat Li country which belongs to Dongyi,King Shang could not believe that King Zhou would defeat him. When Zhou struggled to Chaoge to wipe out Shang,this fact began to devide the ideas of Gods ideas,Hua began to realize if any rulers can not care for his peoples happiness, The heaven would not care for him,too. To make a firm rule and its rationess,it must be in the moral deeds(not in the heavens ideas or blood inheritage.)From Zhou Dynasty,it began to have Moral and heaven concept together. In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ilishment,the rulers thought that the firm stability of Gods idea is strongly worrying concept.It made the wiping out of Sha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Zhou,which is not only the changing of the dynasties,but also the chang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s.The culture of Zhou is the source of Chinese humanity spirits. Its enbodyment is in spite of believing the God,but not believing the ghoast,People believe their own stuggles,which is the main success of the people.It began to spread the rational process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Humanity spirits,Ghoast belief,Moral Heaven concept,Blood relationship Heaven Concept, Rational process
1 見陳復《先秦齊文化的淵源與發展》,第一章〈東夷族與商文化對先齊文化的影響〉,第一節“文獻里的東夷人生活”,第32~36頁。
1 見《春秋左傳注疏·昭公二十四年》卷第五十一,《十三經注疏》第六冊,臺北:藍燈文化出版公司,公元1995年,第885頁。
2 見《逸周書·明堂》卷六,第五十五,朱又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國學基本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公元1968年,第100~101頁。
3 見陳復《先秦齊文化的淵源與發展》,第一章《東夷族與商文化對先齊文化的影響》,第四節“東夷人與商人的淵源”、第五節“商王朝在齊地的經營”與第六節“夷與商共釀的風俗”,第45~59頁。
4 見(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二,《夏本紀》第二,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年,第41頁。
5 見《尚書正義》卷第十四,《康誥》第十一,《十三經注疏》第一冊,臺北:藍燈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201頁。
6 見《尚書正義》卷第十六,《君奭》第十八,第247頁。
7 見《尚書正義》卷第十七,《立政》第二十一,第261頁。
8 王明珂先生表示:“由于農業與畜牧的不兼容以及因此造成的資源競爭,使得定居與移動、農業與畜牧逐漸成為人群分別‘我們與‘他們的重要根據。公元前1300年至1000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逐步東進打敗商人,并以分封諸侯將其勢力推廣至東方。這時華夏邊緣仍不明顯;沒有一群人自稱華夏,而周人的西方盟邦中還有一部分是相當畜牧化、武裝化的‘戎人。克商之后的周人越來越東方化,相對的在他們眼中那些舊西方盟邦就越來越‘異族化了。公元前771年,終于戎人與周人決裂,周人因此失去渭水流域。”見其《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七章〈華夏邊緣的形成:周人族源〉,臺北允晨文化公司,公元1997年,第188頁。
1棄與禹同時,他或許即是在面對禹建立夏朝,已然讓夏人蔚然獨立于黃帝民族外,致使黃帝民族中衰,為化解黃帝民族的危機(那不只是政治危機,還包括經濟危機),故而帶領周族全體向夏族學習農業的關鍵人,其子孫則繼承遺策,不斷推動著「全盤夏化」的治國要略。筆者估計這是《周本紀》要特別強調他善于農事的原因。
2 見《史記會注考證》卷四,《周本紀》第四,第64~65頁。
3 還有混夷(或名昆夷,犬夷,犬侯),見杜正勝先生《古代社會與國家·封建與宗法》,《周代封建的建立(上)》,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年,第335頁。他認為周太王能在岐下立足,同樣靠著武力與混夷斗爭而獲取土地,其引《詩經·大雅·綿》的原文說:“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駿矣,維其喙矣。”意即無能殄絕混夷的慍怒,同樣不敢廢其聘問鄰國的禮節。筆者揣測這種處境應該要相對而論,如果情況并不比來岐山前來得好,那舉族遷居就沒有實質意義。因此,合理推測岐山的生活空間尚能容許兩族各自獨立發展。
4 見《表記》,《禮記正義》,臺北藍燈文化出版公司,《十三經注疏》第五冊,1995年,卷五十四,第915頁。
1 見《湯誓》,《尚書正義》,臺北藍燈文化出版公司,《十三經注疏》第一冊,1995年,卷八,第108頁。
2 見陳啟云:《“儒家”、“道家”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中的定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歷史論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18~119頁。
3 見《無逸》,《尚書正義》,卷十六,第241頁。
4 (日本)瀧川龜太郎注《殷本紀》,《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公元1986年,卷三,第60頁。
5 (東漢)班固《東夷列傳》,《后漢書》(四),臺北:鼎文書局,公元1994年,卷八十五,第2808頁。
6 見《尚書正義》卷第十,《西伯戡黎》第十六,頁144~145。
1 見《尚書正義》卷第十四,《康誥》第十一,第201頁。
2 見同上,第206頁。在《詩經·大雅·文王》的詩里,同樣訴說著周人‘天命靡常的想法:‘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見《毛詩注疏·大雅·文王》卷第十六,《十三經注疏》,第二冊,公元1995年,第535~536頁。
3 見其《古代社會與國家》貳“國家起源與發展”,“夏商時代的國家形態”(下篇),第251~254頁。
4 見《史記會注考證》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第二,第550頁。
5 轉引自《史記會注考證》,見同上,第550~551頁。
1 見陳復《先秦齊文化的淵源與發展》,第二章“姜太公封國于齊面臨的處境與應變”,第四節“姜太公因應夷俗的改革”、第五節“統治兼顧理想與現實”與第六節“姜太公與周公旦的異同”,第81~96頁。
2 見陳復《周公制禮作樂的背景與影響:氣候生態的變化與人文精神的發展》,《孔孟學報》,第八十九期(2011年9月),臺北《孔孟學報》編輯部,第363~386頁。
3 瀧川龜太郎注《魯周公世家》,《史記會注考證》卷三十三,第566~567頁。
4 瀧川龜太郎注《魯周公世家》,《史記會注考證》卷三十三,第567頁。
1 關于周公東征的整體時間,瀧川龜太郎說:“《書》曰二年,《詩》曰三年,一以月計,一以歲言,其實同耳。”同前注。
2 《詩經·大雅》里有《文王》詩說:“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文王》,《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第535~536頁。“天命靡常”這個觀念使得人文精神因此滋生,這并沒有因其不斷變化而否認“天命”的存在,反而是透過人在世間的奮勉來確認自己獲得“天命”,這是人的主體意識的首度出現,使得“天人合一”的思維型態從其間獲得孕育與發展。
3 雅斯培《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與俞新天譯,第一章《軸心期》,北京華夏出版社,公元1989年,第7~14頁。
1 見《昭公十八年》,《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八,第841頁。
2 見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第二章《殷商及西周時代之宗教信仰》,臺北麥田出版公司,公元2004年,第53頁。
3 見《中庸》,《禮記正義》卷三十一,第915頁。
4 見《史記會注考證》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第三,第5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