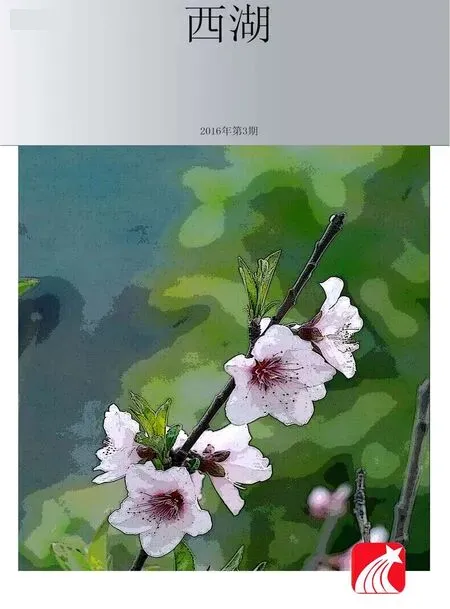自傳與公傳:一九七九(四)
董學仁
自傳與公傳:一九七九(四)
董學仁
有些詞語就是歷史
順著一條坡路上山,順著一條坡路下山,需要兩三個小時。路是戰備年代的柏油路,不寬,把一大片風景區割開。這不叫登山,叫遛山。
身邊是老顧、老劉、老李,三人加我,都是在媒體干了多年的人,五十多歲,再幾年退休。周末遛山,議論時事,打撈歷史;下山時臨近中午,去一家粗糧飯店喝酒后,微醺,各自散去。
有一次下山,我忽然指向一個小男孩,“看這孩子,多年輕啊。”他們看見小男孩胖胖墩墩,兩歲左右,就都笑了,說我幽默。我是當正經話說的,沒想到幽默,可是從活到這個年齡段有些文化的人看來,已經是幽默了。可見,幽默有多種,而身邊有頭腦反應挺快、人生感慨挺多的朋友,是件好事。
老劉說起一件事,我覺得更幽默。
1979年,老劉說。
有個人叫年廣久,開始雇工人炒瓜子。他的傻子瓜子出名了,小作坊擴大到十二個工人。這時就有人打個報告,送到國家最高層,說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有個著名論斷: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
沒人敢懷疑馬克思寫得不對,即使懷疑有不對,也沒人敢提出來。老劉說,傻子瓜子給中國的改革理論出了個難題。
老劉說,讓不讓傻子瓜子再干下去,要不要把年廣久抓起來,北京討論了好幾次,也沒出結果。后來最重要人物知道了,拍板說先不處理,放一放,看一看。
馬克思真寫過這句話?
有人說有,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雇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八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是資本家。
有人說,這是生搬硬套,并非馬克思原意。資本家與小業主的區別,雇工數應該大大超過八人。其實馬克思也說過,他的有些數字是隨意假設的。
還有人看了那一章,說是一段繁瑣的計算和表述,繞著圈子,沒看明白。
這樣一來,中國形成了“七上八下”的雇工理論:雇了七個工人,還是社會主義;如果雇了八個,是資本家。由此還造出兩個中國人能明白的新詞,一個叫“個體戶”,雇工七個以下;一個叫“私營經濟”,雇工八人以上。
“私營經濟”這個新詞,替代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舊詞,也替代了幾千年經濟變化的民族歷史。
后來我才知道,關于雇工的事,以及年廣久的事,都比老劉說的復雜。
上世紀五十年代,自古以來的私有經濟被摧毀,雇工成了剝削,在中國消失。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公有制經濟大崩盤,按照官方說法,改革開放開始。1979年,廣東農民老陳承包了八畝魚塘。1980年,高層官方文件再次重申不準雇用工人。1981年,老陳魚塘規模擴大,雇工五人。
這觸動了一根敏感的神經:在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允許剝削雇工?
老陳的事,北京的報紙討論了三個月,發表文章二十一篇,還有高層官員去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考察雇工,看見雇工現象世界各地都有;問題是要有個合理的解釋。
這次討論和考察的最大收獲,是理論家從馬克思那里推導出“合理的解釋”:八人以下叫作“請幫手”,八人以上就叫“雇工”。八人以下不算剝削,這成為社會主義正統的政治經濟學標準。
此后出現了傻子瓜子雇工十二人,忽然之間成為理論上的資本家。人們開始傳說,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
年廣久是個文盲,只會寫自己的名字。他七歲在街上撿煙頭掙錢,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二十六歲因投機倒把罪判刑一年。那種投機倒把罪是個“口袋罪”,可以裝入許多種商業活動。當年賣水果不賺錢,他去販魚,就犯了投機倒把罪。二十九歲那年又因為販賣板栗被抓。如果這一次年廣久因雇工出了事,也會以投機倒把罪論處。
好在有高層最重要人物為他說話,這一次沒進監獄,還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年廣久學乖了,1984年向工商部門提出聯合經營,蕪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掛牌,離資本家的身份也遠了一些。
在官方政策上真正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制,還要等到1987年。在那年的高層官方文件中,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被徹底放開。但在1989年底,雇工問題又有反復,私營經濟來了真正的麻煩。年廣久又去坐牢,將近半年,那案子拖了兩三年,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證據不足,判了個流氓罪。有趣的是,再過半年左右,高層最重要人物去南方巡查時,重提傻子瓜子不抓更好的往事,消息傳來,年廣久無罪釋放。
有時候法律并不是法律,但是,人不能免于恐懼。
年廣久的聯合經營,以及許多人把自己出資經營的私人企業掛在公有體制下面,都是為避開“資本家”和“剝削者”身份的做法,通行全國,俗稱為戴“紅帽子”。但他們遇到了更大的麻煩,比如河北老馮。他辦了一個戴“紅帽子”的商店,資金、經營權都是自己的,用掙來的四萬多元還了貸款,被當地法院以詐騙、貪污罪判處死刑;當了三年死囚后,才被最高法院無罪釋放。
那幾年,這樣的黑色幽默,也太多了。
有個組織,叫作“打擊經濟犯罪工作組”。他們到處巡視,如果見到一座新建的三層樓,看著氣派,馬上會想到經濟犯罪:這戶人家不搞資本主義,能蓋這樣的樓嗎?據說1982年,浙江省某市“供銷大王”李某被抓捕的理由,最初只有一條:“將軍也沒有住上這么好的房子。”
上面說的這些,有的已經被遺忘,有的正在被遺忘、終將被遺忘。
那時到現在,還沒過幾十年呢。
雇工、“紅帽子”、流氓罪、“七上八下”、掛靠企業、私營經濟、個體工商戶、投機倒把罪,等等,它們支配社會的時間短,參與歷史的時間也短。
在很多時候,詞語就是歷史。有些詞語沒人打撈就沉了下去,它們只能被人們遺忘。
還有一個詞語,剝削,也會被遺忘的。這個詞語讓人類吃盡了苦頭。有了資本剝削工人的理論以后,社會被分成剝削和被剝削兩大陣營,就有了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兩大階級陣營斗了一百多年,喪失了上億人的性命、十數億人的幸福。
按理說,剝削是在資方強勢、勞方弱勢時才有的,而雙方互相制約、趨于平衡才是常態。為了建立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那些仁人志士以及流氓無賴,合力建了新型社會,極度壟斷,沒有競爭,就產生了更大的危險和沖突:資方即政府,獲得了絕對強勢;勞方淪陷了,處于絕對劣勢。
方向錯了,離開原定目標的距離更遠。
這時候,再討論關于剝削的概念、判斷和推理,討論它們是否正確,已經多余。
但我需要知道,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國完全進入市場經濟,實現了按要素分配報酬,我能分配多少?在這方面,我讀到一位中國學者的形象比喻。
他說,在閉合串聯電路中,如果串聯有若干電阻,那么根據阻值不同,每個電阻分得一部分電壓,加起來就是總電壓。假設我們把從商品或服務的生產直到滿足人的需求看成一個閉合電路,而勞動、管理、資本、銷售、消費等環節都看成是一個個電阻,這些環節其實就是要素,每個要素所得的分配就相當于電路中分得的電壓。
他還說,就像在電路中電壓分配是自動的,在市場經濟中,各要素分配的多少是市場自發實現的。誰來享用、享用多少,實際上由市場說了算。
我就想起曾經是我同事的老張。有一天,他覺得自己被人剝削了,就去自謀生路,當了老板。當了兩年,效益還好,他又發現當老板沒有休息的時候,下了班都得想著經營,賠了錢得自己承擔一切后果,就覺得他被員工剝削了。于是他又去給別人打工,下了班自由自在,沒有壓力,到月底拿固定的薪水。
聽他講起他的經歷時,總躲不開“剝削”這個詞語,但語氣還是很快樂的。
要看秦始皇焚的什么書
大學生活的第二天,我多了一個壞習慣。
新教材發下來了,十多本,在宿舍床上攤開;看完目錄,再翻到后面隨意看看,就覺得那幾本教材太糟啦。
我曾在西長甸廢品收購站里找到一套唯物主義哲學教材,是前蘇聯大學教科書的中譯本。它的敘述簡潔,明確,層層遞進,關系分明;新出現的概念都用黑體字印刷,還在頁底注釋附上完整定義,以及與相關概念怎樣區分。那是一本很想讓人看懂的書。我不是特別喜歡唯物主義,但在那年月,書店里差不多都是毛澤東著作,找一本能讀進去的書挺不容易,于是,那套教材我讀得相當認真。
新發下來的那本唯物主義教材,內容陳舊,語言枯燥,沒有重點,想說的事情說不明白。我可以預料,學了新教材后,我先前頭腦里明白的東西會糊涂,清澈的東西也會渾濁。
想到這里時,北面的窗子開著,我的手腕稍一用力,新教材就飛起來了,落在窗外看不見的地方。
北窗外是荒草叢,不擔心砸到人。但課程還沒開始,教材先扔出窗外,這可不是個好習慣。
接著扔出去的是形式邏輯學教材。
大約一年前,我讀過一本《故事里的邏輯》,還記得其中很多故事。比如,有個故事說,在古希臘,人們有什么疑問會找到哲人請教。有一個人淹死在水里了,死者家屬要向撈尸人買回遺體,問哲人能不能少花錢。哲人說,撈尸人只能把這具尸體賣給你,你是唯一的買主,盡管壓價。他們走后,撈尸人來了:尊敬的老師,我能不能把撈到的尸體高價賣給死者家屬?哲人說你盡管抬高價格,死者家屬在別處是買不到的,你是唯一的賣主。后來那具尸體賣了多少錢,那本書沒有說,說的是與邏輯相關的問題,比如一個人對待同一件事物,作判斷時要前后同一,不能矛盾。
我記憶中那本藍色封面的書,與新發教材相比,章節大體一致,內容更多一些,還包括了詭辯論的常用方式,以及怎樣戳穿它們。我打開新教材讀了一章,眉頭皺了起來,心想還是不讀它更好。它也舉了一些實例,幫人理解各種原理,但是,如果它的實例不夠生動,編寫時的邏輯思路也不明晰,我為什么要受苦遭罪地跟著它重學一遍?
它很快就飛過開著的窗子,找那本唯物主義哲學教材作伴去了。
還有一本心理學教材,也這樣飛走了。
沒有教材也不影響上課。第一學期就開了心理學,老師梳著短發,四十多歲,講課頭也不抬,讀著教材,像是大會發言。但我還是喜歡這門課程,下課時跟老師說,想去她家里借書看。
老師的家在學生食堂與學院衛生所之間,從教學樓出來幾分鐘就到了。她用鑰匙開門,告訴我在門外等幾分鐘。從開著的門里,我看見她拉起書架的布簾,用笤帚掃起一大片灰塵。灰塵飛落之后,我就可以進去了,彎下腰在她的書架上挑書。那是個比較小的書架,即使擺滿了,也只能容納一百多本,與我想象中大學教師的書架,有著挺大差距。
我想挑的是介紹國外心理學的書籍,普通心理學也好,社會心理學也好,文藝心理學也好,都會對我的心智有一些啟發。在我的想象里,那些書籍不會像國內教材那樣,空泛,刻板,小心謹慎,大部分用來詮釋革命導師們并非心理學的觀念。要是有介紹弗洛伊德的就更好了。讀大學前,我已經找到一些論及弗洛伊德學說的文章,雖然用的是批判性口吻,仍然可以從它們引用的片斷里,看到被批評者的深刻。我是書店里的常客,遺憾的是,在我上大學那年,弗洛伊德的專著還不能出版。
從老師家里出來,我沒有帶走一本書。
那天中午稍過,我去了心理學教研室主任的家。有人指給我看,主任五十多歲,穿著白色襯衫,正在一棵樹旁下象棋。本來他們坐在樹蔭下,但日光不停移動,他們已經曬在陽光里了,滿臉汗水。我對象棋也有很大興趣,就在旁邊為他支招,我想如果他的那盤棋贏了,就愿意借書給我了。
教研室主任的書多一些,也沒有落著灰塵。
我仍然沒有找到想看的書,但是弄明白了一點,我想看的書,教研室主任在他的大學時代也沒有讀到。那時候新政權建立了,不允許舊政權的任何思想傳播,同時關閉了國門,與外國的學術思想不再往來。
我借走了他大學時代的課堂筆記,那是他二十多年前一筆一筆寫下的。他的老師講課,一定還留著舊時的影響。
他的老師的老師,上課是不需要教材的,想講什么就講什么,沒有障礙。
在我的回憶里,不止一次地提到西長甸廢品收購站,是因為我對它充滿了感激。我是那家收購站里不占編制、不拿工資的美工,唯一的酬勞是允許我翻揀它收購來的舊書,想看什么就帶回家去。
那些年月,階級斗爭波濤洶涌,大學關門了,圖書館關閉了,出版業受到嚴格控制,但我找到了一條通道,與先前的時代連接起來。這通道就是廢品收購站里的舊書。
離開中學校門,再走進大學校門,這中間有七年時光,可以讀書。
我學會了怎樣用比較短的時間,從西長甸廢品收購站小山一樣堆積的舊書里,挑出有價值的好書;這是一種經驗,要看過很多不該看的書,才能養成。于是,我在1979年跨進大學校門,首先發現的不是可以看的好書,而是不該看的壞書。
記得有句名言說,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
這句話是錯誤的,只有好書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壞書不是進步的階梯,而是退步的滑梯,能讓人類迅速倒退到愚昧時期,并且比先前所有的愚昧更甚。我記得這句名言是高爾基說的,這就更不能原諒了,他所處的時代,壞書已經開始驅逐好書,危害他的國家,并且蔓延出去,成為人類退步的滑梯。如果他算得上作家,應該是能看清楚的。
在我讀大學之前和之后的好長時間里,一直不把教材當成書,但它確實是書,所以也有好壞之分。簡單一點來說,凡是那種大學統一教材,規定整個國家都要使用,并且從講師到教授,講出違反教材觀點就要受到處罰的統一教材,基本上都不是好書,因為它們殺死了眾多的思想,只留下一種思想。
唯一的思想不是思想。
這可能是從秦始皇那個年月開始的,把先前留下的好書燒掉了,只留下自己編寫的東西。
我在先前的回憶里,寫過這樣的觀點:人生都有不幸運的時候,有的人甚至一生都不幸運。他們即使讀了大學或者讀完碩士博士,也僅僅學到一些知識的皮毛,沒有形成自己的學問,甚至沒有從狹隘、偏見、歪曲和有害的知識中掙扎出來的本領。他們沒有走到正確的方向,對人類的進步沒有益處。
作家關注的僅僅是人
越戰退伍老兵,甚至越戰還沒有結束,就成了一個名詞。
他們身心疲憊,厭棄戰爭,懷疑這世界上還有崇高,還有正確,懷疑他們只是時鐘上的指針,指示著別人規定的時間,而他們自己,不經常被人注意,很容易被人忘卻。有時,我寫到忘卻這個詞,忽然覺得中文里的這個詞,可能具有愿意忘記和主動忘記的意思。
在我看過一些越戰電影后,最初的感覺就是這樣,并且以為越戰退伍老兵,是從越南戰場回來的一批美國年輕人的專有名詞。
后來我終于發現,這個名詞的外延更大一些,還包括了從越南戰場回來的一批中國年輕人。發現這一點時,已經太晚了,他們差不多進入了老年人的行列。
我是在他們散亂的回憶里發現他們的。按越戰退伍老兵的數量來說,他們是不愿意回憶戰場的人。如果那場戰爭確實像他們感受的那樣,你讓他們怎么回憶往事?
比如,你怎么讓名叫李健的越戰退伍老兵,回憶他被自己人的槍彈擊中,然后又被戰友們當死人埋葬的往事?
他的一名戰友,在回憶中寫到了一場暗夜里的烏龍戰,先寫的不是李健,而是另一名年輕人:“也許是受到戰爭的驚嚇,加上神經的高度緊張,不一會他又把身上的四顆手榴彈全部投了出去,不知炸死了多少戰友和民兵。發現情況不對,睡在我左上方幾米遠的團長聽到是自己人在打自己人后,馬上氣憤地站起來大喝一聲:你們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趕快停火!”
“如再打幾分鐘,我們必死無疑。”戰友接著寫道:“停火之后,我們發現團部的李健(排級干部)受傷嚴重,子彈從臀部進去,從肩膀出來(當時是在睡覺),因流血過多、暈死過去,我們以為他犧牲了,就把他用雨衣包好后(面向中國)就地埋葬了。天亮之后,部隊準備出發,繼續突圍。由于沒有發現敵情,團長就叫各連和民兵把昨晚傷亡的人員抬走,包括尸體。誰知,李健被挖出來后還沒死,兩個民兵把他抬了回來。至今活著,只是走路有點影響。”
他們那批老兵,有許多故事至今難忘。
某位烈士的眼睛一直不肯閉上,無論戰友怎么用手抹他的眼睛,他總是不肯瞑目,戰友們急得都哭了。后來,烈士的一位老鄉來了,對著烈士遺體說:“兄弟,你放心地去吧,你的老娘就是我的親娘,我會伺候她一輩子的。”戰友再去抹他的眼睛,烈士就閉上了雙眼。
有越戰退伍老兵回憶,他們殺死了一名越軍女兵。
“這個越軍女兵最后坐在一塊石頭上再也跑不動了,我們圍在周圍,先叫翻譯喊話,勸降,可她非但不投降,竟然從衣服里掏出一支手槍放在腿上,既不走也不開槍。她就這么坐著不動,瞪大著眼睛,滿頭大汗又驚恐地看著周圍。”
他寫道:“走近仔細看清楚了,她有二十五六歲的樣子,相貌一般,腹部隆起,從氣質和神態看,應該是越軍部隊里的一個女干部。大概是因為懷孕沒法隨部隊突圍,被留在山上。”
戰場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現,但是誰愿意殺死懷孕女兵?那名老兵說,從她腹部隆起的程度來看,腹中胎兒有五六個月大了。
“勸她要想想肚子里的孩子,還把干糧水壺都扔給她,她也不吃。不管我們如何苦口婆心,費盡口舌,把嗓子都喊啞了,她就像聾子一樣,軟硬不吃。大家漸漸都失去了耐心,最后由翻譯向她提出了最后警告,結果她仍然不肯投降。”
老兵的回憶錄還說,戰場有戰場的規則和底線,既然一個有武裝的敵人不肯投降,也就只好擊斃了她。子彈都打在她的頭部,沒有一個人愿意打她的胸腹部位。
作為一個有經驗的寫作者,我在這名老兵的文字中看出他的痛苦。許多年后他會懷疑,這樣的戰場規則和底線是不是對的?
可是在戰場上,你沒有懷疑的時間。
一名退伍老兵回憶說,“當我們走到一個院子中間時,一個七八十歲的越南老頭拄著拐杖晃晃悠悠地從室內走了出來,用手揮動著向我們示意,可能是叫我們不要打他,他沒有武器。突然,室內沖出一個老太婆掏出一顆手榴彈向我們扔來。走在最前面的團部盧干事當場被炸死,幾個戰友受傷。走在前面的戰友沒想更多,端起沖鋒槍,一梭子彈全打在老兩口身上,那老頭和老太婆當即斃命。隨后,我們一同前往屋內搜查。在搜查中,我們驚訝地發現,室內機槍、六○炮、地雷、手榴彈等常規武器樣樣都有,大家被嚇壞了。”
還有人回憶,一個只有十三歲的越南少年,扛著蘇聯人提供的武器,打毀了中國軍隊三輛坦克。隨后,那少年被打死。
讀了這些回憶,我覺得,人類應該坐下來討論一下了。
未成年人、懷孕女兵和七八十歲的老者,在某些國家被允許、鼓動和組織起來加入戰爭,這應該被禁止,人類的傷亡才會小些。
亞非兩洲的戰爭規則和底線,與歐美兩洲有什么不同?能不能趨向統一?比如,如何免除士兵當俘虜的恐懼,在敵方那里不被嚴酷虐待,回到故國不被嚴厲懲罰?
在一些國家變好之前,千萬不能先變壞了。
關于1979年的中越戰爭,有兩國之外的媒體報道說,在諒山西北方向,雙方進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東方戰場罕見的戰役級交戰。
有位退伍老兵,網名叫“活著的烈士”。在他的回憶里,寫到的一件事好像與網名有關:臨近前線,找人問路,他看見一個人民公社的廣場上有很多人在做木箱。旁邊完工的木箱,堆了好幾層高。
“你們生產這么多木箱是裝什么用的?他們的回答嚇我一大跳:我們做的是棺材。棺材!我差點沒喊了出來。老鄉見我一臉愕然的樣子,又補充道:這是埋烈士用的,其他幾個公社都在趕做呢。”活著的烈士寫道,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那么多的棺材,心里真的是害怕了,真怕以后有一天把我也裝在其中一個箱子里,戰士變成了烈士。
一名越戰老兵回憶,從他們連抽出十個人去前線,誰都不知道具體會去哪里,這支隊伍就定名為“援柬抗越”,因為越南出兵柬埔寨,并占領了柬埔寨首都金邊。
連隊組織歡送宴會,還喝了不少好酒,副指導員在歡送會上朗誦了一首詩:《一支心中的歌——獻給援柬抗越的十名戰友》:
富饒的柬埔寨早已是彈坑累累,硝煙彌漫,那舉世聞名的吳哥窟會不會被越寇燒光?也許你們在想,不屈的高棉民族正在椰林中頑強地射擊,那復仇的子彈正穿透敵人的胸膛。當看到我們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就像久別重逢的戰友啊,熱淚盈眶。前輩們用鮮血和生命染紅的無數面錦旗,我們要獻身世界革命,為連隊再度爭光。
送別戰友時,那首深情的詩歌感動著許多人,但由于書寫者不知實情,對世界革命的表白用錯了地方。柬埔寨七百萬人左右,在波爾布特統治下大約四年,死去大約四分之一人口。活下來的高棉民眾,已經把趕走波爾布特的那批越南軍隊,當成了解放者。
有一名越戰退伍老兵,很多年后當了一家房產集團老總,接受電視欄目邀請時說到了那段時光。
他說起進入陣地第一天的情形,“副連長看見我了,他說我們放假三天第一天你就趕上了,因為敵方也有很多會說漢語的,雙方的電臺兵自己就在電臺里約定過年了放假三天。”
此時,那場戰爭打了幾年,越打越小,快要停下來了。
我們這邊過年吃得很好,一到過年都會把牛肉罐頭還有很多罐頭運到一線,他說,看到那邊發東西很少,我們這邊一個兵就把罐頭扔過去了,結果這個罐頭一扔過去,對面那幫兵就嘩一下全沒了,全躲起來,等了半天,這才發現扔過來的不是手榴彈,扔的是個罐頭,大家又出來了。我們這邊把罐頭扔給他,他們那邊就把木薯和發的煙葉扔給我們,互相作一些交換。
他的回憶里,意識形態的色彩已經淡去,那片戰場的審美感受很濃。
“站起來后感覺有點像在羅布泊,周邊的景色一點都不真實,但它非常美。就像我后來看的 《阿凡達》。”他說,因為大片的橡膠樹全被炸斷了,枝被炸斷之后,白色的橡膠就流出來了,夕陽西下的時候,溫度很低,陽光發紅,而天光又很冷,“然后你就聽見風聲,聽見鳥叫,但聽不見任何人聲,所以那個時候你覺得很不真實,但是非常美。”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有一本外國小說,寫的是主人公怎樣當上教皇,人物和情節是虛構的,選舉的場面看來并非虛構。在梵蒂岡最后投票的日子,人們要等上一兩個星期,眼睛盯著天空,如果大教堂煙囪里飄出黑色煙霧,那表示前一天投票無效;如果飄出一股白色煙霧,就表示新教皇產生。
我的興趣被小說勾起,就找了資料看,想確定那個場面是否真實。我還想知道,到了二十世紀的后一半,什么樣的人被選出來擔任教皇?如果再加上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在那個位置能做些什么?
1978年,八十歲的保羅六世去世不久,六十五歲的約翰·保羅一世也去世了,大教堂的煙囪里兩次飄出白色煙霧。那一年底選出的新教皇,是約翰·保羅二世,1920年出生的,五十八歲,比較年輕。
新教皇原名叫卡羅爾,波蘭人,是五百年來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皇。他曾經是位學者,年輕時還是運動員、演員、劇作家和語言學家,能說十一種語言,都很流暢。
但是,卡羅爾經歷中有太多不幸了。一是來自家庭的,母親在他八歲時死去,父親在他二十一歲時死去;他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在他十一歲之前都已死去。一是來自社會的,在他十九歲那年“二戰”爆發,德國軍隊占領波蘭,他在狂轟濫炸中逃難,總算逃到東部,卻遇到蘇聯軍隊從東部入侵,只好回到德軍占領區。德國人關閉了所有大學,把教授們關進集中營,驅趕大學生去做重體力勞動。那時他在大學主修語言學,同時研究戲劇,不得不中斷學業,去野外采石場謀生。
這些不幸,對他的人生發生了整合作用。有一篇文章說,這使他產生了從事神職的愿望。他瞞過納粹政權,一邊工作,一邊秘密學習神學課程。“二戰”總算結束了,僥幸躲過納粹最后大屠殺的卡羅爾,先在某大學教倫理學,后在天主教大學里任教,二十六歲立為神父,四十三歲時立為克拉科夫總主教。
“二戰”結束,波蘭人處于蘇聯的控制下,新一輪苦難開始。
有一部電影《卡羅爾》,很難找到它的碟片。看過的人說,其中有卡羅爾“二戰”后與政府情報人員的交鋒。對手陰險,冷酷,當然還有些無賴;卡羅爾呢,不懼強權,用智慧和寬容回擊他們,沒有丟掉他的理性、原則、信仰和人格。
電影沒找到,找到了它的一些臺詞,像是卡羅爾說的:
“我們得哭,痛苦必須被減輕,拿出來讓每個人都看看。”
“國家不能剝奪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國家不能用警棍代替正義感,這么做的國家注定要滅亡。”
“歷史總是會讓事情順著時間表走下去的。”
還有一段話,“你們決不能失去信心。你們得相信希望的力量。你們得相信愛比死亡更偉大。你們決不能膽怯,決不能失去自由的思想,因為基督用它使人類自由。”
1979年,約翰·保羅二世做了許多事情。
人們熟知的兩件事,一是他為伽利略平反,在公開集會上正式承認,三百多年前伽利略受到的教廷審判是不公正的。二是他前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在“死亡之墻”前下跪祈禱。奧斯維辛集中營位于波蘭境內,死在那里的,有教過他的幾位教授,還有他認識的一些宗教人士。
實際上,對歷史進程更有影響的一件事,是約翰·保羅二世在1979年訪問波蘭。
當時的波蘭與一些東歐國家,內政外交都歸前蘇聯控制,像是仆從國。但波蘭與其他東歐國家不完全一樣,它可能是世界上天主教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據估計有90%的人是天主教徒。
讓我們知道這個數字的,是蘇聯克格勃的絕密檔案。克格勃最為擔心的事情,是波蘭政府不能將天主教置于它的政治控制之下。
他們早已認定卡羅爾是一個危險的反對派,在宗教自由與人權問題上都不妥協,還在一次布道中宣稱,“如果政府當局不能為民眾接受,教會有權批評它在各方面的活動和表現。”他們可以根據波蘭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認定卡羅爾在宗教禮拜儀式上散布煽動性叛國言論,判處一至十年徒刑。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波蘭安全與情報局拘留波蘭大主教長達三年之久。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他們再也不敢逮捕紅衣主教了。這種做法,會引發波蘭國內與西方國家的強烈抗議。
歷史往后退一點,退到斯大林時代,克格勃最頭痛的“意識形態顛覆活動”,不是各種修正主義,而是有組織的宗教。即使在他們的大本營蘇聯,不允許其他政黨存在,也只能謊稱尊重宗教自由,暗地里派遣情報人員,逐漸滲入或全部替代宗教界高層人士。
如果這歷史退到“二戰”時期就停下來,人們會看見,納粹德國也有與此相似之處。他們害怕宗教組織民眾的力量,但又不敢完全廢除教會,只能用反抗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罪名,將教士們投入集中營或驅逐出境。
糟糕的是,卡羅爾成為教皇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訪問他的故國波蘭,克格勃又無法阻止他。
他們無法阻止。這就是卡羅爾說的,“歷史總是會讓事情順著時間表走下去的。”
有篇文章說,1979年夏天,當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訪問波蘭時,沒有人能夠預測,這次訪問推進了波蘭團結工會在次年成立;也沒有人能夠預料,這次訪問引發了民間社會在東歐和中歐國家的復蘇,從而導致蘇維埃制度在東歐的瓦解。
1979年夏,新教皇訪問波蘭,抵達華沙機場的第一個舉動,是跪下來親吻故鄉的土地。
在布道中,他反復勸波蘭人用信仰的力量壯大自己。“從人類歷史上排除耶穌,是反人類的原罪。”他說,“領導波蘭明天的是耶穌!”
復蘇的信仰激情,感染了整個波蘭。據說在隨后九天內,有一千三百萬人參加了教皇主持的彌撒活動,約占波蘭人口的三分之一,余下人口的大多數在電視中看了他在波蘭巡行的盛況。
其中有一天,新教皇為一百萬人做了彌撒。這天的彌撒主題,是紀念圣斯坦尼斯拉夫。他本是古代克拉科夫的一位殉道主教,但因為敢于要求皇帝尊重上帝的法律,并提倡自由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不允許國家侵犯,后來被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賦予了新的意義:波蘭國家道德和社會秩序的守護神,自由的護衛者,反對不公正國家的象征。
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正在競選總統的里根,看到這些電視畫面時感動流淚,他意識到,這個世界上除了有美國和蘇聯,還有信仰,這是強大的第三種力量。而另一位美國人,作家伯恩斯坦評價說,對當時被蘇維埃主義統治了三十五年的波蘭來說,教皇的來訪,等于是在刀劍和十字架之間,劃出了界線。
后來,一名波蘭政府官員在回憶錄里寫到約翰·保羅二世帶給他的鼓舞力量。他說,我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比“他們”強大。
《圣經》說,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約翰·保羅二世訪問波蘭,就做了這樣的事情。
十年之后,波蘭共和國建立。
“二戰”末期,斯大林曾經帶著輕蔑的語氣問道:“教皇統率多少個師?”沒人敢當面告訴他,教皇一個排的兵力也沒有,但他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責任編輯: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