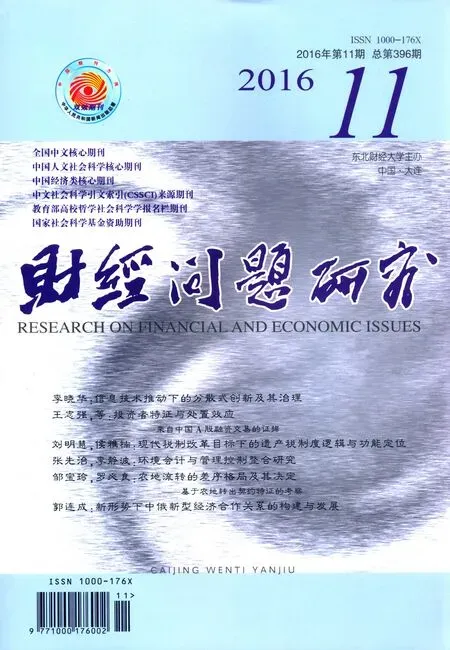新常態下宏觀審慎工具的有效性
——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
陳明瑋,袁夢怡,王 博
(南開大學 金融學院,天津 300350)
?
新常態下宏觀審慎工具的有效性
——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
陳明瑋,袁夢怡,王 博
(南開大學 金融學院,天津 300350)
本文分別選取貸款價值比率(LTV)上限與資本充足率(CAR)下限作為我國信貸類與資本類宏觀審慎工具的代表,并以此建立了一個包含各類金融摩擦因素在內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模型緊密聯系新常態下我國貨幣政策導向,通過寬松型利率政策沖擊的數值模擬,擬合分析了LTV上限與CAR下限兩類宏觀審慎工具對穩定我國金融系統運行與實體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研究結果表明,信貸類與資本類宏觀審慎工具,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單一利率型貨幣政策沖擊所引發的信貸激增和銀行杠桿驟升等失衡性金融波動;兩類宏觀審慎工具的運用能夠與傳統的利率政策工具形成有效的配合互補,在保證經濟總產出的前提下,抑制金融順周期效應,實現我國金融體系與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
宏觀審慎工具;貸款價值比率;資本充足率;DSGE模型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暴露了金融系統的內在脆弱性,這促使經濟學家和政策當局逐漸意識到,順周期效應引發的“金融不穩定”現象潛藏著巨大的系統性風險。基于微觀審慎理念的傳統金融監管框架,已經無法繼續適用于自由化程度在不斷加深的現代金融體系。因此,2009年國際清算銀行(BIS)正式提出了“宏觀審慎”監管概念,界定宏觀審慎政策為“視金融系統為統一整體,以抑制金融失衡、防范和應對系統性風險、實現金融系統穩定運行為目的”而制定的相關監管政策。
在我國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中,通常將經濟增長視為首要調控目標。政策工具的選擇也往往是出于拉動增長的目的,故而在政策組合方面,政府當局也更傾向于使用非市場化且直接效應明顯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組合。然而,隨著我國經濟轉型,新常態下宏觀經濟顯現出明顯的變革趨勢,增速換擋使得傳統增長目標的地位相對下降;而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等一系列舉措將增加我國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和風險傳染性,加大潛在系統性風險暴露的可能,維護金融穩定的相對重要性顯著提升。在調控重點由傳統單一增長目標向增長與穩定雙重目標轉換的同時,這也觸發了對我國宏觀經濟監管框架重構的要求。而在重構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過程中,如何選擇有效的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則是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依據Lim等[1]的宏觀審慎工具分類標準,通常可以將宏觀審慎工具劃分為信貸(如LTV上限)、流動性(如準備金率)與資本(如資本充足率)三大類。而根據Claessens等[2]的統計研究,目前我國最主要的宏觀審慎工具為流動類的準備金率、信貸類的貸款價值比率(Loan-to-Value,LTV)以及資本類的資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CAR)三種。而在這三者之中,由于準備金率同時也是我國最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之一,且在近年的實際操作經驗中,主要履行的是貨幣政策工具職能。因此,為剝離干擾、有效探討宏觀審慎工具的影響,本文將準備金率劃為貨幣政策工具范疇,并最終選取了在我國使用頻率較高的LTV上限與CAR下限,分別作為我國信貸類和資本類宏觀審慎工具的代表,對其在應對順周期效應與維護金融穩定方面的有效性進行深入研究。
國內外現有文獻關于宏觀審慎政策的討論主要集中于以下兩類:
一是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替代互補效應。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單一貨幣政策的系統性風險防御功能遭到廣泛質疑。后危機時代,各國在其監管框架中逐漸納入了為配合貨幣政策實現金融穩定的宏觀審慎政策。然而,對于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際配合效果,現有理論研究仍存在較大爭議。Caruana[3]認為,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是互補關系,且其政策目標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沖突,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將減少宏觀審慎政策的使用頻率;王愛儉和王璟怡[4]利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對我國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模擬分析,結果顯示,我國宏觀審慎政策對于貨幣政策具有輔助作用。因此,我國在進行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應當配合使用兩種政策,發揮協同作用。而White和Borio[5]卻認為,貨幣政策并未將金融穩定納入其指定目標當中,且總量調節行為很可能導致貨幣政策產生金融順周期效應,這與宏觀審慎的逆周期調節原則是相背離的,因此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二者之間存在內生沖突。與此同時,Montoro和Moreno[6]則認為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既可以是互補關系,也可以是替代關系。
二是關于宏觀審慎工具的有效性分析。IMF對宏觀審慎工具運用提出了四項原則:能有效控制系統性風險累積,并能為壓力情形提供足夠緩沖;套利空間要足夠小;作用目標是系統性風險根源,而非風險的表層因素;最小化宏觀經濟(包括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扭曲作用。Montoro和Moreno[6]認為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由于我國香港監管機構沒有使用LTV上限等宏觀審慎監管工具,造成了我國香港房地產價格泡沫; Claessens等[2]通過對48個國家的微觀銀行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債務收入比率與貸款價值比率上限等宏觀審慎工具的使用有助于抑制經濟繁榮期內的信貸擴張幅度。
盡管國內現有文獻已經對我國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匹配效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關于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探討則仍停留在以資本充足率為代表的資本類工具較為單一的層面。然而事實上,以LTV上限為代表的信貸類宏觀審慎工具在我國的實際運用時間更久、操作經驗更加豐富。那么,信貸類宏觀審慎工具在我國的作用效果如何呢?與此同時,2014—2015年間我國貨幣當局連續多次使用利率工具,以降低基準利率的方式實施寬松型貨幣政策,但2015年我國M2卻并沒有顯現大幅擴增跡象,信貸增速也維持在正常區間之內。那么,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否與配合貨幣政策使用的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相關呢? 本文將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納入LTV上限與CAR下限,對信貸與資本這兩類最主要的宏觀審慎工具代表在我國實際應用中的有效性進行模擬分析,并利用數值模擬階段,研究兩類宏觀審慎工具對我國金融系統與實體經濟的影響差異。
二、基準模型
在Iacoviello和Neri[7]框架基礎上,本文加入以銀行部門為代表的金融中介機構,擴展了傳統的DSGE基準模型。同時,還通過加入LTV為代表的信貸類審慎工具變量與CAR為代表的資本類審慎工具變量,完善了帶有各類摩擦因素DSGE模型的構建。
(一)家庭部門

(1)

與此同時,家庭部門為滿足自身效用,還可能存在向銀行借貸的行為,假定在第t-1期和第t期內,家庭部門的貸款分別為Lt-1、Lt,則家庭部門受到的預算約束為:
(2)
其中,PH,t為家庭部門在第t期所持有不動產Ht的價格;RL,t-1為第t-1期的貸款利率,本文結合居民貸款的實際情況,設定家庭部門在第t期初按t-1期的貸款利率償付第t-1期的貸款Lt-1;Dt為家庭部門在第t期的存款,RD,t-1為第t-1期存款Dt-1的利息;TC,t為居民在第t期向政府繳納的稅款;wt為家庭部門的工資率。

根據模型設定,由于家庭部門在第t期內存在存款行為,因此除預算約束外,家庭部門還會受到借貸約束的限制:
(3)
其中,LTVt(Loan-to-Value)為家庭部門貸款價值比率上限,反映了銀行部門發放貸款的風險偏好,根據Iacoviello和Neri[7]模型的設定,LTVt值越大,說明銀行部門放貸的風險偏好越高。本文在家庭部門加入動態LTV上限特征是為了擬合當商業銀行的借貸不受宏觀審慎監管約束時,銀行部門對家庭部門的借貸約束條件中,其貸款價值比率上限會隨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此時動態LTV上限代表的是銀行部門的風險偏好水平,即動態LTV上限將滿足:
(4)
其中,αLTV為當期LTVt關于前一期LTVt-1的時變自回歸因子,且滿足0<αLTV<1,αH、αN、αY≥0。
(二)企業部門
模型沿襲經典DSGE模型關于企業部門的基本設定,認為企業部門通過雇傭家庭部門勞動力為Nt,租用家庭部門的資本為Kt,生產最終產品為Yt,生產函數為Cobb-Douglas形式:
(5)

PtΠt(i)=Pt(i)Yt(i)-PtwtNt(i)-PtqtKt(i)
-PtACP,t-PtTE,t
(6)

(三)銀行部門
對銀行部門的討論是模型的主要部分。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傳統DSGE模型往往并沒有意識到銀行等金融機構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所肩負的重要作用。危機之后,Borio和Zhu[10]通過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指出銀行對于金融系統穩定運行的重要性。而從現實角度分析,近年來壞賬違約事件在我國頻頻發生,我國商業銀行所承擔的系統性風險是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去杠桿與解決債務負擔更加成為現階段我國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務。因此,在傳統DSGE模型中納入對銀行體系的分析判斷,已成為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基于新凱恩斯分析框架的主要研究范式。而本文在對銀行系統進行建模時,不同于傳統文獻僅關注銀行資產負債表約束下的經營最優化行為,更側重探討銀行系統在不同審慎監管體制中對經濟波動傳遞作用的差異。因此,在對銀行部門的建模過程中,我們引入了資本充足率這一宏觀審慎監管工具,以體現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的資本類宏觀審慎監管約束。
模型設定銀行在第t期,以利率RD,t吸收居民存款Dt(位于商業銀行的負債端),并以利率RL,t進行放貸Lt(位于商業銀行的資產端)。此外,商業銀行還存在凈資本Zt(即所有者權益)。因此,銀行部門存在資產負債表等式的約束條件為:Lt=Dt+Zt。
Adrian和Shin[11]指出,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率與資本充足率之間的交互影響,會改變其風險認知程度,進而影響銀行的信貸供給行為。而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則會嚴格受到巴塞爾協議的監管,設eB為巴塞爾協議要求的資本充足率,則銀行監管約束條件為:Zt≥eBLt。
銀行作為企業,其經營本質仍為追求其無限期內的自身收入最大化:
(7)
其中,βB為銀行部門的折現因子[7]。ACB,t為銀行的調整成本,與商業銀行偏離監管資本充足率的程度有關,即ACB,t為以凈資本形式表示的二次項調整成本:
(8)
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低于監管要求時,銀行將受到懲罰;而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過高時,會產生影響其賺取利差收益的成本。
(四)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在本文模型中的作用主要是進行宏觀政策的調控。根據泰勒規則[12]:
(9)

(五)均衡出清
根據模型設定,經濟體總產出的出清條件為Yt=Ct+It(1+ACI,t)+ACP,t+ACB,t+Gt。其中,Gt為政府支出。 根據前文設定,政府部門的收入與支出同樣也在第t期出清,即:
TC,t+TE,t=Gt
(10)
三、參數校準與數值模擬
(一)參數校準
本文在進行參數校準時使用的實際數據為1996年第1季度至2015年第4季度的我國實際宏觀數據。其中,以銀行間7天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表示我國的政策利率,*通常意義上,我國政策利率應當為1年期定期存貸款利率,但由于我國政策利率的時變性較低,為保證參數估計的有效性,本文以變動頻率較高、數據可得時段較長且數值大小接近政策利率的銀行間7天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代替我國真實的政策利率。以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表示我國總產出,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表示我國消費,以CPI環比數據表示我國通脹水平。同時,為保證本文所校參數符合模型的基本假定,本文對我國實際經濟數據進行了季節調整以剔除季節性波動的干擾;同時對利率之外的數據進行了HP濾波處理以剔除其趨勢性因素。數據來源為CEIC數據庫。為更加貼合我國經濟的實際運行情況,在參數的文獻參考方面,本文偏重于選取國內學者對于各參數的研究成果;對于國內學者未考量過的參數,本文則主要參考國外經典文獻對該參數的貝葉斯估計結果,以盡量減少校準誤差;對于具有特殊經濟含義的參數(例如貸款價值比率上限的穩態值),本文選取經驗數據代表。主要模型參數的校準結果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參數的校準結果
(二)數值模擬

1.商業銀行貸款價值比率(LTV)上限的宏觀審慎效果
當不采取LTV上限監管工具時,若出現正向貨幣沖擊,由于政策面因素的影響,銀行風險偏好顯著增強,貸款價值比率較沖擊前,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這也直接增加了銀行的信貸供給意愿,擴張了銀行對私人部門的貸款規模。而銀行信貸供給擴張必然將通過增加銀行總資產的方式,造成抬高銀行自身的杠桿倍數的結果。在各變量不采用宏觀審慎政策而只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的變化情況下,可以得出簡單的結論,若我國貨幣當局只使用寬松的利率工具對宏觀經濟進行貨幣政策調控,會顯著擴張我國銀行系統的信貸供給規模,增加銀行部門的杠桿水平。
然而,根據美國次貸危機的經驗教訓,銀行部門如果因為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而對宏觀經濟形勢持有過分樂觀的態度,那么過高的風險偏好會讓銀行部門不斷提高其貸款價值比率的上限水平,造成過激的信貸擴張,增加高杠桿風險,加劇了銀行系統內在脆弱性。可見一國當局利用LTV上限審慎工具對銀行部門的風險偏好進行監管是十分必要的。當我國貨幣當局利用LTV上限工具對銀行體系進行宏觀審慎調控時,即使通過降低利率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由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銀行部門的風險偏好水平,維持其放貸的比率上限,導致銀行對私人部門信貸增加水平較無LTV上限監管時存在明顯的下降,這也降低了銀行系統杠桿的增加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銀行系統暴露其系統性風險的可能。與此同時,在現實層面,盡管2015年我國貨幣當局多次采取降低存貸款基準利率等相關政策,但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與人民幣貸款余額增速仍處于合理范圍,并沒有出現大幅提升的現象。因此,理論模擬與實際經驗相結合,我們可以得出結論,LTV上限這一宏觀審慎工具與寬松型貨幣政策的匹配運用,既能夠保證信貸的平穩增長,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增長泡沫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正面效用。
貨幣政策沖擊對總產出的影響結果同樣是我們關注的焦點。這是因為,宏觀審慎政策的實施,其主旨在于進行逆周期調控,防止上升期波動過大,引發泡沫風險。然而,如果宏觀審慎政策在平抑過度信貸波動的同時,還會產生影響信貸對實體經濟支持的副作用,那么LTV上限工具的運用合理性仍需更進一步的探討。慶幸的是,盡管LTV審慎工具會在一定程度上熨平貨幣政策帶來的信貸供給擴張,但卻并沒有影響信貸從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的傳導。這說明,就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情形而言,若只實行寬松貨幣政策,那么相比配合宏觀審慎政策運用時所增加的這部分信貸,將會仍主要流入金融類投機活動,而并不會增加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反而容易引發資產價格的泡沫式暴漲現象。
2.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CAR)下限的宏觀審慎效果
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直接促使巴塞爾協議III的誕生,2009年,我國也加入了巴塞爾銀行監督委員會,并從2013年開始實行新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圖與國際監管體制接軌,正式對我國商業銀行的總資本充足率設定了下限標準,要求其不得低于巴塞爾協議III中規定的10.5%。因此,本文在對CAR下限這一宏觀審慎工具的影響作用進行模擬時,設定公式Zt≥eBLt中eB的值為10.5%。同時,通過取消銀行部門(Zt≥eBLt)關于資本充足率的約束條件,模擬我國政府不采用資本充足率工具時的運行情形。基于近年我國多次實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貨幣政策背景,我們仍然有必要模擬分析CAR下限監管與寬松型利率工具相配合時的總和政策效果。與前文引入貨幣政策沖擊方式一致,我們繼續利用比較分析研究方法,判斷發生正向貨幣政策沖擊時資本充足率工具的宏觀審慎效果。
DSGE模型模擬結果表明,貨幣當局通過降低利率實行寬松型貨幣政策時,若配合資本充足率CAR下限監管工具的使用,能夠通過平抑銀行部門的風險偏好增加幅度,降低信貸的擴張程度,緩解銀行大幅增加杠桿壓力,減緩內部脆弱性,保障金融系統穩定運行。理論上,在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中,利率直接影響了信貸的借貸成本,可以理解為直接刺激了信貸需求的增加。而資本充足率則可以通過約束銀行部門而直接影響信貸的供給端。具體而言,由于我國銀監會對商業銀行實行總資本充足率監管,為滿足銀監會所設定的下限要求,盡管銀行的風險偏好會因為房地產等抵押品價格的急速攀升而有所增加,但其程度顯然仍會處于銀行自身的可控范疇內。這是因為隨著風險偏好的增加,銀行會選擇擴張其信貸供給規模,而由于CAR下限監管的存在,對私人部門貸款的增加同樣也會引起銀行自身對觸及監管底線遭受懲罰的擔憂。因此,CAR下限工具在應對貨幣政策沖擊時,會呈現出較為靈敏的審慎作用。CAR下限具與貨幣政策相配合并沒有阻礙貨幣政策對我國實體經濟的作用效果,影響總產出增長趨勢,而僅僅是在防范系統性泡沫的發生。資本充足率對總產出的這種審慎作用,同樣可以利用沖擊的傳導機制闡釋。貨幣政策對實際經濟的作用是間接性的,主要通過利率價格和信貸的需求供給等傳導渠道間接影響實體經濟活動。因此,CAR下限這一宏觀審慎工具的運用在保障金融體系平穩運行、穩定發展之時,并不會對實體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效應。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在傳統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納入了以貸款價值比率(LTV)上限為代表的信貸類宏觀審慎工具變量和以資本充足率(CAR)下限為代表的資本類宏觀審慎工具變量,同時結合現階段我國宏觀經濟的實際運行情況,引入了寬松的利率型貨幣政策沖擊,模擬分析了兩類最主要的宏觀審慎工具在當前我國經濟新常態中的運用效果。DSGE模型的數值模擬分析結果表明,無論是以LTV上限為代表的信貸類宏觀審慎工具,抑或是以CAR下限為代表的資本類宏觀審慎工具,在面對新常態下我國貨幣當局為刺激經濟復蘇而多次實行的寬松型利率沖擊時,均能夠表現出良好的平抑信貸規模驟然擴張和銀行杠桿大幅上升的效果,實現了與貨幣政策的有效互補,在保障經濟總產出增長的前提下,避免了因金融過激波動而引發的宏觀風險。因此,在我國宏觀經濟新常態下,宏觀審慎工具的運用在抑制金融失衡、防范系統性風險方面有效性顯著,基本能夠實現配合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系統穩定運行的目標。
現階段我國宏觀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特殊時期。伴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金融業態也隨之呈現出明顯的調整變革。新常態下結構性改革進程中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等系列措施增加了宏觀經濟體系內潛在的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穩定成為新常態下與增長同樣重要的任務,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面臨著調整重構。基于本文宏觀審慎工具的有效性結論,新常態下,為保障經濟平穩過渡轉型,我國貨幣政策當局在運用傳統貨幣政策穩定經濟增長的同時,還應當積極配合使用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完善宏觀審慎監管體制的構建。
此外,當前我國實行的“一行三會”模式,獨立運作的成分較大,不利于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內跨部門的交流合作,應當建立央行與各金融監管部門就審慎監管職能的溝通橋梁,利用多重宏觀審慎工具與貨幣政策工具形成有效的配合互補,避免貨幣政策的負面溢出效應所引發的失衡風險,實現金融穩定與宏觀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1] Lim, C.H., Costa, A., Columba, F.Macroprudential Policy: What Instruments and how to Use Them? Lessons From Country Experiences[R].IMF Working Papers, 2011.1-85.
[2] Claessens, S., Ghosh, S.R., Mihet, R.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to Mitigate Financial System Vulnerabilit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3, 39(1): 153-185.
[3] Caruana, J.Macroprudential Policy: Working Towards a New Consensus[R].BIS’s 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 and the IMF Institute High-Level Meeting on the Emerging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2010.
[4] 王愛儉,王璟怡.宏觀審慎政策效應及其與貨幣政策關系研究[J].經濟研究,2014,(4): 17-31.
[5] White, W.R., Borio, C.E.V.Whithe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he Implications of Evolving Policy Regimes[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s Symposium, 2003.
[6] Montoro, C., Moreno, R.The Use of Reserve Requirements as a Policy Instrument in Latin America[DB/OL].http://bis.org, 2011-03-14.
[7] Iacoviello, M.M.,Neri, S.Housing Market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an Estimated DSGE Model[DB/OL].http://ssrn.com, 2008-10-16.
[8] Dixit, A.K., Stiglitz, J.E.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3): 297-308.
[9] Kim, J.Constructing and Estimating a Realistic Optimizing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0, 45(2): 329-359.
[10] Borio, C., Zhu, H.Capital Regulation, Risk-Taking and Monetary Policy: A Missing Link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2, 8(4): 236-251.
[11] Adrian, T., Shin, H.S.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Monetary Economics[J].Hand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0, 3(1): 601-650.
[12] Taylor, J.B.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J].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993, 39(1): 195-214.
(責任編輯:巴紅靜)
2016-08-19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深化政策性金融改革研究”(14AZD03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全球金融體系變革下的跨國公司投資”(14JJD790030)
陳明瑋(1989-),男,山西晉中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研究。 E-mail:cmw721@126.com
袁夢怡(1989-),女,遼寧大連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研究。 E-mail:yuanmengyi1989@126.com
F820.2
A
1000-176X(2016)11-0059-07
王 博(1981-),男,山東齊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研究。E-mail:wangbowangbo200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