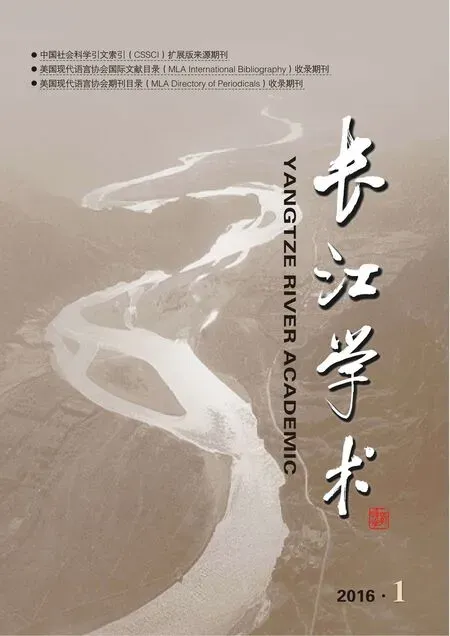偵探外衣里的詩(shī)心
——旅美華裔作家裘小龍?jiān)L談
〔美〕陳璇
(美國(guó)林登伍德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
偵探外衣里的詩(shī)心
——旅美華裔作家裘小龍?jiān)L談
〔美〕陳璇
(美國(guó)林登伍德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
在偵探小說(shuō)中加入大量的中國(guó)古典以及西方現(xiàn)代派詩(shī)歌,是裘小龍寫作的一大特色,現(xiàn)代詩(shī)歌翻譯家與詩(shī)人的背景和身份使他的偵探小說(shuō)別具一格。裘小龍不僅塑造了一個(gè)完全不同于陳查理(Charlie Chan)的東方形象,而且還讓西方社會(huì)看到了一個(gè)更商業(yè)、更現(xiàn)代的中國(guó)。訪談內(nèi)容主要圍繞著裘小龍的詩(shī)歌和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展開(kāi),即便“這不是一個(gè)寫詩(shī)的年代”,但是裘小龍卻以獨(dú)特的方式在他的偵探小說(shuō)中繼續(xù)著詩(shī)的探索。
詩(shī)歌意象派翻譯偵探小說(shuō)歷史反思
裘小龍,男,1953年出生于上海。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他因翻譯T·S·艾略特和美國(guó)意象派詩(shī)人的詩(shī)作而出名。1988年,獲得美國(guó)福特基金資助前往T·S·艾略特的故鄉(xiāng)——美國(guó)圣路易斯市,研究現(xiàn)代主義詩(shī)歌,并在華盛頓大學(xué)獲得比較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此后,他在華盛頓大學(xué)教授中國(guó)文學(xué),并定居圣路易斯,現(xiàn)專職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2000年,他以一部英文小說(shuō)《紅英之死》征服了西方讀者,成為第一位獲得世界推理小說(shuō)大獎(jiǎng)——“安東尼小說(shuō)獎(jiǎng)”的華人。到目前為止,他已經(jīng)出版了9部“陳探長(zhǎng)系列”偵探小說(shuō),這些小說(shuō)被翻譯為二十多種語(yǔ)言,使裘小龍享譽(yù)世界。同時(shí),他還出版了三部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翻譯選集以及一部短篇小說(shuō)集《紅塵歲月》。
2015年12月,一個(gè)溫暖的午后,筆者在美國(guó)圣路易斯市裘小龍先生的寓所,采訪了裘小龍老師。
一、關(guān)于詩(shī)歌
問(wèn):前不久,您最新的偵探小說(shuō)《上海救贖》(Shanghai Redemption)入選Wall Street Journal 2015年最好的十本書籍之一,可以說(shuō),這是您獲得美國(guó)主流社會(huì)認(rèn)可的又一次證明。但這并不是您的作品第一次獲得殊榮,早在2000年,您的第一部英文小說(shuō)《紅英之死》就贏得了世界推理小說(shuō)大獎(jiǎng)——安東尼小說(shuō)獎(jiǎng),因此,許多評(píng)論家都稱您是一位進(jìn)入了美國(guó)主流社會(huì)的華裔作家,請(qǐng)問(wèn)您怎么看待這樣一個(gè)說(shuō)法?
答:也不能一定就說(shuō)是進(jìn)入了美國(guó)主流社會(huì)吧,這得看從哪個(gè)角度來(lái)說(shuō)。其實(shí),以前WallStreet Journal也評(píng)過(guò)我的另外一本書,說(shuō)是他們認(rèn)為——不僅僅是那一年,是所有從古到今吧——最好的十本小說(shuō)之一,但是這個(gè)WallStreetJournal有時(shí)候也不一定那么權(quán)威。至于進(jìn)入“美國(guó)主流社會(huì)”,這就看你怎么去定義了,我在舊金山的一個(gè)朋友,他也是用中文寫作的,他有一次在國(guó)內(nèi)的報(bào)道上也這么提過(guò),但他的定義就比較簡(jiǎn)單,他說(shuō)如果你進(jìn)到美國(guó)書店,你能看到他的書,不是偶爾一次,而是幾乎每次去都能看到,那么這個(gè)大概就算是美國(guó)人能接受。因?yàn)樗X(jué)得,主流社會(huì)也好,一般讀者群也好,如果覺(jué)得你的書不值得一看,或者說(shuō)書店都覺(jué)得這個(gè)書以后是賣不掉的,那么這就比較難說(shuō)了。這是他的一個(gè)定義,算是一家之說(shuō)吧。
問(wèn):我覺(jué)得這真的是一個(gè)了不起的成功,您不僅能夠用第二語(yǔ)言英語(yǔ)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而且還得到了英語(yǔ)社會(huì)的普遍認(rèn)可,并獲得了極高的榮譽(yù),這太不簡(jiǎn)單了!您是如何從一位中國(guó)詩(shī)人轉(zhuǎn)變?yōu)橐粋€(gè)在西方社會(huì)頗受關(guān)注的偵探小說(shuō)家的呢?我知道這個(gè)問(wèn)題很大,那么,我們今天的采訪能不能從您在國(guó)內(nèi)的求學(xué)和創(chuàng)作生涯談起?
答:我最早是在77年考入華東師大的,是恢復(fù)高考以后的第一屆大學(xué)生。第一年恢復(fù)高考的時(shí)候有一個(gè)規(guī)定,當(dāng)然后來(lái)被取消了,就是說(shuō)就算你沒(méi)有念完本科你也可以去考研究生。當(dāng)時(shí)是一個(gè)什么樣的背景呢,因?yàn)楫?dāng)時(shí)77年第一次恢復(fù)高考,77年底第一次恢復(fù)研究生考試,那時(shí)沒(méi)有這么多符合年齡段的大學(xué)畢業(yè)生去考研究生,所以就破格,只要能考得過(guò),你就可以去讀。我是大學(xué)念了半年之后去考的,因?yàn)槟菚r(shí)候想得也很簡(jiǎn)單,反正考不上也不算什么事,我可以繼續(xù)念我的本科,所以我就去試,然后就考上了。考上了之后,78年就去讀中國(guó)社科院的研究生,當(dāng)時(shí)我考的是外國(guó)文學(xué)專業(yè),我的導(dǎo)師是卞之琳。那時(shí)的情況是這樣,首先你必須過(guò)了初試跟復(fù)試,然后定專業(yè)的時(shí)候?qū)熯x學(xué)生。導(dǎo)師選就是說(shuō),他覺(jué)得你這個(gè)人可不可以搞詩(shī)歌,當(dāng)時(shí)卞之琳老先生要我寫詩(shī),他說(shuō)如果你要跟我搞詩(shī)歌研究呢,你自己得會(huì)寫詩(shī),所以我就給他寫了幾首詩(shī),他看了以后還挺滿意的。
問(wèn):在這之前您創(chuàng)作過(guò)詩(shī)歌嗎?
答:沒(méi)有。當(dāng)時(shí)寫完以后,卞之琳先生跟其他幾位老師講,說(shuō)可以,他要我,說(shuō)我的詩(shī)寫得不錯(cuò)。其它幾位老師就跟我說(shuō),老卞都講了你這首詩(shī)可以拿去發(fā)表了,我后來(lái)就真的拿去發(fā)表了,從這以后我就開(kāi)始了寫詩(shī)。我后來(lái)還聽(tīng)我的另一位老師講,當(dāng)年徐志摩對(duì)卞之琳也是一樣,徐志摩比他更極端一點(diǎn),他都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卞之琳的同意,就把卞之琳的詩(shī)拿去發(fā)表了。所以這批老先生,現(xiàn)在想起來(lái),確實(shí)對(duì)年輕人的幫助和提攜很大,就是他不是很在乎條條框框的東西,他就是只要我喜歡,就這么做了。
問(wèn):您曾說(shuō)過(guò),當(dāng)年卞之琳先生都是在家給您授課,頗有古風(fēng)“弟子”的意味。作為卞之琳先生的關(guān)門弟子,您能不能談一談當(dāng)時(shí)在他家上課時(shí)的情形,以及他對(duì)于您在詩(shī)歌創(chuàng)作和翻譯上的影響?
答:當(dāng)時(shí)我們社科院是沒(méi)有自己的研究生院的——有研究生院這個(gè)名,但是沒(méi)有這個(gè)地兒,我們是借了北京師范大學(xué)的地方上課,所以老師上課確實(shí)很不方便,連教室都沒(méi)有,要上課還得跟北師大打招呼。卞先生帶我的時(shí)候年齡已經(jīng)比較大了,所以他也不喜歡到北師大來(lái)借個(gè)教室給我一個(gè)人上課,他覺(jué)得挺沒(méi)勁的,因此他就說(shuō),那你每個(gè)星期到我家來(lái)上課吧,他那時(shí)住在北京東城區(qū)的干面胡同,我每個(gè)星期就去那兒上課。其實(shí)想起來(lái),他對(duì)我的創(chuàng)作影響確實(shí)挺大的,因?yàn)樗舷壬险n可能跟現(xiàn)在學(xué)校里上課不一樣,他很隨便,去了以后大家就坐下來(lái),沒(méi)有任何提綱地亂聊,想到哪兒就說(shuō)到哪兒。又因?yàn)樗窃?shī)人,他有時(shí)就比較喜歡講自己怎么寫詩(shī)歌,以及跟誰(shuí)跟誰(shuí)交往,誰(shuí)的詩(shī)寫得怎么樣,誰(shuí)的詩(shī)寫得不行,就講這些東西,一講就是兩三個(gè)小時(shí),反正大家都是很隨便地聊,沒(méi)有像后來(lái)那種很正兒八經(jīng)地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樣,我覺(jué)得這種關(guān)系其實(shí)更多地就像是種弟子到家的感覺(jué),就是你去了當(dāng)然也有上課的成份,而更多的是有一種師生情誼在里面。但是有時(shí)候他也會(huì)問(wèn)我,你最近寫了什么詩(shī)啊,拿出來(lái)看看,然后就給我分析詩(shī)歌。我想這對(duì)我以后寫詩(shī)的影響很大,其實(shí)包括我寫小說(shuō)也都是受到了他的影響,因?yàn)樗?8年在英國(guó)的時(shí)候就在寫小說(shuō)。當(dāng)年他那部小說(shuō)基本上是快寫完了,但是50年代初回國(guó)的時(shí)候,就覺(jué)得自己的小說(shuō)太資產(chǎn)階級(jí)情調(diào)了,就把它燒了。然后到他帶我的時(shí)候,他自己也后悔了,他說(shuō)這個(gè)東西要是不燒就好了。所以后來(lái)他鼓勵(lì)我說(shuō),以后你也可以寫小說(shuō)啊,不一定只寫詩(shī)歌。想起來(lái)可能那個(gè)時(shí)候就覺(jué)得他那個(gè)英文小說(shuō)是很神圣的,因?yàn)槭冀K沒(méi)有看到過(guò)嘛,不知道他寫的到底是什么樣子,可能就是從那個(gè)時(shí)候在我心里種埋下了一顆寫小說(shuō)的種子吧。
問(wèn):我看到您除了發(fā)表詩(shī)歌作品以外,1984年您還發(fā)表了一篇中文小說(shuō)《同一條河流》,那應(yīng)該算是您的第一篇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吧?
答:對(duì),我大概就寫過(guò)這么一篇中文小說(shuō)。那篇我也不知道是為什么,在那個(gè)之前和那個(gè)之后都沒(méi)再寫過(guò),可能當(dāng)時(shí)正好上海文學(xué)的編輯部有幾個(gè)朋友,大家一起聊天,聊著聊著就說(shuō)起有這么個(gè)故事,大家說(shuō)能寫成小說(shuō)我也就這么寫出來(lái)了。但是正兒八經(jīng)地搞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是我到美國(guó)之后的事情。
問(wèn):您當(dāng)時(shí)還在國(guó)內(nèi)的時(shí)候,作為詩(shī)人和詩(shī)歌翻譯家在文壇已經(jīng)有一定的影響了,中國(guó)的八十年代,詩(shī)歌氛圍很濃,您所經(jīng)歷的文壇及詩(shī)壇情形是怎樣的呢?
答:當(dāng)時(shí)八十年代的詩(shī)歌特別火,這是跟現(xiàn)在完全不一樣的,真是特別火。那個(gè)時(shí)候北京的《詩(shī)刊》每個(gè)月的印數(shù)是10萬(wàn)本,當(dāng)時(shí)所有的報(bào)亭里面都能看到《詩(shī)刊》,文學(xué)青年也是很時(shí)髦的一個(gè)事情。我是88年底到美國(guó)來(lái)的,那時(shí)上海電視臺(tái)還經(jīng)常找一些詩(shī)人去做節(jié)目,說(shuō)明詩(shī)歌還是蠻受重視的。詩(shī)歌流派也很多,八十年代初的時(shí)候,朦朧詩(shī)人是一批,他們的詩(shī)是屬于半官方性質(zhì)的,(官方?jīng)]有怎么去打壓它,但它又確實(shí)不是官方講得太多的。)另外還有一批年輕的第三代、第四代詩(shī)人,我跟他們都有一些交往,但是其實(shí)哪一派我都算不進(jìn)去,如果硬要分派的話,我可能應(yīng)該是屬于學(xué)院派的,但是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是沒(méi)有學(xué)院派這個(gè)講法的。很奇怪,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搞創(chuàng)作的基本上都不是一本正經(jīng)在大學(xué)里念書的。我跟他們交往不是太多,還有一個(gè)因素就是因?yàn)槲耶?dāng)時(shí)有很多的時(shí)間是在翻譯詩(shī)歌,后來(lái)我到社科院工作,我主要的任務(wù)就是要寫評(píng)論,主要是寫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雖然我和這些詩(shī)人經(jīng)常有來(lái)往,但是并沒(méi)有特別去說(shuō)大家要是一個(gè)流派啊,一個(gè)風(fēng)格啊什么的。而且那個(gè)時(shí)候,不僅僅是詩(shī)歌創(chuàng)作,詩(shī)歌翻譯其實(shí)也很火,當(dāng)時(shí)像艾略特的詩(shī)集,都是好幾版好幾版地印,一拿出去就銷完了。那個(gè)時(shí)候,還有一點(diǎn)真是跟現(xiàn)在不一樣,就是年輕的作家不管是詩(shī)人也好小說(shuō)家也好,都覺(jué)得自己對(duì)社會(huì)負(fù)有重任,覺(jué)得要改變這個(gè)社會(huì)。想起來(lái)蠻有意思的,一方面你特別容易碰到麻煩,就是說(shuō)如果你這篇東西被上面點(diǎn)名了,你就是bigtrouble,這是肯定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你又覺(jué)得挺高興的,因?yàn)槟阌X(jué)得這個(gè)東西確實(shí)很有影響,上面都點(diǎn)你名了,那個(gè)時(shí)候確實(shí)有一種匹夫有責(zé)的感覺(jué),就是真覺(jué)得自己寫的東西能改變社會(huì),至少在某一方面能改變一點(diǎn),我想這種感覺(jué)現(xiàn)在大概都沒(méi)有了。
問(wèn):您覺(jué)得這種能改變社會(huì)的感覺(jué),是青春的激情使然,還是當(dāng)時(shí)整個(gè)的社會(huì)環(huán)境確實(shí)賦予了詩(shī)歌這種能力?
答:我想兩方面的因素都有,但是后者的因素可能更大一點(diǎn)。因?yàn)榈谝唬?dāng)時(shí)確實(shí)是受眾大,你在《詩(shī)刊》發(fā)一首詩(shī),至少有十萬(wàn)個(gè)讀者,你就會(huì)覺(jué)得,我這個(gè)確實(shí)能影響到很多人。當(dāng)時(shí)有些詩(shī)從詩(shī)性的角度來(lái)講,它的藝術(shù)造詣并不怎么樣,但是它確實(shí)影響很大。我記得當(dāng)時(shí)有一首詩(shī)的題目是《將軍你不能這樣做》,作者是葉文福,現(xiàn)在想一想,這可能也就是像口號(hào)一樣的政治宣傳,但那個(gè)時(shí)候,我想看的人肯定都不止十萬(wàn)個(gè),它確實(shí)能讓大家認(rèn)識(shí)到官僚的特權(quán)以及不公平的社會(huì)現(xiàn)象,大家爭(zhēng)相傳閱,看的人都是熱血沸騰的。第二,當(dāng)時(shí)經(jīng)常有些什么筆會(huì)啊作協(xié)會(huì)議啊等等,國(guó)家都挺重視的,當(dāng)時(shí)開(kāi)作協(xié)會(huì)議和作家代表大會(huì),規(guī)定總書記是要出席和講話的,而且還是在人民大會(huì)堂開(kāi)的,我曾去開(kāi)過(guò)一次,那種感覺(jué)真好,就是會(huì)給你一種你真的是在參與國(guó)家的建設(shè)的感覺(jué)。在那種情況下,就算你不那么青春,熱血也是會(huì)沸騰起來(lái)的。
問(wèn):您在當(dāng)時(shí)還參加過(guò)哪些詩(shī)歌活動(dòng)呢?除了詩(shī)歌翻譯之外,還參加了詩(shī)歌研討啊朗誦啊這些活動(dòng)嗎?
答:那個(gè)時(shí)候詩(shī)歌朗誦還不怎么普及。詩(shī)歌活動(dòng)方面,我參加了1986年的第二屆全國(guó)青年作家會(huì)議,我的印象是當(dāng)時(shí)幾個(gè)朦朧派、后朦朧派詩(shī)人都來(lái)了,他們是作為正式代表受邀請(qǐng)來(lái)的,還有一些人是不能官方邀請(qǐng)的,他們也來(lái)了。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文壇還是蠻復(fù)雜的,很敏感,但是那次會(huì)議我的印象蠻好,大家都是會(huì)上講,會(huì)下也講,講得很多也很熱烈。(如果我沒(méi)記錯(cuò)的話,那次正好碰到胡耀邦那個(gè)事件,北京有學(xué)生上街游行,所以搞得氣氛也蠻緊張的。)另外,因?yàn)槲沂亲骷覅f(xié)會(huì)的會(huì)員,大概也是86年吧,有一個(gè)中美作家會(huì)議,它當(dāng)時(shí)是每?jī)赡暌淮危淮卧谥袊?guó)開(kāi),一次在美國(guó)開(kāi),中國(guó)方面會(huì)派一個(gè)十來(lái)個(gè)人的代表團(tuán),美方也組織一個(gè)代表團(tuán),大家就一些文學(xué)問(wèn)題進(jìn)行會(huì)談。那個(gè)時(shí)候就覺(jué)得這真的是一個(gè)big deal,因?yàn)槟菚r(shí)出國(guó)確實(shí)也不容易,而且你還是經(jīng)過(guò)多次篩選出來(lái)代表國(guó)家出去的,所以確實(shí)是big deal,覺(jué)得這是一個(gè)很大的榮譽(yù)。當(dāng)時(shí)這個(gè)中美作家會(huì)議搞得真是挺隆重的,中國(guó)也特別高興有這么個(gè)機(jī)會(huì)可以跟美國(guó)的作家在文學(xué)上直接交流。
問(wèn):80年代后期出現(xiàn)了各種詩(shī)歌民刊,然后以民刊為中心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詩(shī)歌流派,您當(dāng)時(shí)有沒(méi)有參與哪一種詩(shī)歌流派?似乎在當(dāng)時(shí)那種青春激情的裹挾下,很難不加入任何一派吧?
答:我跟他們都有些接觸,但是也算不上加入哪一派。當(dāng)時(shí)那些詩(shī)人真的是很青春,他們會(huì)在之前沒(méi)跟你打過(guò)任何招呼就過(guò)來(lái)敲你的門,說(shuō)我是誰(shuí)誰(shuí)誰(shuí)的朋友,他們說(shuō)你的詩(shī)寫得好,我今天就來(lái)看你,然后你就陪他聊天,有時(shí)候來(lái)的人還會(huì)說(shuō),我今天晚上旅館還沒(méi)有找到,那行啊,那你就住在我這兒吧。上海當(dāng)時(shí)有一個(gè)大世界,后來(lái)改成青年宮,現(xiàn)在這個(gè)地方已經(jīng)沒(méi)落了,但是建筑還在,就是西藏路那個(gè)口子上,它以前是一個(gè)entertainmentcenter,很popular。那時(shí)候里面有一個(gè)搞宣傳的,跟我同樣的年紀(jì),同名,叫王小龍。他那兒是當(dāng)時(shí)上海的大本營(yíng)之一,而且因?yàn)槲腋乃浇灰残U好的,我家離大世界又特別近,所以他們那兒經(jīng)常有人來(lái),我也過(guò)去和他們一起聊。再加上王小龍還是正兒八經(jīng)搞宣傳工作的,所以他那兒經(jīng)常有這樣的事情,天南海北來(lái)的人很多。大概兩年以前,我還在洛杉磯時(shí)報(bào)給他寫過(guò)一篇詩(shī)評(píng),他們當(dāng)時(shí)正好需要一篇關(guān)于中國(guó)的文章。其實(shí),我覺(jué)得這個(gè)是很不公平的,中國(guó)這些搞詩(shī)歌的人現(xiàn)在都已經(jīng)被大家遺忘了。他現(xiàn)在在國(guó)內(nèi)拍紀(jì)錄片,也搞得很好,但是遺憾的是詩(shī)歌這個(gè)東西再?zèng)]有時(shí)間去搞了,很多其他的詩(shī)人也都是差不多的境地。但那個(gè)時(shí)候,確實(shí)是只要有朋友來(lái)了,沒(méi)地方住,那就在大世界住下來(lái),當(dāng)時(shí)他還在那兒開(kāi)班講詩(shī)歌,搞得蠻熱火的。在當(dāng)時(shí)的詩(shī)人中,我跟王小龍算是走得很近的,他當(dāng)時(shí)是寫城市詩(shī),寫citylife的。我比較喜歡他的風(fēng)格,他基本上以口語(yǔ)入詩(shī),在日常生活中的點(diǎn)滴中表述深厚的意蘊(yùn),但更為難得的是,他能夠把詩(shī)的節(jié)奏感處理好。我覺(jué)得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有一個(gè)問(wèn)題其實(shí)始終沒(méi)有解決好,就是它的節(jié)奏或者說(shuō)音樂(lè)性的問(wèn)題,因?yàn)楣诺湓?shī)是講究平仄的,它的韻律都是現(xiàn)成的,只要你懂它這一套就行了。但是,現(xiàn)代詩(shī),比如說(shuō)徐志摩的一些詩(shī),到現(xiàn)在為止,大家還在念、還能記得起來(lái),不一定是因?yàn)樗N(yùn)含了什么大的思想,他的詩(shī)像《再別康橋》啊《沙楊娜拉》啊,這些詩(shī)都有現(xiàn)代漢語(yǔ)的節(jié)奏,或者音樂(lè)感。王小龍的詩(shī)呢,跟他們不一樣,但他也是在往現(xiàn)代漢語(yǔ)詩(shī)的節(jié)奏上下功夫,我覺(jué)得他做得很好,可惜后來(lái)整個(gè)大壞境就不讓他繼續(xù)往下走了。我的老師卞之琳,他也曾專門就現(xiàn)代詩(shī)的節(jié)奏寫過(guò)一些文章,他就認(rèn)為,現(xiàn)代詩(shī)不可能像所謂豆腐干詩(shī)一樣,每一行都幾個(gè)字,他認(rèn)為現(xiàn)代詩(shī)需要一種自然的節(jié)奏,他將這種自然的節(jié)奏叫做“頓”。就像英文中有iambicfeet,每一行詩(shī)有5個(gè)feet,或者6個(gè)feet,那么中文呢,因?yàn)槟悴豢赡芤詥卧~作為foot的單位,你只能將一個(gè)詞組或者意義組作為一個(gè)“頓”,比如說(shuō),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這就三個(gè)音節(jié),盡管七個(gè)字,那么一行詩(shī)里面,譬如說(shuō),第一行是五個(gè)頓,那么第二行最好也是五個(gè)頓,當(dāng)然,你可以有一些變化,但是不應(yīng)該第一行來(lái)十個(gè)頓,第二行來(lái)三個(gè)頓。但是卞先生的這套,也主要是在理論上提倡,他到后來(lái)也沒(méi)有堅(jiān)持下去,因?yàn)楹髞?lái)寫詩(shī)的好像都顧不上這個(gè)了。其實(shí)我覺(jué)得這個(gè)是很基本的問(wèn)題,就是說(shuō),不管是什么體,都不應(yīng)該忽視現(xiàn)代中文詩(shī)歌中音樂(lè)感、節(jié)奏感的問(wèn)題。當(dāng)然也有不少人在這個(gè)方面做了嘗試,但是現(xiàn)在大多數(shù)詩(shī)人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都是顧不上的了。
問(wèn):現(xiàn)代的這些詩(shī)歌中您覺(jué)得比較有印象或者節(jié)奏上做的比較成功的,您能舉出幾個(gè)例子嗎?
答:王小龍有幾首詩(shī)我覺(jué)得很不錯(cuò),比如說(shuō)他有一首詩(shī)叫《紀(jì)念》,是寫給他的父親的,我覺(jué)得在節(jié)奏上他做得相當(dāng)不錯(cuò)。然后他還有一首《出租汽車總在絕望的時(shí)候到來(lái)》,也很好。我覺(jué)得他的詩(shī)還有一個(gè)好處就是比較幽默,這個(gè)是非常難得的。因?yàn)橹袊?guó)詩(shī)大都是抒情,有時(shí)候甚至是濫情,而他就能一方面好像在抒情,一方面好像自己在挖苦自己,這一點(diǎn)也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shī)歌當(dāng)中經(jīng)常可以看到的,但在中國(guó)詩(shī)中就比較少見(jiàn),就是它一方面抒情,但同時(shí)它又頭腦保持得比較清醒,就是說(shuō),這個(gè)東西,說(shuō)到底它也就那么回事,不值得要死要活的,有一種客觀的距離和反諷的態(tài)度在里面。
問(wèn):您當(dāng)時(shí)從事詩(shī)歌翻譯多還是創(chuàng)作多?在您的朋友圈里面,您主要是以一個(gè)翻譯家的形象出現(xiàn)還是以一個(gè)詩(shī)人的形象出現(xiàn)?
答:可能在寫詩(shī)的圈子里面他們更多地覺(jué)得我是搞翻譯的,所以我覺(jué)得我是哪兒都不沾邊,這樣也蠻好的。對(duì)于他們搞理論的來(lái)講呢,他們覺(jué)得你是寫作的。我的記憶里面,當(dāng)時(shí)作家協(xié)會(huì)下面是分組的,有詩(shī)歌組,有翻譯組,我至少是兩個(gè)組,我記得當(dāng)時(shí)翻譯組我還是小頭頭,詩(shī)歌組我也是成員,等于說(shuō)我是跨界的。我覺(jué)得這樣也有好處,因?yàn)楫?dāng)時(shí)除了政治之外,有時(shí)候大家競(jìng)爭(zhēng)得也很厲害的,特別是寫詩(shī)歌的都有一種我要當(dāng)老大的氣勢(shì),而我呢,因?yàn)楸桓阍?shī)歌的認(rèn)為是搞翻譯的,所以可以遠(yuǎn)離這些競(jìng)爭(zhēng)。當(dāng)時(shí)誰(shuí)要做頭呢,還確實(shí)是蠻神氣的事情。北島可以算是當(dāng)時(shí)詩(shī)歌的頭頭之一,我跟北島基本上是同一代人,北島他作為頭,其實(shí)也是有很多政治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最早的時(shí)候,他們的作品被幾個(gè)漢學(xué)家拿到了,翻譯到了國(guó)外,然后因?yàn)樗麄冋紊嫌行┑胤剑凑债?dāng)時(shí)的標(biāo)準(zhǔn)看起來(lái)是比較敏感的。因此這就把他的名聲給炒起來(lái)了,因?yàn)楫?dāng)時(shí)上面越是點(diǎn)你名,你就越紅。我們那個(gè)時(shí)候,如果國(guó)外有些漢學(xué)家把你作品翻譯出幾首了,或者上面點(diǎn)了一下,像北島的詩(shī)歌當(dāng)時(shí)有一陣子是能發(fā)表,但是一年譬如說(shuō)只能發(fā)表兩首,它內(nèi)部是有一些規(guī)定的,這種消息一經(jīng)傳出以后,他就很紅了。所以我們這一代的幾個(gè)朦朧詩(shī)人,像北島、楊煉、舒婷,都是當(dāng)時(shí)確實(shí)比較紅。還有一些年紀(jì)其實(shí)跟他們差不多,比如說(shuō)王家新、李小雨等人,他們當(dāng)時(shí)都是在《詩(shī)刊》這樣比較官方一點(diǎn)的刊物上發(fā)表詩(shī)歌,就是說(shuō)他們的東西主流刊物登得比較多一點(diǎn),可能就沒(méi)有那么紅。這里面的情況很復(fù)雜,有時(shí)候確實(shí)搞不清楚,所以我覺(jué)得我這樣其實(shí)也蠻好的,反正我哪兒都不太沾邊。
問(wèn):您當(dāng)時(shí)翻譯的主要是美國(guó)意象派詩(shī)歌和現(xiàn)代主義詩(shī)歌,而且您好像對(duì)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特別有興趣,因?yàn)槟粌H在美國(guó)出版了三部英文版的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選集,同時(shí)在您的偵探小說(shuō)中,您也引用和翻譯了不少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回到八十年代,您當(dāng)時(shí)創(chuàng)作的詩(shī)歌是一種什么類型的詩(shī)歌呢?
答:創(chuàng)作詩(shī)歌我肯定受到了意象派的影響,這是無(wú)疑的,同時(shí)我也受到艾略特的影響,我很欣賞他的那些現(xiàn)代主義詩(shī)歌,當(dāng)然我的老師卞之琳對(duì)我的影響,肯定也有。我用中文寫作的時(shí)候,受這三個(gè)方面的影響比較多。后來(lái)我改用英文寫作之后,我更傾向于從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中去汲取素材。確實(shí)如你剛才所講的,我的小說(shuō)里面有不少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的翻譯,這是因?yàn)槲冶緛?lái)就很喜歡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我覺(jué)得如果要把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歌的成就跟古典詩(shī)歌來(lái)比的話,那確實(shí)是有一段距離的。不管是音樂(lè)感的效果也好,或者意境來(lái)說(shuō)也好,還是從整個(gè)用字的技巧來(lái)說(shuō),古典詩(shī)歌都是一個(gè)高峰。而我在小說(shuō)里面引用古典詩(shī)歌呢,一方面是因?yàn)槲蚁矚g古典詩(shī)歌,另外一方面其實(shí)也有一些是意外的因素,因?yàn)槲冶緛?lái)是特別喜歡艾略特的,我很想在小說(shuō)里面引用他的詩(shī)歌,但是我的出版商不干,他們說(shuō)因?yàn)檫@個(gè)東西涉及到版權(quán),你要引用它的話,如果它的版權(quán)沒(méi)到期,就會(huì)很麻煩,哪怕你只引用幾行,都得付不少錢,否則人家是可以告你的,所以他告訴我別引。
問(wèn):所以您小說(shuō)中的現(xiàn)代詩(shī)歌都是您自己創(chuàng)作的嗎?
答:我有不少是自己創(chuàng)作的,還有不少就是把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拿過(guò)來(lái)翻譯成英文現(xiàn)代詩(shī)。在小說(shuō)中加入詩(shī)歌其實(shí)最開(kāi)始是一個(gè)嘗試,當(dāng)初我跟出版商是這么講的,我說(shuō)中國(guó)古典小說(shuō)里面是有詩(shī)歌的,所以我的小說(shuō)里面加入詩(shī)歌,這個(gè)也算是一個(gè)發(fā)揚(yáng)傳統(tǒng)吧,這是一。第二呢,我蠻喜歡人家講的那種lyricalintensity,就是所謂抒情的強(qiáng)度,因?yàn)閷懶≌f(shuō)你不可能一直就停留在同樣的強(qiáng)度,有些時(shí)候你是敘事比較多一點(diǎn),有些時(shí)候你的抒情成分可能要多一點(diǎn),這就像莎士比亞說(shuō)的那個(gè),有些地方要blankverse,有的地方你是prose就行了,本身在narration上的intensity是應(yīng)該有所區(qū)別的,所以我覺(jué)得有些地方你放幾首詩(shī)進(jìn)去也有比較好的效果。最初的時(shí)候,出版社他們也不大相信,他們覺(jué)得你是寫偵探小說(shuō),好像跟詩(shī)歌關(guān)系不大,但是我比較堅(jiān)持,所以他們就跟我說(shuō),那咱們先試試看再說(shuō)吧。結(jié)果書印了以后,讀者的好評(píng)還蠻多的,書也得獎(jiǎng)了,也有不少讀者寫信到出版商那兒去,說(shuō)他們喜歡里面的詩(shī)歌,甚至有另外的一些出版商,說(shuō)他們要幫我出版詩(shī)歌,他們說(shuō)出版詩(shī)歌他們并不能付給我多少錢,但他說(shuō)他至少可以幫我印,不用我出錢。所以第一本小說(shuō)出來(lái)以后,我就好像是騎虎難下了,因?yàn)槌霭嫔逃X(jué)得每個(gè)人寫的東西都得有自己的特色,他覺(jué)得在偵探小說(shuō)中加入詩(shī)歌成為我的特色了,那我就得保持下來(lái)。當(dāng)然,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最早在華盛頓大學(xué)教書的時(shí)候自己也教過(guò)一些詩(shī)歌,也翻譯過(guò)一些,所以當(dāng)然也有比較懶的成分在里面,現(xiàn)成的東西我在小說(shuō)里面用一下,所以就是這好幾個(gè)因素都湊起來(lái)了,偵探小說(shuō)里面的詩(shī)歌就一直保持了下來(lái)。
二、關(guān)于小說(shuō)
問(wèn):偵探小說(shuō)在西方是一種特別成熟的小說(shuō)類型,具有廣泛的讀者基礎(chǔ),在寫作上也有一定的模式,您的小說(shuō)對(duì)西方的偵探小說(shuō)進(jìn)行了中國(guó)式的發(fā)揮與改造,是您對(duì)西學(xué)的了解促使您做出了這種最能夠贏得美國(guó)主流市場(chǎng)認(rèn)同的選擇嗎?或者說(shuō),您在最初考慮寫英文小說(shuō)時(shí),是否做過(guò)這種理性的思考呢?
答:并沒(méi)有,其實(shí)我本身是很喜歡偵探小說(shuō)的,我以前也經(jīng)常看。可能這兩天St.LouisPost-Dispatch會(huì)發(fā)表一篇文章,不是我寫的,但是會(huì)寫到我跟住在圣路易斯的一個(gè)美國(guó)桂冠詩(shī)人Mona Van Duyn之間的一些交往,她是一個(gè)很好的詩(shī)人,但是她已經(jīng)去世了,以前我每次去她家,她家里都放著偵探小說(shuō)。很奇怪,有不少詩(shī)人,都喜歡偵探小說(shuō),可能覺(jué)得寫詩(shī)蠻累的,就看看偵探小說(shuō)換換腦筋。
問(wèn):或者是不是因?yàn)閮烧咧g有一定的聯(lián)系性呢?在您的偵探小說(shuō)《紅旗袍》的破案過(guò)程中,您多次提到“意象”這個(gè)詞,給我的感覺(jué)就是,是不是您寫偵探小說(shuō)的過(guò)程與您寫詩(shī)或者解讀一首詩(shī)的過(guò)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答:真有可能是這樣。因?yàn)榘蕴匾残U喜歡偵探小說(shuō)的,他的詩(shī)中那種意象之間的跳躍,就像你講的,可能就像各種線索,有了這些線索你才能弄明白一首詩(shī)。美國(guó)有一個(gè)批評(píng)家,叫艾倫·維利(Alan R.Velie),他在談《紅旗袍》的時(shí)候也談到過(guò)跟你接近的觀點(diǎn),他就認(rèn)為陳探長(zhǎng)是將解析艾略特時(shí)磨練的分析技能運(yùn)用到對(duì)謀殺案的偵破中,說(shuō)我實(shí)際上是在用各種各樣的西方批評(píng)方式在寫這本書。但是,回到我怎么會(huì)去選偵探小說(shuō)這個(gè)問(wèn)題上來(lái),因?yàn)槲?6年還是97年的時(shí)候第一次回國(guó),你知道中國(guó)你六、七年不回去變化就特別大,當(dāng)時(shí)我看到上海的變化就覺(jué)得蠻驚訝的,所以我就想,我可以寫點(diǎn)東西來(lái)記錄一下這種變化,我當(dāng)時(shí)確實(shí)寫了一首詩(shī),一首英文長(zhǎng)詩(shī),后來(lái)也發(fā)表了,但是我自己并不滿意。我覺(jué)得如果你要寫社會(huì)的變化,詩(shī)不一定是特別好的媒介,因?yàn)樵?shī)歌主要反映的是你自己的心靈,而當(dāng)時(shí)感受到的那種震驚,那整個(gè)的震撼的感覺(jué),哎呀,怎么變成這個(gè)樣子了,詩(shī)歌是寫不出來(lái)的,因此那時(shí)就想寫小說(shuō)了。寫小說(shuō)呢,我最早并沒(méi)有想過(guò)要寫偵探小說(shuō),但是構(gòu)思中的主人公跟現(xiàn)在的主人公有點(diǎn)接近,也是一個(gè)知識(shí)分子,我就是希望借這個(gè)主人公來(lái)想一想,為什么中國(guó)社會(huì)會(huì)有這些變化,整個(gè)的前因后果都好好地想一想。但是,我碰到了一個(gè)結(jié)構(gòu)問(wèn)題,因?yàn)槲覜](méi)寫過(guò)長(zhǎng)篇小說(shuō),因此結(jié)構(gòu)就特別難掌握,但是偵探小說(shuō)有一個(gè)好處,就是你從結(jié)構(gòu)主義的角度來(lái)講,它是有幾個(gè)比較固定的模式和元素的,一般你首先總得制造懸念,然后你總得去破案,最后你總得有個(gè)結(jié)論,所以我就想那干脆把我要寫的東西放到這么一個(gè)現(xiàn)成的模式里面去,這也是偷懶的一個(gè)辦法,結(jié)果沒(méi)想到出版商看了以后很喜歡,然后跟我說(shuō),你還得往下寫,于是我就這么繼續(xù)寫下來(lái)了。但是,事后想起來(lái),我確實(shí)也受到了西方一些偵探小說(shuō)的影響,因?yàn)楝F(xiàn)在西方偵探小說(shuō)當(dāng)中有一個(gè)流派,就是所謂的社會(huì)學(xué)流派,sociological,他們的重點(diǎn)不是說(shuō)誰(shuí)殺了誰(shuí),而更多的是在什么樣的社會(huì)和政治文化背景當(dāng)中,這樣的案子會(huì)發(fā)生。那么,這個(gè)就跟我的初衷其實(shí)蠻接近的,因?yàn)槲冶緛?lái)就想寫這個(gè)社會(huì)的變化,人物為什么會(huì)是現(xiàn)在這個(gè)樣子。那么,在無(wú)意當(dāng)中我也就進(jìn)了它的這個(gè)路子了。寫這個(gè)路子最有名的是兩個(gè)瑞典作家,叫麥·荷瓦兒(Maj Sjowall)和派·法勒(Per Wahloo),我受他們的影響蠻大的,其實(shí)很滑稽,他們兩個(gè)都是共產(chǎn)黨員,他們的初衷是要寫資本主義的黑暗,結(jié)果寫著寫著就成了出名的偵探小說(shuō)家了,所謂sociological approach就是他們開(kāi)的頭。
問(wèn):您小說(shuō)中的故事都是發(fā)生在一定的中國(guó)背景里,在特定的時(shí)期,中國(guó)出現(xiàn)的很多詞匯可能就簡(jiǎn)單的幾個(gè)字,但它的背后卻蘊(yùn)含了很多的心理暗示的內(nèi)容,外國(guó)讀者對(duì)于這些就很難完全理解,您在您的英文小說(shuō)中是如何處理這種情況的呢?
答:你這個(gè)觀點(diǎn)很對(duì)。有一次我在香港參加一個(gè)文學(xué)會(huì)議,國(guó)內(nèi)有一個(gè)作家叫韓少功,他寫了一本書叫《馬橋詞典》,被翻譯成英文了。當(dāng)初這本書要找commentator,我談的就跟你的觀點(diǎn)很接近,我說(shuō)這個(gè)東西很難,因?yàn)樵谝粋€(gè)語(yǔ)言里面,譬如說(shuō)“知識(shí)青年”這個(gè)詞,我們這一代人對(duì)這個(gè)詞的理解就自動(dòng)地加載了好多積淀的成分在里面,就是這么這么回事情,當(dāng)時(shí)是沒(méi)辦法的,是不想去也得去,后來(lái)就逼著你到農(nóng)村去什么的,一提到這個(gè)詞,所有的聯(lián)想就全上來(lái)了。可是這個(gè)東西,你用英文來(lái)寫,它就是educatedyouth,對(duì)于西方讀者來(lái)說(shuō),這個(gè)根本就沒(méi)有那種聯(lián)想意義的,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說(shuō)這個(gè)人是受過(guò)教育的年輕人,這就跟中國(guó)讀者讀到的完全就是兩回事情了。“文化大革命”也是,我這一代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是很心酸的一段經(jīng)歷,而一般的西方讀者,他們看到culturalrevolution,他就會(huì)認(rèn)為革命還是好事情的嘛。所以這個(gè)東西要解釋清楚確實(shí)很難,因?yàn)槿绻闶菍慳cademicpaper,沒(méi)關(guān)系,你可以在下面加“注”,人家一看就知道這是怎么回事情,而你寫小說(shuō)是不能這么做的。處理這個(gè)到現(xiàn)在為止對(duì)我來(lái)講都是蠻困難的一個(gè)事情,我爭(zhēng)取盡量地通過(guò)背景描寫,通過(guò)對(duì)話,或者有時(shí)通過(guò)設(shè)計(jì)一些小的場(chǎng)景,使這些東西讓英語(yǔ)的讀者以及其他語(yǔ)的讀者知道,哦,原來(lái)是這么回事情。但是我不能去加注,一加注這個(gè)小說(shuō)就讀不下去了,這樣一來(lái)reading flow就給打斷了。
問(wèn):您以前從事的是詩(shī)歌翻譯和創(chuàng)作,是相對(duì)嚴(yán)肅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研究,現(xiàn)在您創(chuàng)作的是偵探小說(shuō),如果大家把它定義為通俗文學(xué),你對(duì)此有什么樣的感受?
答:我自己倒覺(jué)得這個(gè)沒(méi)什么,我覺(jué)得,第一呢,如果我寫一本很modernist的、很現(xiàn)代主義的或者很后現(xiàn)代主義的小說(shuō),只有兩三百個(gè)讀者的話,那我寧可寫我這個(gè)。因?yàn)槲矣X(jué)得從接受美學(xué)的角度來(lái)講,一個(gè)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它跟讀者的接觸當(dāng)中,作品寫出來(lái)沒(méi)人看,那也就是沒(méi)有生命了。但我也試著在偵探小說(shuō)的模式里面盡量地加入一點(diǎn)其他的文化的、知學(xué)的,以及其他比較嚴(yán)肅的東西。比如說(shuō)明年五月份將出版的第十本偵探小說(shuō)《BecomingInspectorChen》,我在形式上就把它打亂了,每個(gè)章節(jié)都是一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故事,這些故事都跟主人公陳超這個(gè)人有點(diǎn)關(guān)系,都跟他怎么會(huì)變成現(xiàn)在這么一個(gè)inspector有聯(lián)系。這可能也是所謂后現(xiàn)代派的觀點(diǎn),因?yàn)橐郧按蠹叶加X(jué)得人的身份是一種賦予,但是我覺(jué)得,其實(shí)人的身份是在跟其他人的交往中不斷地建構(gòu)起來(lái)的,它從來(lái)不可能說(shuō)是一成不變的,這種建構(gòu)過(guò)程有時(shí)候連你自己都沒(méi)有意識(shí)到,有些事情看起來(lái)跟陳超沒(méi)有什么關(guān)系,但實(shí)際上過(guò)了多少年以后就影響到他會(huì)去做現(xiàn)在這個(gè)決定了。以前傳統(tǒng)的小說(shuō)人物多是平面人物,這個(gè)人就是這么回事情,或者說(shuō)這個(gè)人是因?yàn)榻邮芰耸裁礃拥慕逃妥兂闪嗽趺礃樱怯袝r(shí)候很多人和事你是很難用一句話來(lái)講清楚的。存在主義哲學(xué)認(rèn)為,你是做了什么樣選擇所以你得接受怎么樣的后果,但問(wèn)題是,好多選擇都是人家在給你做,并不是你自己做的,所以你才變成現(xiàn)在這樣的人了。就像很多時(shí)候選擇是被推到陳探長(zhǎng)面前的,比如說(shuō)80年代國(guó)家為大學(xué)生安排工作,所以本來(lái)是熱愛(ài)文學(xué)的他陰差陽(yáng)錯(cuò)地成為了一名警察;很多選擇也可以被與自己有關(guān)或者無(wú)關(guān)的人輕易決定,而自己可能完全不知情。在《Becoming Inspector Chen》中,我就想通過(guò)這樣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觀點(diǎn),來(lái)反思陳探長(zhǎng)在中國(guó)這么一個(gè)急劇變動(dòng)的社會(huì)中的是如何成長(zhǎng)為現(xiàn)在的陳探長(zhǎng)的。
問(wèn):對(duì)于您的偵探小說(shuō)系列的評(píng)價(jià),西方社會(huì)很多贊譽(yù),但是在國(guó)內(nèi)也有一些消極評(píng)價(jià)。可能因?yàn)槟鷮懙轿母镆约拔母飳?duì)現(xiàn)代人心理造成的一些影響,再加上您身處西方社會(huì),這些消極評(píng)價(jià)估計(jì)難以避免。東方主義是您很熟悉的西方理論之一,那么,您在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中有沒(méi)有刻意去回避這個(gè)問(wèn)題?
答:我覺(jué)得你這個(gè)問(wèn)題很好,從寫第一本書開(kāi)始我就有意識(shí)的盡量不要去搞東方主義那一套。在一本小說(shuō)里面,我還故意借主人公的口對(duì)美國(guó)來(lái)的一個(gè)警察專門講了一段話,他說(shuō),你們好像都覺(jué)得中國(guó)人是留著辮子的,只會(huì)martial arts,只知道kungpao chicken,其實(shí)你們這個(gè)觀點(diǎn)不對(duì),他就拿自己舉例講,說(shuō)他也蠻喜歡你們美國(guó)的艾略特的詩(shī)歌,他也喜歡英語(yǔ),所以不要老是把東方主義這套東西拿去套。其實(shí),我應(yīng)該說(shuō)是從第一本書開(kāi)始,就有意識(shí)地避免去寫一些像有些電影里面那種比較落后的、或者原始色彩特別濃的東西,應(yīng)該說(shuō)我寫的都是相當(dāng)現(xiàn)代的,而且都是寫發(fā)生在大都市里面的故事,我覺(jué)得東方主義是應(yīng)該避免的。至于“文革”,我覺(jué)得,第一,我沒(méi)有一本書是直接寫文革題材的,我確實(shí)寫文革對(duì)這個(gè)主人公有很大的影響,而且經(jīng)常會(huì)在書里面寫它對(duì)人物所造成的心理陰影。我覺(jué)得,現(xiàn)在國(guó)內(nèi)對(duì)文革的處理有的時(shí)候有點(diǎn)像掩耳盜鈴,這不僅僅是中國(guó)這一個(gè)國(guó)家的浩劫,而且從整個(gè)globalage的角度來(lái)講,為什么會(huì)發(fā)生這樣的事情,本身都是很值得反思的,人性的黑暗,我們必須要正視。像文革這些東西,我覺(jué)得現(xiàn)在是寫的太少了,而不是太多。因此我覺(jué)得這也是我的責(zé)任的一部分,我知道這個(gè)事情,我就一定要寫出來(lái),如果說(shuō)國(guó)內(nèi)的批評(píng)家要怎么想,那我就管不了這么多了。有一些官方的批評(píng),比如說(shuō)我寫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因?yàn)橐ビ懞梦鞣阶x者,我覺(jué)得這個(gè)是很荒謬的。新批評(píng)里面有一個(gè)觀點(diǎn),叫做intentional fallacy,就是說(shuō)去猜測(cè)一個(gè)作家的意圖是很荒謬的事情。因?yàn)檎f(shuō)實(shí)話,有時(shí)候作家自己都不知道,我為什么要寫,你憑什么去說(shuō)我寫這個(gè)就是為了要去討好西方讀者呢,這個(gè)我覺(jué)得是根本就是不能成立的。譬如說(shuō),你舉出例子來(lái),我是哪兒討好了西方,或者說(shuō)我寫的這個(gè)不是真實(shí)的東西,這個(gè)可以大家拿來(lái)討論,說(shuō)我這個(gè)是夸張得過(guò)頭啦,或者這個(gè)完全是編造的,但往往事實(shí)比小說(shuō)中寫的還要嚴(yán)重多了。所以像他們這種說(shuō)法,基本上我也不會(huì)去理會(huì),他們?cè)敢庠趺凑f(shuō)就怎么說(shuō)吧。
問(wèn):現(xiàn)在國(guó)內(nèi)把像您這樣在海外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華人作家稱為離散作家,您如果同意這種稱呼的話,您覺(jué)得您更屬于哪邊,您覺(jué)得在哪邊讓您更有一種安定的感覺(jué)?
答:我覺(jué)得其實(shí)隨便用什么稱呼都行,這個(gè)無(wú)所謂,這只是一個(gè)標(biāo)簽。但是我自己呢,有好多西方的讀者問(wèn)過(guò)我,說(shuō)為什么我到現(xiàn)在為止還沒(méi)有怎么去寫西方的東西,因?yàn)樗麄冇X(jué)得你是完全有能力寫西方的小說(shuō)的,我也想過(guò)這個(gè)問(wèn)題,后來(lái)我也跟他們討論過(guò),我說(shuō),可能是一種心理上的因素,我覺(jué)得我在寫中國(guó)的東西的時(shí)候我有自信,這并不是說(shuō)我一定能寫得怎么好,但是至少我寫中國(guó)的東西我還是有把握的,但是要我寫西方的東西,譬如說(shuō)寫美國(guó)人或者寫法國(guó)人,我就不那么自信。
問(wèn):在您的偵探小說(shuō)大獲成功之后,您創(chuàng)作了一本短篇小說(shuō)集《紅塵歲月》,我很喜歡這本書。如果說(shuō)偵探小說(shuō)使您獲得了美國(guó)主流社會(huì)的認(rèn)可,在您贏得一定的聲譽(yù)之后,您是否會(huì)多創(chuàng)作詩(shī)歌以及像《紅塵歲月》這種更具文學(xué)性卻在市場(chǎng)上不占優(yōu)勢(shì)的作品?
答:確實(shí)是這樣,這也正是我的想法。因?yàn)槲椰F(xiàn)在,比如說(shuō)出些詩(shī)選或者翻譯詩(shī)選,以及包括出版像《紅塵歲月》這樣的文學(xué)作品,這個(gè)從經(jīng)濟(jì)收益上來(lái)講,它們肯定不如偵探小說(shuō),但是我現(xiàn)在基本上能做到不一定在意這個(gè)事情,只要我自己覺(jué)得有意思,我就可以出版。
問(wèn):您到目前為止已經(jīng)出版了三部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選集,在編選的過(guò)程中,您比較傾向于選擇哪一些古代詩(shī)人的作品呢?
答:這里有我個(gè)人的一個(gè)看法。以前,有一個(gè)翻譯中國(guó)詩(shī)歌的美國(guó)學(xué)者,叫阿瑟·韋利(Arthur David Waley),他有一個(gè)觀點(diǎn)我很贊同,他說(shuō)翻譯詩(shī)歌還得考慮你翻譯過(guò)來(lái)以后這個(gè)翻譯過(guò)來(lái)的詩(shī)還有沒(méi)有那個(gè)form,或者說(shuō)讀上去還是不是一首詩(shī),如果你翻譯過(guò)來(lái)以后讀上去不是詩(shī)了,那他就不用這首詩(shī)了。我是很贊同他的這個(gè)觀點(diǎn),但是具體來(lái)講呢,因?yàn)槲乙郧跋矚g意象派詩(shī)歌,我覺(jué)得有些詩(shī)它在中文里面很好,比如說(shuō)像杜甫的一些詩(shī),議論性較強(qiáng),從中文文字來(lái)講很好,但翻成英文以后,很難將原詩(shī)的文字韻味轉(zhuǎn)達(dá)出來(lái)。這倒不一定是說(shuō)翻譯者的功力不夠,當(dāng)然,翻譯的人的功力不到,確實(shí)也是個(gè)問(wèn)題。一些議論性的詩(shī)歌,它有好多典故,這些你在英文當(dāng)中是翻不出來(lái)的。但是有些詩(shī)歌呢,比如說(shuō)像李商隱的詩(shī)歌,他用意象、用象征用得比較多,這種詩(shī)你翻譯的時(shí)候比較取巧,翻成英文以后,它還是一首詩(shī),所以我選的時(shí)候,我就選翻譯過(guò)來(lái)還能是詩(shī)的。當(dāng)然有時(shí)候翻譯過(guò)來(lái)不是,我扔掉的也有的不少。就是說(shuō),你必須翻出來(lái)以后讀起來(lái)還有詩(shī)的味道。那么,有些像通過(guò)意境、意象、象征來(lái)表現(xiàn)的詩(shī),我就選得比較多,而那些議論得比較多的詩(shī),在中文里很漂亮,在英文里卻是沒(méi)辦法傳達(dá)的,我就選得比較少。有些杜甫的詩(shī),他的議論是很好的,像“兩朝開(kāi)濟(jì)老臣心”,你翻成英文是什么意思呢,兩個(gè)朝代,一個(gè)老official,他很loyalty,西方讀者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這種就是沒(méi)辦法翻譯出來(lái)的東西。而意象呢,在這個(gè)語(yǔ)言里面它是一個(gè)意象,你翻譯過(guò)來(lái)以后,它還是一個(gè)意象,當(dāng)然可能它的內(nèi)涵會(huì)有一點(diǎn)不一樣,但這個(gè)還是能搬的。
問(wèn):您現(xiàn)在主要從事哪一些工作呢?詩(shī)歌創(chuàng)作和文學(xué)評(píng)論還在繼續(xù)嗎?
答:有。有一本詩(shī)集也是將在法國(guó)和意大利先出版,叫《陳探長(zhǎng)詩(shī)選》。
問(wèn):《陳探長(zhǎng)詩(shī)選》?它選的都是您在小說(shuō)中用到的詩(shī)歌嗎?
答:不一定,光用小說(shuō)里面的肯定不行,因?yàn)樽x者會(huì)覺(jué)得是受騙了,都看過(guò)了,你得有些新的,就是小說(shuō)里面還沒(méi)有的,或者小說(shuō)里面只用了一部分的。其實(shí)這也是一個(gè)trick,因?yàn)槟阏f(shuō)是我的詩(shī)選,人家不會(huì)去買,而說(shuō)是陳探長(zhǎng)詩(shī)選,人家就去買了。出版社就是靠陳探長(zhǎng)的fans來(lái)保本,至少不賠錢。但是,這個(gè)詩(shī)選在英國(guó)和美國(guó),到現(xiàn)在為止還在研究當(dāng)中,因?yàn)樗麄冇X(jué)得這樣做還是不能賺錢。文學(xué)評(píng)論方面呢,前兩年我去澳大利亞的一個(gè)大學(xué)做了一段時(shí)間的訪問(wèn)學(xué)者,碰到那兒的一個(gè)學(xué)者,也是一個(gè)教授,他是教creative writing的,他現(xiàn)在有一種寫批評(píng)的方法叫Fictocriticism,虛構(gòu)批評(píng),我蠻喜歡的。他所謂的虛構(gòu)批評(píng),就是把批評(píng)文章寫得不像學(xué)院派,有的時(shí)候像講一個(gè)故事,或者講一段經(jīng)歷,但它又不是寫一個(gè)短篇小說(shuō),它往往就是講一段自己的小的經(jīng)歷,將這段經(jīng)歷跟他要講的文學(xué)的東西聯(lián)系起來(lái)。我看過(guò)他幾本這方面的書,我自己也蠻感興趣的,所以前陣子也寫了幾篇這種所謂的虛構(gòu)批評(píng)的文章,因?yàn)榭赡芫褪怯X(jué)得,自己小說(shuō)寫得多了,也不想再去寫那些人家看上去就只是學(xué)院里面的東西,而更傾向于寫一般的讀者也可以讀的東西,但是呢,這也不會(huì)妨礙你在這個(gè)里面去講你所謂現(xiàn)代的、后現(xiàn)代的東西。
問(wèn):您覺(jué)得您現(xiàn)在還在維持著一個(gè)學(xué)者的身份嗎?還是更多的是一個(gè)小說(shuō)家的身份?
答:我沒(méi)有刻意去追求什么,我覺(jué)得寫小說(shuō),那些批評(píng)的理論肯定還是要去看的。如果說(shuō)我寫的東西跟其他偵探小說(shuō)作家寫的東西有一點(diǎn)不一樣,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就跟我的文學(xué)理論的背景有關(guān)系,我比較喜歡那些理論的東西,這些理論你不一定要在小說(shuō)里面直接去展現(xiàn),但它肯定還是會(huì)影響你的創(chuàng)作,而且這個(gè)影響會(huì)給你一種不同的視角來(lái)看問(wèn)題。
A Poet Under a Detective’s Cloak:An Interview With Chinese-American Writer Qiu Xiaolong
〔US〕Chen Xuan
(School of Humanities,Lindenwood University)
Infusing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classical and western modernist poetry into his detective fictions is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features of Qiu Xiaolong.Qiu’s background and identity as a translator and a poet make his detective fictions distinctive from others.Qiu not only creates a new Chinese character which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Charlie Chan,but also introduces a more commercialized and modernized China to the western society.This interview mainly focuseson Qiu’s poems and detective fictions.For him,even though“this is not an era for poetry”,Qiu has been continuing to explore poetry creatively in his detective fictions.
Poetry;Imagism;Translation;Detective Fiction;Historical Reflections
責(zé)任編輯:方長(zhǎng)安
陳璇(1983—),女,湖北武漢人,美國(guó)林登伍德大學(xué)中國(guó)研究系講師,文學(xué)博士,主要從事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