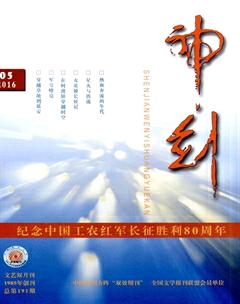懷想寓言時代
傅逸塵
面對21世紀初年文學的種種頹敗之相,不能不有一種愧對先鋒文學之感:一方面是我們屈從于世俗大眾文化話語對先鋒文學藝術實驗和終極關懷的遏止、批評甚至清理;另一方面是理論界對歷史轉型所必然要出現的價值觀念的變異和文化道德的喪失缺乏應有的預判、闡釋和引領,以至于轟轟烈烈的先鋒文學在遭遇冷落之后陡然間便土崩瓦解,好像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湮沒無聞。愧對之后便是難以言說的懷想。或許并不是懷想先鋒文學本身,而是懷想先鋒文學曾經嘔心瀝血構建的寓言時代。寓言不應該成為昔日衰敗的黃花,它的光彩足以輝映21世紀初年中國文學的救贖之路。
對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批判已經無法補救地證明了我們的無知與淺薄,而將中國一九八五年前后崛起的先鋒文學等同于西方的后現代主義文學則不免失之于簡單與粗暴。新時期先鋒文學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本質區別在于,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學所表達的是“存在”的“毫無意義”,以及蟄伏于其中的“地獄”“虛空”“無”,是失去了安全感后的惶惑與痛苦,這是二戰后整整一代,甚至兩代人的普遍心理與情緒。在語言探索中表現了語言外表意義業已喪失,成為一種無法解決的不確定的游戲,從而徹底拒絕了宏大敘事。而新時期先鋒文學在背棄傳統的同時卻極力構筑文學的寓言城堡,而且與宏大敘事保持著異質同構狀態,其深度模式的營造使得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理性空間得以從未有過的拓展。進入21世紀,當我們面對以消費為主導、由大眾傳媒所支配的、喪失了時代主流話語的頹敗的文學世相的時候,我們確實不能不愧對先鋒文學,無法不懷想文學的寓言時代。
蕭瀟是典型的80后,敏感、感性甚至略帶矯情的氣質在她的小說中顯露無遺。故事層面并不出奇,也談不上好看,甚至于有點寡淡的味道。她的獨特并不在于題材的怪異與主題的超驗性探求,而在于以獨特的藝術感受觸摸物象,用細膩入微的感覺方式去描繪肖像,以至于敘述語言也形成了自己的個性。所謂的“喬張造致”,并不停留在小說的能指層面,而在于所指的寓言化深度模式的構建,這使得蕭瀟的小說具有了理性化色彩和哲學思辨的品格。無論是《大悲咒》中對二人轉演員現實生存狀態與精神心理空間的帶有悲憫情懷的逼視和拷問,還是《白雪》中對精神/肉體、高雅/凡俗、歷史/當下、傳承/變異等等對立存在的重新拆解與建構,都是為了表達對人類生存的終極關懷以及尋找家園的近似于烏托邦的精神。蕭瀟小說文本與外在世界的深刻遇合,傳達出尖銳對立卻又渾融一體的隱喻效果,這無疑是一種高級的小說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