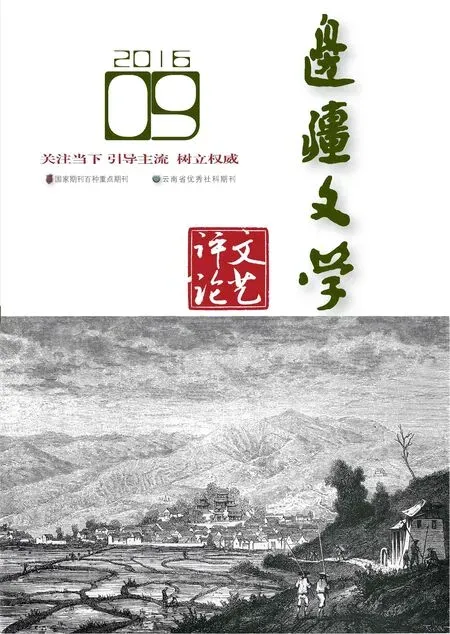一夢江湖去五年,歸來風物故依然
——作家竇紅宇其人其作
◎孔蓮蓮
一夢江湖去五年,歸來風物故依然
——作家竇紅宇其人其作
◎孔蓮蓮
一、竇紅宇和他的三部長篇
第一次見竇紅宇應該是五年前,是在曲靖的一個五星級酒店里,他邀約我們三個曲靖師院的文學博士和他聊文學。他上身立領T恤,下身牛仔褲,運動鞋,寸頭,黑邊眼鏡,一笑就露出了殘缺的四環素牙。見了面,他對我們仨恭敬而客氣,飯菜很豐盛。那時他的第三部長篇《斑銅》剛剛在大型文學刊物《十月》出版,他暢快不羈地給我們聊他的這個作品,并欣喜地告訴我們他已經將這部小說的版權賣給了北京一家著名的影視文化公司,價錢不菲。杯酌間他給我們講了很多他和文學名人的軼事。在當時,我這樣的文學菜鳥,以為他就是個像樣的文化名人,心中頗為歡喜和仰慕。那次聊到很晚,他話鋒不減,興趣盎然,但是我卻睡意襲來,終于沉不住氣,打斷他的興致,要求回家。竇紅宇似乎顯得有點興味索然,但還是禮貌地送我們離開,他甚至為我們叫了輛出租車,并闊綽地把出租車費提前墊付了。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曲靖作家,感覺曲靖作家很有名士之風。回來的路上,王博士揶揄我道:“孔老師,你以后說話要注意,在知名作家面前還是應該收斂一下個性。”我才覺悟,心中有些不安。之后,再沒和竇紅宇有聯系,雖然彼此互留了聯系方式。
再次和竇紅宇見面是我博士畢業,從北京回來后。受我的同事梁競男博士的邀約,他帶了一群曲靖的作家朋友聚餐。依然是以前的那副打扮,只是肚腹比以前大了。依然是把酒談文學,相聊甚歡。也許是我在京城長了見識,也許是竇紅宇的人生狀態在發生變化,這一次,我感覺他的名人范兒淡了。又經過幾次吃飯喝酒,我已經叫他“竇哥”了。
對于我們大多數的草根來說,竇紅宇確實有資本驕傲一下,名士之風是有家傳的。他祖上乃師宗竇氏,若參觀過師宗的“竇氏祠堂”,你就知道竇氏的輝煌歷史,比如岳陽樓長聯的作者竇垿就位列其中。竇紅宇的父親是大學教授,母親是醫生,出身書香門第。竇紅宇還有一段輝煌歷史不可不提,他曾經是云南大學中文系銀杏文學社的第四任社長,他那時作社長還有個外號“豆殼”。我親耳聽到《邊疆文學》主編潘靈,大學時代和竇紅宇一起玩文學的哥們,見面時還叫他“豆殼”。那時候做銀杏文學社社長可比當學生會主席風光,要曉得,銀杏文學社的第一任社長可是大名鼎鼎的于堅詩人。
我曾經問過他大學畢業后為什么不留省城,卻回到小城市曲靖。他一直含混其辭,說當時有一個叫“曲靖藝術研究所”的單位很吸引他,他就回來了。(當然后來他還是轉行去了《曲靖日報社》)。我卻認為他回曲靖的真正原因,不外乎云南人“家鄉寶”的心態。他曾經寫過一篇在我看來很有立場的散文《一個人與一座城市》,在文章中他說:“是的,我離不開曲靖了。從生活的層面上說,這叫‘住慣的山坡不嫌陡’,從文化的層面來說,這叫存在的必然性。套用海德格爾“詩意地棲居”這句話,我已經在這座城市中找到了‘詩意’,并開始了真正地‘棲居’”。我想,曲靖多么需要這樣的熱愛本土,認同本土,書寫本土的優秀作家啊!
竇紅宇的文學實績體現在他的三部長篇小說上。這讓他不僅在曲靖,就是在整個云南甚至全國范圍的長篇文學界,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一路花瓣》,發表于2003年《大家》第一期。2006年,被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改編成電影《扣人心弦》播出。2004年1月,被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以“十月小長篇”的形式出版發行。小說貌似講述了一個小城里發生的警匪懸疑故事,而就內容實質來看,卻又是一個愛情故事。在充滿欲望與邪惡的人物關系中,因著那青春時期的愛情而讓故事有人性之花綻放,散發出了芬芳。這部歷時一年半寫成的長篇已經展現了竇紅宇創作上的獨特才華:故事講述的精彩性和通俗性,對市井各色人物的身份把控和善惡觀照,小說語言,特別是人物語言的地方性和個性化。
竇紅宇的第二個長篇小說《你帶我回家》,2007年《大家》第一、第二期連載。小說共26萬字,斷斷續續歷時四五年才寫完。這部小說相比于其他兩部,影響力不夠大,但是據我來看,這部反映城鄉矛盾的作品,是值得閱讀和研究的。故事延續著竇氏小說耐讀和有趣的特征,很巧妙的是,雖然他的主要筆墨寫城市人性的貪婪欲望和道德缺失,但他是通過一個叫郭金平的鄉下人為妹尋仇的個人經歷反觀和對照來表現城里人的惡。他對幾個城市姑娘的個性化塑造,立體多面,饒有趣味。僅就構思和主題來說,足夠讀者好好品評。
他的第三部長篇《斑銅》,是給他帶來最大聲譽的作品,發表于《十月》2011年長篇專號第三期。發表后,即被北京唐德影視改編成40集電視連續劇(目前正在拍攝中)。2015年3月,被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并獲得當年由《都市時報》評選的“云南十大好書”獎。關于這個作品,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讀書感受,雖然這個作品的評論文章不少,包括著名作家洪峰對小說《斑銅》的介紹。
二、古典而清澈的《斑銅》
一個曲靖的作家,為一座小城的一個傳統工藝寫了一部傳奇。之前,沒有人用小說的方式開掘這個彈丸之地的歷史。此一點,是《斑銅》的突破之一。那個在小說中被叫做“遠平”的地方,坐落在滇東北的一隅,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銅鄉。斑銅,一種精湛的制銅手藝,在作家生動穩健的故事講述中,伴著革命的煙火,斑駁滄桑,漸漸浮出地表,閃耀著古典而清澈的光芒,再次被21世紀的我們看到。
這段從1923年到國共內戰結束大約25年的歷史,正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開創階段。然而作家竇紅宇對故事的講述方式卻是古典主義的。此乃《斑銅》的突破之二。在小說語言上,他對古典白話文有意模仿,采用文白夾雜的方式,在小說結構上,則是采用了“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中國話本小說的體制,話本小說通過題詩表達主人公或者寫作者的情感和評價,這個技巧被竇紅宇運用得純熟而巧妙。這些讓我們看到了作家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向往和追慕。除了這些古典主義的小說技法,更重要的,從小說的精神旨趣來看,同樣體現著作家對傳統文化的回歸。
當讀到小說《斑銅》的尾聲:“入夜,段騎龍手牽慧珍,立于金鐘山頂之文昌殿前”時,一個中國式的“有情人終成眷屬”,“正義戰勝邪惡“的“大團圓”結局呈現出來,之后,作者假借張慧珍之筆,用一篇氣勢磅礴,蕩氣回腸的《斑銅賦》結束了傳奇的講述。回顧《斑銅》編織出來的人物倫理關系網,清澈單純,一望了然,我們看到了一個幾乎沒有倫理糾結的故事。作家竇紅宇為人物關系預設的道德倫理標尺是一個很傳統很古典的觀念,那便是“有情有信”。以此道德標尺,他如全能的上帝,裁決了他筆下的人物命運。甚至,他用他“有情有信”的標尺裁決了歷史。他讓重情重義的人獲得情義也贏得民眾,他讓失信他人失信歷史的人得到懲罰走向毀滅。因著《斑銅》的這點徹底,它的作品表現出與很多類似題材作品的不同。這點不同是古典主義的勝利,也使得竇紅宇的歷史敘事風格在21世紀的后文化環境中得以奇葩般地綻放。莫言的《紅高粱》或者陳忠實的《白鹿原》,這些同樣是把家族變遷與革命歷史復調講述的“史詩性”故事,都有一個沖破傳統倫理的女性,《紅高梁》里的戴鳳蓮,《白鹿原》里的田小娥,她們死了,前者在死前有一段她個人與上天的訴說,表達了她對自我的堅持;后者的死令白鹿原村的人站成兩派,修廟派和建塔派,前者把她奉為神,后者將她當做鬼。以上作品都能看到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在人物關系和歷史關系上的沖突、斗爭、妥協和融合。但是《斑銅》沒有這么多的糾結和斗爭,當張慧珍這個集結著對愛情的堅貞,對造銅工藝的執著,對家鄉親人的大愛于一身的完美女人成為小說的女一號時,女二號瑤巧兒被她映襯出來的污穢和惡劣就讓人無法容忍。而作者最后給瑤巧兒的死設立的罪名是“虎毒不食子”,這是一個具有傳統倫理意義的罪名,是一個具有永恒意義的普世價值判斷。《斑銅》的清澈單純更在于他對傳統之德的持守與歷史之正的選擇合二為一。這讓他很正統的處理了人性善惡與政權善惡的關系。從小說整體寓意來看,文薇生的弱與酸,瑤巧兒的貪與狠的人性成為國民黨政權失敗的歷史注腳;而段其龍和張慧珍等人的“有情有信”成為共產黨政權獲取民心并奪取政權的有力人性根基性佐證。如果說《白鹿原》是一條從黃土高原漫延伸展下來的泥沙俱下,寬廣渾厚的大江 ,《斑銅》則是一條從烏蒙山脈的高峰上匯集雨雪,奔流而下的瀑布溪流。實際上,高山上的瀑布溪水才是大江大河的真正源頭。
通俗文學與先鋒文學的不同在于,前者把持的道德倫理標尺是大眾化的,后者往往超越大眾化的倫理標尺,建構一種不為大眾所接受的倫理范式。可是,著名通俗文學大師金庸的武俠小說在俗與雅,在批判與構建的問題上,卻有著常讀常新的意義。中國文學,用了整整一個世紀,與其他文化樣式合作完成了中國現代性啟蒙的任務。站在21世紀的潮頭回望這段以西方文化作樣板的文化啟蒙的歷史,“矯枉過正”的事實每每令國人焦慮甚至捶胸頓足。不失時機的回歸中國傳統,包括回歸中國漢語傳統,中國小說傳統,中國倫理傳統,甚至中國工藝傳統等等,是懷有本土情結的作家們樂此不疲的事情。在以上意義上,《斑銅》做到了,《斑銅》的成功,說明了傳統文化的偉大生命力。
三、復雜而多聲部的《大地生》及其他
在作者的授權之下,我想說說他已經付梓但還沒有面市的長篇小說《大地生》(將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這又是一部“一夢江湖去五年”的心血之作。這個作品是他對前幾部長篇的又一次超越。
竇紅宇自己說:“《大地生》這部作品,雖然只有32萬字,但卻花費了我五年多的時間(2011年至2016年)。在此期間,我只專心寫作這部作品,從來沒有發表過任何文字。”
關于這個作品的故事梗概和思想內涵,竇紅宇本人這樣理解:
“這部作品講述的,是一個名叫沈如石的作家寫作一部名叫《大地生》的作品的過程。是在講述一個做著英雄夢的小城知識分子在不斷變革的當下社會中所受到的歧視與侮辱,其實,進一步揭示的,是歷史和現實,文化和強權的博弈。
這部小說共十五章,每一章都分為歷史部分和以附記形式出現的現實部分。歷史部分,以半文半白的近似話本的形式,講述了一個英雄的將軍,國軍王牌軍軍長王胄抗日犧牲的一生。而現實部分,以現代的、西方化的語言方式,講述了作家沈如石寫作這部小說的全過程。”
竇紅宇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不斷和我交流。他最先完成了歷史部分,即抗戰英雄王胄將軍的故事。竇紅宇曾經告訴我,為了寫王胄,他去省外的王胄將軍墓地拜訪過幾次。每次拜見,他都會在他墓前叩拜大哭。所以,他對英雄的敬仰和臣服是骨子里的。這是他和年輕一代作家的不同之處。看完王將軍的故事,我寫了這樣一段:
“作為一部向反法西斯70周年獻禮的作品,是極為忠誠的。小說兼顧了愛國之義和愛滇之情。小說有大手筆,戰爭場景的設置頗顯功力,沙場情景再現較好,英勇精神表現充分。在情節和人物關系上有精彩之處,但還不夠細膩和精致。有些重要場景可以再雕琢。
小說采用通俗敘事的方式。通俗性作品最大的特點是人物形象的類型化,人性表現的理想化,情節安排的曲折傳奇化,可以滿足大眾化的讀者審美期待和欲求。如果單從以上來說,這部小說沒有超越通俗路線。小說的文本似乎在尋找一條通俗性和民族性融合的路,如何能結合的更好,以后應該怎么走?這是作家需要面對的命題。
小說著力塑造的國民黨的高級將領王胄將軍,簡潔概括就是:對軍隊“嚴苛”,對共產黨有“情義”,對日本鬼子“仇恨”,對百姓“愛”,對女子“敬”,對妻子“念”,對父母“孝”,在戰場上“瘋”。寫盡王胄之勇猛無畏和英雄氣概。甚至,王胄因著他的偉大的信仰,可以在富貴榮華之上有超脫。小說對王胄作戰之英勇的描寫多于其作戰之智慧的表現,使得作品氣勢有余而靈動不足。”
他對我的評價沒做反應,而是繼續埋頭創作。2016年3月,竇紅宇即將去北京魯迅文學院作家高級研修班學習,走之前,他把全稿發給我,希望能聽到我的意見。在讀完小說的現實部分,即作家沈如石的生活狀態時,我讀出了《廢都》的味道,我以一個女性讀者的身份,漸漸冒出了無名火,并噴薄而出,向竇紅宇質疑:
“沈如石已然一副舊式文人的架勢,除了珍饈美饌,更有眾多美女圍繞。在有了美(藍秀紅),錢(蔣玉蓮),以及后代撫養保姆兼美食保姆(曲珍)的陪伴之后,竟然還有王藍這樣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美女子隨時恭候,成為他躲避世俗的一片清凈地。沈如石的人生還有什么不滿意?當某個女子對他有背叛,他又何必尋死覓活,來一段矯情做作的離騷之嘆!當他知道林雷,一個不該死的殺人犯被槍決后,他為此喝得爛醉如泥,仿佛看出了一點文人的正義和擔當,然而,一旦有女子和美食引誘,那點悲憫和來自社會良知的疼痛,立刻消失,繼續著自己食色美事。他什么都想要,給當政者爭搶,可惜沒搶過,最后還是靠當政者給沈如石出了口惡氣。與有錢者茍合,竟然也讓蔣玉蓮破產,還好這個女人真心實意的愛文人,最后成為沈如石的一個依托。沈如石為了擺平各個女人,賣身寫作,甚至放棄掉自我的獨立思考權力。沈如石才是最應該被批判的知識分子!小說的結尾卻讓各個女子結局悲慘,而讓沈如石繼續著他的名利雙收。試問,作品的思想高度在哪里?作家的思想高度在哪里?作家的高度應該在于他能超越小說中的沈如石,看到沈如石的問題,并用情節和人物命運達到批判的意義!僅僅讓沈如石為王藍哭天搶地一番,是不足以體現出一個作家的反省精神和懺悔品格,更不能體現出作品的思想深度。”
我把這段文字用微信發給竇紅宇的時候,他正坐在去北京的火車上瞌睡,他開玩笑說被我的憤怒“嚇醒了……”然后又道: “好,評得好!孔老師息怒,我覺得你生氣,說明我寫成功了!”我很無語,他的男徒弟旁邊的一句幫腔讓我感覺到了自己的偏激:“其實沈如石的惡已經通過王將軍的善矯正過來了”。是的,作為一部完整的小說,完善的王將軍和不完善的沈如石同是竇紅宇筆下的人物,我們在閱讀這部小說的時候,不應該割裂開來。而我對兩個部分的不同閱讀體驗正是因為我割裂這個作品本身的合一性。所以,下面一段竇紅宇關于自己作品的聲明是重要的 :
“所以,這部作品在長達五年多的創作中,充滿了文本實驗的性質。一方面,傳統話本的形式與現代小說的“混搭”,我力圖在形式上讓讀者感受到一種傳統語言與現代語言的撕裂感,從而進一步體會到傳統和現代的撕裂。另一方面,在故事內容上,小說自然呈現出了一種宏大的歷史和卑微的現實的撕裂感,英雄的將軍與現代小人物的撕裂感。沈如石在這部作品中所表現的,就是一個有著英雄夢想又不斷在現實中反抗、妥協的小城當代知識分子無奈的命運。”
《大地生》是竇紅宇長篇創作史上的又一次嘗試,成功與失敗,只有從廣大讀者的反映上才能知道。
竇紅宇花費了他人生15年的時光,不緊不慢地完成了他的四部長篇小說。他說:“在曲靖生活,適合沉下心來寫長篇小說。”曲靖,這個被評為全國“十大宜居城市”之一的滇東北小城,以它舒緩的生活節奏和低成本的生活質量養育了一群慵懶又詩意的文人。這群人可以每天對著太陽,對著野花,對著青山,對著綠草思忖幾個小時,然后用十幾分鐘寫出片斷文字。
但是今年四個月的北京之行改變了竇作家的某些創作想法。也許魯迅文學院的氛圍刺激了他,也許是文化中心的成功節奏刺激了他,他開始寫中短篇了。令人欣喜的是,一個長篇小說家,改寫中短篇竟然上手很快,已經有捷報傳來:新創作的中篇小說《青梅了》,2016年7月被國家級文學刊物《十月》留用,即將發表;短篇小說《我要去北京》,2016年7月被著名大型文學刊物《山花》留用,即將發表。
竇紅宇從北京回來了,我們一群文人又可以吃喝了。他說:“我要寫中短篇啦!”這直接就是皇城的節奏啊。讓我用一首蘇軾的《浣溪沙》表達祝福吧:
一夢江湖費五年。
歸來風物故依然。
相逢一醉是前緣。
遷客不應常眊矂,使君為出小嬋娟。
翠鬟聊著小詩纏。
(作者系曲靖師院青年教師,文學博士)
責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