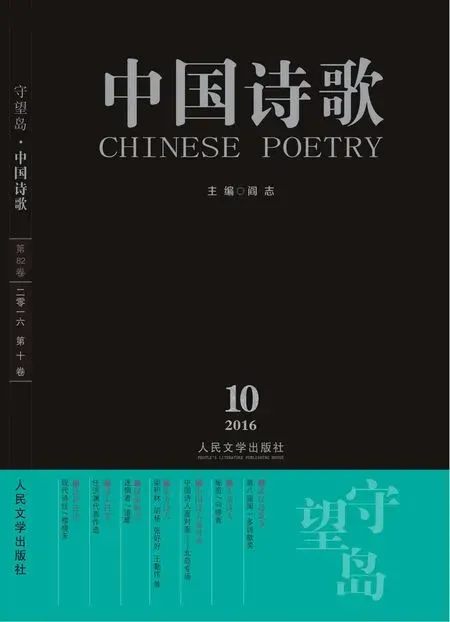茅草的詩
茅草的詩
MAO CAO
杏
杏跟著姥姥進城來了
躲在一個竹籃里偷偷地看我
她紅紅的臉酸溜溜的心事
還在回憶與我的過往
那時候她長在樹枝上
飽滿的身體把樹枝壓彎
我調皮又貧窮
一心想攜著她去私奔
現在我掏出人民幣
把一籃杏全買下來了
我大口大口地咀嚼她們
感覺不到當年的味道
迎春葉
迎春花不愿意再做迎春小姐
躲在迎春藤里不肯出來
我走過春天
走了整整一個季節
也沒有看見迎春花的身影
迎春藤站在路兩邊
派出一些葉子來歡迎我
回來
樓道里擠滿了人
樓上有一間更大的辦公室
大家都想去
都拼命地往樓上擠
我從我的小辦公室里走出來
猶豫不決
一步三回頭走到樓道前
天就黑了
窗玻璃上的霞光轉了一個彎
我面對窗戶心隨霞光飛去
樓上的那間大辦公室與我的書房偏差太大
算了吧
我還是轉身回家
聽老歌的感受
一支死去的歌曲活過來了
它想找到它曾經呆過的地方
想找到唱過它的喉嚨
想看到那張熱情洋溢的臉
結果它沒有如愿
世界已經面目全非
它活過來是孤獨的
一個不合時宜的人走在大街上
東張西望怪模怪樣
除了幾只耳朵對它有點兒熟
它對什么都不熟悉了
陽臺
陽臺掛在半空中
依附在墻上
飛不起來也掉不下去
供室內的人出來
曬一曬陽光除一除霉味
吸一吸新鮮空氣
贊一條褲
一條沉不住氣的褲
遇到一點豐滿就和盤托出
本是一個遮遮掩掩幾千年的地方
現在原形畢露
不留一絲兒余地
擠出一個心臟的形狀
我恍惚聽到怦怦的心跳聲
恍惚看到一只蝴蝶
飛出峽谷
飛過流水淙淙的小溪
衰老
歲月一直跟蹤我
跟蹤我五十多年
我一直想甩掉它
可是甩不掉
現在它猛撲上來
對我的肉體進行圍剿
細菌和病毒組成聯軍
把一些器官追得東奔西逃
靈魂是肉體的叛徒
它得救了
它目睹肉體老態龍鐘
在我的書房里朗誦小說和詩歌
父親的拐杖
父親手里的拐杖
跟在老黃牛的后面
聽著老黃牛的腳步聲辨識方向
父親走在望不到盡頭的犁溝里
探索著要走的路
父親手里的拐杖
撐著我頭頂上的夜空
月亮星星不會掉下來砸傷我
父親手里的拐杖是我命運的杠桿
撬起我腳下的道路
我從低處走向高處
走進了大學住上了高樓
父親看著我走穩了住安定了
倒在了我起步時的那個低處
羨慕
草莓苗生活在陽臺上
我兒子養著它
我兒子把目光澆給草莓苗
草莓苗懷著一顆草心
回報給兒子潔白的花朵
夜晚的我
走進夜晚
我躺在自己的影子里
太陽來臨
把影子從我身體里拉出來
這個季節的花朵
花嘟著嘴
不說話
扮一個撒嬌的相
風搖動它的肩膀
它不回答
兀自在黃昏里靜靜開放
紅紅的嘴唇咧開
想笑
想一吐為快
其實都不是
等采花的人來
以色彩示人
失眠者
失去了職位和酒杯
也失去了睡眠
嫦娥靜悄悄地站在窗外
不再進來陪他
那些好聽的詞從耳朵里撤退
回到了制作它們的嘴里
而那些嘴緊緊地閉著
再也不肯松開
妻的聲音重復而又單調
他喝著一杯白開水
沒有一點味道
一朵花的裸照
白玉蘭在太陽下分娩
剛剛降生的白玉蘭又白又嫩
一位老人坐在陽臺上曬太陽
他瞇縫著眼想
白玉蘭是不是早產了
綠葉的襁褓還沒來得及準備
這時候樹下走過來一位新娘
攝影師的燈光一閃一閃
熒屏上留下了白玉蘭的裸體
留下了老人的淚光
兩棵含笑樹
太陽沒有推動辦公樓
把辦公樓的身影推倒在地
辦公樓的陰影逮住了一棵含笑樹
另一棵含笑樹見勢不妙
跑到了陽光中
被陰影逮住的那一棵含笑樹
想笑笑不出來
跑到了陽光中的那一棵
炸蕾怒放
上班的人下班的人
都不愿意走近陰影中的那一棵
繞道也要走在陽光中去
灌木
1
喬木有向上爬的本錢
灌木長不高
灌木不認為自己長不高
老怪喬木遮住了自己
2
喬木一手遮天
灌木生活在它的陰影里
灌木想走到沒有喬木的地方去
卻邁不開步
宿福州三明大廈601房間
4月8號至11號
我下榻福州市三明大廈601房間
準備參加明天的會議
這恰好符合我的人生
坐了一天的車有點勞頓
走進房有一種到家的感覺
把門打開把窗戶打開
讓風吹進來
坐在床上盤著腿
看電視入了迷忘記了在哪里
上衛生間沖個澡
跟在家里一樣
晚飯后站在窗前
前面是滿城的燈光
感覺妻子就在我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