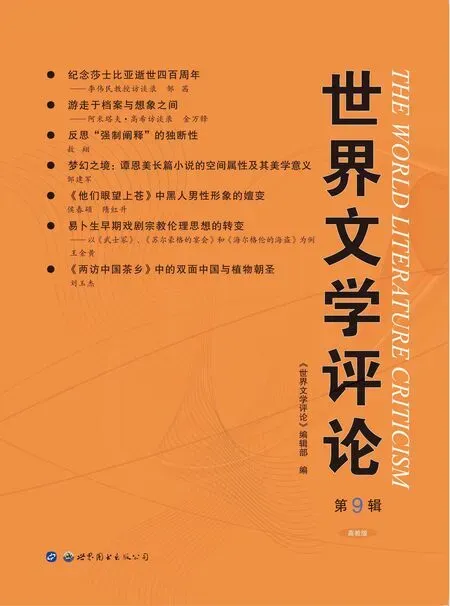廢名小說中的“橋”:從物象到意象
高 爽
廢名小說中的“橋”:從物象到意象
高 爽
廢名的小說對“橋”的書寫主要有地理景觀的再現和文學景觀的闡發兩種方式。在廢名的小說中,作為地理景觀的“橋”區分著城市與鄉村,同時也為兩個不同空間中人的交往提供了場所。城與鄉的空間差異在人際往來中得到了彌合,溫暖樸素的人性光輝使得“橋”的兩端不再隔膜。“橋”與人的互動也推動了地域文化的生成,“橋”演化成為了“奈何橋”這一民俗符號,它標記著此生與來生的差異,也象征著人生的終極拷問。這一文化符號的形成反過來影響了作家的創作,他賦予了“橋”以彼岸和人生選擇的文學景觀意義,使“橋”最終成為了廢名小說中個性化的意象符號。
地理景觀 文學景觀 廢名 橋
“景觀”強調的是特定地理空間的可視性特征,具有物質和觀念的兩個層面的意義,廢名對“橋”的書寫就存在著側重物質層面的再現和側重觀念層面的象征兩種方式,前者是指將“橋”作為地理景觀進行再現式描寫,如果說小說所描繪的特定地理空間使得這一文體“具有內在的地理學屬性”[1],那么再現于小說中的“橋”無疑是廢名的文學空間中不可或缺的地理學標記;后者則是作者對“橋”對這一景觀的個性化文學解讀,它不再僅僅只是景觀的再現,開始具有了特定的象征意蘊。對于“橋”的象征意蘊,論者歷來多有關注,其思路主要集中在意象內涵分析和審美心理分析兩個層面:前者著重分析“橋”所象征的內涵,將“橋”視為人生之橋,提出“‘橋’意象的出現,暗示了人物成長的重要轉折”[2],并在此基礎上將研究視野從廢名擴展到京派文人,認為在廢名的影響下,“京派作家豐富和增加了橋意象的符號功能”[3];后者則注意到“橋”對作家審美心理的構建所產生的影響,認為這一意象“明顯來自童年的心理殘跡”[4],論者通過分析“橋”的審美特質揭示作者傾注在意象上的思想觀念,借以理解廢名的生命哲學。然而上述兩種研究思路均建立在對“橋”的象征意義分析的基礎上,忽略了廢名作品中對于“橋”的地理景觀特征再現。
具體到廢名的文學創作,其小說中的人和事大多以故鄉黃梅為背景,故鄉風物大量出現,營造出了“略帶牛糞氣味與略帶稻草氣味的鄉村空氣”,作品中那些“小溪河、破畫、塔、老人、小孩,這些那些,是不會在中國中部的江浙與北部的河北山東出現的。”[5]廢名小說鮮明的地域特色使其成為了地理景觀研究的典型文本,而“橋”作為小說中地方性地理景觀的典型代表,則是作家建構文學地理空間的重要媒介,它連接著自然、人文環境和作家本人的審美傾向、創作個性,不僅參與建構了廢名的故鄉想象,也為“橋”這一文學景觀的意義生成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廢名小說中作為地理景觀和文學景觀的“橋”,理解“橋”的景觀意義。
一、作為地理景觀的“橋”
在文學地理的研究中,地理景觀被視為特定“價值觀念的象征系統,而社會就是建構在這個價值觀念之上的。從這個意義說,考察地理景觀就是解讀闡述人的價值觀念的文本。”[6]對地理景觀的解讀實際上是對特定區域的自然環境、人的價值觀念以及社會意識形態三者互動的理解與闡釋,因此,對廢名小說中“橋”地理景觀意義的考察能夠揭示自然環境、社會文化和人的互動。
(一)“橋”的地理空間特征:城與鄉的界線
廢名的童年離不開故鄉的橋。廢名的家在黃梅縣城,城外岳家灣的外家是童年的廢名常去的地方,一路上過橋、過河、走鄉村小道,其小說中許多風景描寫正是以此為原型,“小橋城外走沙灘,至今猶當畫橋看”,沿路的小橋沙灘成為了廢名終生懷念的風景。出縣城南門到外家不過一里半的路程,一路上卻要過三座橋,對廢名來說,橋這頭的城市生活于自己百害而無一利,橋那頭的鄉村自然風光則仿佛是一本天然的教科書,為他的童年增添了絢麗的色彩,也成就了他后來的文學事業:“我所受的教育完全與我無好處,只有害處……只有‘自然’對于我是好的,家在城市,外家在距城二里的鄉村,十歲以前,乃合于陶淵明的‘懷良辰以孤往’,而成就了二十年后的文學事業。”[7]一邊是僵化乏味的城市日常生活,一邊是生機盎然的鄉村世界,橋是連接兩個世界的媒介,更是區分彼此的界線。
城市與鄉村隔橋相望,構成了彼此的風景。城外過河西走,壩下竹林里住著三姑娘一家,三姑娘溫柔淑靜,父親去世后更是對母親格外體貼。正二月間城里賽龍燈,鄰近村上的女人相約進城看燈,而三姑娘卻推辭不去,堅持留在家里陪媽媽。村人們像一陣旋風一樣簇擁著進城,三姑娘卻只在壩上遠遠向縣城望著,護城河正值枯水期,行人紛紛棄橋不渡,摩肩接踵直接走河床上的沙灘到對岸,遠遠望去“一簇簇的仿佛是遠山上的樹林”,“木橋儼然是畫中見過的,而往來蠕動都在沙灘”[8]。媽媽埋怨三姑娘老守著自己不進城玩,三姑娘就嬌惱著仍舊伴媽媽坐在燈下,遠處傳來城里喧天的鑼鼓聲,三姑娘和媽媽只無聲地捆著第二天早上要賣的白菜,“鑼鼓喧天,驚不了她母子兩個,正如驚不了棲在竹林的雀子。”對于三姑娘來說,橋那頭城市的喧鬧只是遠方的風景,而竹林里母女二人的寂靜無聲才是生活本來的樣子。三姑娘總是穿著一身舊衣服,卻也意外地合身好看;母女二人種菜賣菜為生,不富裕卻也足夠生活。一切都是這樣樸素,一切又都是這樣恰如其分,三姑娘就好像竹林和遠山的精魂,無聲地散發著玉石一般溫潤的光輝。與三姑娘的淑靜相對照的則是“我們”的熱鬧,城里的我們“望見三姑娘都不知不覺的站在那里笑。然而三姑娘是這樣淑靜,愈走近我們,我們的熱鬧愈是消滅下去”[9]。河上一座小小的橋將三姑娘留在了寂靜詩意的彼岸,對城里的“我們”來說,三姑娘才是真正的風景。
橋作為區分城鄉的獨特地理景觀,在空間上將城市與鄉村分離開來,廢名童年經驗中的橋正處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它連接著兩個完全不同的地理空間,也標記著城鄉的距離與差異。
(二)“橋”與人的互動:人情的彌合
橋雖然區分了城與鄉,但橋的兩端卻并不是斷裂對立的兩個世界。浣衣母李媽青年喪夫,帶著兒女住在城外河邊的茅草屋里,她的茅草屋就在城門外橋頭邊,每日里行人熙熙攘攘,出城到河邊洗衣服的婦人和女孩、剛剛放學歸來的少年、守城的士兵,來來往往無不經過李媽的門口。“橋”為李媽的茅草屋帶來了熱鬧與生機,而待人寬厚的李媽正是在同各路鄉鄰打交道中方才顯示了其性格的樸素之美。她不貪心,城里太太轉送給她的禮物她轉手就送給了鄰居王媽;她和駝背女兒都十分愛孩子,常常義務地承擔起幫城里太太照看小孩子的任務;對待進城賣柴的鄉下人,她不僅沒有瞧不起,還準備好涼茶和點心招待在自己門前歇腳的鄉人。對于“橋”這頭的城里太太來說,李媽雖然也和自己一樣,算得上是城里人,但又比自己命運更悲慘、生活更艱難,因此她們對李媽總是多照顧幾分;對于“橋”那頭的鄉下人來說,李媽是城里人,但又比其他城里人更和善更熱情的人,得到李媽的照拂,他們也就格外感激。如果說“橋”的兩端是城市與鄉村這兩種差異性的地理空間,那么李媽就是溝通二者的媒介,正是有李媽這樣博愛而寬厚的地母形象存在,城與鄉之間差異的裂痕才得以在溫暖的人性光輝中得到彌合。橋作為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中間物,則為這種彌合提供了場所和可能。
(三)“橋”的社會文化內涵:符號的生成
“景觀不僅僅是一種‘事物’,而且也必須看成一種意識形態的或象征主義的過程,具有積極地形成人與人之間、人與其物質世界之間關系的力量。”[10]因此,當景觀呈現出符號意義,也就具有了形塑人們的文化母體功能。橋作為黃梅常見的地理景觀,從物質層面看它標記著城鄉的空間差異,同時也為兩個空間內人的交往提供了可能、參與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在此基礎上,“橋”作為黃梅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了地域文化的建構,塑造了廢名的文化心理。
鄉下的橋不僅僅是渡河的工具,也是民間傳說的“主角”。《菱蕩》中陶家村的橋相傳是何仙姑為度擺渡老漢升天而修,修完橋仙姑還順便洗了洗手,于是橋邊又有洗手塔。“橋”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媒介,那里有仙人,也有鬼蜮。人死后究竟是和仙人一樣進入極樂世界,還是被牛鬼蛇神帶入地獄,都得過了奈何橋才見分曉。黃梅城外二里東岳廟每隔三年舉辦一次“過橋”,廟里和尚在草地上臨時架起木橋,代表通往地獄的奈何橋,“老太太們過了黃梅縣東岳廟山上的橋,則死后到地獄里去可免過奈何橋。據說奈何橋非常的難過。”[11]當過橋演變成了過奈何橋,橋也不再等同于普通的行路,它成為對人一生功過是非的考察,要到達彼岸,必先經過“過橋”的考驗。奈何橋象征著巨大的考驗,這一民俗符號督促著人們時時與人為善。因此,當廢名談起“過河拆橋”這種自私自利的行為時,還不忘評論一句:“此人總一定不會過奈何橋。”[12]
從“橋”到“奈何橋”,橋這一地理景觀以其地理空間特征為人與人的交往提供了可能,那片土地上樸素又溫暖的人際關系不僅彌合了空間上的差異與隔膜,還推動了當地社會文化的生成,最終形成了極具地域特色的黃梅文化。當“橋”這一地理景觀呈現出民俗符號的象征意義,它也就反過來構成了黃梅人的文化心理,作為地域文化影響著廢名的創作。
二、作為文學景觀的橋
所謂文學景觀,是指“與文學密切相關的景觀”[13],判定一個景觀是不是文學景觀的內在標準在于它是否被賦予了“文學的內涵和審美的價值”。“橋”作為廢名小說中頻繁出現的典型景觀之一,無疑是其文學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類文學景觀。在廢名的小說中,“橋”的文學景觀意義一方面表現為此岸與彼岸的區隔,過橋意味著超度;另一方面,“橋”又不同于普通的行路,它象征著一段艱辛的旅途,需要忍耐住痛苦才能到達彼岸。
(一)彼岸與超度
“橋者過渡之意,凡由這邊渡到那邊去都叫做橋。”[14]橋意味著此岸到彼岸的區隔,過橋也就象征著對彼岸的追尋。小林和細竹、琴子游八丈亭,過橋時原本走在前面的小林停下來讓細竹、琴子先走,他站在岸邊看兩個女孩過橋。細竹走到橋中間站住了,掉轉頭來看小林為何還站在岸邊,“細竹一回頭,非常之驚異于這一面了,‘橋下水流嗚咽’,仿佛立刻聽見水響,望她而一笑。從此這個橋就以中間為彼岸,細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風采,一空倚傍。”[15]這座橋在小林的記憶里本是渡不過的,以前他總是畏縮地站在橋這一邊,不敢過去。然而橋對岸的風光又深深吸引著小林,他曾幾次跑來看,“跑到了又站住,站在橋頭,四顧而返”對岸的風景尚未曾領略,橋中間細竹的一回頭又成了新的風景。小林終于過了橋,到達了期盼中的彼岸,但橋中間回眸的細竹卻成了成年的小林到達不了的新的彼岸。“靈魂永遠是站在這一個地方”,而未曾到達的彼岸總有吸引著自己的風景。但實際上發現了彼岸仍在橋那邊的小林實際上已經是“超度到那一岸去了”,唯有不執著于橋那頭的風景,才有可能真正抵達超脫的彼岸。
(二)選擇與人生
雖然彼岸永遠都在橋的那一邊,但人卻必須永遠在路上。如果說奈何橋是生命旅途盡頭的終極拷問,那么人生旅途中走過的每一座橋都是一次考驗,而如何過橋則象征著不同的人生選擇。
琴子和細竹一同出門,走到一座青石橋前,細竹眼里只有對岸花樹的美景,石橋于她僅僅只是過河的工具,于是她一躍就到了對岸,忙不迭地伸手攀了花枝來聞。而琴子卻絲毫不為彼岸的芳草綿綿、野花綴岸所吸引,她眼里只有橋下的淺水澄沙,走到橋中間,本來宜于遠望對岸,琴子卻只是心里知道對岸的風景,仍舊低頭深視橋下流水,貪戀彼岸風光的細竹早已等得著急,忍不住抱怨:“瞎子過橋沒有你過得慢!”[16]同樣是過橋,活潑天真的細竹貪戀的是對岸的風景,穩重謹慎的琴子則感到了“過橋”的深意,即使心里知道對岸的繁花似錦也仍舊不慌不忙一步一步過去,不放過橋上的風景。到了對岸,琴子還在橋頭立住,望了望來路,“這時她的天地很廣”。不忘來路、不失初心,心知對岸的美景卻也不急于求成,琴子就這樣一步一步安然走過人生之橋。總是被各種各樣美麗的東西吸引著的細竹則在對岸的繁花中收獲了人生的趣味。與其說“橋”是考驗,倒不如說是一種選擇,每一次過橋都意味著一次人生的抉擇,而不同的過橋方式則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三、從地理景觀到文學景觀
廢名賦予“橋”的文學景 觀意義實際上根源于“橋”這一地理景觀的內在特征,廢名小說的地域特征不僅表現在故鄉風物的大量出現,還表現為意象內涵的地域化色彩。卞之琳曾將廢名所構筑的文學空間歸結為“南中水鄉的產物”,他還專門提到,自己的《古鎮的夢》在內容上“同有南中水鄉僻地人物事物風貌,與廢名早期小說有些相通”[17]。卞之琳的這首詩中同樣出現了“橋”這一意象,但他筆下的“橋”明顯地是江南水鄉之“橋”,與廢名筆下的“橋”完全不同。
《古鎮的夢》寫的是江南小鎮上兩種寂寥的聲音,算命的瞎子和敲梆的更夫日復一日地在鎮上走,鎮上的一花一草、一家一戶對他們來說都再熟悉不過,“是深夜,/又是冷清的下午:/敲梆的過橋,/敲鑼的又過橋,/不斷的是橋下流水的聲音。”古鎮上的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其中,他們與整個小鎮渾然一體,物物相應,生生不息。“橋”上人間的聲音與“橋”下流水的聲音交相輝映,世俗的日常生活與古鎮的地理風貌通過“橋”和諧地融為一體。同是描繪南中水鄉僻地風貌,卞之琳的橋是“板橋流水,楊梅枇杷”[18],而廢名的橋則是“楊柳小橋城下渡,三條河水盡西流”[19],一為煙火氣,一為鄉野氣,前者精致,后者活潑。廢名的橋通往的是不同于此岸的鄉村世界,橋兩端城與鄉的空間差異是卞之琳的江南水鄉所沒有的,這一地理景觀差異直接影響了“橋”的文學景觀意義的生成。
廢名賦予“橋”的象征意義在于“彼岸”和“選擇”,而卞之琳賦予“橋”的則是連結與溝通。《圓寶盒》中“橋”的象征意義曾引發卞之琳和劉西渭的爭論,劉西渭認為,橋“隱隱指著連結過去與未來的現時”[20],而卞之琳撰文回應,“橋”這一意象指的是“感情的結合”[21],感情的結合中一剎那之間獲得了可以千古的“道”與“心得”。又因為一切都是相對的,對“我”來說足以千古的“心得”對別人來說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裝飾,然而詩中的“橋”并非實際存在的物象,而是詩人意識中的“橋”,“橋”與“圓寶盒”的小大之辨反映了人的意識與世界的相對性。然而無論是劉西渭的解讀還是卞之琳的自述,“橋”這一意象在他們看來都象征著某種結合。
廢名與卞之琳對于“橋”的書寫存在的差異實際上還是源自他們對于“橋”這一物象的不同認識。卞之琳筆下作為物象呈現的橋連結著世俗生活與自然宇宙,體現著人與自然共處的和諧狀態,因而在賦予“橋”以文學景觀意義時,作者選取的也是這一地理景觀所起到的連結和溝通的作用;而在廢名的文學世界中,橋的兩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這頭是城里的日常生活,而那頭是新奇活潑的鄉村世界,“橋”是連接,更是隔斷。在此岸的生活與彼岸的風景中,廢名偏愛的是后者,因此,他賦予“橋”的象征意味則更側重于“過橋”和“橋”那頭的彼岸。“橋”在廢名和卞之琳的作品中所呈現出的差異正反映出不同空間中的地理景觀對于其文學景觀意義所產生的影響,景觀的物質特性參與建構了與之對應的地域文化,而地域文化又對作者的文化心理產生了塑形作用,最終影響了作品意象的生成與建構。廢名小說中“橋”的地理景觀意義和文學景觀意義的互動實際上也體現了地理空間對于文學創作的影響。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頁。
[2]石明圓:《論廢名小說中的“橋”與“墳”意象》,載《文藝爭鳴》2007年第1期,第90-93頁。
[3]閻開振:《“橋”的意象與京派文學》,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5期,第77-88頁。
[4]饒新冬:《思索生命——廢名小說意象讀解》,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5期,第4-11頁。
[5]沈從文:《論馮文炳》,載《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3頁。
[6][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頁。
[7]廢名:《黃梅初級中學同學錄序三篇》,載《廢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6頁。
[8]廢名:《竹林的故事》,載《廢名集(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頁。
[9]廢名:《竹林的故事》,載《廢名集(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頁。
[10][英]薩拉·L·霍洛韋、斯蒂芬·P·賴斯等編:《當代地理學要義 概念、思維與方法》,黃潤華、孫穎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250頁。
[11]廢名:《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停前看會》,載《廢名集(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34頁。
[12]廢名:《芭蕉夢》,載《廢名集(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02頁。
[13]曾大興:《文學景觀研究》,載《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第76-80頁、第114頁。
[14]廢名:《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五祖寺》,載《廢名集(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5頁。
[15]廢名:《橋·橋》,載《廢名集(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頁。
[16]廢名:《橋·路上》,載《廢名集(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頁。
[17]卞之琳:《〈馮文炳選集〉序》,載《馮文炳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頁。
[18]卞之琳:《尺八夜》,載《新詩》1936年10月10日。
[19](清)梅雨田:《黃梅竹枝詞》,載《黃梅縣志(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0頁。
[20]劉西渭:《魚目集》,載《大公報·文藝》1936年4月12日。
[21]卞之琳:《關于〈魚目集〉》,載《大公報·文藝》1936年5月10日。
Title: The Bridges in Feiming's Fictions: From Objective Images to Subjective Images
Author: Gao Shuang is from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area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implication of the bridges in Feiming's f ction can be explored from two angles of "the objective reappearance of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and "the symbol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terary landscape". Bridges as geographical landscape mark the boundary lin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since it is the major road between these two areas. And the rural-urban differences can be bridged by the friendly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in the f ction, which leads to the unsophisticated folkways in the local area.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ocal people and the landscape, bridges make sense in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the author's hometown, which symboliz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nd the last key to the heaven. This culture symbol affects the creation of Feiming and forms the typical image in his f ctions.
Geographical Landscape Literary Landscape Feiming Bridges
高爽,武漢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