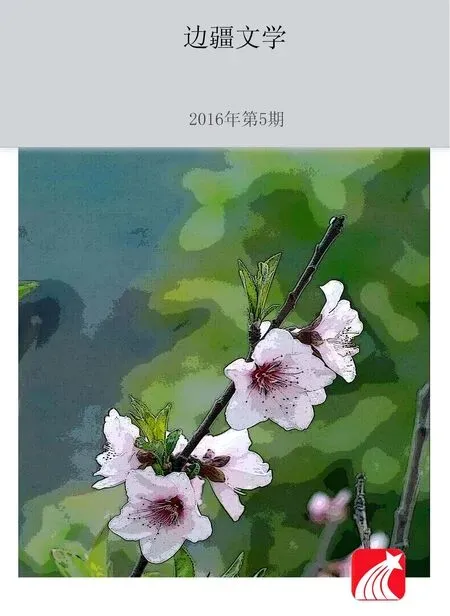詩歌是民族精神之“根”
——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詩歌綜論
◎黃 玲
詩歌是民族精神之“根”
——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詩歌綜論
◎黃玲
一、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詩歌現狀
在這8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中,詩歌都是表現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在一個社會化轉型的時代,民族詩歌承擔著諸多重任。正如吉狄馬加所言:“今天,全人類,包括我們每一個民族,都站在一個現代和傳統、歷史和未來的十字路口上。每一個民族要想獲得自己的通行證,通過這個十字路口,毫無疑問,她的民族歷史和文化就是最好的通行證。”[1]通過詩歌這些民族可以向時代發出聲音,表達和證明自己的存在。
下面我將把《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各民族卷中收入的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詩人的作品進行簡要的梳理總結,或許每個民族目前取得的詩歌成就并不相同,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們都在努力尋找著目標和方向,用詩歌打造著本民族通向現代和未來的文化名片。
1、阿昌族詩歌
“阿昌族卷”共收入12位詩人的24首詩。其詩中最常表現的主題是民族歷史文化和對故鄉、田園的懷想。從他們的詩歌中,經常可以見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和意象。比如一句“遮帕麻和遮米瑪的子孫”就足以概括阿昌族詩歌的文化亮點,體現出一個民族文化上的共性和追求。應該說老一輩詩人在寫作上有比較自覺的民族意識,其作品的民族特色也比較突出。因為他們對民族文化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明確的藝術追求。
曹明強在接受采訪時曾經對自己的寫作特色有過總結:“我早期的詩著重寫我的媽媽、我的大山、我的民族。我們這個民族人數很少,很多人因此心懷自卑,但我要去歌頌自己的民族,讓他們對自己的民族產生認同感。這些年來,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們民族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大家的民族自豪感被激發出來了。我想,我們的文學作品應該去表現、強化這種心理”。[2]他的詩《蹬起來,窩羅》,既是這種思考的具體實踐,也可以視為阿昌族當代詩歌中的優秀之作。對弘揚阿昌族民族文化有很強的藝術感染。
趙家福也說:“阿昌族是一個很弱小的民族,她能夠發展到今天,不知走過了多少坎坷路,不知道背負了多少包袱。當 我在作品中反映這些的時候,會有一些辛酸的歷史和記憶,會有對整個民族發展的憂慮和期盼。作為這個民族的一分子,這些東西同樣體現在我們身上,并通過文字 表現出來。”[3]他的組詩《太陽之戀》由《遠古的夢》和《遠古的愛》組成,從現代人的視角對天神遮帕瑪造天、遮米麻造地,以及創造人類的傳說進行了想象和重構,為讀者“還原”出遠古時期的民族生存景象。和民間詩歌比較,這組詩運用了現代思維和多重視角,體現出鮮明的主體性,把詩人的自我融入民族歷史。詩人回望民族歷史的激情能給人一種震撼之感,他和天地對話,和祖先對話的視角已經超越單一的民族界限,上升到對大地上眾多生命存在的關懷與追問:“我聽見鳥鳴聽見祖先說話的聲音,遠遠地昭示源源生命永恒之謎”。詩人的目光所及的太陽,是世界萬物的靈魂和源頭。
另一位詩人孫家林也對民族歷史文化表達過相同的意思:“我比較注重本民族的歷史,因為你不懂自己民族的歷史,就不會體會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深沉的。我自己的作品沒有什么花哨,更講究歷史的厚重感。”[4]他的詩歌《我的筒裙花喲》視角很小,選擇阿昌婦女身上的筒裙花作為切入點,卻并不僅僅只是為了表現某種民族風情,而是有深深的憂思彌漫其中。曾經被視為民族驕傲和自豪感的事物,在詩人現代意識的觀照下,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所以他在詩的結尾中發出呼吁:“啊,親愛的姐妹們,快把砍刀放下。快去接受知識甘露的滋潤,來年織出更美麗的彩霞。”
具體到詩歌寫作中,民族的歷史文化應該由一些具體事物來體現。比如戶撒刀既是生活用品,就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象征,它與阿昌男人已經成為一對密不可分的存在。甚至在女性詩人的筆下,它們也是被歌頌和贊美的對象。朗妹喊的一首詩題目就叫《戶撒刀與阿昌人》,她以充滿激情的語言表達著對力量和勇氣的贊美:“每一個打刀的男人都是樂師”,是贊美阿昌文化中的浪漫主義精神,突顯了阿昌文化中的獨特審美。“每一個打刀的男人都是一把刀”,則是贊美阿昌族民族精神中尚武和勇猛的歷史傳奇。這首詩取的是女人的視角,對男性的歷史和精神進行了歌頌與升華。但是最后一句詩卻把全詩綰收起來,把男人和女人的不可分離表現得非常生動:“阿昌的女人是刀鞘”。無論如何勇猛的男人,只有當他和女人共同創造,不可分離之時,世界才會更加完美和諧。
囊兆東、孫家奇、趙興源的詩都在表達熱愛故鄉的主題,但風格上各有千秋。
曹先鵬的組詩《心靈之約》和李偉的組詩《習慣了》,都沒有追求民族特色的表達,而是在兩性之情的領域去書寫主體心靈的思悟,強烈的情感能給讀者以感染。文炯貝琶在組詩《月光》中吟唱故鄉、親情,也有軍旅生活的投影,內容比較豐富。趙家健的《荷花》屬于詠物抒情之作,體現了詩人對生活哲理的思考。其中還有已故詩人孫庭園的一組古詩詞作品選,主要寫故鄉的山水風物,有傳統文化的底蘊,雖然民族特色并不鮮明。
“阿昌族卷”中收入的詩歌不是阿昌族詩歌的全部作品,但是已經收入了重要的詩人和代表性作品,基本可以體現出阿昌族當代詩歌的水平和質量。無論詩的題材還是寫作風格都比較多樣化,民族特色并不是唯一的追求。生活在全新時代的民族詩人們,目光和視野已經變得開闊和多元。但是從總體上看,那些以民族歷史文化為題材的詩歌,更有力度和厚重之感,更能體現一個民族的詩歌風格。
2、布朗族詩歌
“布朗族卷”收入5位作者的21首詩歌,從作者隊伍上看有一定危機感。
布朗族是一個有著豐富民間文化的民族,生活中流傳著很多和茶有關系的古歌和民間歌謠,體現著一個民族的古老歷史。但是在現代詩歌的寫作中,卻面臨一些問題和困境,應該引起關注。
“布朗族卷”中收入的21首詩歌,作為布朗族當代文學創史者的巖香南的作品有6首,但基本是民歌的風格。比如《話兒再甜也不能當糖吃》,《問你小妹何方人》,就是民歌體的敘事之作,最初就是收入《中國民間情歌》一書。其余兩首《布朗山河換新顏》、《布朗山上如霞似錦》,采用的是新舊對比的視角,表現布朗族生活的巨大變化。另外兩首《茶的歡歌》、《茶樹之歌》,書寫了茶和布朗族的古老歷史和親密關系,民歌風依然明顯。
俸春華的《索瑪烏》雖然標注為“布朗族史詩”,其實應該是取材于布朗族史詩,是對民族歷史的書寫和表現。詩的結構比較宏大,內容豐富多姿,但是基本沒有脫出民間史詩的框架。他的另外兩首詩《月亮·小魚》和《小鳥》,更有現代詩的特色,主體性比較突出,借月亮和水中小魚、森林中的小鳥,含蓄地表達了某種深層的復雜情感,能引人遐思。
鮑啟銘的《教師勉語》,是對教師職業的歌頌和贊美。沒有民族特色,但對教師的職業有生動形象的描繪和贊頌,情感真摯樸素。
陶玉明的詩收入兩首,《瀾滄江畔走來的精靈》應該是首組詩,其中分別書寫了“黑精靈”、“蜂桶鼓”和“故園”,都是對布朗族民族文化的形象表達。詩的意象都和布朗族古老的事物相關,是對歷史和傳統的追思與懷想,通過它們在詩里營造了濃郁的民族文化氛圍,體現了作者對民族的某種責任意識。《山谷中,那五星紅旗飄揚的地方》,是對辛勤培育布朗孩子成長的教師的感激與贊頌。
值得一提的還有90后詩人郭應華的詩,他的加入為布朗族詩歌帶來了新鮮的氣息。他有向民族歷史文化學習的自覺意識,在《布朗依依》的組詩里詩里他也和其他詩人一樣,盡力捕捉和民族歷史有關系的事物和意象,來抒發自己對民族文化的崇敬感。組詩分為三節,分別是“艾洛卜我”、“蜂桶鼓舞”、“戀戀竹筒茶”,每一種事物都是布朗族文化的寫意。難得的是郭應華在詩歌藝術上的追求已經達到了某種高度,他的詩和老一輩詩人之間已經拉開很遠的距離,可以和當代詩壇接軌和對話。這一點在他的另一組詩《自我抒情》中體現得更為充分。他的詩已經超越民歌體的時代,直接進入現代詩的詩境,體現了比較純熟的詩藝。
比如來看看《煙波深處的玉蝴蝶》這首:
這個時候,你可能看著季節
也可能眺望遠方歸航的郎
陽光一束束拍打著
空氣,池塘或者是一枚熟透的柿子
看得出隱隱約約的一抹紅
此時,我正從柳后經過
一只玉蝴蝶?醉了一湖秋水
有人說時間總是一種巧合
我打掃干凈這一石階
等你上岸
詩中和布朗族的文化完全沒有關系,但是卻和人類復雜多變的感覺、心境有關系。玉蝴蝶的意象在詩中翩翩起舞,扇動著時間和思緒。這組詩讓人看到了郭應華在詩歌上所達到的高度。作為一名布朗族青年詩人,他在詩歌中的追求同時也提高了布朗族當代詩歌的水平和境界。老一輩詩人們多年來的努力奮斗,為布朗族詩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現在已經到了新一代詩人大顯身手的時候。
3、德昂族詩歌
“德昂族卷”中數量最多的文體是詩歌,一共收入12位作者的58首詩。這似乎也說明在德昂族當代文學中,成績最大的文體是詩歌。
德昂族當代詩歌也經歷著由民歌體到現代詩的轉變過程。老一輩作者們從民間詩歌那里學習,開始寫一些民歌體的詩,拉開德昂族書面文學的帷幕。那些今天看起來顯得比較簡單幼稚的作品,其實承擔著為一個民族的書面文學奠基的重任,其意義不容小視。它們體現出的時代感和率真的情感表達,有一種樸素之美。
真正為德昂族詩歌爭得榮耀,把德昂族詩歌帶上一定高度的,是艾傈木諾和她的詩。她身上有好幾個“第一”:第一個德昂族女詩人、第一個出版詩集的德昂族詩人、第一個以詩集獲“駿馬獎”的德昂族詩人。她的詩讓德昂族詩歌真正實現了從民歌體向現代詩的轉變過程。雖然身影單薄,后來者寥寥,但以艾傈木諾目前的創作實力來看,是可以為德昂族詩歌的發展起好引領作用的。
4、獨龍族詩歌
“獨龍族卷”收入的詩歌從數量上看并不少,一共是12位作者的31首詩。對一個人口不到一萬的民族來說,已經是一個可喜的進步。
約翰的《獨龍橋》是獨龍族當代詩歌的奠基之作,以民歌體的形式傳達出獨龍族人對新生活的喜悅之感。這首詩和新學光的《杜鵑獻給來自北京的使者》,是獨龍族作者在20世紀80年代發表的僅有的兩首作品。其意義自然非常獨特。
進入新世紀之后,才有更多的獨龍族作者加入到詩歌寫作的隊伍中來。比如李新明、馬文德、巴偉東、李明元、新學先、楊向群、陳建華、陳雪芹、陳清華、曾學光,集合起一支十余人的寫作隊伍。這個民族的詩歌同樣經歷著由民歌體向現代詩的轉變過程。一些詩人的出現 ,使這種轉變成為可能。他們有著新的觀念、新的藝術技巧,以及對待世界的不同的態度。他們的詩在民族特色上可能不如老一輩詩人那么突出,但是具有更為廣闊的視野和高度。
一批70后詩人是獨龍族詩歌的中堅力量。
巴偉東的《獨龍招魂曲》,曾學光的《雄鷹之夢》,《獨龍江》,陳清華的《蒼狼》,陳建華的《獨龍江》等作品集中代表了獨龍族詩歌由傳統詩向現代詩轉變的成果,傳達了一個民族渴望走向世界,與現代化生活接軌的向往與追求。就像陳建華在《穿越時空隧道》一詩中寫的那樣:
一條隧道/穿破高黎貢的肚腹/將兩個世界連接了起來 /一邊是“太古”之民/一邊是“現代”文明……
90后詩人陳雪芹的詩體現了新一代獨龍族詩人在詩歌藝術上的追求與提升。她的詩并不局限于民族特色的表現,而是以更廣闊的目光和視野去探求歷史縫隙中的秘密,在詩的觀念和技巧上都有一種進步。比如在《倉頡》一詩中,她這樣寫:“多遙遠多糾結多想念多無法描寫/疼痛和瘋癲你都看不見/想穿越想飛天想變成造字的倉頡/寫出能讓你快回來的詩篇……”這首詩意象和想象力都非常豐富,在個人情感和歷史傳說的糾纏中制造了新的審美效果。
從這些青年詩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獨龍族詩歌的希望和理想。
5、基諾族詩歌
“基諾族卷”收入8位作者的28首詩歌。
和其他民族一樣,基諾族很少有專門的詩歌作者,很多人在小說、詩歌、散文的文體中都有成果,三種文體兼而有之。所以基諾族的詩歌作者隊伍年齡結構比較豐富多元,從50后到80后都有出現。
其中羅向明的詩《基諾山,我的故鄉》,曾獲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為基諾族文學帶來了榮譽。這是一首抒情性很強的詩,抒發了作者對民族和故鄉的一片深情,有濃烈的感染力:
“在那茂密的原始森林里/有一只美麗的翠鳥在飛翔/基諾山/你是我生長的地方/我愛你綠色的原野和美麗的山寨。”“在那茂密的原始森林里/有基諾族的村莊和竹樓/基諾山/你是我可愛的故鄉/勤勞善良的基諾人民/正繪制美麗的圖畫/播種幸福和愛情。”
對基諾山風情和生活的書寫,構成了當代基諾族詩歌的主要內容。詩人們開始寫作時,那么迫切地急于表達出對民族和故鄉的濃厚情感,抒發出對新生活的贊美與感悟。所以他們的詩歌在生活氣息和民族風格方面有突出的表現。
比如張志華的詩《雨林中的基諾山》,《思念基諾山》,張云的詩《美在基諾山》,陶亞男的詩《故鄉情懷》,書寫的就是詩人對民族和故鄉的熱愛和贊美。比較集中出現的意象如茶園、竹樓、云海、太陽鼓……構成了基諾山的基本審美意象。詩人們在努力建構和創造著屬于本民族的詩歌形象。
此外的一些詩跳出民族和地域性書寫,在人類情感和心靈世界的豐富方面有所探索,拓展了基諾族詩歌的表現范疇。如陶潤珍的短詩《小鳥飛走的時候》,只有8行,但對女性情感的描寫卻有其獨到之處:
小鳥飛走的時候/江邊的蘆葦搖動著/你走過身邊的時候/我的心顫抖著。
人不在林中的時候/知了鳴叫著/你不在眼前的時候/我輕輕呼喚著。
這首詩寫得輕盈而空靈,傳達了朦朧美好的少女情懷。
張志華的詩題材范圍比較廣泛,除了民族和故鄉他還寫軍營、寫人的情感的豐富性。《英烈之魂》就是對全國緝毒英雄的贊美。
基諾族詩歌已經有了很好的發展基礎,但還期待著代表性詩人和作品的出現。培養年輕一代詩人,讓他們盡快成長起來是當務之急。
6、景頗族詩歌
“景頗族卷”收入16位作者的56首詩,其作者和詩歌數量在8個民族中居于前列。其題材和表現形式都比較豐富,體現出比較成熟的詩歌風格。
書寫故鄉和民族,仍然是景頗族詩歌的主要特色。站在故鄉的土地上開始寫作,這是一種自然的選擇。詩人和故鄉永遠是一種水乳交融的關系。而景頗山這個故鄉同時也是民族生活的地方,是民族文化生長聚集的土地。所以,在詩人們的筆下和詩行中,景頗山、目瑙縱歌都是無法繞過去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意象。穆直·瑪撒的《目瑙抒懷》《在等戛山》,木然·麻雙的《目瑙曲》《寧貫瓦》,木然·諾相的《景頗人》,龍準·勒排早當的《瑞麗情懷》等詩中,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是詩歌表現的重要對象。詩人們通過書寫,希望重新建構和夯實民族文化的根基。這是一種自覺的詩歌意識。
也有一些詩人繞開這些已經固化的內容,尋找著詩歌的突圍方向。他們的詩歌體現出更加多樣化的風格。比如岳丁的詩,就體現出強烈的現代性色彩,在人性的世界努力探索。他的詩寫《人論》,寫《冬妮婭,我想去筑路》,還寫《星期六的思想》、《樹上的魚》:“樹上的魚翹著尾巴/身子忽閃忽閃/聲音忽閃忽閃/目光忽閃忽閃/沒有固定的眼睛/羞花閉月,躲躲閃閃/我迷戀這種氣質。”這樣的詩拓展了景頗族當代詩歌的領域,也提升了景頗族詩歌的品質。
景頗族女詩人群體的出現也值得提及。“景頗族卷”的詩歌部分收入了一批女詩人的作品,分別是勒普·創藏坤努、勒王·果鮮、恩昆·寬寶、恩昆·麻保、恩昆·瑪芳、梅合東、梅何·木瑟等人。她們已經構成一個女性詩歌群體,這在景頗族詩歌史上是一件值得贊頌的事。在8個人口較少民族中也是唯一一個形成女性詩歌群體的民族。 她們的詩清新活潑,生動細膩,在情感表達上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性別意識在詩歌中也體現出覺醒的傾向。勒普·創藏坤努的一首詩就名為《我是女人》,對自己的性別身份并不避諱:“我是女人/一個很平凡的景頗女人/一個只有你愛著的淳樸的女人。”她的詩寫自我,寫母親和奶奶,對女性的性別身份有明確的認知和理解。90后詩人勒王·果鮮的詩《突然在某一天遇到了你》在情感表達上輕盈而空靈。恩昆·寬寶的《思念》中的情感則是強烈而深沉的傾訴。梅何·木瑟的《一個你,一個我》,在愛情中尋找著哲理。這些女詩人的出現,在景頗族詩歌史上絕對是一個值得書寫的事件。
7、普米族詩歌
“普米族卷”中收入15位作者的119首詩。其詩歌數量在8個民族中居于首位,體現了普米族在詩歌文體上的重要收獲。其中已故詩人何順明的《啊,瀘沽湖》,獲得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為當代普米族詩歌揭開了序幕。詩中抒發著對故鄉、祖國的宏大情懷:
“啊,瀘沽湖——生我養我的慈母
多像一顆晶瑩的寶珠
閃亮在祖國的胸脯。”
近年來普米族已經成長起一支比較成熟的詩人隊伍,在全國性報刊上發表了很多有影響的詩作,所以他們不僅在云南,甚至在全國詩壇都有一定影響力。這對一個只有三萬多人口的民族來說,是一個文學奇跡。
其中殷海濤的詩對民族歷史文化比較關注,他的敘事長詩《神奇的花鳥》就取材于民間題材,可以視為詩人對民族文化的學習和吸收。魯若迪基、和建全、和文平、曹翔,這批60后詩人的詩成功實現了與現代詩的對接,他們的詩已經擺脫民歌體的影響,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有很大的提升。
魯若迪基的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沒有比淚水更干凈的水》(后來成了他一部新詩集的名稱)。它以深沉的情感表達和濃郁的詩意傳達了詩人對故鄉刻骨銘心的愛戀,讀來令人感動。“人口較少民族”這個概念對魯若迪基寫作心理的影響是潛在而深遠的,這在“人口較少民族”的詩人中是一個特例。他有詩人的敏感與自覺,也有哲人的縝密與多思。所以他的詩既關注世界上“大”的事物的壯麗與雄偉,更在意“小”的事物的豐富與生動。《小涼山很小》是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詩人在詩中探索著關于“大與小”的哲理表達。
和文平的詩對民族的歷史文化有深入思考和表現,他在《白色的河流》、《送魂線》、《阿媽的頭帕》《穿裙子的年齡》等作品中,對普米族文化有細致表現。其詩風深情、悠揚,為一個民族吟唱著最動情的歌謠。和建全在《祭祖節》中,渴望與祖先的心靈對話,其實是對民族精神的溯源,以詩歌尋找民族的靈魂。曹翔的詩在描寫到故鄉和民族的相關事物時,流淌出一種圣潔的憂傷感。類似于“閃著淚花的星星”這樣的意象在他的詩里制造出一種浪漫的風格。他的詩寫故鄉和民族,但更注重主體心靈對歷史的感受,現代精神和審美意識提升了他詩歌的品質。
70后的詩人以蔡金華為代表,他的詩中有一些關于人生和命運的思考,比如《南方本土》、《放飛十月》、《雛鳥》,借自然之物思考著世界的哲理。他的詩中還有親情、民族和大地,展示著詩人和世界的親密關系。
80后的詩人中戈戎比措的詩體現出很好的勢頭,他迄今已在《民族文學》等全國性報刊發表作品多首,他的出現喻示普米族詩歌后繼有人。他的詩有著80后的特色,和民族、歷史的關系不如60后、70后詩人那么緊密,其詩風體現出更開闊、高遠的視野。他擅長用創造性想象對民族生活內容進行拓展,從更高的角度來抒發人和世界的關系。在《黃昏的隨想》、《秋日隨想》中透露了他的詩追求表達的是:“一切愛戀與歌唱/一切背叛與忠貞/一切火塘里涌動的悲憫。”他的詩里也出現高原、山野、神鷹等事物,但并不指向具體的民族,而是借詩歌創造出一個神性的世界。如他在《高原之神》中所宣稱的:“而一路高歌的我/是大地的王者/是那片高原上神話和夢幻的孩子。”和戈戎比措的王者霸氣相比,同為80后的曹媛的詩寫得更舒緩明麗,有女性特色。她寫故鄉、親情,情感表達如同小溪淙淙。
普米族當代詩歌的實力和后勁,正是通過這些詩人的努力得到體現。
8、怒族詩歌
“怒族卷”收入12位作者的34首詩。從整體上看,當代怒族詩歌還處于發展階段,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整體基調上看,怒族詩歌是積極向上的,表達了一個民族的詩人對故鄉、民族的深厚情感,以及對生活的理想和信念。已故作家羅世富的《怒江情》,施玉英的《怒蘇情韻》,李金榮的《故鄉感懷》、《石月亮》,李鐵柱的《心靈歇息的地方》,陳軍的《阿茸》,都是對怒江山水和怒族歷史文化的追溯與贊頌,充滿令人感動的情韻。地域和民族特色比較鮮明,讓人感受到了一方山水養一方人的哲理。
還有一些青年作者在嘗試著書寫生活的思考與感悟,角度和題材比較廣泛。比如劉文青的《青春短笛》,桑梅芳的《離別》,胡永春的《墻角的蘭花》等等,他們書寫的是生命深處柔軟而寶貴的感受和體驗,雖然沒有突出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但同樣是對人類精神之域的探索與表達。只是在詩的藝術性方面還需要努力。
以上對8個民族各卷中收入的詩歌作品進行研究的簡要的梳理和歸納,因為歷史和文化的原因,每個民族在詩歌上所取得的成就各不相同,但是都在努力學習和寫作,爭取在當代詩歌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詩人應該站在時代前沿,用自己的詩歌來表現生活,讓人們通過詩歌看到一個民族的精神。從這個角度上看,他們的作品是成功的。他們的作品體現了民族文學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當然,如果要通向更高的高度,每個民族的詩人都還需要繼續努力。
二、詩歌的焦慮與堅守
統觀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詩人的創作,有的已經在民族文化傳統的學習與繼承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探索,寫出了優秀的作品。有的還在傳統的門前徘徊游走,尋找著入門之徑。但隨著寫作的深入,他們總歸會被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吸引,走上回歸之路,為傳承、堅守民族文化而努力。
所謂堅守,意味著對詩歌懷有不可催折的信念,以執著的精神為之努力。對一個民族來說,詩歌是精神的號角,是傳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徑。但是在一個經受著商品經濟浪潮沖擊的時代,詩歌也面臨種種困境,需要詩人以堅韌的精神去守望自己的精神信念。
一些敏感的詩人的作品中已經體現出明顯的文化焦慮感,所以他們的詩歌中有強烈的精神訴求感。獨龍族詩人巴偉東的《獨龍招魂曲》就是一例。他在詩的結尾吁嘆著:“魂魄啊,魂魄,我的魂魄/歸來……”他所呼喚的不僅僅是詩人個體的魂魄,更是民族文化的魂魄。普米族青年詩人戈戎比措也在詩中發出質疑:
“群山以怎樣的方式佇立?
靈魂的方向
是否刻滿荊棘?”
人口較少民族的詩人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們都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意識,肩上承擔著民族詩歌發展的重任。這種焦慮感體現在對一些承載著古老意蘊的事物上面,比如“我的獵槍已蒙上厚厚的塵土/擱置在寂寞和清冷中”(和建全《我的獵槍》)。進入城市的詩人,對故鄉總會懷有一種失落和惆悵的心態:“而我/是故鄉的一根草/在城市的霓虹燈下/無根無跡地飄著。”(勒普·創藏坤努(《夢里故鄉》))。類似的情緒在一些詩人的作品中時隱時現,暴露了他們內心深處的焦慮與迷惘。詩歌是可以招魂的,既為詩人自己,也為民族文化的復蘇。
責任感越強的詩人,文化焦慮感會越沉重。如果能在此基礎上堅持思考與追問,必定會對他的詩歌寫作形成一種動力,使詩的境界和內涵得到提升。如一位評論家所言:“在轉型社會里,詩人就是在了解歷史和現實的背景中,為社會的進步與成長,去探尋真相,讓大眾明曉自己的處境,以及對未來的憧憬,這或許才是有希望的寫作。”[6]直面現實的寫作對民族詩人來說,也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用詩歌的方式為自己民族的發展進步吹響號角,這是詩人不可推辭的責任和義務,也是詩人的光榮。
詩歌的堅守除了需要詩人有自覺的責任意識外,還需要詩人建立起自覺的“精品意識”,在詩歌的寫作上多出力作。因為只有真正的藝術作品才能打動讀者,把思想和藝術的美感傳遞給更多的人。
【注釋】
[1][5] “詩,時代涌動的悠遠回聲——對話詩人吉狄馬加”,2013年09月11日 人民日報。
[2][3][4] 保護阿昌族共同的精神家園——當代阿昌族作家訪談。來源:中國作家網2013年08月07日。
[6] 劉波.“直面現實、歷史與傳統的新格局”,2014中國詩論精選。
本文為2015年度中國作協少數民族作家重點扶持項目成果之一
(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云南民族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