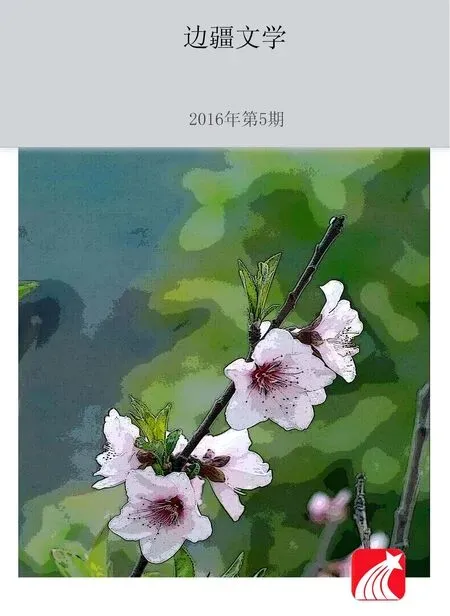時空中的穿梭者
——和曉梅小說敘事藝術探析
◎馬 丹
時空中的穿梭者
——和曉梅小說敘事藝術探析
◎馬丹
作為一個有著女性意識和民族意識的作家,和曉梅擅長以民族的視角思考女性的命運,她的敘述安靜、綿密、低沉,寫盡了女性一生命運的沉沉浮浮。和曉梅有意無意的和現實世界保持著疏離感,她所屬意的是那個已在塵埃中逝去的世界,她領著讀者掀起過往的一角,像個好奇的孩子,打量著已被塵封的過去,以獨特的敘述方式拂去歷史的塵埃,復活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重述那些過往生命中的故事。
和曉梅有著嫻熟的敘事能力,很少采用線性敘事的方式,而是在交錯的時空中完成故事的敘述,她像個技術精湛的“織布女”,用“敘述”這把梭子重新組合時空,在多時空維度中的展開故事,卻無雜亂之感,獨特的敘述風貌賦予了作品更為豐富的內涵。
一
從處女作《深深的古井巷》開始,和曉梅就不安于單一的敘事方式,她借鑒了電影中常用的敘事手法,以時空的轉換引發敘事,從“一口古井”牽出塵封的舊事,以“走出古城”結束這段舊事的敘述,這是一場關于愛情的糾葛,“二伯父”、“二伯媽”、“三伯父”都是這場愛情漩渦中的主角,但和曉梅并未以他們三人為敘事視角,而是以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我的父親”為敘事者,“旁觀者”的身份能夠抑制強烈的感情色彩,從容不迫地進行敘事,節制的敘事給作品留下了回味的空間,盡管這篇小試牛刀之作敘事還稍顯雜亂,敘事的角度和語言有些錯亂之感,但已經能夠看得出和曉梅對敘事藝術探索的端倪。
和曉梅的小說大多都以旁觀者的角度來進行敘事,將敘事時間和事件時間分離,突破線性敘事的局限,通過敘述將事件拆解為一個個片段,不以事件的發展為敘事動力,而以敘事者的所見、回憶、感慨等推動故事的敘述,《女人是“蜜”》套疊了兩個故事,洗衣女人的故事和“阿菊旦”的故事,兩個故事的敘述都是以旁觀者的角度來進行,洗衣女人的故事主要是通過“我”的所見和猜測,阿菊旦的故事是通過外婆來講述,兩個故事相互穿插。套疊的敘事方式在和曉梅小說中很常見,她通過這種方式將不同的時間共時的呈現出來,《情人跳》雖然以 “第一天”、“第二天”順序的方式進行敘述,但在敘述時又打破了順序的時間觀念,將“吉”的故事和“五姨”的故事共時的呈現出來,《蠱》 中“水月白”的故事中穿插了她母親的故事,而母親的故事又是“水月白”故事的起因,《水之城》中母親的故事和農兒嫫的故事交替進行,《未完成的成丁禮》在北京與瀘沽湖,現實與回憶之間交錯敘事,澤措的故事、母親的故事、父親的故事共時呈現,相互映照。
和曉梅偏愛用第一人稱“我”敘事,但“我”一般不參與故事的發展,主要是一個講述和審視的角度,在“我”的心理時間中展開敘事,“心理時間是人的心理感覺的時間,它可隨敘事者的主觀意志而變化不定,在心理時間里,自然時間可以被延長、緊縮、省略”[1],以心理時間敘事一方面可以打破物理時間對敘事的限制,另一方面主觀化的敘事能更精準地傳達人物的心緒和感情,與傳統的敘事相比較,心理時間敘事不再專注于事件發生的過程,而著意人物的感受與思緒,敘事呈現出片段化特征。《水之城》以“我”的視角講述母親與恒之的故事,但沒有完整的敘述事件的來龍去脈,而是通過一些場景的描寫來進行敘事,在描寫這些場景時,沒有肆意、粗暴的進入到母親的內心,而是以“我”的所見所感間接的表現,在描寫母親看見恒之,喊叫追趕的場景時,以“我”對聲音細膩的感受將母親的焦急、匆忙、慌亂表現出來,“母親的聲音聽起來是那樣尖利,像一塊鋒利的刀片。充滿了那種劃破肉體的血腥氣息”[2]“我的耳朵里只聽到母親高跟鞋踏在青石板路上發出的清脆而凌亂的聲音,就像一只躲避獵人追捕的馬鹿一樣”。
在和曉梅看來,時間的流逝不是“奔流到海不復回”,而是以回環往復的姿態前行,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間節點并非涇渭分明,而是互相包裹,難解難分,人物的命運具有重復和相互映照的特點,《情人跳》中“吉”與“木”的私奔與情死是“五姨”的過去,而作為同樣未能與愛人情死的人,“五姨”又在某些方面映照了“木”未來的命運,《水之城》以母親的改嫁為結局,而之前有意敘述的農兒嫫改嫁的事件則可視為在某些方面是對母親命運的預敘。疊加的時間觀念在敘事中也時有顯現,《未完成的成丁禮》在回憶與現實中交替進行,其間又插入未來的思緒,“想起這次逃離,多年以后的澤措依然時時感覺羞愧”[3]《水之城》以“兒童視角”進行敘事,“我”是在場的敘事者,但這一視角并非凝固不變,“老實說,我很同情母親,許多年了,只要一想起那一次她拉著我的手瘋狂地去追一個叫什么“恒之”的男人,而那男人卻像躲魔鬼一樣躲避她,我就依稀能夠格外深刻地感受到她當時那份因屈辱而帶來的絕望心情,我的心依舊忍不住一陣悸痛”,在這一片段中,“我”的身份由“在場者”切換為“回憶者”,敘述的時態由現在時變為過去時,正在發生的事被拉回到逝去的時空中。
二
小說是時間的藝術,情節總是在一定的時間中發展,傳統敘事學將時間作為敘事的重要維度加以研究,構建了較為系統的敘事時間理論,而對空間的關注則不夠深入,空間敘事學的出現開始引發對敘事空間的關注,在空間敘事看來,“空間不僅具有人們能看見能觸摸的物理實體性質,更重要的,它還生產出人們看不見摸不著但又彌漫于空間各個角落的社會關系、權力運作乃至人的思想觀念等形而上的意識形態內容”[4]。
和曉梅是一位“造境”高手,她不吝筆墨對環境進行細描,不是為了細致客觀的展現環境,而是為故事造設空間,空間在她的作品中充滿了隱喻意味,是敘事的基調和氛圍,細致梳理她小說的敘事空間,出現頻率較高的有雪山、古城、深巷等,雪山在納西文化中有著獨特的內涵,是通向玉龍第三國的入口,在玉龍第三國,有情人能得到愛神的庇護。在和曉梅小說中雪山不僅是物理空間,還隱含著文化意味,《情人跳》中當惱羞成怒的魯若老爺和魯若太太追趕“吉”到雪山時,也被雪山所隱藏的“情死”文化所感召,內心突然釋然了,“魯若老爺那些零亂打結的斑白頭發在魯若太太的手下一縷一縷地變溫順”[5],“雪山”以文化空間和心理空間的形式參與推動敘事。古城、深巷是《水之城》和《深深古井巷》主要的敘事空間,作為物理空間,古城、深巷是故事發生的環境,作為文化空間,深巷、古城浸潤著歷史感,有著傳統文化的象征意味,作為心理空間,褪色的古城,逼仄的深巷容易讓人產生神秘、悠遠和壓抑的心理感受。在和曉梅小說中,空間并非只是故事所展開的環境,還以其獨特的文化意蘊、心理意義等參與敘事。
空間敘事弱化時間了對敘事的掌控能力,通過對情節的非線性安排,空間的并置,轉換和敘事片段的組合來推動敘事,在進行空間的轉換時,和曉梅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夢境、回憶、儀式、幻覺等,夢境以超越時空的方式,將現實以變形的方式表現,《水之城》中“我”屢屢夢到農兒嫫的場景就是對她命運的交代,回憶的敘事方式能打破線性的時間觀念,在不同的時空中自由的穿梭,《女人是“蜜”》以回憶的方式在呈現不同的時空,將“洗衣女人”的故事、“阿菊旦”的故事共時呈現出來,形成比照。儀式在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從俗性空間抵達神性空間的通道,儀式不是外化的表演,而是內化于心的,《情人跳》“吉”與“木”內化的“情死”儀式,讓他們能夠感受到來自“玉龍第三國”的召喚和庇護。《未完成的成丁禮》中澤措在北京地鐵站走下臺階的瞬間產生錯覺,仿佛向下的臺階通向瀘沽湖邊的寧靜歲月,臺階扮演了過渡的道具角色,空間由北京切換為瀘沽湖邊,伴隨著空間切換的是時間的轉換,由“當下”轉為“過去”。
時間與空間是敘事的兩個重要維度,“時間敘事”與“空間敘事”并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方法,而是以互相交融的形態而存在,“時間敘事”是在一定的空間中展開的,而“空間敘事”則暗含著時間觀念。在和曉梅小說中,“時間敘事”與“空間敘事”并行,呈現出獨特的敘事風貌。
三
就作品的立意而言,和曉梅的小說并無太多獨到之處,但獨特的時空觀念、非線性的敘事手法為這些作品添彩不少。敘事手法不僅僅是技巧,還關乎作品的意義呈現,獨特的敘事手法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讀者的“陌生化”期待視野,而是力圖以手法的變更實現視野及意義的轉變。在技巧的使用方面,和曉梅已經很熟稔,但就意義的深度開掘,她還有一段路要走,《賓瑪拉焚燒的心》是她對自己創作的一次突破,敘事的手法與遲子建的《額爾古濟河右岸》十分相似,將兩部小說進行比照,便可發現和曉梅在文化內涵的深度思考和呈現方面的欠缺。
目前,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關注,有重文化性輕文學性的傾向,從民族文化的角度切入較多,主要闡釋作品所呈現的文化特質,這本是無可厚非的,文化的獨特性是少數民族文學的亮點,但文化與文學的轉變機制是非常復雜的,過于強調文化性,少數民族文學將淪為文化研究的注腳,而對表現手法,敘事方法等文學手法加以關注,能瞥到文化對文學的滲透不是流于表面的磅礴大雨,而是潤物細雨,看似無影,卻無處不在。
【注釋】
[1]姚皓華:強調心理時間的敘事時間模式—從敘事時間范疇看郁達夫的小說,《學術交流》[J] ,2005,(09),
[2]和曉梅:水之城,《中國作家》[J],2003,(02):31-50
[3]和曉梅:未完成的成丁禮,《邊疆文學》,2009,(01):90-97.
[4]余新明:小說敘事研究的新視野—空間敘事,《沈陽大學學報》,2008,(02):79-82.
[5]和曉梅:情人跳,《邊疆文學》,2006,(08 ): 4-26.
(作者系昭通學院教師,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
責任編輯: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