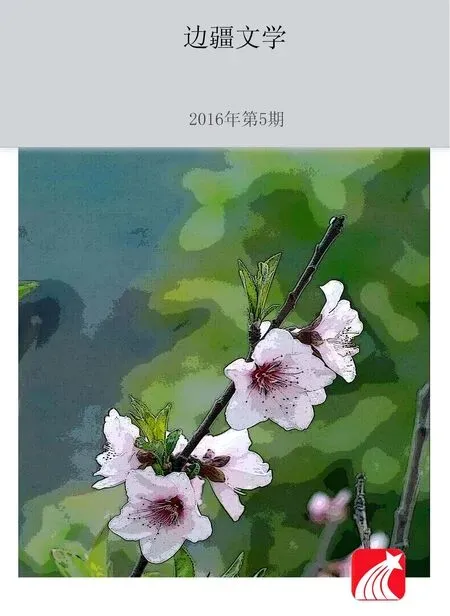民族、命運以及女性
——和曉梅文學作品研討會
◎宋家宏等
民族、命運以及女性
——和曉梅文學作品研討會
◎宋家宏等
主持人語:和曉梅是云南近年來創作豐厚的一位小說家,很有特色,評論對她的關注不夠。“云大評刊”論壇組織了一期討論,年輕的批評寫作者們對她的小說直言不諱地說出了他們的看法,這對推動讀者了解和曉梅的創作,是有意義的。本期“新銳批評”轉發了“云大評刊”的討論,并配以幾篇短論,相對深入地解讀了和曉梅的小說。稍有不足的是對和曉梅的長篇小說涉及不夠,然而,那是和曉梅很重要的作品。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今天,要讀者認真地讀一部長篇小說有多難!作家寫長篇小說實在是一件需要謹慎對待的事。(宋家宏)
主持人:宋家宏(云南大學教授、云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討論者:云南高校教師及研究生十余人
記錄整理:唐詩奇
時 間:2016年6月13日
地 點:云南大學文津樓云南文學研究所216室
主持人宋家宏:各位朋友,大家好!“云大評刊”本期(第三十一期)討論的是云南作家和曉梅的小說。她是云南作家中這幾年來小說創作成就很突出的一位,而且她的創作在不長的時間里發生了很明顯的變化,這一點大家讀她的作品會有感受,我這里不多說了。她居住在麗江,離中心城市有點距離,但她的小說與同類型的作家很不相同,我也不想多做評述,還是請各位自己判斷。這一期我們準備更多地采用空中連線的方式進行,整理的時候仍然保持“云大評刊”的一貫風格。請傳稿來的各位同仁仍以片斷的方式進行。同時,完整的附稿也是非常需要的。
一、印象:和曉梅作品的總體觀感
主持人宋家宏:是不是先說說大家對和曉梅小說的總體感受?
陳方(云大2013級研究生):和曉梅作為一名納西族女作家,其創作的立足點無疑多來自于民族和女性,民族和家族是其寫作的重點,以獨特民族的視角對女性命運和生命的表達。但和曉梅的眼光并沒有局限于少數民族題材,她的思考也上升到了對命運和生命過程的關照。
郭鵬群(昆明學院副教授):和曉梅的小說有一種神奇的魅力,可以抵達人的心靈深處。……她的小說,是以現代人的眼光,審視古老的納西族文化,并在對人性的挖掘中直擊人生的無力感。
唐詩奇(云大2016級研究生):從開始獵奇式的窺探,到沉醉在這個浪漫的美夢中,再到忽然從夢中驚醒,透出生命的蒼涼。和曉梅擁有這樣的能力,讓人一步步淪陷在喃喃的納西古語之中。
徐睿(山西太原學院教師):就閱讀感受而言,和曉梅的小說無疑是非常好看的。這種“好看”體現在由措辭精美、敘事完整和引人入勝的情節所構成的可讀性,體現在她用斑斕的色彩詞匯為讀者繪制的文字畫卷呈現出的視覺美,也體現在她通過對多種意象的靈活運用、敘事視角的嫻熟轉換和貫穿作品始終的巫性靈氣所展現出的藝術性……
軼名:在讀和曉梅的小說時,我竟會眩暈,就像是跌落到另一個時空的感覺。和曉梅小說有意拉開與現實的距離,傳奇色彩較濃,納西文化增添了作品的神秘色彩,放蠱、殉情、念咒、祭祀等這些遠離現代文明的文化符號,增添了作品的傳奇性與神秘性,但和曉梅無意以獵奇的心態去描繪和展現,讓她動容的是這些儀式的背后的心,她所關注的是隱藏在儀式背后的人物命運。
孔蓮蓮(文學博士、曲靖師院教師):和曉梅的作品以她漫衍而直感的語言,神秘主義的文化呈現,以及對女性命運的特殊熱情,再次讓我讀到了“巫”的氣息。確實,以上特征深受 “文壇三巫”(林白,陳染,海男)的女性主義作家的影響。但是,除了以上的特征之外,作為一位納西族的后裔,她以血濃于水的深情表達著對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和種族的依戀、崇拜、審視和批判。
張旭(2015級研究生):她的文字背后蟄伏著她的生命意識,這種生命意識是她作為一個納西族對自己文化歷史的一種自覺地反思,這種生命意識包含了她對本民族女性的理解和同情,她借此作為出發點,建立自己寫作的王國。
朱彩梅(現代文學博士、云南師大教師):其作品致力于當地少數民族題材的書寫,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濃郁的民族風情。在寫作中,她有意識地去嘗試、探索民族性與現代性、本土性與世界性的融合,但目前,漢語表達的艱難和超越自我局限審視民族文化的困難,如兩塊巨石,雙雙橫亙在她寫作的道路上。
陳林(蘇州大學文學博士):從愛神康美久蜜金到英雄連長,再到當下的“成功人士”,和曉梅的小說超越性別、民族、地域,她的創作把獨特的個人經驗融合到歷史意識中,寫出了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人的生存境況與文化心理的變化。只有把她的小說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曉梅把握世界、書寫世界的獨特方式,才能看到她為我們勾畫出的不同文化形態下鮮活的心靈的歷史,這些真實的心靈世界構成了歷史真實不可或缺的側影。正是從這個角度,我認為和曉梅是一位頗有抱負的寫作者。
二、女性視角下的生命觀照
主持人宋家宏:和曉梅是一位女作家,我們討論一位女作家時往往會從她的性別意識入手 ,這其實并不公平,但女作家的性別意識又是與生俱來的,它不自覺地呈現在作品中,讀者很容易就看到了這種女性意識,和曉梅的作品是不是這樣的?
徐睿(山西太原學院教師):縱觀和曉梅的作品,我們不難從中讀出其對女性命運和精神世界的持續關注。身為女性的和曉梅基于自身性別體驗的女性言說,細膩的情感表達和納西族人、東巴后人、知識分子等的多重身份,均使她的作品增添了更具感染力和說服力的別樣魅力。她既是民族歷史的傳承者又是親歷者,既是作品中受難的女性本身又能站在知識分子的高度冷靜思索女性的過去與未來、存在和價值。
陳思穎(云大2014級研究生):和曉梅在多篇小說中展現了對女性的關注,尤其是納西族女性的書寫展示了作為一個女性作家所具有的敏銳和細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作者和曉梅就是一個女性主義的話語者,她只是運用獨特的女性生命體驗詩意的表現納西族美麗女性的苦難、愛恨以及美好的人性。
陳琴(云大2014級研究生):在她的筆下,納西女性特別的美妙常常讓人過目難忘,與美相呼應的是納西女人感情的純真高潔,她們為了愛情常常是義無反顧,無視世俗的任何障礙,可以拋棄財產、名譽、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和曉梅在一個個委婉動人的故事里,有著人們期盼而現實生活中難以尋覓的肝膽熱血俠骨柔腸,女性的肉體與心靈之美被推到了極致。
唐詩奇(云大2016級研究生):正如陳琴所說的,這樣的母題拋開納西族“玉龍第三國”的美麗傳說,很容易找到相類似的故事。不同的是,和曉梅對女性的關注不僅僅限于對愛情和自由的追求,更在于對自我命運的把握和反思。同時,和曉梅尖銳地指出女性在情感上的弊病和悲哀,過于盲目的愛情讓她們陷入了極端的痛苦之中,一定程度上注定了她們的悲劇命運。
劉敏(云大2015級研究生):“大部分女人,不過是活在一張自結的網中,活得平淡,寂寞而痛苦。”這也許是大多數納西女人的命運寫照。……然而和曉梅并沒有把女性的悲劇一味偏執的歸結到男性,而是引導我們走向了對民族文化的反思,對生命存在價值的追問。
徐睿(太原學院教師):在和曉梅所構建的女性世界里,很少出現充滿陽剛之氣、果敢決絕的男子漢形象,就連外貌都大多是矮小、蒼白、孱弱的。男女之間的情感關系主要表現為女性的犧牲和男性的索取與不作為,從而使得犧牲和付出,成為和曉梅筆下女人可憐、可惜、可嘆的愛情模樣。……與傳統愛情故事中,落難的女性總是由生活經驗豐富、有勇有謀的男性拯救不同,和曉梅筆下男性形象的弱化和男權神話的消解注定女性從困境的解脫主要依靠以下兩種方式來實現,即:女性群體的互助和女性的自我救贖。
軼名:是的,與鮮活的女性形象相比較,她對男性形象的塑造則太漫不經心了,甚至有些敷衍了事,類型化、模式化,基本處于失言、甚至失真狀態。《女人是“蜜”》是一曲關于女性命運的哀婉之歌,對女性,作者傾注了一腔熱血,對男性,則橫眉冷對,但過度的將兩性關系對立起來,是否會導致女性情感的虛空感?無所依托的虛空。
徐睿(太原學院教師):源于有意識地想要在男權文化的天空下做一個翻轉的想法,使得她作品中這種顯而易見的女性寫作和女性關照,不光是一種“我、我的身體、我的自我”式本能表達,更是一種想要以一個“民族代言人”的角色,為她們發聲言說的自覺性女性寫作。
三、納西文化的代言人,抑或反思者?
主持人宋家宏:和曉梅還是一個納西族作家,云南有的少數民族作家有的在刻意強調,有的又在有意識地回避自己的民族身份,這有很復雜的原因,和曉梅與他們不同,她不回避,但也不刻意地強調。說和曉梅是一位納西族女作家,不僅僅是說明她的身份,其實更重要的是她的作品里有很明顯的民族意識,大家在讀她的作品時應該明顯地感覺到這一點。
張旭(云大2015級研究生):作為納西族的作家,和曉梅的小說里無法忽略的是納西東巴文化的影子。作家的民族意識,對于納西文化的自覺認同,通過地域、語言、民族文化、風俗習慣作為媒介完成。……和曉梅對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一方面是贊賞,以至于在小說中反復的描繪納西族的風俗文化,語言習慣;另一方面,這些文化認同心理背后又隱含著作家對本民族價值以及出路的思考。
朱彩梅(現代文學博士、云南師范大學教師):
其民族思維、信仰,在小說中常化為“我說是這樣就是這樣”的一錘定音、不容質疑的肯定語調,很像《圣經》的“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如對殉情者的描寫,與彝族《阿詩瑪》、白族《蝴蝶泉的傳說》、傣族《召樹屯》及漢文化中流傳的《梁祝》相比,其殉情主題作品淡化了絕望、哀傷、凄美的意味,在《情人跳》中,她的敘述語調堅定不移,很好地傳達出相愛而不能自由結合的納西族戀人對待殉情那種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誠、執著,在他們的意識深處,殉情是超越生命、到達另一片天地延續幸福生活的美好寄托與理想。此種作家思維、信仰與作品語調、內容的呼應、和諧,頗為珍貴。
陳思穎(云大2014級研究生):她善于挖掘本民族生活題材的特點,將地方色彩和濃郁的民族特色串聯成神奇的傳奇故事。沒有將寫作的目的指向對舊時的封建落后、迷信思想的譴責,而是將自己獨有的民族文化注滿新鮮血液讓人們重新感受納西族文化的生命氣息。和曉梅所寫的納西族文化除了增加小說的傳奇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對蒙昧與文明共存的納西文化的審視。
馬丹(昭通學院教師):作為一個有著女性意識和民族意識的作家,和曉梅擅長以民族的視角思考女性的命運,她的敘述安靜、綿密、低沉,寫盡了女性一生命運的沉沉浮浮。和曉梅有意無意的和現實世界保持著疏離感,她所注意的是那個已在塵埃中逝去的世界,她領著讀者掀起過往的一角,像個好奇的孩子,打量著已被塵封的過去,以獨特的敘述方式拂去歷史的塵埃,復活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重述那些過往生命中的故事。
陳林(蘇州大學文學博士):“玉龍第三國”所代表的超歷史范疇暗示了存在不可改變的事物,它與我們的有限性和脆弱性達成象征性的妥協。盡管“情死”文化包含著反抗現存秩序的因素,但更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退縮,它回避、消解了社會危機。
陳琴(云大2014級研究生):對情死的態度值得斟酌。情死并不是因為對生命態度的隨意性,而是對一種極端文化的反抗。但在文中,情死成了納西族的一種傳統、一種習俗、一種規矩,凡是不能在一起的就得死,這種帶有虛幻性、自欺性、附帶盲目的奴性的行為,是必須指出來的。
王瑞(云大2014級研究生):幾乎每一位民族作家都會婉曲地表達對民族傳統、文化記憶在現代文明發展浪潮中流散與消失的憂慮與警惕。阿來、霍達、曉雪等作家們都在作品中流露出主流文化沖擊下本土文化邊緣化的危機感。和曉梅也不例外,對文化全面商業化的疑慮與憂思、對跨國文化產業對本土現實包裝及生產的反感、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的失落與錯置的創傷體驗等諸多情緒的認知與記錄,使和曉梅的作品逐漸顯現出了一種挽歌情調。全球化的時代,人們無可避免地面臨著“史實性的消退,以及我們以某種積極的方式來體驗歷史的可能性的消退”。和曉梅以她優美婉曲的文字試圖還原逐漸消逝的記憶,在不斷城市化、全球化的社會和文化空間中尋找文化之根。
馬丹(昭通學院教師):目前,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關注,有重文化性輕文學性的傾向,從民族文化的角度切入較多,主要闡釋作品所呈現的文化特質,這本是無可厚非的,文化的獨特性是少數民族文學的亮點,但文化與文學的轉變機制是非常復雜的,過于強調文化性,少數民族文學將淪為文化研究的注腳,而對表現手法,敘事方法等文學手法加以關注,能瞥到文化對文學的滲透不是流于表面的磅礴大雨,而是潤物細雨,看似無影,卻無處不在。
郭鵬群(昆明學院副教授):建議作者多閱讀少數民族歷史,特別是土司制度、漢族統治、國共政治、民族關系等,盡快的擴大自己的民族視野與社會容量。
四、對具體作品的討論
主持人宋家宏:我們還是從具體作品的分析評價,她的哪篇作品給你印象最深?也可以說說那篇作品的問題所在。
陳林(蘇州大學文學博士):和曉梅二十出頭發表處女作《深深古井巷》頗為令人驚訝,這讓人聯想到現當代文學史上那些才華橫溢的年青作家。《深深古井巷》是和曉梅最出色的作品之一,這部小說在她的整個創作中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它已觸及和曉梅小說藝術的“內核”及諸多相關問題,之后的作品多為它的延伸和擴展。從現當代文學史的角度看,這部小說可置于張愛玲的《金鎖記》、陸文夫的《小巷深處》、蘇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系列中加以考察。放到這些名篇佳作之中,《深深古井巷》依然有它的奪目之處。
孔蓮蓮(文學博士、曲靖師院教師):說到這個作品,讓我想起了曹禺的具有強烈的現代啟蒙精神話劇《雷雨》:一個雷雨一樣性格的女人以及由此產生的封建家庭悲劇。和曉梅的這個作品則是通過一個漢族女人陰鷙的性格完成對納西家族傳統文化的破壞。小說每個場景的設置都比較精心細膩,隨著敘述節奏徐徐展開,作者把我們帶到獨特的納西族家族文化中來,這里有專制的家長制,也有粗暴蠻橫的男權文化,還有著微妙糾結的民族矛盾。敘述者經常跳出故事的敘述,以一種身處世外的理性眼光,既寫出了對本民族的愛和同情,也寫出了對本民族的批判和沉痛。
王瑞(云大2014級研究生):小說《有牌出錯》是和曉梅作品中我最喜歡的一部,作品中塑造的女主人公“我的奶奶”也是我最喜愛的人物。“奶奶”聰明過人、有著颯爽英姿,講江湖義氣的男子風范,她的一生可謂傳奇,與《紅高粱》里“我奶奶”似有幾分相似。她所追求的并非只是自由自主的愛情,她真正在意的是要擁有能夠自我掌控的人生,一如她始終能夠掌控的賭局。在這篇小說里和曉梅回答了女性的生命價值——自主、自由。
孔蓮蓮(文學博士、曲靖師院教師):《蠱》這個作品在我看來,是最有想象力和異域風情的小說。剛一開始讀,以為是武俠小說,讀到最后,發現竟然是一個情感小說。作者比較聰明的將納西族人的歷史、神靈以及女人的“情死”等民族風情帶入故事。南方的古絲綢之路,麗江古城,馬幫;兩位外形、性格和功夫了得,卻不堪情蠱的大俠;一個體弱貌美,情淚點點,對愛情至死不渝的納西族姑娘:以上地域、時代和人物的設置,即使沒有多少思想性,也足以吸引讀者的眼球。
軼名:我倒覺得《蠱》過度的求奇求異了,以武俠的形式來講述這個故事實在不是一個明智之舉,過于奇異的故事反而會傷害到作品的內質,讀者會更關注表層的故事形式,難以沉靜下來體察人物的內心。
陳方(云大2013級研究生):《未完成的成丁禮》也非常有意思。作者通過將澤措與威廉這一個人不同時間的不同身份并置在一起,將繁華的北京和質樸的瀘沽湖畔并置,將現代性與民族性并置,產生出巨大的差別,都市的爭名逐利和古老樸實家族的愛的滋養,以表明澤措成長的代價。成長不僅僅只有溫情,還有撕裂。而緩解疼痛的方式,則是遺忘。
陳林(蘇州大學文學博士):革命的槍聲在《連長的耳朵》里響起。連長不得不飲下自己槍管里的最后一顆子彈,即便如此,他也擺脫不了遭受懷疑、難證清白的困境。最大的荒謬莫過于,連長不僅喪失了聽力,還喪失了與戰爭相關的某些重要記憶。沒有記憶意味著時間性的消失。歷史的真相無人知曉,戰后的世界竟是一片意義荒蕪的不毛之地。連長變成“完全沒有身份的人”,除了戰爭遺留下的疼痛,沒有什么能夠證明他的存在。這讓人想到余華《一九八六年》里不斷割裂自己身體的歷史教師。
馬丹(昭通學院教師):在技巧的使用方面,和曉梅已經很熟稔,但就意義的深度開掘,她還有一段路要走。《賓瑪拉焚燒的心》是她對自己創作的一次突破,敘事的手法與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十分相似,將兩部小說進行比照,便可發現和曉梅在文化內涵的深度思考和呈現方面的欠缺。
郭鵬群(昆明學院副教授):她的長篇小說《賓瑪拉焚燒的心》,已經顯示了較為深厚的藝術功底,頗有前途。但社會容量不夠,思想厚度不足,與《塵埃落定》等相比差距較大,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朱彩梅(現代文學博士、云南師范大學教師):我認為《賓瑪拉焚燒的心》有故事,有傳奇,而缺乏形象生動的人物,缺乏直面存在的追問。她淺表化的敘事展現了各民族的習俗、儀式,但描寫偏向于外部生存環境,沒有向內挖掘,很少深入到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倫理沖突,未能觸及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中人物內心深處的掙扎和精神疑難,是浮光掠影式的。……賓瑪拉家族、威廉都是作者生命的表達形式,但是,比之沈從文、張承志、阿來創作少數民族文學的深入、深刻,和曉梅小說缺乏深厚的歷史感,缺乏雄闊的生命氣象,缺乏從某個高度去發現、挖掘自己民族傳統中內在因素的意識、視野和思想能力。
趙靖宏(德宏師專教師):相比于諸如《賓瑪拉焚燒的心》這類小說,《青昌街紀事》顯然看不到“納西”的影子,沒有民族元素,更像是在探討人的成長和愛的關系,探索人存在的意義。
陳林(蘇州大學文學博士):小說《青昌街紀事》沒有給出明確的故事時間,歷史敘事比較隱晦、曖昧,不過從細節中依然可以判斷,小說以一條街道里的紛繁亂象,管窺的是“文革”至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歷史。在文學的歷史敘述中,這段時間一直是敘事的重要內容之一,“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知青文學”、“改革文學”的敘述焦點均在于此。放到這樣的文學史系列中,這部小說顯然有些另類。那些暗無天日的殺戮背后的意識形態色彩被淡化了,暴力仿佛只是一代又一代昌青街青年的力比多宣泄,小說僅僅在某些細節處提示我們與當時的紅衛兵武斗和“革命”聯系起來。我們知道,那些無休止的令人發指的殺戮實際上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年青人的內在沖動而忽略了悲劇的社會性。它與墻上頻繁更換的標語密切相關。這些標語改變著人們的命運,人物的活動也因此是歷史化的。從“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到“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的標語替換,提示了中國歷史從革命向后革命時代轉移。昌青街的青年在社會轉型中走出他們的故鄉,和曉梅的小說也穿越歷史回到當下,然而,我們對歷史的反思遠未完成,諸多問題依舊懸而未決。
孔蓮蓮(文學博士、曲靖師院教師):這個作品(《青昌街紀事》)帶著少有的理性批判精神,只是,她對昌青街的故事更多的是一種“現象”的描述,而缺少更深層的根源追索。
五、得與失:談談和曉梅的藝術創作
主持人宋家宏:大家多從思想意識這方面說了和曉梅的小說,能不能更多地從藝術這個角度說一說呢?包括她的小說藝術上的不足。
陳思穎(云大2014級研究生):和曉梅的小說注重敘事技巧的運用,作者擅長在小說中進行多條線索,多故事的穿插,不斷打斷讀者的閱讀,最后出其不意地將多個故事統一歸為一條線索,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這種敘事擴張了小說的空間,使小說跨越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框架束縛。
馬丹(昭通學院教師):和曉梅還偏愛用第一人稱“我”敘事,但“我”一般不參與故事的發展,主要是一個講述和審視的角度,在“我”的心理時間中展開敘事。……以心理時間敘事一方面可以打破物理時間對敘事的限制,另一方面主觀化的敘事能更精準的傳達人物的心緒和感情,與傳統的敘事相比較,心理時間敘事不再專注于事件發生的過程,而著意人物的感受與思緒,敘事呈現出片段化特征。
孔蓮蓮(文學博士、曲靖師院教師):和曉梅的小說講述故事的節奏控制很好,她對故事場景的設置也很有想象力和畫面感,細節的處理很見功力。同時,她的很多小說的敘述常常帶著“間離”效應,敘述者常常跳出故事本身,對故事進行評價和預設,顯示出知識分子寫作者的共性。這也使得她帶著納西迷離氣質的敘述里多了些現代氣息和理性精神,從而較好的平衡了民族性與現代性,神秘迷離與“去魅”寫實的關系。
軼名:獨特的敘事成就了和曉梅,但也限制了她的視野,過分倚重敘事技巧,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會導致其對作品主題深度開掘的忽視。
王瑞(云大2014級研究生):故事的類型化、氣氛的陰郁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張力,不夠收放自如。在對民族、地域的塑造上少了幾分歷史感和厚重感,過多的集中在表現個體上,少了整個群體的整合力。但是,這是一個有才情、有責任的作家,她試圖用文字還原逐漸消逝的文化記憶,指出時代的癥候,敢為失語的文化吶喊,可以說,和曉梅是有力量的!
蔡漾帆(云大2015級研究生):我發現和曉梅的小說喜歡采用冷色調。這種冷色調描寫,代表女性的陰性的冷靜、內斂,但是和曉梅筆下的女性在這種陰冷的沉默中爆發出生命之光,如同黑暗中沉靜的湖面突然沖出一個火熱的太陽。而且,和曉梅作品中時常出現神秘的動物意象,如貓和蛇,都帶有極其濃郁的神秘色彩,黑暗且憂郁。和曉梅選擇這類動物,表現出女人的神秘、憂郁、孤獨,讓人有一種心靈無處安放的感覺。
陳林(蘇州大學文學博士):說到貓這類的動物意象,我補充一點。在《深深古井巷》中,李兒翠和她的貓既合二為一,又一分為二,既是誘惑之源,又是引起恐慌與悲劇的病灶。如果說李兒翠是本能欲望的化身,那么那只不知年齡、超越時間、帶著鬼氣的成精之貓則是一種超我力量的象征。納西族三兄弟都受到李兒翠的誘惑,但那只貓無時無刻不在某個角落以鬼魅的超越之眼注視他們,以示警告、威脅,前者召喚著欲望,后者則豎起了警戒牌。小說的深層結構是一個俄狄浦斯式的弒父娶母的悲劇,它超出個體、民族而具有更為普遍的文化心理內涵。
馬丹(昭通學院教師):和曉梅還是一位“造境”高手,她不吝筆墨對環境進行細描,不是為了細致客觀的展現環境,而是為故事造設空間,空間在她的作品中充滿了隱喻意味,是敘事的基調和氛圍。
朱彩梅(現代文學博士、云南師范大學教師):
和曉梅的作品,尤以《賓瑪拉焚燒的心》為代表,在表達上普遍存在用語刻板、對話生硬的問題。作者想渲染故事之神奇,刺激讀者的獵奇心,但不免空洞、乏力,有些甚至顯得故弄玄虛。從節奏與謀篇看,為串入故事或講一些新奇事件而硬設一些人,硬造一些事,很多穿插與前后文并無內在關聯,有重復堆砌、畫蛇添足之嫌。而且全篇幾乎都是概述性描寫,看上去像是另一部鴻篇巨著的梗概綱要。整體而言,作品語言字句上處處抹不去作者的主觀痕跡,文字背后卻無精神支柱,缺乏一種來自作者心性自然流淌的氣韻、神采。
陳琴(云大2014級研究生):個人覺得她的語言的應用太過個人化,雖然有助于對鮮明的個人風格的建立,但換句話說,作家所擁有的使用語言的能力并不能只有一種。小說最重要的是語言,語言多樣化會極大豐富一個作家的作品,用太過個人化的語言反而會使這個人的作品成為類型化,只用一種語言來寫作品很可能會導致最后寫作的失敗。
朱彩梅(現代文學博士、云南師范大學教師):總體而言,和曉梅獨特的民族身份、生活環境、生命體驗,是一座別人求之不得的寫作資源寶庫,但其現在作品多是民族學、人類學的價值意義甚于文學。好在她的寫作是在路上的,如果能不斷提升表達、敘事的能力,敢于直面存在的真相,獲得超越民族、反觀自身的普世視角和思想力量,把荒誕、奇異的境遇中人物靈魂深處的隱秘描述出來,把民族生活中那種原始趣味、野性力量營造為氣息、氛圍傳達出來,她的作品將獲得真正震撼人心的力量。這是可以期待的!
主持人宋家宏:通過這期云大評刊的討論,大家對和曉梅的小說創作有了一個較為深入的了解,各位的評價并不一致,而且也都暢所欲言,這是好事,有不同意見,有爭議,才會推進理解,也才會對作家以后的創作產生一點啟示。和曉梅的創作之路還很漫長,她也是一位可以聽取不同看法的作家。
謝謝!
責任編輯: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