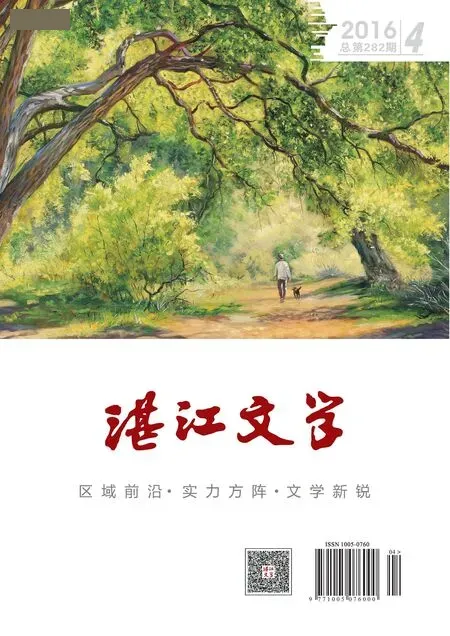先生的時(shí)代
※ 袁家驊
先生的時(shí)代
※ 袁家驊
“先生”這個(gè)稱呼由來已久,是對(duì)有學(xué)問者的尊稱。在源遠(yuǎn)流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曾經(jīng)誕生了無數(shù)的先生,比如有獨(dú)立思想主張的春秋先賢,唐宋盛世星光燦爛的博學(xué)鴻儒。時(shí)代也曾賦予它豐富多樣的含義,一個(gè)頗具豐富內(nèi)涵的稱謂;一種“一蓑煙雨任平生”的修為;一種即將遺失的悲涼情懷……但在我們的民族文化中,它另有深意,那就是對(duì)三尺講壇上教書匠的稱謂。
在世人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里,并非所有的教師都配稱“先生”。比如網(wǎng)絡(luò)上曝出的“校長性侵門”事件,不但令“斯文者”蒙羞,更令國人憤慨。震怒之余,人們?cè)诎@道德文化淪喪的同時(shí),卻愈加珍惜曾經(jīng)的名士風(fēng)流,不禁把視線再次投向了百年前的民國;再次打量那個(gè)縱橫交織的時(shí)代;再次“觸摸”那些學(xué)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先生們。
民國先生們皆有深厚的國學(xué)根基,不但有藏之名山、傳之后世的佳作,更對(duì)西方的民主科學(xué)感同身受。先生們既提供了學(xué)問坐標(biāo),也示范了風(fēng)度與風(fēng)骨。他們懷著教育救國的理想,苦心孤詣、艱難前行。“先生”二字的稱呼,既溫潤儒雅又端莊肅敬。
蔡元培時(shí)代的北大校園既有長辮子的國粹派辜鴻銘,也有提倡中西合璧的學(xué)衡派吳宓;既有革新思想的新文化領(lǐng)袖胡適,也有堅(jiān)持舊文學(xué)的黃侃在課堂上大罵倡導(dǎo)新文學(xué)的師弟錢玄同有辱師門。
“中國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的傳奇人生一半是學(xué)問。1917年,年僅25歲、只有中學(xué)學(xué)歷的的梁漱溟靠著發(fā)表在《東方雜志》上的一篇《究元決疑論》登上了北大的講壇。梁漱溟人生的另一半是在中國發(fā)起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yùn)動(dòng)。他在山東鄒平做鄉(xiāng)村建設(shè)實(shí)驗(yàn),發(fā)動(dòng)農(nóng)民成立自己的組織,爭取自身的利益,倡導(dǎo)“倫理本分,職業(yè)分途”,演繹了獨(dú)具風(fēng)格的一生。
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并稱清華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院“四大導(dǎo)師”之一的的陳寅恪先后在哈佛大學(xué)、柏林大學(xué)、巴黎大學(xué)等歐美名校留學(xué)16年,通曉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多國語言,對(duì)藏語、梵語、西夏文、蒙文、滿文、印度文均有研究。他以德式研究的縝密探究東方文化的博大沉雄,紙中夾著故國百萬雄兵。蔣介石歷來對(duì)一流的文人特別重視,想找人寫一本“太宗傳”,他知道陳寅恪是中國隋唐史的泰山北斗,派人拿重金上了陳家,但是陳寅恪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其魏晉風(fēng)骨,名滿天下。
一個(gè)時(shí)代的偉大,既在于這個(gè)時(shí)代有多少人能夠有所為,更在于這個(gè)時(shí)代有多少人敢于有所不為。1936年蔣介石約見竺可楨,希望他能出任浙大校長。竺可楨提出三個(gè)條件:“財(cái)政須源源接濟(jì);用人校長有全權(quán),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shí)間以半年為限”。這三條得到了蔣的允諾,他走馬上任。前二條國民政府基本兌現(xiàn),竺可楨一干就是十三年,到1949年離任時(shí),浙江大學(xué)已建成“東方的劍橋”。民國時(shí)大學(xué)的獨(dú)立,令人欣羨。
北大校長蔡元培和清華校長梅貽琦都力推“教授治校”制度,所有的大事交給教授會(huì)和評(píng)議會(huì)決定,校長從不干涉,從而最大限度保障了學(xué)術(shù)自由和學(xué)識(shí)之上。“所謂大學(xué)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梅貽琦心中的大學(xué),他說,“校長的任務(wù)就是給教授端茶水、搬搬椅子。”
在西洋人眼中最有影響力的東方學(xué)者辜鴻銘可謂名士風(fēng)流,以自己的“玩世不恭”游戲政壇。在京城一次宴會(huì)上,座上的政要名流們高談闊論著中國的時(shí)局,一位外國記者趁機(jī)問辜鴻銘,“中國政局如此混亂,有什么醫(yī)治的良方?”他大聲喊道,“有,把在座的政客和官僚,統(tǒng)統(tǒng)拉出去槍斃掉,中國政局就會(huì)安定下來。”頓時(shí),人們面面相覷。
1962年,擁有32個(gè)博士頭銜的胡適在臺(tái)北猝然辭世,蔣介石親自題寫挽聯(lián):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公祭胡適當(dāng)日,臺(tái)灣有30萬人參加送殯和路祭,胡適夫人江冬秀忍不住向長子胡祖望感嘆:“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這樣,不容易啊!”
有人曾這樣評(píng)價(jià)民國時(shí)代的先生:在波瀾壯闊的民國文化、烽火連天的抗戰(zhàn)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歸中,先生們宛如一座座頑強(qiáng)的燈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法國作家莫洛亞在《雨果傳》里說:“時(shí)間可以淹沒小丘和山岡,但是淹沒不了高峰”。當(dāng)我們把眼光投向那一片學(xué)術(shù)天地的時(shí)候,發(fā)現(xiàn)里面遠(yuǎn)不止幾座山峰,而是一片連綿起伏的山脈,群山巍峨,高聳云天。當(dāng)辜鴻銘對(duì)臺(tái)下狂傲的北大學(xué)生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鞭子是無形的”;當(dāng)陳寅恪所撰寫的“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刻上王國維紀(jì)念碑;當(dāng)劉文典沖蔣介石喊出“大學(xué)不是衙門”;當(dāng)胡適諄諄告誡學(xué)子“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的時(shí)候,他們鮮明的個(gè)性和風(fēng)骨躍然紙上:或深沉雅致、溫潤如玉;或勇猛精進(jìn)、慷慨悲歌。
歲月如煙,斗轉(zhuǎn)星移。當(dāng)距我們最近的季羨林、南懷瑾等先生們一個(gè)個(gè)遠(yuǎn)去的時(shí)候,我們不僅要問,在當(dāng)代思想界、文化界執(zhí)火炬不斷前行的有幾個(gè)?能夠數(shù)十年秉燭夜行,不為利祿而變節(jié)的有幾個(gè)?始終忠于真理、不愧屋漏的有幾個(gè)?成為一代導(dǎo)師、知行合一的先生有幾個(gè)?當(dāng)知識(shí)分子面對(duì)利益誘惑,弄虛作假、學(xué)術(shù)交易時(shí),我們不禁要問,追憶先生的風(fēng)采能否讓他們心生共鳴,擔(dān)當(dāng)起歷史責(zé)任?
當(dāng)我們凝視先生們遠(yuǎn)去的背影,在字里行間回憶他們的音容笑貌,的確能感受到那個(gè)時(shí)代的繁華與寂寥。我們有懷念,懷念逐漸老去的那個(gè)朝氣蓬勃的年代;我們有嘆息,嘆息現(xiàn)代繁華迷離中的暮氣沉沉;我們?cè)诤魡荆魡灸軌蛞I(lǐng)時(shí)代前行的先生橫空出世,在這個(gè)風(fēng)云變幻的時(shí)代一競風(fēng)流。
數(shù)十年來,尋找先生,尋找缺失的時(shí)代精神雖然不絕于耳,然應(yīng)者寥寥。在歷史的記憶與無奈現(xiàn)實(shí)的博弈中,仁人志士如果僅僅將懷念滯留在泛著書香的文字中,徜徉在無限的夢(mèng)幻中,卻不能知行合一,不能將群星閃耀的歲月刻入歷史的年輪中,那么嘆息與呼喚也是枉然。
袁家驊,資深媒體人,曾任《走近中國》《時(shí)代動(dòng)漫》雜志主編和甘肅衛(wèi)視《堅(jiān)持》欄目、深圳財(cái)經(jīng)生活頻道《商旅生活》欄目策劃總監(ji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