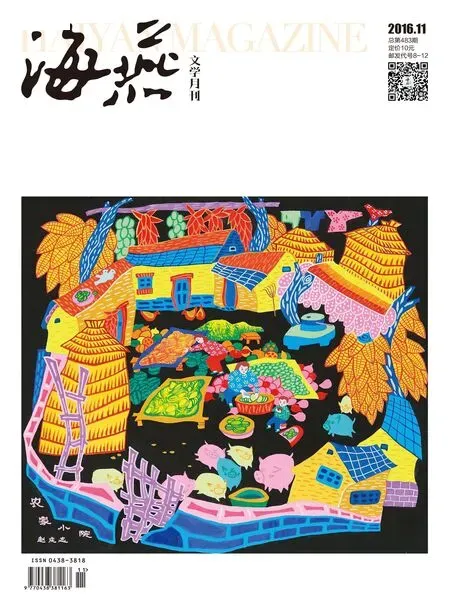蜀籟
□梁平
蜀籟
□梁平

梁平
梁平,當代詩人。著有詩集十部、詩歌評論集一部,長篇小說一部。現為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委員、四川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成都市文聯主席、《草堂》詩刊主編。
說文解字:蜀
從殷商一大堆甲骨文里,
找到了“蜀”。
東漢的許慎說它是蠶,
一個奇怪的造形,額頭上
橫放一條加長的眼眶。
蠶,從蟲,
彎曲的身子,
在甲骨文的書寫中,
與蛇、龍相似,
讓人想起出入山林的虎。
所以蜀不是雕蟲,
與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里,
那些人面虎鼻造像,
長長的眼睛突出眼眶之外的
縱目面具有關,
那是我家族的印記。
龍居古銀杏
銀杏樹千年的婉約,
因半闋宮詞殘留,
而凄凄慘慘、悲悲切切。
花蕊夫人親手植下的情愫,
隨蜀王旗的降落,
飄散如煙。
分析來自La Esperanza地區調查的數據。首先,參與超市供應鏈的概率被評估為社會經濟,農業,交易成本和組織變量的函數。這一分析結果表明,社會經濟和農業特點無統計顯著性差異。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調查人口的同質化,主要包括條件相似的小規模農戶。然而,交易成本與生產低質量風險,運輸和分級問題這些因素有非常重要的相關性,構成了農民在超市供應鏈中的參與約束。相反,供應鏈中相對較高的價格和對買家的信任,對農民加入又有積極的作用。有關交易成本的結果與本研究分析框架中的理論預期是一致的。
后宮的閑適不再,
王妃的高貴被囚車帶去北上,
銀杏幸存下來,
幸存了西蜀遠去的風姿。
歷經唐朝五代十國的沒落,
賢妃的花間明艷,
把兩代蜀君的威儀,
淹沒在辭藻里。
花蕊夫人,
后宮抖落的脂粉百世流芳。
站在風頭上的銀杏,
穿越了連綿不斷的戰火,
和那些花間詞一起,
仰仗水的滋潤。
一千年了,
依然郁郁蔥蔥。
龍居寺的晨鐘暮鼓,
敲打古銀杏的根須、枝蔓,
就像是舒筋活血。
陽光流淌,覆蓋了整個身體
龍居山有了龍脈。
一地芙蓉含笑,
半山梅蘭邀寵,
隱約都是花蕊的影子。
漢代畫像磚
漢代留在磚上的舞樂百戲,
具體成宴飲,
具體成琴笙歌舞。
每塊磚都有了醉意,
微醺之中,
搖擺舊時的世間百態。
三個官場上男人,
打坐杯盞之間,
頭上的官帽也有些醉了,
醉看三個妖艷的長袖,
舞弄靡靡之音。
原來這景象由來已久,
原來,如此。
另外三個像是真的抒情,
撫琴的撥動高山流水,
流淌婉轉;
吹笙的送來夏日清風,
徐徐漫向心扉。
隨風、隨水的蕩漾,
格外楚楚動人。
以這樣的方式定格在磚上,
那個久遠的年代。
或歌、或泣,
或由此而生的更多感受,
都是后人的權利。
風化的是圖像,
風化不了的是漢時的胎記。
雍齒侯
《史記》有云
背叛過劉邦的雍齒侯,
在劉邦稱帝以后,
加封為什邡大吏。
朝廷上下,
無不刮目相看。
劉邦內心里的雍齒,
只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從自己的咬牙切齒中辨認。
雍齒內心里的劉邦,
也不會因為一頂烏紗,
而改變。
以后的雍齒,
從正史上消失了,
比其他受封的文武百官,
多了些寂寥與清冷。
八百里疆土,因為冷寂,
風調雨順,草長鶯飛。
不是所有的干戈,
都能化為玉帛。
橫放在天地之間的一桿秤,
稱出劉邦用人的重量,
稱出雍齒為官的重量,
一次冊封,
一面班駁的銅鏡。
青銅·蟬形帶鉤
曾經在野地里瘋舞的蟬,
最后的飛翔凝固在戰國的青銅上,
成為武士腰間的裝飾。
束腰的帶加一只蟬做的扣,
隊伍便有了蟬的浩蕩,
所向披靡。
張翼、閉翼,
蟬鳴壓啞了進軍的鼓角,
翅膀撲打的風聲,如雷。
旗幟招展,將軍立馬橫刀,
即使面對槍林箭雨,
城池巍峨,固若金湯。
一只蟬與那枚十方王的印章,
沒有貴賤、沒有君臣之分。
大王腰間蟬翼的轟鳴,
也有光芒。
蟬在盆底的詠嘆,已經千古。
蟬形帶鉤的青銅,
比其他青銅更容易懷想,
更容易確定自己的身份。
如果帶鉤上見了血,那只蟬,
就不再飛翔,那一定是,
生命的最后一滴。
瓦子庵的張師古
徐家場瓦子庵晾曬的布衣,
是這里農民所有的行頭。
布衣沒走出八百里家園,
庇護清瘦的美髯,
撫弄出一卷《三農經》,
與鳥獸共其作息,
與草木共其春秋。
清的江山比其他朝代,
更需要土地滋養。
瓦子庵的張師古不知道,
甚至也不知道有一個賈思勰,
和自己一樣埋頭農事。
農人想的是土地上的莊稼,
一點心得罷了。
乾隆皇帝也穿過布衣,
那是微服私訪。
這里離朝廷太遠,
李白有嚇唬人的《蜀道難》,
衙門不驚動瓦子庵,
沒有俸祿,沒有花翎,
卻有了張師古的農學。
《齊民要術》與《三農經》,
難有仲伯之分。
兩人身份倒是天上地下,
唯有土地不理會這些。
種豆想的是得好豆,
種瓜想的是得好瓜,
瓦子庵,被我一首詩記住。
儒家學宮
雍城青石路通向北宋,
儒學在這里落地。
儒家學宮距錦城百里之外,
秀才趨之若鶩。
八方文墨,或點或染,
浸潤了名不見經傳的小城。
小城有了大學問,
即使曲阜的孔子有靈,
也難以相信這樣的景象。
水流向遠、向一種遼闊,
河岸上奔走的風,
浩蕩無痕,大音稀聲。
明末那場飄搖的風雨,
掀開屋頂上的瓦礫,
砸得地面生疼、生出扼腕長嘆。
學宮坍塌的狼藉里,
線裝《論語》一頁頁脫落,
呼呼作響,四處飄散。
天空到處是雨做的云,
一碰就會變成淚,傾盆。
青石路病臥在地上,
石頭與石頭之間長滿雜草,
土地開裂,不能發出聲音,
所有的路都指向不明。
康熙在折子里看見了,
皇恩浩蕩,裝訂失散的《論語》,
儒家學宮的每一片新瓦,
都是書香浸泡,
大街小巷都有了芬芳。
李冰陵
李冰最后的腳步,
在這里,一部巨大的樂章,
休止了。
這是和大禹一樣,
因水而生動的人,絕唱,
成為生命歸宿的抒情。
長袖洛水,是他最溫潤的女人,
與他相擁而眠。
那雙官靴上的泥土很厚,
盡管水路從來不留痕跡。
他在自己杰作的落筆處,
選擇放松,回味逝去的煙雨,
烏紗、朝服閑置在衙門了,
秦磚漢瓦搭建的紀念,
只有水潤的消息。
牌坊、石像、頌德壇,
影印在李公湖清澈的波光中,
都不及他在岷江上的攔腰一截。
游人如織,織一種緬懷,
織出濤聲作都江堰的背景。
塵封的記憶深埋在水,
所有的動靜,都脈脈含情。
高橋
一座橋,與高景關遙遙相望,
鎮守鎣華山寺門前飄飛的香雪,
彈指就是五百年。
建橋御使以一夫當關之勢,
扼住古道咽喉。萬歷年間的欽命,
加冕了高橋的貴族身份。
橫跨的鐵索封存了記憶,
高橋要塞,從來不近戰事,
倒是香火愈燒愈旺。
橋上過往的凡夫俗子,
拜天拜地,朝拜四十八堂,
晨昏只是一閃念。
白云山的白云比雪更白,
披掛在高橋,模糊了身份,
銀裝素裹,分外妖嬈。
那里的清新恍若隔世,
一個來回,就干凈了自己的身子。
翰林的文墨落地生根、開花,
從橋上下來,皆是大雅。
富興堂書莊
堆積在檀香木雕版凹處的墨香,
印刷過宋時的月光,沒名號的作坊,
在光緒年間成了富興堂。
書莊額頭上的金字招牌,
富一方水土,富馬褂長衫,
西蜀行走的腳步,有了新鮮的記載。
以至于很遠很遠的地方,
可以看見,印刷體的雍城,
煙火人間的生動日子。
蜀中盆地的市井傳說,
節氣演變、寺廟里的晨鐘暮鼓,
告別了人云亦云。
畢升復制春夏秋冬的神奇,
在富興堂檀木雕版上解密,
古城興衰與滄桑,落在白紙黑字上。
萬年臺子
原木穿逗結構搭建的樂樓,
無法考證緣起的年代,
其實沒有一萬年。
臺上的形形色色很近,
水袖舞弄歷朝的帝王將相,
看過一千遍。
人們伸長了脖子,
迎接一次虛擬的圣駕,
再帶回到夢里,慢慢咀嚼。
萬年臺子的泛濫,
像春天雨后冒出來的蘑菇,
沒有不生根的地方。
神廟、會館,甚至富家大院,
也要吊一個臺子在閣樓。
生喪嫁娶,奠基拆墻,
只要鑼鼓哐鐺一響,
生旦凈末丑魚貫而出,
粉墨登場。
川劇在萬年臺子上,
籠罩了歲月綿長的滄桑,
臺下都是一種仰望。
幕后的幫腔一嗓子喊過村外,
村頭的槐樹醒了,狗擠進人堆,
與主人一起回味以往。
皮燈影戲
羊皮、牛皮或者厚紙板,
削薄,削成穿越時光的透明。
燈光從背后打來,三五件道具,
一個人角色轉換,
十指翻動春夏秋冬,
在皮制的銀幕上剪影,
剪成一出川戲。
一壺老酒醉了黃昏,
皮燈前攢動男女老少,
從長衫沿襲到時尚的T恤,
都好這口,很過癮,
比起那些堂皇的影院,
多了些說不清道不明的
懷舊。
幕前與幕后,
跟著劇情瘋跑,
南征北戰,喜怒哀樂。
皮燈影戲的劇團,
導演和演員一個人,
劇務還是這個人。
上演千軍萬馬,
轟轟烈烈,氣吞萬里如虎。
也有煽情的兒女情長,
悲悲切切,千結難解。
收場鑼鼓一響,影子露出真相,
也是明星,前呼后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