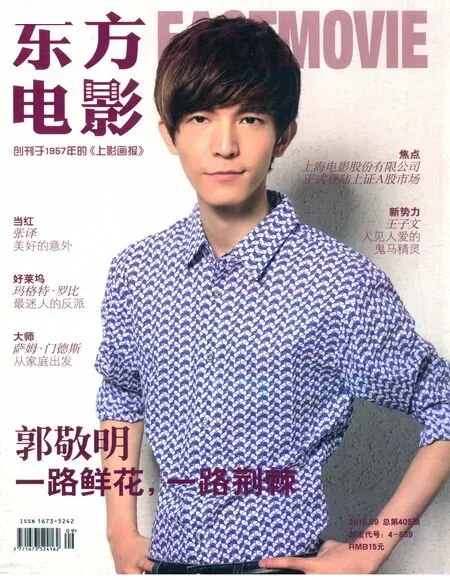惠英紅人生如戲
文/張雨虹
惠英紅人生如戲
文/張雨虹

究竟是人生如戲,還是戲如人生?對于惠英紅,她的人生遠比戲來得精彩,“我的一生是別人的兩生”。采訪過一些女星,但像她那樣有故事的實在是不多。采訪當日,有一個記者給惠英紅提了個建議,說希望能有機會看到她把自己的經歷搬上銀幕,會比憑空編出的故事更引人入勝。惠英紅笑著表示如果有機會,會定下心來寫寫自己的一生,她愿意分享自己的喜怒哀樂,那些不平衡,那些迷失,以及找回平衡,走出迷失。如今,她說自己即將進入人生的下一個十年,是時候開始另外一段征途了。
人生在世,珍惜最重要
芬姨在《幸運是我》里說了一句話,“沒有可惜,只有珍惜”。這也是坐在沙發上,面露遺憾的惠英紅想要告訴我們的。
臨近8月底,前一天剛結束《幸運是我》北京首映式的活動,就連夜乘飛機趕來上海,這樣馬不停蹄的日程還需要5天。在這些日子里,惠英紅可能將面對很多的記者,然后不斷講述她和她母親的故事。其實這對于她來說,實在不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然而她卻笑著說,“我就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珍惜親人的重要性。”每當談起母親,惠英紅的情緒就會跌宕,內疚的情感充斥了大部分的談話,“我媽今年91歲,她躺在床上就像一個胚胎,什么都不懂,縮成小小的……一見到她,我就想如果當初我能意識到她已經生病,也許她現在還會知道我叫大紅。”說罷,她的眼眶紅了。
在《幸運是我》中,惠英紅出演一位患有阿茲海默癥的獨居老人。老人性情喜怒無常,善良而孩子氣。惠英紅在戲里時而歇斯底里,時而倉皇無措,因為記不住亞視頻道而急得滿眼淚水,也會在被戳穿病情后絕望地嘶喊“我不想死了都沒人知道”。拍攝周期短短二十多天里,即使不斷經歷情緒大起大落,惠英紅卻說,演這樣的角色并不辛苦,因為這就是她幾十年來面對的生活—她的母親得的就是這種病,而片中的情境,許多都是她與母親的曾經與日常。“看到劇本的時候覺得太像我和我媽的生活了,點點滴滴都像。”女演員們都喜歡在戲中漂漂亮亮的,然而惠英紅為了演好戲中她與母親一起生活的真實場景,決定全程素顏出演。駝背,消瘦,腹部隆起,不瘦也不矮的惠英紅為這部戲徹底塑造了一個新的體型,“在做造型的時候,我和導演說我堅持要用她(母親)的體型,去顯示那種老,而不是靠化妝。這種老是從內里老出來的,而非外表。而且我媽因為看電視總是喜歡縮著,骨架變得畸形,連帶著肚子也突出,所以我演的時候塞了東西。”

對于兩次奪得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的惠英紅來說,這部戲并不能體現她真正的演技,因為她更像是在模仿,模仿她的母親。而這次的演出,在她的口中變成了一次自我救贖,一次對母親的道歉。懷著內疚的心來模仿,來回憶曾經發生的點點滴滴,必會觸發內心深處的淚水,然而這一切都只能自己咽下。“每一段都是我和我母親之間發生過的,每次拍的時候都會有點難過,但我不能表現出來,現場還有其他人,即使我再不舒服,我也要裝,對不對?”然而有一場戲惠英紅實在裝不下去了。那場戲拍的是芬姨看到核磁共振的成像片,在知道自己得病的時,整個人坐在地上崩潰了,無言地流淚。戲里的淚,其實與戲外的淚相通。“我媽70歲的時候摔了一跤,大腿骨摔碎了,然后醫生發現她有很嚴重的老年癡呆,覺得她是因為這個病才會摔跤。之后做了核磁共振,當我看到那個片子的一瞬,我整個人都在發抖,心里面疼得不得了,眼淚嘩啦嘩啦地流。那么大的頭顱,可是顯示在片子上都是白色的,懸空一個雞蛋大小的腦,大部分功能都喪失了。演那場戲時,我就和導演說,你不要喊卡,你讓我把情緒沉淀下來,我想把我看到‘雞蛋’那一刻的那種害怕表現出來。所以我用我自己的那個情緒去演,那種無助,那種跌倒在地的無力。”后來,這場戲演完,當場務已經開始整理燈光,惠英紅還坐在地上,滿臉淚痕。她說,那場戲是她最“心苦”的一場戲。沒有什么比后悔更痛苦的了,從得知母親患病那天起,惠英紅懂得,原來生活比戲更重要,原來珍惜比可惜更珍貴。

美酒需佳釀,美人需雕琢
喬治·艾略特說過,最幸福的女人,像最幸福的民族一樣,沒有歷史。“但有歷史沒歷史由不得你來定的,全憑命運的安排,怎么辦呢?如果命運規定你一定當不成最幸福的女人,那么就當個最堅強的女人吧,堅強到可以把自己的故事當成一個故事,不介意跟任何人分享;堅強到把自己的心情當成一個心情,無所顧忌地告訴記者和他人。”說這些話的時候,惠英紅點燃一根細細的女式煙,眼睛嫵媚,笑容爽朗。讓人想起張愛玲所說的,“有一種郁郁蔥蔥的身世之感。”雖然這已經是幾年前的心境了,但惠英紅還是那個惠英紅。
美酒都有余味,好的酒最令人回味的不是甜也不是酸,而是最后舌尾上的那一點點的澀。而有故事的惠英紅最令人回味的不是她的演技,而是她身后那裊裊輕愁的如戲人生。出身名門,卻一朝家族落敗,4歲開始在紅燈區和港口碼頭賣口香糖填補家用;12歲開始去舞廳跳舞,到17歲被香港導演張徹發掘,開始做電影女主角,紅極一時,成為“邵氏”當家打女,在22歲獲得第一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然而伴隨著香港武俠片的沒落,惠英紅經歷了從天堂到人間再到地獄的心理轉變,一度患上抑郁癥。當自殺未遂被救回,看到母親的那一刻,她猛然醒悟。豁然開朗后的惠英紅,生命似乎剎那間煥發了光彩,以前忽視掉的那些最重要的東西,都覺得異常珍貴,“那段日子讓我感受到了,人世間最重要的是愛,不只是男女之愛,還包括家人、朋友的愛。”好強是惠英紅的弱點,也是她的長處,2010年第二次重回金像獎頒獎舞臺宣告了她的涅槃。“我現在拍戲那么努力,是因為我曾經掉下來過,現在好不容易有個機會就要好好抓住。不是為了錢,錢我并不缺,而是說隨隨便便你好像就放棄了什么東西,被逼著離開很丟臉。我希望的是能夠做出一個好的成績,不要再次掉下來。”回顧自己人生的跌宕起伏,面前的惠英紅一臉倔強。
惠英紅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會息影,但即使息影,也必須是以最優雅的姿態離開生活了小半輩子的舞臺。她說她已經有些厭倦了40多年重復做一件事情,是時候該享受人生了。“人生就是每個階段都會有變化,每過一個十年就有一個變化,現在我50多歲了,那我拍電影拍了40多年了。我這輩子做了三個行業,第一個是乞討,第二個就是跳了兩年半的舞,第三個是到現在都是演員,我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井底之蛙。我打算再拍一段時間,疲累了就停下來去讀書,重新再學畫畫。這是我希望的,當然有希望就有可能成功,我希望在我老的時候,我是一個畫家。”在我看來,她的這個希望更像是想要彌補內心的一個遺憾,也是自己的一個真正渴求。“我就是想當一個畫家,我一直覺得我在畫畫的時候是最松弛的,也感覺自己是最女人、最優雅的時候。”作為打女出身的惠英紅,常被人評價說沒有女人味,而她自己也曾調侃說,大概就是因為自己太強勢,才導致至今還沒能結婚,男人大概都怕了我。不過現在,她可以自由選擇脫下堅硬的外殼,露出內心的柔軟,回溯到遙遠的舊年,正值二八芳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她的新人生,這才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