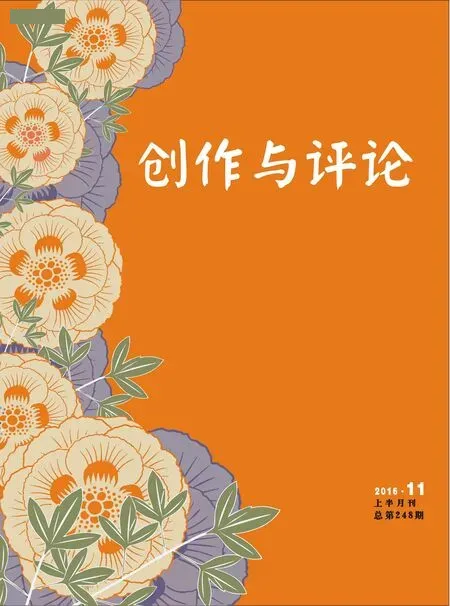歸鄉者、懸置者與時代病人
——小昌小說論札
○馬 兵
歸鄉者、懸置者與時代病人
——小昌小說論札
○馬 兵
在很多場合,小昌都強調過他作為一個“80后寫作”的“遲到者”的身份。的確,大約在五年前才開始嘗試小說創作的小昌,錯過了他的同行和同輩那些蒙“80后”之名的高光時刻,無緣分享那些世俗的榮耀和商業回報,但也得以免于某種固化的審美趣味和寫作觀念的裹挾。因此,在我看來,“遲到者”于他反而是種優勢,至少可以讓他在自己擇定的寫作路子上從容地走下去,并補充別人所無的生活經驗,他筆下那些困陷在時代深處的年輕人我們也許能在別的作家筆下找到類似的形象,但是他賦予這些形象的微觀情感和體驗深深鐫刻著自己的印記。童年的鄉土記憶、富士康的工作經歷、大學教師的職業身份都構成他寫作的資源或者塑造其寫作的態度,讓這個“遲到者”在他所屬代際的創作潮流中始終保持著一種和而不同的樣貌。也正因此,小昌的寫作時間雖然不長,但在嶄露頭角之后迅速地成長為廣西文壇最具潛質、最具辨識度的年輕作家之一,并讓我們對他未來的創作充滿了期望。
一、陌生的歸鄉者與失效的記憶共同體
從魯迅的《故鄉》《祝福》開始,歸鄉者一直構成現當代文學史上鄉土敘述的重要聲部,而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鄉土社會出現“本質性”的解體和轉型,更是出現了一大批以歸鄉者為敘事主體的小說,以《歸鄉記》為名的小說就有數篇。小昌在處理鄉土經驗時,也往往依托歸來者的視角,較為有代表性的是《小河夭夭》《泡太陽》《飛來一爿村莊》等三篇。
一般而言,以歸鄉者來敘述鄉土暗含著某種權力的秩序,歸鄉者多是自城市攜帶某種或正或反的現代價值觀念而來,在鄉間居停的過程中,他們以自己的眼睛掃視故土,并往往凝結著對故鄉精神狀貌的質詢和批判,此即所謂的“看”與“被看”模式。但是在小昌這里,“看”與“被看”始終是一種雙向的關系,歸鄉者看故土故人,也被故土故人所打量,他在上述小說中不斷處理“故人相遇”,可故人間的陌生感卻層層累積,他看不懂故鄉人,故鄉人也不明白他,這使得歸來者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了陌生人。而且我們分明可以感覺到,小昌筆下的歸鄉者深陷于一種無力感之中,他們都是從城市敗逃而來的青年,也清楚地知道并不能在故土收獲安慰,因此,除了對親情、愛情和友情某種想象的拯救,歸鄉的行旅所帶來的絕非療救或情感的代償,而毋寧是更深一層的自我分裂和更深一層的放逐感。
有評價認為《小河夭夭》寫當前農村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但無意把這些信息朝著深刻主題的方向發展,我的看法卻恰恰相反,看起來,小昌好像是繞過了三農問題中那些最尖銳的內核,而是信筆游走在家庭瑣事的邊沿,然而這些家庭瑣事投射的訊息不正深刻映射著農村的倫理危機嗎?在有著長久的“倫理代宗教”的文化體系的鄉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都帶有強烈的人倫實用色彩,倫理的觸須牢牢系于社會道德生活的最基層即家庭倫常的層面,進而積淀為規約人們日常生活的一種“習慣法”。但在現代性為主修辭的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能夠對鄉土生活提供“禮治”和信用的倫理體系已經崩坍,以至出現大面積的倫理頹勢,鄉民們失去了借以維系生活整體性的依持,鄉土道德的畸變也隨之層出不窮,這或許是鄉土現代轉型必要的代價,威脅的卻是人在倫理秩序中的歸屬感。小昌以歸來者的眼睛專注這一切,其實正體現了他的敏銳。《小河夭夭》中設置了一條主情節線,即堂弟小磊和丹丹隨意而又潦草的婚姻,丹丹看不上小磊,帶著孩子逃回娘家,又被夫家的人設計把孩子搶回來。兩個其實并沒有長大的年輕人,在外面世界的誘惑和家族觀念的控制下,既想做主又做不了主,近乎游戲地結合生子又分開,夫家和娘家的搶子,各自都充滿算計,在他們身上已經完全看不到婚姻在鄉土禮俗中的意義,也看不到為人父母的責任和自律。與之相比,《飛來一爿村莊》有著更具隱喻力的表現,歸鄉者洪順約請同宗的洪仁和洪義兄弟一起吃飯,兩兄弟雖然一富一窮,但對鄉土的潰敗和劇變一樣感同身受且無力超脫,那些作為鄉土精魂的東西煙消云散之后,“仁義”就勢必成了反諷的注腳。而且在小昌塑造的歸鄉者身上,城市生活并未賦予他們榮耀的相比于鄉村的身份位階優勢,在禮治的倫理觀被實利的倫理觀取代之后,無權無錢的歸鄉者在鄉下也成了不體面的存在。《小河夭夭》里,對敘述者“我”有所寄望的丹丹,在后來失望地發現,城里歸來的這個哥哥并不比她更有見識。“我”對丹丹不幸的婚姻處境除了道義上的支持,再無力提供更多的什么,而且在丹丹求助的時候,“我”灰溜溜地逃走了。這是一個拯救失敗的故事,甚或連拯救都稱不上,“上過大學”、在城里工作的那點“出息”在歸鄉之后顯得蒼白無比。而在《泡太陽》里,“我”要辭掉老師的工作,考一個公安局的副科長,才有和做了鄉長的舊友重續友情的可能。
由此我們也就理解為什么小昌一定要在這些小說中安排那么多絮叨甚至到任性地步的閑筆,因為他看似漫不經心的敘述實際上始終關聯鄉土畸變最尖銳的部分,比如,他在《小河夭夭》和《泡太陽》中都寫到鄉村空巢化后,年事已高的老人排著隊倚著墻曬太陽,他們被村里人稱為“敢死隊”,因為不定期地他們中就會有一個死去,把空位留給新來者補充。小昌筆下那些承擔敘事功能的回鄉青年也總能捕捉到這種畸變沉積的痛點,如點穴一般,由一點而及全身,可見,他的敘述之輕和之散并非是對巨大之物的抵消或化解,而更類似一種迂回,有點像卡爾維諾闡釋過的思路,當生存的沉重構成一種脅迫時,為了避免被它約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這個世界,以另外一種邏輯、另外一種認識與檢驗的方法去看待這個世界”①。因此,小昌的敘事是輕逸而非逃逸,他態度的松弛其實是一種有意為之的控制,是對預設悲情的寫作慣性的拒絕,何況他也不是用卡爾維諾那種飛揚式的輕逸,其敘述者的目光還是不離令他陌生的鄉土,他只是小心地祛除這個過程中人們通常會有的焦灼和痛切——焦灼和痛切本身并不是問題,然而一旦煽情化,就會成為廉價的文學良心秀和對底層寫作的媚俗,對此,我們都應該不陌生——而故意代之以絮叨,在這種調性的反差中將自己的觀察更富有張力地傳遞出來。畢竟,文壇并不缺乏對鄉土現狀正面強攻的以重擊重的作品,小昌無意再為之添磚加瓦,而且那樣也并不符合他的敘述者的年紀和閱歷。這樣看來,小昌的以輕擊重既是一種小說的方法論,也契合了青年歸鄉者的微觀視野。
有意味的是,在小昌筆下,那些對現在的故鄉感到惶然又倦怠的年輕人無一例外地都在嘗試用記憶對抗消逝,用對記憶的重演召喚舊日的朋友與分裂的自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首先“回鄉”敘述模式本身便預設了“昔我往矣”與“今我來思”的比照,而記憶是貫穿其間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價值和信仰缺位的背景下,記憶成為確認自我歸屬和身份認同的重要甚至的唯一的倚靠,歸鄉者希望借助與朋友一起共在的記憶,尤其是對那些少年時代細節的打撈,以建立一個記憶的共同體,將他們從虛無中救渡出來。為此小說對記憶的憑吊設計了一些具有儀式化的場景:在《小河夭夭》中,敘述者“我”回鄉的目的之一是要把自小玩大的幾個朋友強哥、麗姑等約在一起,舉行一場水閘邊的聚餐;在《泡太陽》中,“我”備好酒場,引來夏海濱和杜文壇兩個舊友喝酒;在《飛來一爿村莊》中洪順、洪仁和洪義三兄弟則在酒后一同敲開了大雁兒家的門。然而,就像三篇小說接下來所展示的那樣,歸鄉者與朋友借助野餐或酒宴結成的記憶共同體不但脆弱,而且注定是要破產的。《小河夭夭》中直接讓聚餐變得走樣的是開著汽車、帶著招搖的女助理前來赴會的強哥,強哥告訴敘述者的是:“真搞不明白,你現在怎么喜歡上這個了”;《泡太陽》中因為之前的芥蒂,使歸鄉者和兩位發小的酒場不像是諒解,而更像是心照不宣的掩飾;而在《飛來一爿村莊》里,三兄弟找上大雁兒的門,可是大雁兒早已不是當年的純真少女,并隱約透露她和村里的黑老大有著曖昧的關系。作為鄉村巨變的一部分,強哥、夏海濱和大雁兒以各自的方式瓦解了歸鄉者的牽記,暴露出歸鄉者一廂情愿地構建起的記憶共同體內部離心力的強大,根本是他所無力調控的。
記憶重塑機制的失效,等于耗盡了歸鄉者歸鄉的行為意義。《小河夭夭》的結尾,敘述者決意返城,在遠眺村子時,眼神聚焦在一個“小白點上”,那是二爺墳頭上的白幡,一個死亡的象征。在《泡太陽》的結尾中,敘述者也固執地問起被夏海濱撞死的瘋子沙武,同樣是一個關于死者的收束。我不知道這是否是一種巧合。拒絕遺忘的歸鄉者無法在故鄉復原記憶,而當他回城時,他攜帶著的卻是死亡的訊息,也隱喻般地宣告了鄉土記憶的終結。
二、穿行于虛無與懸置者的自證
小昌在多篇創作談中都談到過對生命無聊感的體會,比如他說:“活到現在,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里度過。學校生活真是無聊透頂,當然其他生活多數也是無聊的。無聊是種宿命吧,至少對我而言是種宿命。……記得有一次,朋友們喊我去踢球,我也很有熱情,換了鞋上場了,大太陽在頭頂上閃耀著。我站在隊友中間,突然恍惚了,把球傳出去有什么意思,要不就射門,射進了又有什么意思。所有人一瞬間褪去質地,只剩一副輪廓。球在腳下,我呆住了。很多人喊我快傳呀,快傳呀。我的球很快被搶走了。我一屁股蹲在地上,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巨大失落。玩不到一塊兒去了,他們和足球都讓我感到厭倦。我灰溜溜地離開了足球場,后來再也沒去踢過。我感到無聊,幻滅感接踵而至,幸好有文學。文學讓我覺得有那么點意義。”②
他講述了一個富有情境感的時刻,并告訴我們選擇寫作,在某種程度上即是來回應無聊的宿命。他的說辭還是一貫輕松,攜帶著一點調侃,可是如果幻滅和虛無真是其寫作發生的起點,便不得不說,小昌在一開始的創作即帶有本質性的向度,也具備一種相當有勇氣的創作品格。坦白說,寫作虛無毫不新鮮,而且已然構成80后寫作的重要面向,在現有的80后寫作積累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處理虛無體驗的作品,不過仔細分辨就會發現,這些虛無體驗基本是在兩個路向上展開:一是歷史虛無主義,某種程度上歷史虛無主義構成了80后寫作的發生學背景;一是青年亞文化的青春創傷記憶,那種類似為賦新詩強說愁的孤獨和迷惘。小昌的虛無書寫和二者都有關聯,但又都不相同,他更偏重于在存在主義的視閾中看待虛無,把虛無視為一種存在的本源性情境,而非與年齡和代際相關的某種情緒展示的裝置或道德的潰敗感。存在主義神學家保羅·蒂利希在《存在的勇氣》中表達過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將生命的幻滅、恐慌和由此引起的焦慮體驗,看做可稱之為“執勤的自我肯定的表現”,因為“沒有帶預感的恐懼,沒有驅迫性的焦慮,任何有限的存在物都不可能生存。按照這個觀點,勇氣是這樣一種狀態:它欣然承擔起由恐懼所預感到的否定性,以達到更充分的肯定性”③。因而我想,小昌創作中大量處理虛無經驗,也應放在這一理解的框架下考察,即我們必須理解他在描述混沌生活中那些無法被所謂的正能量收編的負面情緒和思想時,是在描述一個存在的充實感不斷被損耗的緩慢過程,還是敢于置身虛無的核心,把個人的空虛呈現為某種豐富的和普遍的時代癥候。
小昌有個小說叫《幻病者》,敘述者總是幻想自己可能會得上各種疾病,并不斷在醫院做各種體檢,此外,就是約會各種姑娘,而當一個女孩告訴他在她之前他有個黑人男友時,敘述者又開始擔心自己會染上艾滋。沒有明確目的感的約會,總是出狀況卻查不到病因的身體,敘述者希望借前者拯救后者,到末了卻發現從靈魂到肉體的焦慮越來越深。如果我們把“病”作為物的世界的隱喻,把“愛情”作為意義世界的隱喻,那這個小說可以被解讀為物和意義共同將人導向虛無的故事。就小說本身而言,《幻病者》有點主題先行,也談不上精彩,不過它在小昌城市題材的作品中具有某種總括的意味,他筆下的虛無形象幾乎都被懸置在物的世界與意義的世界之間,無論在哪一端都找不到可以填滿空虛的“充實”。他這類作品數目不少,包括《我夢見了古小童》《被縛的卡夫卡》《三座椅》《找個美死人的地方奔跑》《車輛轉彎》《老頭》《沒有人是一座孤島》《貓在鋼琴上昏倒》《大俠》等等。
就像他前面談到的,在足球場上的某個瞬間自己突然被巨大的失落感擊中,小昌在小說中也很擅長在常人習焉不察的地方洞察到荒誕和虛無,并通過對這種情境的提純使某一生活即景的切片陡然具有一種縱深。比如在《車輛轉彎》中,虛無感的觸發來自于汽車在轉彎過程中擴音器傳出的“車輛轉彎,請注意安全”的提醒音。小說中的“他”在凌晨某刻被這個聲音籠罩著,他拿起一副啞鈴想砸向那個聲音,可是“連聲音的出處在哪里都不知道”,“只是聽上去感覺讓人荒謬極了”。他被這個聲音逼迫著下樓去尋找聲源,可怎么也找不到。在尋找聲音的過程中,他驚擾了一對幽會的男女,這讓他想起了自己那個已經分手的情人。他來到情人家門外,設想進入房間會如何,而等他真的走進去,房間里卻空無一人。他沮喪地跑出女人的家門,向自己家奔去,又一次聽到“車輛轉彎,請注意安全”的聲音一句一句,如影隨形。和《幻病者》一樣,《車輛轉彎》中的“他”被代表物的世界的無意義的聲音擾動著,他想尋找異性的陪伴來作為抵抗獲取某種意義,卻一無所獲。這篇小說其實可以換一個名字叫“幻聽者”,它用表現主義的風格寫出了生活中常充塞于耳邊的聲音如何轉化為城市生活寄居者的異化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小說的開頭和結尾恰恰用了寄居蟹的意象。
與之類似的還有《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從題目上看這個小說即有一種隱喻的訴求。鄧恩的這句布道詞常被用來表達獨立個體之間的共在和關情,以因應人本然的孤獨。但在小昌這里,他更像是在提供一個反證。同《車輛轉彎》一樣,小說中的人物沒有名字,第三人稱代詞“他”和“她”可以被隨意替換成“你”或者“我”,暗示這不是一個人的遭遇,而是所有人。“他”和“她”是一對住在酒店的夫妻,他想一人出去走走,便留她在酒店里。小說接著向我們呈現出,她和他,她和小姨,她和他的母親,她和邂逅的男人之間的交流悖論,一面是渴望溝通,一面是隔閡和心防,無論在哪一種關系中,她都無法找到確實的支撐,而且她越陷入人際交往的鏈接之中,疏離感就越強。“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之下,卻如王家衛的電影一般,成了“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彼此的距離感無從填補。就像西美爾指出的那樣,距離心態“最能表征現代人生活的感覺狀態”,人們“對于孤獨,既難以承受,又不可離棄,即便異性之間的交往,也只愿建立感性同伴的關系,不愿成為一體,不愿進入責任關系”。④
在關于虛無的表述中,小昌普遍采用一種低姿態的敘述視角,并且故意流露著對形而下之物尤其是性與肉體的偏好。比如,他在很多小說中都描寫過一個叫萬青青的女人,并不放過時機地提及敘述者對這個女性的意淫。另外,那些承擔虛無情境的男性敘事者往往身份不明,也不受世俗或體制的束縛,并且經常嘲弄主流的價值觀念,看起來跟一些新生代作家和70后作家寫作虛無的路子相似。但是小昌并未停留在個人化的失敗或沮喪上,在他筆下,形而下的沉迷并不是一種惡趣味,而更像是點燃虛無感的一枚引信,雖然他不并具備深廣的哲學意識和思辨能力,可他關注的始終是引發形而下行為的那個背后的形而上的動機。而且就像前面說的,敘述者并不能通過欲望的滿足獲得充實的生命感,他寫形而下的行為是在內部瓦解身體沉溺的幻覺。另外,在這類作品中,他通常把情境置于故事之上,使得每一則小說都帶有寓言的質地。有論者以為,小昌如此處理,會削弱現實感。的確如此,僅從閱讀的層面而言,它們散漫甚至是支離,普遍代入感不強。不過,我想這或許正是小昌的苦心所在,他曾表達過,自己“想成為那種具某種精神向度的一類作家”,因此,我更傾向于將他對肉身的書寫和情景化的結構方式理解為通往精神之路的入口。
站在更高的要求上,也許可以苛責小昌的作品只是穿行于虛無,卻沒有洞穿虛無的力量和勇氣。但是就像尤金·斯諾說的:“在我們這個時代,虛無主義已經變得如此普及而且到處彌漫,已經徹底而深深地進入了今天所有人的腦海和心靈,以致不再有任何抗擊它的‘前線’;那些認為自己在抗擊它的人經常使用的武器就是它的,結果是他們自己對抗自己。”⑤萬青青和圍繞在她身邊的各種男人都在以“自己對抗自己”,而小昌則在以他們布成面對虛無的文學“前線”,從虛無內部推動我們對此的反省,這種直覺和自覺在青年一輩作家中是相當珍貴的品質。
三、麗麗的墮落與“反撲青春”的另一種講法
作為一個正在成長的青年作家,小昌也面臨著一個“致青春”的經驗轉化問題,他自己稱之為“反撲青春”,在前面兩類作品中,我們其實也都能提煉出不少源于作家個人經歷的青春元素,比如對第一人稱敘事的偏愛,對校園某個片段的感懷,對青春詩性一面消逝的傷悼,對代際流行文化的記憶等等,較為典型的如《浪淘沙有個萬青青》和《我夢見了古小童》。同很多“致青春”的作品一樣,這兩個小說書寫的也是理想和愛情的隕落,不過,對于隕落故事的具體講法,小昌有著自己的考量。
不妨以《我夢見了古小童》為例,這個小說的結構與情節同前面提到的《幻病者》很相似,第一人稱的敘事者“我”也常覺得自己身體有各種不適的癥狀,并且同樣把對女孩的追逐作為填充生命感的手段,“我”和古小童多年來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這期間則是“我”從學校到工廠到讀研再到工廠的潦草生活。在這個被不少人稱之為“后校園”敘事的小說中,面目并不清晰的古小童對于敘述者而言,一直象征著某種對抗生活體制化的力量,象征著讓人生活在別處的念想,她是敘事者與外在世界之間的緩沖,也是一個被不斷客體化的感官反應場,敘事者總是會在人生的各種低潮期找她,并通過對她身體的沉入獲得某種想象的撫慰。然而在現實情境中,古小童的人生軌跡卻是加速下墜的,她的男友換來換去,但生活毫無起色,最后委身在相親節目中,成為一個不自覺的嘩眾取寵者,顯示了消費社會對青春巨大的吞噬力。小說結尾,“我”看到古小童的節目,在夜里夢見她并再次聯絡上她,她期待和我一起去叢林跑步,可“我該怎么給我老婆說呢”?這末了的一句提醒了讀者生活秩序的堅固,聯想到小說開頭寫到的,“我”在看電視時“像一個得了病的老人”“有些頹喪”,暗示著“我”已經被生活規訓成庸碌的同路人,因此,“我”與她自由的奔跑也許只能是一場夢而已。整體上來看,小說中的敘事者并非一個價值完全紊亂的主體,但他確實是一個無力者,在從青春到后青春的轉變中,他依賴古小童來為人生賦意,卻不能允諾或回饋給古小童什么。小說的時間脈絡相對清楚,可是個人的成長卻一直是被擱置和延宕的。另外,雖然加強了情節和細節的比重,這個“反撲青春”的故事因為形式上刻意的蕪雜和散漫,在閱讀上也并不像一般的“致青春”寫作那樣訴諸讀者的共鳴,小昌似乎依然珍視輕慢與否定性的敘述姿態隱含的批判思路和可能達至的那種本質化的表現力。
今年3月,小昌在《青年文學》第3期發表了中篇小說《南門麗麗》,再一次借用一個女孩從工線上的“王麗麗”到“南門麗麗”的隕落故事“反撲青春”。有意味的是,這個小說不但線索清晰,人物也不再面目不清,青春殘酷敘事必然附帶的抒情氣質彌漫全篇,甚至連故事的主副線情節都讓人似曾相識:主線是兩個底層出身的青年想相濡以沫而不能的感情,副線是打工仔的血汗工廠和暴力恩怨。相比于我們前面討論的作品,小昌在《南門麗麗》中顯然來了一次意圖明顯的后撤,這種后撤證明了他寫實功夫的扎實——小說絲絲入扣,打動人心,但也讓人疑竇叢生?他何以要收斂自己的異質性,轉用一個不無俗套的故事,轉用一種常態的敘事方式呢?真的只是像他自己說的,他的寫作無章法可尋,“打一槍換個地方”嗎?
許子東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論文《一個故事的三種講法——重讀<日出><啼笑因緣>和<第一爐香>》,通過對三個講述女人如何貪圖富貴而沉淪的現代文學名著的細讀比較,指出五四以來愛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或是被拯救被啟蒙的對象,或是協助男主人公平衡精神危機的媒介,她們自身的心理欲望反而很少得到重視”,在這個意義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改寫了女人墮落的故事”,指出女性的墮落“不僅僅是由于社會制度的罪惡,也不僅僅是因為主人公一時的道德錯誤,而是基于某種更普遍的人性弱點”,這樣說來,即使“社會制度天翻地覆”,女性墮落的故事“仍會延續”⑥。借用許子東的觀點來看《南門麗麗》,麗麗的命運盡管延續著底層寫作中“男殺人女賣身”的敘事套路,但其墮落的原因又不僅是資本權力造成的階層固化那么簡單,在麗麗的隕落中,對體面生活的追求未嘗不是內因,就像李云雷所觀察到的,這個關于底層青年的愛情故事對底層“并沒有‘關注’的意味,而只是將其中人物的生活與情感狀態‘呈現’了出來”。⑦何況自始至終,小說中都沒有渲染敘事者小興和麗麗在物質上的困窘,這證明小昌的興趣并不在給麗麗的墮落找一條為生活所迫的一勞永逸的借口,他借助一個套路化的故事“反撲青春”,目的還是集中在對精神之困的探討上。
細讀這部小說便不難發現,它幾乎集中了小昌此前寫作的所有向度,且標志性的元素無一缺席:小興不到二十歲,在鄉下已經有了孩子,老婆跟網友私奔,他漫無目的地投奔城市打工;靠拳頭在工廠打出一片天地的義哥夢想是回鄉放羊,后來被人尋仇砍斷手指——這兩個人和麗麗一起勾連鄉村和城市,既映射鄉土倫理的頹敗,又投射城市對農民工身份的巨大脅迫。而大學生羅南總感覺自己得了不治之癥,又是一個神經兮兮的“幻病者”!無論是什么階層的人,都有自己難解的心病,他們都是被抵押給大時代的病人,而他們的病又恰恰證明了他們還沒有喪失感受自身被異化的能力,可又無法在一個理性或秩序的框架中解決這種異化。因此,小昌看似“后撤”的舉動里,實則隱含著更有內力的質詢:比麗麗的墮落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小說中的每一個人在曖昧模糊的生活面前的孤立無援和無盡空虛。
讓我們回到這個小說的結尾:小興和麗麗合謀綁架了傷害過麗麗的吳主管和徐曉敏,可接下來要做什么,他們也不確定,兩個人看著遠處有一段對話:
“感覺活著沒啥意思,你有這樣想過嗎。比如從這里跳下去,摔成個肉餅。”她說。
“你要是跳,我就跳。”我說。
“我跳了,就怕你不跳。”她說。
“我不是那樣的人。”我說。
我把她摟得更緊了。
“很多人在睡覺,燈都滅了,他們睡得可真香。”她說
我說了句他媽的,就從圍墻上翻身下來。在天臺上四處亂找。終于找到一個破花盆。破花盆里的花已經干枯了。我雙手抱起它。
“你要干什么。”她問我。
我向樓下看了看,就把花盆扔了下去。
這是一個典型的小昌式的小說結尾,是意猶未盡也懸而未決,《找個美死人的地方奔跑》《幻病者》《大俠》《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也都用了類似的結尾方式。那個被扔下的花盆是一種“無力”解決的象征,這種“無解”讓小昌的小說具備了一種對“完成性”的抵制。當然可以指責這種無力感,問題是,面對龐大的虛無或茫然,簡單的“完成”,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可能成為一種遁逃之術。而在小昌筆下,那些個時代病者將要繼續盤桓在意義被空耗的地帶,除了幻想,他們沒有隱匿之地。那個扔下的花瓶像刺向風車的長矛,沒有意義,可是他要刺出。
注釋:
①卡爾維諾:《美國講稿》,《卡爾維諾文集·寒冬夜行人等》,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頁。
②小昌:《千樹萬樹梨花開》。
③保羅·蒂利希:《存在的勇氣》,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頁。
④西美爾:《橋與門》,轉引自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34頁。
⑤尤金·斯諾:《虛無主義:現代革命的根源》,轉引自余虹《虛無主義:我們的深淵與命運》,《學術月刊》2006年第7期。
⑥許子東:《一個故事的三種講法——重讀<日出>、<啼笑因緣>和<第一爐香>》,《文藝理論研究》1995年第6期。
⑦李云雷:《我們時代的情感與精神困境》,《青年文學》2016年第3期。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
本欄目責任編輯 張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