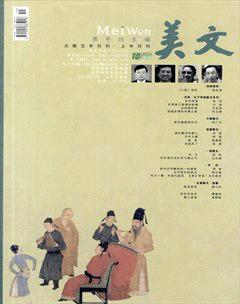蛻變
周淑靜
當灰暗空洞的天際褪去陰霾,當干枯敗落的枝節探出星點新綠,當足下的印記任流年的風沙抹平,當你停靠在街角,眼眸中看著飛逝而過的行人,可曾知否,如今的你已不再如昨。
我想起自己初中時渙散的生活和那個沉淪的我。
斜挎著已經松松垮垮的書包,穿著昨夜偷改過的不合身材的校褲,麻木地嚼著索然無味的口香糖,百無聊賴地走在鮮有人跡的小路上。
已是深秋,寒風凌冽著,狂肆著,卷起道路上散落的枯枝敗葉,落葉隨風在半空中盤旋。我瑟縮著身體,干裂的腳踝僵著,走得愈發慢。一切都如病入膏肓的人一樣令人窒息。也許家才是我的容身之所。
離家兩日。依舊是掛滿爬山虎的磚紅色圍墻,依舊是被雨水沖刷而銹跡斑斑的鐵門,它還是半掩著。踢門而入,這兒遠比外頭更暗、更潮,像囚牢一樣困著我。母親坐在桌前,黯黃的燈光晃動著,她埋著頭,透過鏡片,一筆一畫地記著每日的開銷。本想無聲地回到房間,但陳舊的木質樓梯發出刺耳的吱呀聲,出賣了我的腳步。
“靜,你回來了?”母親放下筆,笨重地挪動著身體來到樓梯口。她散亂著頭發,面色泛白,眼角的皺紋在黃色的屋子里顯得更深了,比起昨日的她,簡直判若兩人。我攥緊雙手。“回來就好,回來就好,是媽媽錯了,媽媽不該誤會你,以后不要拋下我一個人了,我受不起……”她搖著頭,轉身走向廚房,我能清楚地看到她微腫的雙眼里,閃動著斑駁的淚光。
兩天前,昏暗的天際仿佛預示著一場心碎的破裂戲馬上就要上演。我被班主任叫進辦公室,罪名是懷疑我偷了剛上繳的班費——因為我是最后離開班級的。然而這一切我并不知情,無論我怎么辯解都是徒勞,結局便是母親匆忙趕到學校,還了錢,并當著老師的面,刮了我一耳光,丟下一句“不要臉”便走開了。
委屈,無助。我選擇了離家。
天空開始變暗,直到那輪刺目的月亮緩緩升起。我踩著鐘擺的滴答聲走向廚房,兩天未曾進食,饑餓感包裹住全身。昏暗中,我狼狽地尋找食物,無果。就在我絕望地轉身欲走時,忽一眼瞥見灶臺上靜靜放著一碗素面。我如狼似虎地大口吃著,突然一股令人作嘔的的液體從胃涌上喉嚨,然而這偌大的房子里只我孤身一人。
解決了晚飯,我踏著月光,在燈光閃爍,笛鳴交集的街上漫步著,眼前七彩的光斑重重疊疊雜亂著。不知不覺中,我來到那個熟悉的公園。不遠處,有一個頂著白熾燈的面攤子,面攤是一對夫妻開的。妻子有一手煮面的絕活,丈夫幫忙打下手,生意還算紅火。如今,丈夫去外地,一年才回來一次。從那時起,面攤就由妻子一人支撐。夫妻二人有一個女兒。
女兒,就是我。
刺眼的燈光照在母親身上,翻滾的湯水冒出騰騰白汽,母親嫻熟地打理著生意。氤氳的霧氣中,我仿佛看到母親隨著歲月漸漸老去的畫面,而她的眼眸中,總是流露出無法掩藏的憂傷。從前,她應該也是一個如從煙雨中款款而來的女子一樣充滿詩情畫意吧?可如今,她撐開瘦弱的臂膀,擔起生活的重任。
愧疚。心塞。我走向她。
不知是不是風太凜冽,鼻子一陣酸脹。燈光下,水汽籠罩著我,遮住了我眼中的淚水。母親抬頭看到我,驚愕不已,似乎是一個陌生人站在她面前。也許我早該選擇長大,和她一起撐起我們的藍天。
綠葉上的青蟲結為蠶蛹,終會蛻變成半空中翩躚的輕蝶,正如我亦會長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