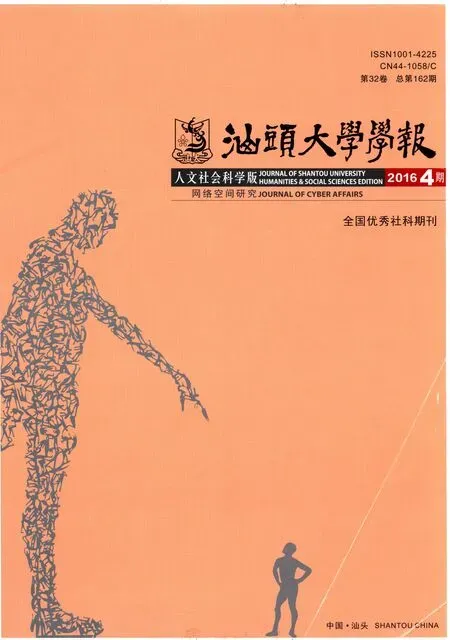互聯網與“人的條件”
鄭永年
互聯網與“人的條件”
鄭永年

鄭永年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互聯網的出現已經急劇地改變了我們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在互聯網空間,傳統意義上的公共和私人領域的邊界完全消失,原本的公共領域變得更加公共,而原本最私性的領域也被毫無邊界地在公共領域得到表現。近年來,日本最受歡迎的“女朋友”只是一個互聯網“程序”而已,人們開始可以和“程序”結婚,能夠直接地影響到人類本身的再生產和生存能力。作為組織政治生活最主要手段的傳統政黨正在被互聯網所取代。無論是英國的公投還是美國的特朗普甚至一些類似伊斯蘭組織,都在充分展現著互聯網的能力和能量。盡管這些例子只是少許,但互聯網已經向人類展示了其改變人類的無限可能性。另一方面,盡管對互聯網的研究文獻已經是汗牛充棟,但對互聯網到底是什么?人們似乎仍然極其膚淺,甚至不得而知。或許,我們可以從當代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人類活動的討論中獲得一些靈感。
1958年,阿倫特出版了注定要成為當代政治哲學經典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作者將人界定為“活動生命”,并將“活動”分為“勞作”(labo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三類。這種區分向人們揭示了這樣一個容易理解但深刻的道理:人類與動物之別在于人類可以工作,制造東西,不像動物只能依靠本性,既不能計劃未來,也不能生產可以在自己生命結束時還可以繼續存在的東西;進而,人更可以行動,這是一群人共同進行而完成的一件事情,這樣的事情可以不朽,因為人們會繼續記得這一件事情,會去理解其意義,只要社群繼續存在他們就是不朽,事件也是不朽。在這關乎人類生命的三個境界之中,無異于動物生活的“勞作”位于最低位,而造就不朽的“行動”則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人們可以從各個方面來界定互聯網的本質,但很顯然如果從互聯網影響我們人類活動的過程來界定其本質,至少從社會科學的意義上,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式。那么,如果從阿倫特對人的看法,互聯網到底促成人類去擁有更多的動物性還是人性呢?正如法國哲人笛卡爾所言,“我思故我在”,人和動物的基本區分是:人是能夠思考的動物。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互聯網給我們人類予什么呢?
作為一種溝通技術,互聯網的主要特征表現為分散性、分權性、個體性、民主性等等。在互聯網世界,沒有人可以像傳統那樣來壟斷公共空間,每一個網民都可以創造屬于自己的無限的公共空間,提出問題并使得討論具有公共性。不過,同時,互聯網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發泄情緒的有效管道,互聯網可以隨意放大人們的情緒,無論是愛還是恨。也不難觀察到,在這個新的公共領域,很多人都是隨大流者,只做選擇,而少了自己的思考。更有甚者,互聯網成為了表現者表現私性的有效工具,把所有私性方面的東西展現在公共空間。個體的表現欲一旦和互聯網的獲利性質結合起來,互聯網更能把事物推向極端。
在互聯網空間,也沒有絕對的道德,所展現的都是個性化了的道德。傳統上,“公共”表明對“私”的遏制和揚棄,“公”不見得沒有“私”,但如果不能對“私”做一定程度的克制,那么就很難產生“公”。與此不同,在互聯網空間,人們往往很難看到傳統意義上的“公”,而所謂的“公”也僅僅只是眾多的“私”的聚合。這是因為在互聯網空間,人們對信息往往只是作一種選擇,沒有綜合能力,也無需綜合,人們只是認同一種符合自己的一個符號、一個理念、一種思想、一個相像社群、組織等等。經過符合“自我”的信息過濾,人們的視野越來越微觀,越來越缺少大局觀。這就是互聯網空間思想自我激進化的邏輯。激進的思維導致激進的個體行為,不僅表現在互聯網空間,更是發生在實際社會領域。在互聯網時代,激進的個體行為已經成為社會新常態。
互聯網不僅影響個體的思想、思維和行為選擇,也影響甚至主導人們的“集體行為”。傳統上,集體行為包含各種“成本”,即學術界所說的“集體行為邏輯”。但互聯網空間的集體行為邏輯和傳統集體行為邏輯相去甚遠。因為高度的分散性和民主性,互聯網空間的集體行為的成本極低,而聚集效應又極高。也就是說,互聯網空間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以最小的成本聚集眾多的人群。無論就其組織功能還是傳播功能來說,在政治上,互聯網正在取代傳統政黨的角色。傳統政黨也一直被視為平臺(platform),即聚集政治傾向性相近的人們去追求一個共同的政治目標。不過,互聯網和傳統的政治平臺又有很大的不同。在精英政治時代,傳統政黨被精英所把持,對事物精英之間容易達成共識。大眾民主時代,政黨往往傾向于民粹主義。在互聯網時代,通過互聯網所作的政治動員無一不具有強烈的民粹傾向性。因為是單個個人的聚合,沒有任何過濾機制,民粹就變得不可避免。在今天的世界,無論是英國的公投還是美國的總統選舉,互聯網和政黨合二為一,但民粹傾向性也越來越強。
在國際層面,互聯網很容易把民粹轉型成為民族主義。這里就出現了嚴重的網絡安全問題。一個國家的網絡遭到另外一個國家的攻擊,攻擊者既可以代表主權國家的政府,也可以是和政府毫不相關的個體。我們提出了網絡主權的概念,希望來保障網絡時代的國家安全。但網絡有沒有主權?網絡主權怎樣體現?所謂的網絡就是把世界各個國家連成一體,不再有“邊界”,有了邊界就很難叫網絡。既沒有邊界,又要保障安全,這顯然是一對矛盾,仍然需要我們尋找有效的方法。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的互聯網那樣提供給我們新的“人的條件”,但同時我們也從來沒有像今天的互聯網那樣給人類本身提出了無限的挑戰。面對互聯網,我們甚至需要重新定義“人”本身。如果人們像以往的數十年那樣,被動地順著互聯網的發展而發展我們自己,我們可能不知不覺轉變成為“非人”。我們在互聯網空間所進行的可能只是一種“勞作”,而非“工作”,更非“行動”。互聯網給我們創造了無限的可能性,但我們是選擇成為互聯網空間的動物,還是經“工作”成為人,或者經“行動”來創造意義,這并不取決于互聯網本身,而是取決于我們人的主觀選擇。不管人們喜歡與否,主導著我們人類的未來不僅僅是傳統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且更是人與互聯網之間的關系。而這也使得互聯網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了非凡的意義。
(責任編輯:左金玉)
互聯網不僅影響個體的思想、思維和行為選擇,也影響甚至主導人們的“集體行為”。
G2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