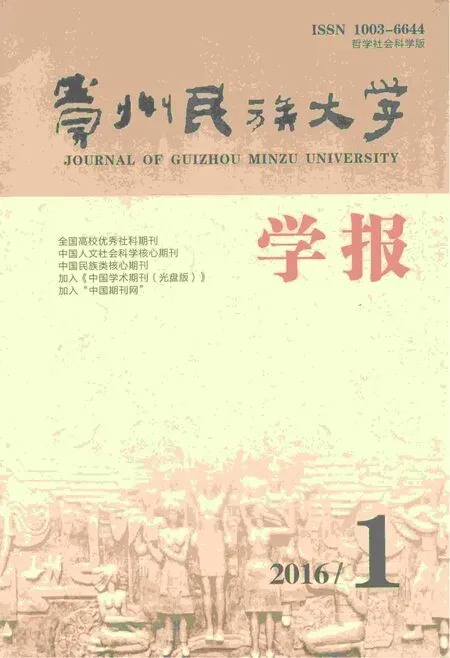在國際民俗學領域發出中國聲音——《亞洲民族學》雜志推出“中國民俗研究”特刊
在國際民俗學領域發出中國聲音——《亞洲民族學》雜志推出“中國民俗研究”特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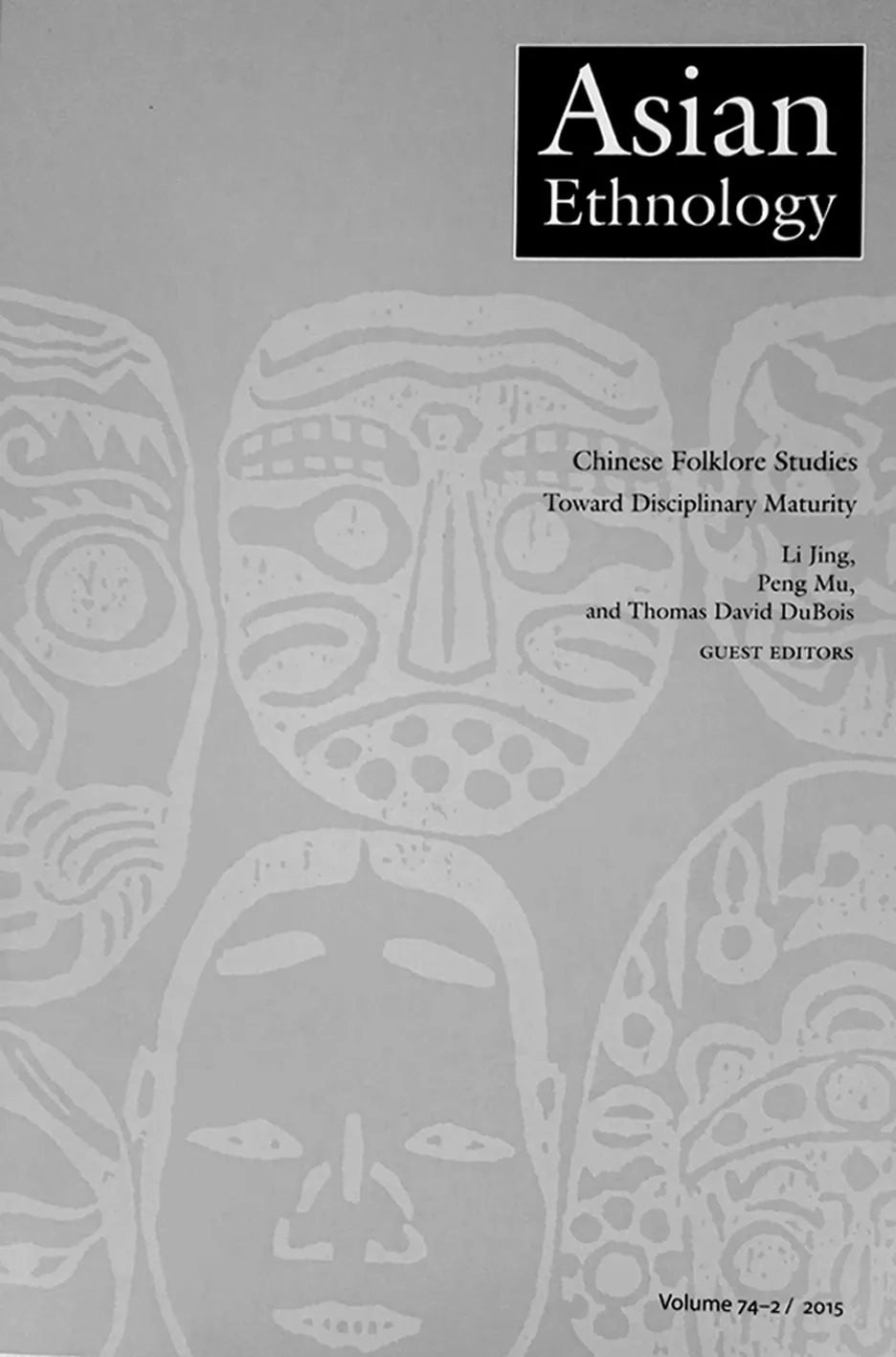
2015年11月,名為“中國民俗研究”(Chinese Folklore Studies)的《亞洲民族學》(AsianEthnology)特刊(第74卷第2期)在日本名古屋出版。經過五年的努力,在國內外學者的精誠合作下,由李靖、彭牧和杜博思(Thomas David DuBois)擔任特約編輯的特刊終于付梓發行。
《亞洲民族學》的創刊可追溯至上個世紀四十年代。1940年,北平輔仁大學在葉德禮(Matthias Eder)及其他漢學家的努力下,成立了人類學博物館。1942年,博物館的下屬期刊《民俗學志》(FolkloreStudies,或譯《民俗研究》)創刊。此后,在葉德禮等外籍教職員以及國內學者趙衛邦等的參與下,該學刊堅持每年一期,用英、法、德語介紹東亞國家的民俗研究情況,包括東亞地區田野調查的最新資料、理論與方法論的進展等。1948年,該刊遷至日本,1963年改名為《亞洲民俗研究》(AsianFolkloreStudies)。直到2008年,因“民俗”(folklore)一詞的局限性,該刊改名為《亞洲民族學》(AsianEthnology),目前由日本南山(Nanzan)宗教與文化研究所以英文出版。作為“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A&HCI)收錄的民俗學國際核心期刊,該刊在亞洲民俗學研究領域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其特色之一是鼓勵亞洲本土學者的研究。
《亞洲民族學》創刊以來,除了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期趙衛邦在此發表了整體介紹中國民俗學研究的論文以外,后來雖然零星有中國學者發表中國民俗研究的文章,但整體看來,呈現出來的大多較為碎片化,缺乏綜合全面的展示。而本期特刊,由六篇中國學者的文章組成,較為全面地呈現了中國民俗學興起的歷史、近年的發展軌跡與當下研究的現狀。
李靖作為特刊的特邀編輯,其《中國民俗研究:走向學科成熟》(Chinese Folklore Studies: Toward Disciplinary Maturity)一文,可視為本特刊的緒論。在總結其他五篇文章的基礎上,該文較為全面地介紹了本特刊的主旨。作者主要從民俗學史的角度切入,在回顧了中國民俗學發端、早期發展中的社會背景及政治傾向后,又分別從三個方面闡明了新世紀民俗學學科的轉向。首先是對“到民間去”(going to the people)的新理解與新實踐,如“民”的概念的轉變。其次是對當下民俗學者身份的重新評估。作者肯定了學術界的獨立性和批判性,肯定了學者們的自我意識。最后介紹了中國學者與國際民俗學界的交流,特別是在國外理論的引進及應用方面。作者提到,在探討這期特刊中主要表現什么時,有兩個引進的概念一直被學者們提及,它們分別是體知(embodiment)和語境(context)。其他五篇文章,分別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這兩個概念,并在實踐中對它們進行了反思與推進。正是在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中國民俗學正在逐漸走向學科成熟。
安德明與楊利慧合作撰寫的《19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民俗學:成就、困境與挑戰》(Chinese Folklore Since the Late 1970s: Achievement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細數了中國民俗學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到當下三十多年的發展情況,展現了民俗學這門學科在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背景中的浮沉命運。該文第一部分為民俗學的復興與重建。這一部分詳細介紹了中國民俗學的學科性質、學科地位及機構設置,還特別提到了為民俗學學科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鐘敬文、張紫晨等老一輩民俗學者。第二部分為理論與方法論的新拓展。民俗學逐漸恢復了學術研究的獨立性,主要實現了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視角三個方面的轉變,其間還涉及到國外理論的譯介與應用。第三部分為民間文學三套集成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這是中國民俗學界三十多年來在社會文化工作中影響最為重大、最為深遠的兩件事。第四部分為困境與挑戰。作者就學科定位、個案與區域研究等方面的問題表達了對民俗學學科前景的思考。
劉鐵梁的《勞作模式與村落認同——以北京房山農村為例》(Village Production and the Self Identific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Fangshan District, Beijing)一文,提出了中國村落研究的新視角。作者通過對房山農村地區的持續觀察,回歸生活本身,看到了村落在工業化影響下產生的“勞作模式”(village Production)的變遷。而村落勞作模式(territorial village production)包含著村民們在特定的生產過程中所累積起來的身體經驗與感性知識,正是這種共享的身體實踐,構筑起了村民們的自我認同及其村落共同體。作者以京郊房山沿村的編筐業為例,從歷史文獻到口述資料,梳理了該地區的城鄉經濟結構的變化,并詳細說明了該項手工業對該地區的生產、生活,特別是村落的集體信仰產生的深刻影響。基于此,作者進一步肯定了勞作模式對村落認同的積極建構作用。
陳志勤的《為了誰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信仰的主體置換與地方文化的再生產》(For Whom to Conserv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Dislocated Agency of Folk Belief Practitioner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Local Culture)一文,可以說是對國內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質疑與反思,特別是在民間信仰方面。作者在浙江省紹興市調查時,發現其大禹信仰與舜王信仰分別被置換為名為“大禹祭典”和“舜王廟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里的置換,不僅是名稱上的,更是主體上的。再加上之前旅游業的發展,該地的信仰文化不斷被再生產。在這個過程中,因利益等因素,原來的信仰主體為政府所代替,連帶著其信仰文化也被重構,而該信仰的真正主體即當地民眾,卻喪失了對自己的文化資源的社會與經濟價值權力,甚至面臨離開家園、放棄記憶的困境。基于這些事實,作者提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基本問題:為了誰而保護。這種“政府主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值得深思的。
彭牧的《不可見的與可見的:與陰間溝通》(The Invisible and the Visible : Communicating with the Yin World)一文,創造性地用實踐理論來探討一個村落的信仰問題。作者從湖南茶陵地區村民們日常生活的身體實踐出發,解釋了當地人如何在缺少制度性宗教的條件下形成有關陰間的概念與信仰。作者參與觀察了該地區陰歷七月的鬼節(中元節),結合自己的體知,細致描述了村民們在祭祀期間的各種活動,如“下飯”、“燒包”等。另外,作者還特別提到了當地的兩種靈媒,一種是業余的,即“顛祖牌”時被祖先附身的普通村民;另一種則是專業的,即“梅爺”,和“查家”、“調魂”等。“梅爺”的存在,以村民們共享的關于陰間的知識為基礎,而這又反過來促進了村民們對陰間的信仰。正是這些“實踐的信仰”(practical belief),使村民們在傳統實踐的“做”中完成了對陰間的想象與確認,并使之代代相傳。
楊利慧的《語境的效度與限度——對神話傳統的民族志研究反思》(The Effectiveness and Limitations of “Context”: Reflections Based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of Myth Traditions)一文,是對學術界“語境”(context)一詞泛濫應用的質疑。作者立足于河南淮陽、重慶市走馬鎮司鼓村、山西省洪洞縣侯村等三個社區的田野調查,提出了對“語境”這一概念之有效性的反思。語境雖然影響著神話文本的構成和變化、神話的講述場合、講述者與聽眾的構成與規模以及神話的功能與意義,但這種影響是有一定限度的。這種限度表現在神話的核心母題、母題鏈的組合與類型、基本情節等方面的穩定性。基于對“語境中的民俗”的反思,作者提出結合文本與語境、歷史與具體表演時刻(the very moment)、區域與比較、集體傳承與個人創造力的“綜合研究法”(synthetic approach)。
本期特刊,突顯了中國學者在民俗學研究領域的不斷探索與進取之心。這組文章不僅較為全面地展示了中國民俗學界最新的理論思考與研究成果;更為重要的是,讓中國民俗學在國際民俗學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種聲音,不僅打開一個了解領略中國當代民俗學學科成熟的窗口,也必定會進一步促進國內外學術界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我們相信,不管是對中國還是世界民俗學界來說,這都將是一個新的開始。
沈燕,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楊 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