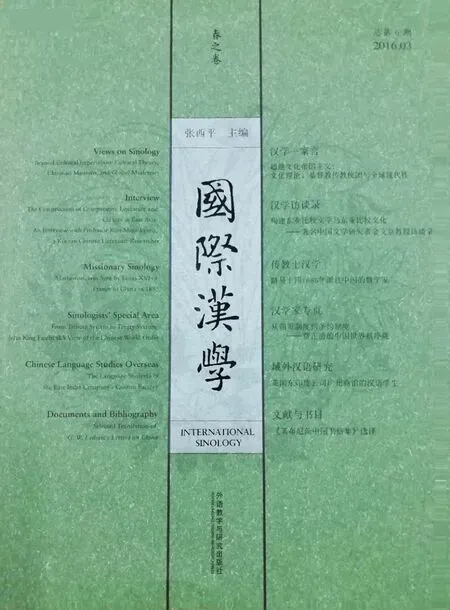魏池、魏智對(duì)北平漢學(xué)的貢獻(xiàn)
□ 易永誼
在20世紀(jì)前半葉,西方對(duì)中國(guó)的興趣,既轉(zhuǎn)化為在華西文出版業(yè)的商業(yè)契機(jī),使?jié)h學(xué)書(shū)籍成為面向西方市場(chǎng)的國(guó)際化產(chǎn)品,又催生西方人研究中國(guó)的學(xué)術(shù)動(dòng)力。法國(guó)商人魏池(Francis Vetch,1862—1944)①魏池,1862年6月27日出生于留尼汪島(Reunion)圣德尼(Saint Denis)省,1919年到北京,后到天津,又到香港,1944年6月29日死于越南胡志明市。共有六個(gè)孩子,魏智為其幼子,出生于法國(guó)伊夫林省拉塞勒圣云(La Celle Saint-Cloud, Yvelines, France),1978年6月3日逝世于中國(guó)香港,享年79歲。本文中關(guān)于VETCH家族的材料,均參考:http://www.geneanet.org.早年從事販賣(mài)福州苦力,再次返華后成為京津兩地的書(shū)商。他創(chuàng)辦了銷(xiāo)售兼出版的法文圖書(shū)館,經(jīng)其子魏智(Henri Georges Archibald Vetch, 1898—1978)的發(fā)展,成為故都北京當(dāng)時(shí)西方人文化圈子的中心。魏智熱衷于搜集與出售中國(guó)古籍善本,代理銷(xiāo)售世界各地的出版物,更重要的是出版了許多漢學(xué)研究的西文書(shū)籍,成為遠(yuǎn)東地區(qū)最負(fù)盛名的書(shū)商。本文援引美國(guó)漢學(xué)家芮沃壽(Arthur Frederick Wright, 1913—1976)②Arthur F.Wright, “Sinology in Peiping 1941—1945,”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 3/4 (1947): 315-372.于 1947年的提法“北平漢學(xué)”(Sinology in Peiping),以此涵蓋與魏池父子出版相關(guān)聯(lián)的學(xué)者、研究機(jī)構(gòu)及其漢學(xué)研究,勾勒20世紀(jì)前40年間以北平為中心、包含天津的漢學(xué)研究概貌。這種前后相承的漢學(xué)出版,將那些中外學(xué)者的研究納入北平漢學(xué)的歷史場(chǎng)域。同時(shí),他們的漢學(xué)興趣借助印刷資本主義的力量,直接推動(dòng)北平漢學(xué)的國(guó)際性傳播。
一、從苦力貿(mào)易到法文圖書(shū)館(La Librairie Fran?aise)
北平法文圖書(shū)館的漢學(xué)出版事業(yè),肇始于曾想販賣(mài)華工發(fā)財(cái)?shù)姆▏?guó)商人魏池之手。魏池具有殖民時(shí)代的典型特征,一心做著發(fā)財(cái)夢(mèng)。為拓展家族的茶葉種植業(yè),他不但使用留尼汪島上原有華工,而且從茶葉產(chǎn)地福建輸入華工。③Keith Stevens, “Henri Vetch(1898—1978):Soldier, Bookseller and Publisher,”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6 (2006): 105.1899年2月,生意失敗的魏池受兩位法國(guó)商人委托到中國(guó)福州進(jìn)口茶葉,并受聘于法國(guó)駐福州領(lǐng)事高樂(lè)待(Paul Claudel,1868—1955)④高樂(lè)待(Paul Claudel,1868—1955),現(xiàn)譯克羅代爾,法國(guó)詩(shī)人、戲劇家、外交家,1895年來(lái)華,于光緒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4月)始任法國(guó)駐福州領(lǐng)事,1905年離開(kāi)福州,轉(zhuǎn)任天津領(lǐng)事至1909年,改漢名高樂(lè)旦。繼任者福理業(yè)(Leonce Flayelle)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到任福州領(lǐng)事。參見(jiàn)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huì)編:《福州市志》(第6冊(cè)),表6-15-5,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開(kāi)設(shè)“喇伯順洋行”(H.C.R)招募華工前往印度洋和馬達(dá)加斯加的法屬殖民地。①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huì)編:《福州市志》(第8冊(cè)),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第233—235頁(yè)。在清代外務(wù)部與地方官員的電函匯總中,法國(guó)部分就有魏池販賣(mài)苦力的檔案史料。魏池除完成法國(guó)政府的任務(wù)外,還鋌而走險(xiǎn)攬私活。1906年2月,魏池因違規(guī)招募前往舊金山的華工,未獲批準(zhǔn)。②陳雅鈴、呂芳上編:《清季華工出國(guó)史料1863—1910》,臺(tái)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第523—538頁(yè)。1907年,中國(guó)銀行及錢(qián)鋪凍結(jié)魏池的招工錢(qián)款。③《止付魏池招工存款(福州)》,《申報(bào)》,1907年5月4日。到1908年,魏池原違規(guī)招募到墨西哥的華工五百二十余人,僅存百余人。④《清季華工出國(guó)史料1863—1910》,第545頁(yè)。魏池販賣(mài)華工的不人道作為,遭到清政府與民眾的譴責(zé),終因發(fā)財(cái)夢(mèng)碎而返回歐洲。
魏池的第四個(gè)兒子魏智于1900年至1907年曾隨其父母到福州。1916年,魏智從英屬塞舌爾群島(Seychelles)回到法國(guó)馬賽,并遇見(jiàn)他父親。由于魏池不懂英語(yǔ),魏智一度成為旅行推銷(xiāo)員父親的助手兼秘書(shū)。⑤Stevens, op.cit., p.117, 120, 123.1917年,魏智在法國(guó)楓丹白露炮兵技術(shù)學(xué)校接受軍官培訓(xùn),翌年以陸軍中尉軍銜被派往前線(xiàn),并因指揮得當(dāng)而被授予十字軍功勛章。1920年6月,魏智在波蘭華沙擔(dān)任教官期間被遣散退伍。⑥Ibid., pp.123-125.此后,魏智來(lái)到北京,追隨已在1919年重返中國(guó)的魏池。初抵北京,魏池供職于法國(guó)遣使會(huì)北堂印書(shū)館。⑦北堂印書(shū)館有多種稱(chēng)謂:西什庫(kù)天主堂印字館(Extyp Lazaristarum, Pekini)、遣使會(huì)印字館(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Pékin)、北堂印字館 (Pei T’ang Press, Presses du Pé-t’ang)等。該館為整個(gè)北京地區(qū)首家近代意義上的印刷機(jī)構(gòu)。⑧范慕韓:《中國(guó)印刷近代史初稿》,北京:印刷工業(yè)出版社,1995年,第97頁(yè)。魏池本為商人,在該處學(xué)到技術(shù),掌握出版運(yùn)作后,就另創(chuàng)自己的法文圖書(shū)館(La Librairie Fran?aise)。⑨黃光域編:《近代中國(guó)專(zhuān)名翻譯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3頁(yè)。“La Librairie Fran?aise法文圖書(shū)館”,La Librairie Fran?aise原意為法文書(shū)店,“法文圖書(shū)館”為實(shí)際所用特定的中文名。魏智曾高度評(píng)價(jià)他父親在法文圖書(shū)館的表現(xiàn),認(rèn)為他是一個(gè)出色的組織者和經(jīng)營(yíng)者。⑩Stevens, op.cit.,p.126.
北堂印書(shū)館的印刷技術(shù)與漢學(xué)興趣,影響了此后魏池的法文圖書(shū)館。魏池的法文書(shū)店取名La Librairie Fran?aise與北堂印字館頗有淵源。北堂印字館在1912年出版里昂·亨利(Léon Henry)的《庚子北堂圍困記事》,?Léon Henry, Le Siège du Pé-t'ang, dans Pékin en 1900.Le Commandant Paul Henry et ses trente marins.Pékin: La Librairie Fran?aise du Pé-t'ang, 1912.In-8°, 416 pp.注明該書(shū)寄售處為“北京北堂法文書(shū)店”(En Vente, La Librairie Fran?aise du Pé-tang, Pékin)。自 1920 年起,魏池以“Pékin,La Librairie Fran?aise”為出版商名稱(chēng),在五年間共出書(shū)11種(法文2種,英文9種)。最初的出版物是魏池所著法文詩(shī)集《致無(wú)名戰(zhàn)士》(Au Soldat Inconnu,1920),?Francis Vetch, Au Soldat Inconnu.Pékin: La Librairie Fran?aise, 1920.In-8, broché à la chinoise, couverture illustrée.7 pp.中國(guó)風(fēng)格裝訂的平裝書(shū),封面標(biāo)識(shí)為播種女神(La Semeuse),意為法蘭西守護(hù)神瑪麗安妮(Marianne)播撒種子。序言稱(chēng)該詩(shī)集為1919年魏池所著一首愛(ài)國(guó)詩(shī)的節(jié)錄,即節(jié)錄自魏池在北堂印字館(Pékin Presses du Pét'ang)出版的三卷本法文詩(shī)集《播種女神》(La semeuse,I.Le petit sommali, II.Blondel, III.Blondel console la Raison, 1919)。?Francis Vetch,La Semeuse.Published by Pékin Presses du Pé-t’ang, 1919.Trois volumes in-4° brochés, 300 x 180 mm.30,XII-86 et 54 pp.Pékin: Librairie Fran?aise, 1921.In-8° 250 x.(3 v.:ill.;30 cm)1921年魏池出版詩(shī)集《播種女神》第4卷(IV.La France)。同年還出版《中華鐵路最新袖珍行車(chē)時(shí)刻表》(Chinese Railways Time Table),底頁(yè)有漢字“民國(guó)十年七月初版,定價(jià)大洋貳角正,北京法文售書(shū)處印行”。?Chinese Railways Time Table(July, 1921).Pékin: La Librairie Fran?aise Publishers, 1921.65 pp.(見(jiàn)圖1)可見(jiàn),魏池先以“北京法文售書(shū)處”取名,后用“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

圖1
1923年,法文圖書(shū)館京、津兩館(Peking& Tientsin: La Librairie Fran?aise)合出三本英文書(shū),有英國(guó)人郝?lián)u德(G.E.Hubbard, 1885—1951)的《西山寺廟》(The Temples of the Western Hills),科馬克夫人 (Mrs.J.C.Cormack)的《生、婚、喪》(Chinese Birthday, Wedding, Funeral, and other customs),法國(guó)人馬塞爾(Bouleau Marcel)的《遠(yuǎn)東交易所實(shí)用指南》(Practical Guide to Far Eastern Exchanges)。此外,兩地法文圖書(shū)館各有出版物。北京館同年有辜鴻銘的《尊王篇》(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法國(guó)人寶道(Georges Padoux, 1867—1924)的《中國(guó)金融重建與現(xiàn)有債務(wù)延續(xù)》(The 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a’s Present Indebtedness),美國(guó)人貝光臨(John Earl Baker)的《中國(guó)鐵路債券的投資價(jià)值》(Investment Values of Chinese Railway Bonds)。以上6種書(shū)目顯示,此時(shí)北京館已把出版興趣放在英文書(shū)籍上。除辜鴻銘外,郝?lián)u德、寶道和貝光臨為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政府外籍專(zhuān)家;其內(nèi)容均涉及中國(guó)的研究,例如北京城、中國(guó)文化、經(jīng)濟(jì)以及民俗考察。
根據(jù)史料記載,魏池在1926年為天津法文圖書(shū)館(Tientsin, La Librairie Fran?aise)(見(jiàn)圖2)業(yè)主(proprietor)。①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字林報(bào)行名簿).Shanghai: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Office of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Herald, Limited.1926.p.729.“Tientsin 71 Rue de France Tel Add : Vetch,La Librairie Fran?aise (Publishers, Bookseller,and Stationers) :Vetch, F., prop; Pelagoti, J., Signs P.P.; Bebrof, Miss A.; Poska, M.; Lewandowski, L., tech, dept.; Toug, T.F.,comp; Lindsay, Miss H.; Kazarov, Miss H.; Mazurckievich, M.”該機(jī)構(gòu)兼具出版商、書(shū)商和文具商,位于天津法租界大法國(guó)路71號(hào),并以業(yè)主魏池登記專(zhuān)屬電話(huà)。當(dāng)時(shí)員工有8人,從名字看多為白俄職員。除合出3本英文書(shū)外,天津館在1923年出版德國(guó)人哈克馬克(Adlof Hackmack)著,阿諾德小姐(Miss L.Arnold)翻譯的英文版《中國(guó)地毯》(Chinese Carpets and Rugs),②Adolf Hackmack, trans.Miss L.Arnold, Chinese Carpets and Rugs.48 pp.德文版:Der Chinesische Teppich, von Adolf Hackmack.Hamburg: L.Friederichsen, 1921.法國(guó)耶穌會(huì)士黎桑(Emile Licent,1876—1952,號(hào)志華)的法文《黃河流域十年實(shí)地調(diào)查記》[Hoang ho-Pai ho : Comptes rendus de dix années (1914—1923)],及中文《黃河流域十年實(shí)地調(diào)查記目錄》,英文傳記《周自齊學(xué)士》(H.E.Hseuhsi Chih-chi Chow)。1924年,北京館僅出1種書(shū)籍,天津館有4種書(shū)籍,可知魏池的出版重心在天津。

圖2 天津大法國(guó)路69-71號(hào)法文圖書(shū)館
1925年,北京館并無(wú)出版物,而天津館則出英文書(shū)6種,包括法國(guó)在華東方匯理銀行職員拜林(J.R.Baylin) 的《中國(guó)對(duì)外貸款債務(wù)》(Foreign Loan Obligations of China), 艾倫 (Allen B.G.)的《中國(guó)劇院手冊(cè)》(Chinese Theatres Handbook),蘇聯(lián)教授佩戈蒙特(Michail J.Pergament, 1866—1932)的《中國(guó)司法裁判問(wèn)題》(Questions Regarding Jurisdiction in China),克拉米息夫(V.Karamyshev)的《中國(guó)西北部之經(jīng)濟(jì)狀況》(Mongolia and Western Chin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與《外蒙古喀爾喀的經(jīng)濟(jì)地圖》(Outer Mongolia-Khalkha: Economic Map),寶道的《中國(guó)無(wú)抵押債務(wù)的合并與中國(guó)綜合預(yù)算制定》(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a’s Unsecured Indebtedness and 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Consolidated Budget)。1926年天津館僅出法籍顧問(wèn)愛(ài)斯嘉拉(Jean Escarra, 1885—1955)的英文版《中國(guó)法與比較法哲學(xué)》(Chinese Law and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1種。總之,天津法文圖書(shū)館的出版物,主要關(guān)注在華學(xué)者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濟(jì)、法律與文化民俗的研究。
另有一家可能是魏池接手的書(shū)店,法文名為 Société Fran?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 該店原為三個(gè)法國(guó)耶穌會(huì)士(Charvet,Bonnafous,F(xiàn)ermus)于1926年所辦,不久因負(fù)債被魏池接管。①Stevens, op.cit., p.126.所以,在1927年天津的法文圖書(shū)館地址就由原來(lái)的71 Rue de France拓展為 69-71 Rue de France,職員及經(jīng)理共有7人,有兩個(gè)老職員,書(shū)店法文名稱(chēng)也換為 Société Fran?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 (Ancienne Librairie Fran?aise)(即以前的“法文圖書(shū)館”)。②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1927, p.729.又見(jiàn)《近代中國(guó)專(zhuān)名翻譯詞典》,第 334 頁(yè) :“Société Fran?aise de Librairie et d’Edition 天津法文圖書(shū)館”。在1926年至1929年間,該機(jī)構(gòu)共出版7種書(shū)籍(英文3種、法文4種),其中1926年(3種)有俄國(guó)人薩利姆·貝克(Salim Beck)的英譯《蒙古馬》(The Mongolian Horse),法文《袖珍簡(jiǎn)明法規(guī)詞典》(Code-dictionnaire des familles dit code AAbla),柯姑娘 (Katharine Augusta Carl,1865—1938)的英文《慈禧寫(xiě)照記》(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1927年(3種)有法國(guó)人盧梭旺(E.Lossouarn)的英文版《眼病的檢查與治療》(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of the Eyes within the Reach of Everyone)及其法文版,法國(guó)人邁達(dá)氏(Jules Henri Médard)的《法漢專(zhuān)門(mén)詞典》(Vocabulaire fran?ais-chinois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1929年,有法國(guó)耶穌會(huì)士田執(zhí)中(Fran?ois Théry )的《中國(guó)商會(huì)》(Les Sociétés de commerce en Chine)。總體觀之,在 Société Fran?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 階段,該書(shū)店出版更側(cè)重于法文,除了天津法租界的人脈資源外,可能與接收法國(guó)耶穌會(huì)士所辦書(shū)店有關(guān)。
此后,魏池疏離于書(shū)店生意,而魏智對(duì)其不務(wù)正業(yè)尤感厭煩,導(dǎo)致1929年父子決裂。③Stevens, op.cit., p.127.史料也證實(shí):1927年天津法文圖書(shū)館經(jīng)理由拉諾伊(F.Lanoe)更換為原來(lái)三個(gè)耶穌會(huì)士創(chuàng)辦人之一費(fèi)默思(R.Fermus),其他人員照舊。④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1927, p.680.由此,魏池徹底退出書(shū)店生意,也宣告法文圖書(shū)館的終結(jié)。魏池既無(wú)印刷廠(chǎng),也無(wú)穩(wěn)定的合作印刷機(jī)構(gòu),缺乏鮮明的出版特色。例如《生、婚、喪》(1923)由商務(wù)印書(shū)館北京印刷分廠(chǎng)印制,《黃河流域十年實(shí)地調(diào)查記目錄》(1923)由北洋印字館印制。魏智在結(jié)婚之后切斷與其父親的所有聯(lián)系。1932年魏池在天津宣布破產(chǎn),后離開(kāi)北京前往香港。根據(jù)書(shū)目,魏池在澳門(mén)出版《神與當(dāng)代社會(huì)》(Dieu et la societe contemporaine, 1937)⑤Francis Vetch, Dieu et la societe contemporaine.Macao: Editeur Oriente Comercial, 1937.[42] folded leaves : ill.; 24 cm.84 pp.(現(xiàn)藏澳大利亞國(guó)家圖書(shū)館),在香港出版《法西斯主義:文明的挑戰(zhàn)》(Le Facisme, Un défi a la civilisation, 1938)⑥Francis Vetch, Le Facisme [sic].Un défi a la civilisation.Deuxième édition.[With a portrait.] ff.16.Hongkong, 1938.(現(xiàn)藏大英圖書(shū)館)。魏池在1944年6月病逝于越南。⑦Stevens, op.cit., pp.127-128.或許可以說(shuō),魏池雖然到處碰壁,撰寫(xiě)與出版書(shū)籍仍是他人生末期的重要軌跡。
二、魏智與英商中國(guó)圖書(shū)公司(The China Booksellers)
在1920年至1924年間,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出過(guò)數(shù)種書(shū)籍,此后便沒(méi)有出版信息了。那么,魏池的法文圖書(shū)館究竟何處去了?1925年2月1日上海英文《大陸報(bào)》(The China Press)圖書(shū)版有對(duì)魏池的兒子魏智的專(zhuān)訪(fǎng)。該報(bào)道稱(chēng):“目前,在中國(guó)北方有一個(gè)事件想必會(huì)引起熱愛(ài)讀書(shū)人們的興趣,那就是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和萬(wàn)國(guó)圖書(shū)公司(The China Book Exchange)宣布合并,新公司被稱(chēng)為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The China Booksellers,Limited)。①《近代中國(guó)專(zhuān)名翻譯詞典》,第657頁(yè):“China Book Exchange萬(wàn)國(guó)圖書(shū)公司,China Booksellers, Ld.英商圖書(shū)有限公司;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該公司將以15萬(wàn)美元為資本開(kāi)始運(yùn)營(yíng),并由北京飯店著名書(shū)商亨利·魏智進(jìn)行管理與個(gè)人監(jiān)督。如果企業(yè)運(yùn)作成功,它將會(huì)拓展到涵蓋法文圖書(shū)館在天津和沈陽(yáng)的零售業(yè)務(wù),以及現(xiàn)位于天津的出版業(yè)務(wù)公司。”②The China Press, Shanghai: Feb 1, 1925.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不僅整合了現(xiàn)有的書(shū)業(yè)股份資本,而且給購(gòu)書(shū)者更為廣闊的選擇,特別是在英美版本方面。同時(shí),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的魏智和萬(wàn)國(guó)圖書(shū)公司的瑞金(Leo Samuel Regine)③《近代中國(guó)專(zhuān)名翻譯詞典》,第631頁(yè)。,被譽(yù)為遠(yuǎn)東最負(fù)盛名的兩位書(shū)商。魏智認(rèn)為新公司擴(kuò)大股份資本,可引進(jìn)世界最領(lǐng)先出版商的最優(yōu)秀出版物,例如紐約、波士頓、倫敦、柏林和巴黎。此次整合涵蓋北京地區(qū)三家書(shū)店:位于使館街的萬(wàn)國(guó)圖書(shū)公司、六國(guó)飯店的書(shū)店和位于北京飯店的法文圖書(shū)館。這三家書(shū)店都在原有位置繼續(xù)營(yíng)業(yè)。
另?yè)?jù)別的史料,④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1926, p.859.也可知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是由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與萬(wàn)國(guó)圖書(shū)公司合并而成,由司馬武德(Harold St.Clair Smallwood)⑤《近代中國(guó)專(zhuān)名翻譯詞典》,第657頁(yè):“Smallwood, Harold St.Clair (1883- ) 司馬武德,英國(guó)商人,退休軍官,1919年來(lái)華。”為首的三位英國(guó)商人任董事出資組建,魏智任經(jīng)理,其未來(lái)妻子伊蓮娜(Elena Evreeva, 1900—1984)任助理。公司總部位于東交民巷使館區(qū)馬可波羅路(今臺(tái)基廠(chǎng)大街)5號(hào),另有四個(gè)分支機(jī)構(gòu)分別在北京飯店、六國(guó)飯店、北戴河分店、協(xié)和胡同8號(hào)。1928年,三大股東之一福來(lái)薩(David Fraiser)被阿斯普蘭博士(Dr.N.H.G.Aspland)替代,分支機(jī)構(gòu)只剩下北京飯店、六國(guó)飯店,總經(jīng)理和秘書(shū)設(shè)在司馬武德洋行(H.S.T.Clair Smallwood Co.)。⑥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1928, p.609.同年8月,魏智買(mǎi)下公司股份500股中的400股,成為大股東,最后成為業(yè)主。⑦Stevens, op.cit., pp.126-127.此次合并未涉及法文圖書(shū)館在天津和沈陽(yáng)的業(yè)務(wù),魏池則經(jīng)營(yíng)天津法文圖書(shū)館。但是,魏智不再是魏池的協(xié)助者,而是執(zhí)掌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的經(jīng)理,并繼續(xù)拓展其漢學(xué)趣味的出版事業(yè)。
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的漢學(xué)出版,首先體現(xiàn)在4種北京研究的英文書(shū)籍:法國(guó)外交官馬特爾(D.de Martel)與霍耶(Léon de Hoyer)合著的《北京剪影》(Silhouettes of Peking,1926),生于寧波的英國(guó)人燕瑞博(Robert W.Swallow, 1878—1938)的《北京生活側(cè)影》(Sidelights on Peking life,1927),凌啟鴻的《北京人的社會(huì)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n Peking), 1928],佩戈蒙特的《北京使館界法理性質(zhì)考》(The Diplomatic Quarter in Peking: Its Juristic Nature,1927)。至此,魏池、魏智關(guān)于北京研究的漢學(xué)出版粗具規(guī)模。該公司也對(duì)中國(guó)歷史民俗與思想文化感興趣,如出版科馬克夫人《生、婚、喪》第3版。其次,在華裔學(xué)者的漢學(xué)研究方面,魏智不但出版凌啟鴻的英文著作,在1923年再版辜鴻銘的《尊王篇》(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而且還出版梁?jiǎn)⒊断惹卣嗡枷胧贰返姆ㄗg本,何杰才的1921年哥倫比亞大學(xué)博士論文《中國(guó)門(mén)戶(hù)開(kāi)放政策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in China)。此外,該時(shí)期魏智還出版美國(guó)駐華武官康士丹(Samuel V.Constant, 1894—?)的《中國(guó)軍事英漢雙解辭典》(Chinese Military Terms: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克萊瑟 (Alice L.Cleather)與巴茲爾(W.Crump Basil)的《佛教:生命的科學(xué)》(Buddhism, the Science of Life),資助出版斯特朗(Hilda A.Strong)的《中國(guó)美術(shù)》(A Sketch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令其享譽(yù)英語(yǔ)世界。縱觀發(fā)展脈絡(luò),法文圖書(shū)館北京與天津兩館,分別為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和天津法文圖書(shū)館所延續(xù)。
綜合四個(gè)單位的出版物,其總數(shù)(含再版)可達(dá)38種,其中英文30種,法文7種,中文1種。(見(jiàn)表1)①資料來(lái)源為WorldCat.org(在線(xiàn)編目聯(lián)合目錄,世界上最龐大的圖書(shū)館目錄)。

表1
在法文書(shū)目中,2種為魏池自己的作品,4種為魏池在天津法文圖書(shū)館時(shí)所出。因魏池不諳英文、魏智精通英文,可知魏智一直發(fā)揮主導(dǎo)作用。另外,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在魏智出版事業(yè)中起前后銜接的作用,可從前后時(shí)期的書(shū)目中得到印證:承前者,例如科馬克夫人的《生、婚、喪》1923年由京津兩館合出,1927年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再版;佩戈蒙特1925年在天津館出版《中國(guó)司法裁判問(wèn)題》,1927年又在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出版《北京使館界法理性質(zhì)考》;啟后者,例如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出版燕瑞博的《北京生活側(cè)影》(1927年)、凌啟鴻的《北京人的社會(huì)生活》(1928年),其后1930年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The French Bookstore)再版燕瑞博的《北京生活側(cè)影》,出版凌啟鴻的《中國(guó)之政黨》(Political Parties in China)。此時(shí)期研究中國(guó)的書(shū)籍?dāng)?shù)量最多的當(dāng)數(shù)政治經(jīng)濟(jì)法律類(lèi),其作者如外交官(邁達(dá)、施爾滿(mǎn)、馬特爾、康士丹)、銀行家(郝?lián)u德、布洛·馬塞爾、拜林、霍耶)、在華政府顧問(wèn)(寶道、貝光臨、愛(ài)斯嘉拉)、在華學(xué)者(黎桑、佩戈蒙特、克拉米息夫、盧梭旺、燕瑞博)、來(lái)華商人(阿爾道夫·哈克馬克)。透過(guò)主題與作者分布,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北平漢學(xué)研究者多為業(yè)余漢學(xué)家,其興趣多集中在中國(guó)的政治、經(jīng)濟(jì)、法律、金融等。其間,魏智協(xié)助其父管理京津兩館的業(yè)務(wù),后任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的經(jīng)理。他不但從中積累出版事業(yè)的豐富經(jīng)驗(yàn),而且在出版上表現(xiàn)出對(duì)漢學(xué)研究的興趣。
三、魏智與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The French Bookstore)
魏智的漢學(xué)出版事業(yè)并非一帆風(fēng)順,同樣也有一個(gè)調(diào)適與發(fā)展的過(guò)程。1930年,天津法文圖書(shū)館的負(fù)責(zé)人為魏智,該店名號(hào)既保留魏池時(shí)期的法文 Société Fran?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又始增英文French Bookstore為副招牌;業(yè)務(wù)由“出版商、書(shū)籍銷(xiāo)售商和文具商”,增加了“東方文物、地圖制作者、印刷工、裝訂工、訂閱、代理商、報(bào)紙和雜志零售商”。②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1930, p.780.同年,英商中國(guó)圖書(shū)有限公司的地址注冊(cè)為天津英租界維多利亞路181號(hào),其業(yè)務(wù)為書(shū)籍和文具的批發(fā)與零售,工作人員僅4人,由俄籍猶太人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 1894—1965)任經(jīng)理。①I(mǎi)bid., p.744.此前,阿甫夏洛穆夫于1921年到達(dá)北京,在富有傳奇色彩的莫理循大街,作為一名圖書(shū)經(jīng)銷(xiāo)商,為著名的法國(guó)書(shū)商魏智工作。②Matthias Messmer, Jewish Wayfarers in Modern China: Tragedy and Splendor.Lexington Books, 2012, p.21.
1931年,魏智同時(shí)擁有北京和天津兩家法文圖書(shū)館,統(tǒng)一名稱(chēng)為 French Bookstore (Société Fran?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 既 開(kāi) 始 啟 用法文圖書(shū)館的英文招牌,又保留法文名稱(chēng),以表示對(duì)魏池時(shí)期的延續(xù);其業(yè)務(wù)為“英文、法文書(shū)籍的書(shū)商與出版商”。北京飯店的北京館成為總部,天津館為分部,并搬回原址(71 Rue de France)。③China Hong List(字林報(bào)行名簿),1931, p.729,770.1932年,魏智仍以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為總部,六國(guó)飯店的書(shū)店成為他的分部。④Ibid., 1932, p.783.在天津的法文圖書(shū)館則由合伙人帕拉迪西斯(J.E.Paradiissis)負(fù)責(zé),英文名稱(chēng)始改為T(mén)he Oriental Bookstore(Librairie Fran?aise),附法文名以體現(xiàn)二者的聯(lián)系。⑤Ibid., p.843.1934年天津法文圖書(shū)館中文名改為“東方圖書(shū)館”,英文為Oriental Bookstore (Librairie Fran?aise),仍附注法文店名,未見(jiàn)書(shū)籍出版,人員由3人變成7人,帕拉迪西斯仍為合伙人兼經(jīng)理。⑥Ibid., 1934, p.705.1936年,魏智除了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總經(jīng)理的身份外,第一次以出版人的身份單獨(dú)出現(xiàn),并特別注明是北平輔仁大學(xué)《華裔學(xué)志》(MonumentaSerica)的出版商。⑦Ibid., 1936, p.689.該年,他放棄天津“東方圖書(shū)館”的股份,讓帕拉迪西斯獨(dú)資所有。⑧Ibid., p.726.
自1939年至1941年,“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French Bookstore(Société Fran?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⑨Ibid., 1939, p.654; 1940, p.701; 1941,p.768.以及出版商“魏智”仍在《字林報(bào)行名簿》出現(xiàn)。⑩Ibid., 1939, p.663; 1940, p.710; 1941,p.776.但是“東方圖書(shū)館”[Oriental Bookstore (Librairie Fran?aise)]自1939年 起, 從天津法租界遷到英租界。?Ibid., 1939, p.703; 1941, p.819.魏智在1939年12月10日將名下400股轉(zhuǎn)讓給他的妻子,同時(shí)從北京飯店法人經(jīng)理勞斯丹(Jean-Baptiste Roustan)購(gòu)得38股,以保留自己股東的身份。?Keith Stevens, op.cit., p.129。此項(xiàng)變動(dòng)是因?yàn)槲褐亲鳛榉▏?guó)前軍官應(yīng)召往法屬殖民地越南服役,直到1941年回北平。1941年2月5日,《北華捷報(bào)》報(bào)道:“北平法文圖書(shū)館的亨利·魏智先生,已經(jīng)從印度支那回到上海,在他回到北方之前有望在此地逗留一周。”?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Feb.5 (1941): 216.可知,1939—1941年間的法文圖書(shū)館名義上是魏智在主持,實(shí)際由其妻子代管。因此,1951年“炮轟天安門(mén)”案件的判決書(shū),誤稱(chēng)魏智1941年才到北京任法文圖書(shū)館的經(jīng)理。?“Smashed in Peking,”China Monthly Review (1950-1953), Sep.1 (1951):131.以至于在1950—1953年間法文圖書(shū)館中文部職員,也誤傳魏智1941年才任法文圖書(shū)館經(jīng)理。?于炳熙:《關(guān)于法文圖書(shū)館的回憶》,《文史資料選編》第13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94頁(yè)。
20世紀(jì)30年代是魏智漢學(xué)出版事業(yè)的鼎盛時(shí)期,共出書(shū)90種,此后的40年代走向衰落。具體出版情況統(tǒng)計(jì)如下(見(jiàn)表2)?資料來(lái)源為WorldCat.org(在線(xiàn)編目聯(lián)合目錄)。:

表2
如上所計(jì),魏智在1930年至1951年間共出版127種書(shū)籍(含再版),其中英語(yǔ)93種,德語(yǔ)21種,法語(yǔ)13種,內(nèi)容涵蓋語(yǔ)言文學(xué)、藝術(shù)研究、歷史地理、宗教哲學(xué)、社會(huì)民俗、博物科學(xué)、法律、醫(yī)學(xué)等,其中以語(yǔ)言文學(xué)、藝術(shù)研究及歷史地理研究為領(lǐng)先。魏智大量出版當(dāng)時(shí)來(lái)華漢學(xué)研究者的單行本,不少作者及其作品由此聞名于世。從相近內(nèi)容來(lái)看,其中比較突出者大約可歸為五大類(lèi)。
其一語(yǔ)言研究類(lèi):伊博恩(Bernard E.Read)的《醫(yī)院對(duì)話(huà)》(Hospital Dialogue, 1930),奧爾德里奇(Harry S.Aldrich)的《華語(yǔ)須知》(Practical Chinese, 1931/1934/1938.v.1, v.2), 士 嘉 堡(William Scarborough)的《諺語(yǔ)叢話(huà)》(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1932), 梅 輝 立(William F.Mayers)的《中國(guó)辭匯》(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 1932),科瓦列夫斯基(O.M.Kovalevskij)的《蒙俄法詞典》(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ais,1933),胡恩敦 (James Vivian)、裘德瑞(Raymond Varley)合編的《漢英軍事辭典》(Chinese and English Modern Military Dictionary, 1934/1935),卜朗特(J.J.Brandt)的《摩登新聞叢編》(Modern Newspaper Chinese, 1935/1939/1947)、《 漢 文 進(jìn)階》(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 1936)、《華言拾級(jí)》(Introduction to Spoken Chinese, 1940),吳索福(Sergyei N.Usove)的《華語(yǔ)入門(mén)》(ACourse of Colloquial Chinese, 1937),雜哈勞(Ivan I.Zakharov)的《滿(mǎn)俄大辭典》(Complete Manchu-Russian dictionary, 1939), 戴 遂 良 (Léon Wieger)的《中國(guó)漢字》(Chinese Characters, 1940),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的《法文注釋中國(guó)古文大辭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1947)。以上語(yǔ)言類(lèi)書(shū)籍,多為已有作品的再版,例如《華語(yǔ)須知》和《摩登新聞叢編》再版三次,說(shuō)明魏智抓住了當(dāng)時(shí)來(lái)華外國(guó)人學(xué)習(xí)漢語(yǔ)的需求。
其二文學(xué)與藝術(shù)類(lèi):文學(xué)研究有亨利·哈特(Henry H.Hart)的漢詩(shī)英譯《中國(guó)集市》(A Chinese Market, 1931),吳可讀(A.L.Pollard)的《西洋小說(shuō)發(fā)達(dá)史略》(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1933),阿林敦(Lewis C.Arlington)的法文版《中國(guó)戲劇史》(Le théatre Chinois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nos jours, 1935),阿林敦、艾克敦(Harold Acton, 1904—1994)的《戲劇之精華》(Famous Chinese Plays, 1937),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中國(guó)文獻(xiàn)紀(jì)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939),德騰夫人(Helen W.Dutton)的《幽篁集》(Secrets Told in the Bamboo Grove, 1940)。藝術(shù)研究有:斯特朗的《中國(guó)美術(shù)》(A Sketch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1933),阿理嗣(J.A.Van Aalst)《 中 國(guó) 音 樂(lè) 》(Chinese Music, 1933/1939),樂(lè)維思(John H.Levis) 的《中國(guó)音樂(lè)之基礎(chǔ)》(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l Art, 1936),喜仁龍(Osvald Sirén, 1879—1966) 的《中國(guó)繪畫(huà)藝術(shù)》(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 1936),燕博瑞的《中國(guó)古鏡圖說(shuō)》(Ancient Chinese Bronze Mirrors, 1937),高羅佩(Robbert H.van Gulik, 1910—1967)英譯宋代米芾的《硯史》(Mi Fu on Ink-Stones, 1938)。
其三歷史研究類(lèi):凌啟鴻的《中國(guó)之政黨》(1930),卜德(Derk Boddek, 1909—2003)英譯馮友蘭的《中國(guó)哲學(xué)史》(1937),白蘭士敦(Archibald D.Brankston)的《明初官窯考》(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 1938),濮蘭德(John O.P.Bland,1863—1945)、白克好司 (Edmund T.Backhouse) 的《慈禧太后傳》(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1939),宓亨利(Harley F.Macnair) 的《中國(guó)賑災(zāi)紀(jì)實(shí)》(With the White Cross in China, 1939),愛(ài)斯嘉拉的《中國(guó)的過(guò)去和現(xiàn)在》(China Then and Now,1940), 衛(wèi) 德 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 的《中國(guó)歷史述要》(Chinas Geschichte, 1942)、《史群元國(guó)》(Gesellschaft und Staat in China, 1944)、《周易述要》(Die Wandlung; acht Vort?ge zum I-ging, 1944)。
其四北京研究類(lèi):燕瑞博的《北京生活側(cè)影》(1930),盧因森(William Lewisohn)的《北京的西山》(The Western Hills of Peking,1930),阿林敦、盧因森的《古都舊景》(In Search of Old Peking, 1935/1939),卜德的《燕京歲時(shí)記》(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 1936),陳鴻舜(Hung-shun Ch’en)與侯感恩 (George N.Kates)合著的《北京的恭王府及其王府花園》(Prince Kung’s Palace and Its Adjoining Garden in Peking,1940)。此前,魏池的法文圖書(shū)館與魏智主持的中國(guó)圖書(shū)公司,先后出過(guò)5本北京研究的英文書(shū)籍。這些研究北京的作品日后都成為享譽(yù)英語(yǔ)世界的漢學(xué)名作。此外,該系列還應(yīng)包括以天津法文圖書(shū)館之名出版的莫里斯·法布爾(Maurice Fabre)①法布爾,法國(guó)殖民地的步兵陸軍上尉,1936—1938年駐扎在北京。的《北京:宮殿、寺廟和周?chē)h(huán)境》(Pékin:ses palais, ses temples et ses environs,1937)。所以,較之其他出版物,北京研究的書(shū)籍是魏智的標(biāo)志性成就。
除單行本之外,魏智還出版《華裔學(xué)志》及其抽印本。20世紀(jì)30年代北京有許多來(lái)自西方各國(guó)的漢學(xué)家,逐漸形成以輔仁大學(xué)為中心的國(guó)際漢學(xué)研究圈。出于漢學(xué)研究國(guó)際化的需要,《華裔學(xué)志》定位為研究遠(yuǎn)東人民和文化的國(guó)際性刊物,從1935年創(chuàng)刊至1948年共出版13卷。此前,魏智出版過(guò)不少北平來(lái)華人士的漢學(xué)作品,成為這一國(guó)際漢學(xué)雜志的出版發(fā)行商后,負(fù)責(zé)該刊第1—10卷的出版發(fā)行。從《華裔學(xué)志》1935年的“編輯啟事”可知,投稿者可免費(fèi)獲贈(zèng)該稿抽印本最多25本。該刊抽印本情況具體如下:1935年10種,1936年5種,1937年5種,1938年8種,1939年7種,1940年6種,1941年2種:1942年3種,1943年5種,1945年1種,1946年2種,共計(jì)54種。即這一時(shí)期的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總共出書(shū)127種(含再版),就有54種源自《華裔學(xué)志》的抽印本。
成為《華裔學(xué)志》的出版發(fā)行商,使得魏智作為漢學(xué)出版商的世界性聲譽(yù)到達(dá)巔峰。自1936年開(kāi)始他以《華裔學(xué)志》出版商的身份出現(xiàn),并取古代中國(guó)“九頭鳥(niǎo)”圖案為出版標(biāo)識(shí),沿用至此后香港時(shí)期的魏李出版社(Hong Kong, Vetch and Lee) 。從出版軌跡看,1935年至1940年《華裔學(xué)志》抽印本占據(jù)每年出版書(shū)籍的半數(shù)左右,此后更是單行本書(shū)稿寥落,幾乎全部依賴(lài)抽印本的出版。可以說(shuō)《華裔學(xué)志》的優(yōu)質(zhì)書(shū)稿成為魏智此時(shí)漢學(xué)出版的重要來(lái)源,而抽印本出版也促進(jìn)了當(dāng)時(shí)北平漢學(xué)研究成果的世界性傳播。魏智的出版事業(yè)見(jiàn)證了北平漢學(xué)由業(yè)余漢學(xué)轉(zhuǎn)向?qū)I(yè)漢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也見(jiàn)證了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之后北平漢學(xué)的衰落。
四、魏智與來(lái)華漢學(xué)家的交游
魏池、魏智的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長(zhǎng)期設(shè)在北京飯店。該飯店是來(lái)華西方人的社交中心,他們包括教師、傳教士、醫(yī)生、護(hù)士、漢學(xué)家、商人、藝術(shù)家,還有使館人員和海軍陸戰(zhàn)隊(duì)。例如美國(guó)記者埃德加·斯諾(Adgar Snow,1905—1972)及夫人海倫(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第一次到北京即下榻該處,印象深刻:“飯店是外國(guó)人的社交中心,他們?cè)诜路矤栙悓m的鏡廳建造的舞廳里舉行舞會(huì)。”①海倫·斯諾著,華誼譯:《旅華歲月:海倫·斯諾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shí)出版社,1985年,第82頁(yè)。海倫還提到,飯店樓下就是有名的北京書(shū)店,書(shū)店的老板魏智發(fā)行和收集善本書(shū),同時(shí)還收購(gòu)和出售當(dāng)?shù)鼐用竦牟貢?shū)。“在那里,你可以遇到每一個(gè)真正對(duì)中國(guó)感興趣的人,在交談中消磨整個(gè)下午。”②同上,第71、72頁(yè)。美國(guó)漢學(xué)家費(fèi)正清(John K.Fairbank,1907—1991)與費(fèi)慰梅(Wilma.Canon Fairbank,1909—2002)夫婦,在20世紀(jì)30年代曾住在北京飯店,“我們來(lái)來(lái)去去,相互訪(fǎng)問(wèn),在北京飯店的屋頂花園跳舞,這是北京城內(nèi)上流社會(huì)夜晚游樂(lè)的場(chǎng)所。”③費(fèi)正清著,陸惠勤等譯:《費(fèi)正清對(duì)華回憶錄》,上海:上海知識(shí)出版社,1991年,第140頁(yè)。由此可見(jiàn),魏池父子將書(shū)店設(shè)在北京飯店,處于來(lái)華西方人的交際中心,獲得了各種中西文化資訊與人脈資源,從而為法文圖書(shū)館世界性聲譽(yù)的傳播奠定基礎(chǔ)。
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首先是個(gè)書(shū)店,一方面從歐美采購(gòu)?fù)馕膱D書(shū),賣(mài)給中國(guó)文人或機(jī)構(gòu);另一方面收購(gòu)中文古籍善本,主要是賣(mài)給來(lái)華的西方人。例如1935年北平學(xué)聯(lián)的學(xué)生們,就是從法文圖書(shū)館買(mǎi)到英文雜志《共產(chǎn)國(guó)際通訊》《共產(chǎn)國(guó)際半月刊》以及巴黎出版的《救國(guó)時(shí)報(bào)》。④楊樹(shù)先等訪(fǎng)問(wèn)整理:《姚依林談“一二·九”運(yùn)動(dòng)》,《炎黃春秋》2009年第8期,第64頁(yè)。魏智作為西方人公開(kāi)出售當(dāng)時(shí)政府的違禁書(shū)刊,無(wú)意中為共產(chǎn)國(guó)際資訊的傳播提供幫助。北京飯店是中外人士交匯之處,也吸引了胡適等歸國(guó)留學(xué)生到此處法文圖書(shū)館淘書(shū)。⑤胡適著:《胡適日記全編3》(1919—192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2—663頁(y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人對(duì)魏智法文圖書(shū)館落筆最多的,恐怕是時(shí)任清華大學(xué)教授吳宓。⑥吳宓著,吳學(xué)昭整理:《吳宓日記:1925—1927》,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1998年,第147—148頁(yè)。他經(jīng)常出入該飯店會(huì)客訪(fǎng)友,茶余飯后也要光顧書(shū)店。時(shí)常光顧西文書(shū)店,了解與購(gòu)買(mǎi)國(guó)外新書(shū),成為吳宓等留學(xué)歸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獲得西方學(xué)術(shù)資訊的重要渠道。
縱觀法文圖書(shū)館的出版書(shū)目,魏池、魏智交游的來(lái)華西方人,首先是法國(guó)在華人士,例如北洋政府顧問(wèn)寶道、愛(ài)斯嘉拉,外交官奚居赫,天津北疆博物院的黎桑、德日進(jìn)、羅學(xué)賓,以及北平中法漢學(xué)研究所;其次為英國(guó)在華人士,包括燕瑞博、盧因森、艾克敦、白蘭士敦、樂(lè)維斯、吳可讀;美國(guó)外交官康士丹、胡恩敦、裘德瑞,在華美國(guó)學(xué)者侯感恩、宓亨利、卜德、阿林敦;俄國(guó)人卜郎特(J.J.Brandt,1869—1944)、吳索福、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l-Hostein,1877—1937);荷蘭人高羅佩(Rob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范可法(Marc Hendrikus Van Der Valk,1908—1978); 瑞 典 人 喜 仁 龍(Osvald Sirén,1879—1966)。這些歐洲人或長(zhǎng)期在華工作,或短暫訪(fǎng)學(xué)游歷,但是他們的身份或?yàn)橥饨还佟鹘淌俊⒂浾摺⑼饧蛦T,或?yàn)樵谌A西方學(xué)校的教師,大多非專(zhuān)業(yè)漢學(xué)家。只有當(dāng)1933年德國(guó)大批學(xué)者被驅(qū)逐,其中一部分漢學(xué)家來(lái)到中國(guó),北平漢學(xué)才進(jìn)入專(zhuān)業(yè)漢學(xué)的發(fā)展階段。這些德國(guó)漢學(xué)家有: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1909—1989)、艾鍔風(fēng) (Gustav Ecke, 1896—1971)、李華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羅文達(dá)(Rudolf Loewenthal,1904—1996)、石坦安 (Diether von den Steinen,1903—1954)、衛(wèi)德明。這些于20世紀(jì)30年代來(lái)華的德國(guó)漢學(xué)家,以北平輔仁大學(xué)為中心,帶動(dòng)原先在華任教的漢學(xué)家,逐漸形成《華裔學(xué)志》北平漢學(xué)家群體。
在魏智出版物所勾勒的北平漢學(xué)圖景中,也有華裔學(xué)者的身影,如辜鴻銘、梁?jiǎn)⒊⒘鑶Ⅷ櫋⒑谓懿拧⑷陱?qiáng)、沈兼士、陳垣、英千里、馮友蘭、陳鴻舜。他們的西文著述或譯介,被納入當(dāng)時(shí)在華西方人所主導(dǎo)的北平漢學(xué)研究圈。可見(jiàn)魏智選擇漢學(xué)研究書(shū)稿,也有獨(dú)到眼光。1935年左右,魏智準(zhǔn)備出版華裔漢學(xué)家陳榮捷關(guān)于莊子的博士論文,但因后者沒(méi)有時(shí)間修改整理而未能成功。陳榮捷對(duì)魏智的漢學(xué)出版事業(yè)給予高度評(píng)價(jià):“范馳(Henry Vetch)的總部設(shè)在北京,他出版有關(guān)中國(guó)的書(shū)籍最是積極。”①華靄仁整理,彭國(guó)翔譯:《陳榮捷(1901—1994):一份口述自傳的選錄》,《中國(guó)文化》1997年第15、16期,第341頁(yè)。可見(jiàn),魏智在北平與中外學(xué)人素有交往。
魏智不但與中外學(xué)人保持交往,而且與各研究機(jī)構(gòu)聯(lián)系密切。法文圖書(shū)館的業(yè)務(wù)范圍,魏池的定位為“出版商,書(shū)商和文具商”(1926),到魏智的定位為“書(shū)籍銷(xiāo)售商、東方文物、出版商、地圖制作者、印刷工、裝訂工、文具商、訂閱、代理商、報(bào)紙和雜志零售商”(1930)。其中,法文圖書(shū)館的出版物代理值得注意。1934年,魏智的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有7種代售出版物②China Hong List,1934,p.658.:中國(guó)海關(guān)、南京中國(guó)地質(zhì)調(diào)查局、北平博物學(xué)會(huì)、倫敦英國(guó)總參謀部地理情報(bào)分部、加爾各答印度調(diào)查局、斯德哥爾摩遠(yuǎn)東古物博物館,《遠(yuǎn)東各國(guó)指南與紀(jì)事》(Directory and Chronicle of China, Japan, etc.)。1937年,北京法文圖書(shū)館的代售出版物達(dá)12種,相比1934年新增5種:上海聯(lián)華出版社、北平哈佛燕京學(xué)社、《華裔學(xué)志》、天津北疆博物院、巴黎陸軍地理服務(wù)局。在出版北平漢學(xué)的研究成果的同時(shí),魏智的法文圖書(shū)館借助這些代售出版物,進(jìn)入書(shū)籍與研究機(jī)構(gòu)組成的全球性網(wǎng)絡(luò),參與更為廣闊的東方研究的知識(shí)交換。
余論
魏池、魏智父子的出版事業(yè),并非簡(jiǎn)單的前后相繼,而是既有合作相助,又有不同道路的獨(dú)立取向。他們的教育背景與性格特征的差異,迥異的人生抱負(fù),最終決定了事業(yè)上不同的結(jié)果。魏池初到北京寄身于法國(guó)遣使會(huì)的北堂印字館,步入圖書(shū)銷(xiāo)售與出版行業(yè)。但他只懂法語(yǔ),這局限了他的社會(huì)交往范圍與商業(yè)拓展能力。魏池生活在法國(guó)人和懂法語(yǔ)的白俄人圈子里,始終與耶穌會(huì)士關(guān)系密切。與其父不同,魏智身為法國(guó)人,接受過(guò)正規(guī)的英文教育,其母為波蘭人,他本人也在波蘭工作過(guò)。這種跨文化的身份背景與生平閱歷,使得他擁有魏池所不具備的文化視野。魏智接受他父親的邀請(qǐng),為他父親提供語(yǔ)言方面的幫助,否則魏池執(zhí)掌時(shí)期的法文圖書(shū)館不可能有大量英文書(shū)籍出版。
魏池在華的兩段失敗人生,始于販賣(mài)中國(guó)苦力的失敗,終于書(shū)商事業(yè)的破產(chǎn),而魏智始終堅(jiān)持走其父親所引導(dǎo)的書(shū)商道路。兩個(gè)人的東方開(kāi)拓歷程,就是近代歐洲人在華商貿(mào)與文化活動(dòng)的縮影。魏池從在華販賣(mài)苦力,轉(zhuǎn)向從事書(shū)籍的銷(xiāo)售與出版事業(yè),他的失敗在于商業(yè)契機(jī)與文化興趣的疏離,而魏智的成功就在于將二者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既在西文圖書(shū)與中文古籍的收購(gòu)與銷(xiāo)售上獲得財(cái)富,又始終堅(jiān)持漢學(xué)出版事業(yè)的文化理想。魏智在1951年因涉嫌天安門(mén)炮擊事件,被判10年徒刑,③“Peiping Charges Plot to Assassinate Mao,” New York Times; Aug.18, 1951, p.2.并于1954年被驅(qū)逐出境。即使如此,他仍然于1969在香港成立魏李出版社,重操早年在北平的漢學(xué)出版事業(yè)。從1969年至1973年,魏智在香港出版10本研究中國(guó)的漢學(xué)書(shū)籍,首先是對(duì)北平漢學(xué)出版事業(yè)的接續(xù),如再版科琳娜·拉姆的《中國(guó)節(jié)日膳食》④Corinne Lamb, The Chinese Festive Board.Hong Kong: Vetch & Lee, 1970.3d ed.153 p.illus.19 cm. Line-drawings and paperends by John Kirk Sewall.(1970年第3版,1935年第1版,1938年第2版),白蘭士敦的《明初官窯考》①A.D.Brankston, 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0.with additional material.B-J, xvi, 102 p.illus.(part col.), maps.25 cm.Reprint of the ed.published by H.Vetch, Peking, 1938.,夏士德(G.R.G.Worcester, 1890—1969)的《中國(guó)流動(dòng)人口》(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②G.R.G.Worceste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Junkmen and Their Boats on Sea and River.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0, xii, 90 p.illus.26 cm.(1941年上海別發(fā)印字館初版),哲美森(George Jamieson, 1843—1920)的《中國(guó)家事與商事法》(Chinese Family and Commercial Law)③George Jamieson, Chinese Family and Commercial Law.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0, ii, 192 p.22 cm.(1921年上海別發(fā)印字館初版),威達(dá)雷男爵(Guido Vitale Baron, 1858—1930)的《北京兒歌》(Pekinese Rhymes)④Guido Vitale Baron, Pekinese Rhymes.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2, XVII, 274 pp.北堂印字館初版(Peking: Pei-T’ang Press,1896.252 pp.), 作者1893—1899年任駐京意大利使館華文參贊。,卜郎特的《虛字指南》(Wenli Particles)⑤J.J.Brandt, Wenli Particles.Hong Kong: Vetch and Lee,1973.iv, 178p.25cm初版華北協(xié)和華語(yǔ)學(xué)校1929;同時(shí)密切關(guān)注北京時(shí)代的學(xué)者并推出其新作,出版穆立金與霍特科斯合著的《中國(guó)九岳:在1935—1936年的朝圣記錄》(The Nine Sacred Mountains of China)⑥Mary A.Mullikin, Anna M Hotchkis: The Nine Sacred Mountains of China;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Pilgrimages Made in the Years 1935—1936, 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3, xx, 156 p.illus.26 cm.,赫達(dá)·莫里遜(Hedda Morrison, 1908—1991)著、艾伯華作序的《華山:華西道教圣山》(Hua Shan.The Taoist SacredMountains in West China)⑦Hedda Morrison, Hua Shan.The Taoist Sacred Mountains in West China: Its Scenery, Monasteries and Monks.Foreword and 111 photographs by Hedda Morrison.Introduction and Taoist musings by Wolfram Eberhard.Hong Kong: Vetch & Lee, 1973, xxv,135 pp.; 26 cm.。魏智在香港時(shí)期仍不放棄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熱愛(ài),堅(jiān)持漢學(xué)研究的出版事業(yè),參與皇家亞洲學(xué)會(huì)香港支會(huì)的活動(dòng),試圖接續(xù)早年的理想。他的香港出版事業(yè)可以視為北平漢學(xué)時(shí)代的短暫回應(yīng)。
簡(jiǎn)而言之,魏池與魏智在中國(guó)近乎半個(gè)世紀(jì)的漢學(xué)出版事業(yè),為在華漢學(xué)研究者(外交官、傳教士、記者、學(xué)者以及藝術(shù)家)的著述與譯作,提供一種與國(guó)際漢學(xué)溝通的出版?zhèn)鞑デ馈T跉v史洪流里,他們的出版事業(yè)屢經(jīng)波折而終歸湮滅,卻見(jiàn)證了在華漢學(xué)研究者的聚散離合,其出版物涉及眾多原典型作品與中外學(xué)人,為后人回顧20世紀(jì)前半葉的北平漢學(xué)發(fā)展奠定了史料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