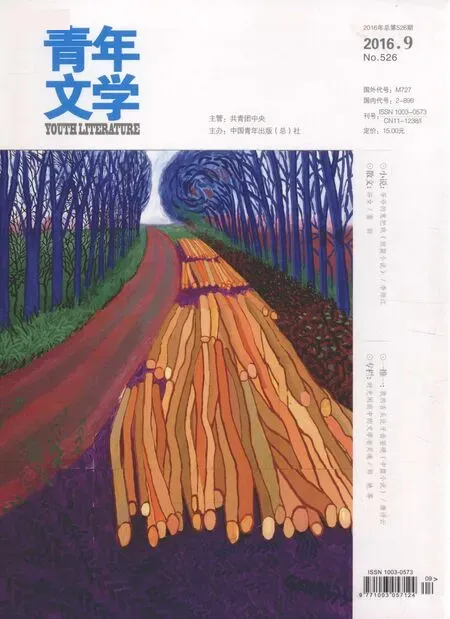文學對話:時光閑逛中的文學老靈魂
——流浪、觀察、絮語與敘述……
⊙ 文/郭 艷 等
文學對話:時光閑逛中的文學老靈魂
——流浪、觀察、絮語與敘述……
⊙ 文/郭 艷 等
主題:時光閑逛中的文學老靈魂——流浪、觀察、絮語與敘述……
主持人:郭 艷
發言人:艾 瑪、楊怡芬、喬 葉、黃詠梅

郭 艷:中國當下的寫作者遠離學而優則仕的古典人生樣態,也不同于近百年中國社會外辱內亂的苦難境遇,同時也日漸遠離政治、階級斗爭意識形態桎梏下板結固化的思維模式;寫作者們被拋入傳統到現代的社會巨大轉型中,個體盲目地置身于無序而焦慮的生活流之中。這些人是時光中的閑逛者,是生活夾縫中的觀察者,是波濤洶涌資本浪潮中的潰敗者,是城鄉接合部逡巡于光明與陰暗的流浪者……而對于這些人來說,當下中國社會狂想般無極限的現實存在,真的如波德萊爾所言“一切對我都成為寓言”。由此從文學史背景而言,中國寫作者與古典文學興觀群怨、怡情養性的詩教傳統斷裂,寫作既無法直接和廟堂國家接軌,又無法真正回到自娛自樂的文人文化狀態。請談談你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以及自身的文學定位。
艾 瑪:其實我并沒覺得我們現在的社會有什么巨大轉型,但生活上的變化我能感受到。我們確實比上一代人多了些選擇。寫作的人比較敏感,應該能感受到生活的變化。一個好作家至少應該能明白,因為這種變化你的生活到了一個什么地步,距理想世界的距離遠了還是近了。而所謂“中國社會無極限的現實存在”,其實要是讀讀幾本中國歷史書,就會發現這些事情差不多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只是因為具體環境的變化,這種“無極限現實存在”表現出來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現代性面孔下的老靈魂依舊。
我可能是非常自我的寫作者,我沒有感化、指引他人的野心和自信,我只是恰好生逢此世,恰好又有熱情寫點東西而已。其實我們這一代寫作者,不要說和以前的士大夫階層、士人比,就是和我們的前輩比,“寫而優則仕”的可能性和我們對這種可能性的興趣都大大減少了。還是那句話,生活在變化。“致君舜堯,再使風俗淳”,一個詩人懷有這樣的抱負在當今社會是不可想象的,這幾乎就是一個卓越的政治家的氣象。你說現在的寫作“無法直接和廟堂國家接軌,又無法真正回到自娛自樂的文人文化狀態”,我想大約是寫作多樣化了的緣故;但不管怎么變,內里的東西還是有傳承的,比如對現實世界的憂思與對理想世界的眺望,每一代寫作者應該都會有。
楊怡芬:先說“詩教”吧。因為有文官體制在,就可溫柔敦厚地接軌廟堂國家。對文官個人,是怡情養性;對和體制疏離的名士,則真的是自娛自樂、詩酒唱和;對民間,可“興觀群怨”,是教化和啟蒙之源。——古典文學“詩教”的社會基礎是文官體制和產生文官的科舉制度一起推動的,這個斷裂,估計從科舉制度被取消的時候就開始了;綿延到現在,再回望,何其遙遠。有時候,甚至懷疑,在教育極其不普遍的古代,這樣的詩教社會是不是“文官體制”居高臨下的一種一廂情愿。
作為一個生活在時空之中的寫作者,有了一定的“寫齡”之后,就難免會回望。您所勾勒的“這些人”,大概是每一個社會轉型中都曾有過的群像,他們心懷對生命的熱忱,無論是閑逛者或是觀察者,當他們投入寫作之時,即是和生活與時光擁抱之時,因為不曾麻木,面對這么多眼花繚亂的現實,重組個體的無序和焦慮,寫下的,或有可能成為寓言。一個寫作者,在做的,無非也是妄圖想留存下關于這個時代的“記憶”而已。對于小說家而言,誠實地寫出“在這個地方,有這么一群人這樣活過”,那也就無憾了。我對自己的寫作,一直是這么要求的。面對那么多文學經典,我會自愧并且懷疑自己寫作的“意義”,甚至有時候,對我的讀者也心懷愧意——時間有限,他們應該去讀更好的經典,如此想下去,是會自疑到不想再寫的;但我同時也想,我還是選擇努力活著,相信自己在時間河流中存在的意義。對我的寫作,我也是這么想的。
喬 葉:我從沒有想過定位這回事。以廟堂國家的宏大角度去看,寫作從來就是一件邊緣之事,沒有體量去和廟堂國家橫平豎直地接軌,但杰出的文學作品會以自己的方式在歷史內部與這些概念血肉相融地運行,成為時代的精微腳注和有力旁白。至于當下這個時代,毫無疑問,對于寫作者而言既是財富也是噩夢,全看你自己的能力。對此我心有惶恐,又常感幸運。無可怨艾,只有盡力。正如哈金所言:“每個人的寫作都是個人行為,文學寫作的終極目的是超越歷史……一切都必須從你的時代開始,只有通過你的時代才能超越你的時代。”
黃詠梅:當下的寫作“無法直接和廟堂國家接軌”,是文學本身所面臨的問題,也“無法真正回到自娛自樂的文人文化狀態”,是作家本身所面臨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導致了我們今天對文學所秉持的態度。曾經聽到一位網絡作家對我說,傳統文學現在已經“美人遲暮”。我對這個詞感到特別驚悚。我們這一批寫作者,是否真的會成為傳統文學的“終結者”?這個問題真的不能多想。寫作的確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寫作者成為或者凝視那些閑逛者、觀察者、潰敗者、流浪者,無論是哪一種,都是對“人”的記錄和研究,以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呈現這個時代中的某一類“人”,優秀的小說往往能將這類“人”變成“我”,更優秀的小說往往會替這個“我”不斷地叩問“我是誰”。我相信,這是時代的文明程度所造就的一代人的寫作,我們應該順應接受。
郭 艷:當下更多作家開始注重現代日常和個體生存經驗的審美維度,而現代日常經驗的文學性和審美維度的轉換則是一個較為漫長的培育過程。而我們當下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陷入被物質遮蔽的境遇,我們怎樣去直擊被遮蔽之后的個體精神生活?藝術不是發現幽暗,而是在幽暗區域掙扎,在探索中抵達光亮。我們如何找到現代性悖論中光亮性的東西,包括意象,也包括意境。請談談您的看法?
喬 葉:其實不用太刻意地去找,因為光亮一直就在那里,只要我們腳步堅定,就能慢慢向它靠近。任何光亮都是如此,包括“現代性悖論中”的光亮。而文學世界里的任何光亮,說到底都是人性的光亮。以我的寫作體驗,每當我在小說里寫到一個人,只要靜下心來,在一個想象的角落里耐心地看著他,都會看到動人的光亮。今年第五期《天津文學》發了我一個短篇,名為《送別》。其中寫到兩個男人在花街柳巷的曖昧之地邂逅,最初是厭惡、忌憚、戒備和仇恨,但漸漸便多了會意和體恤,到后來甚至有了復雜的溫暖和深切的相知——這就是他們的光亮,哪怕他們在最黑暗的地方。
艾 瑪:對寫小說的來說,無論多宏大的主題,你都得從日常入手,日常生活無論多么龐雜,大多都是可知的,只不過每個人的認識程度不一樣而已。要說“日常生活越來越陷入被物質遮蔽的境遇”,對這個問題我覺得不能簡單地談遮蔽與被遮蔽。人們精神空虛、思想貧乏、無所追求是一回事;物質是另一回事,物質本身無罪。記得朱光潛先生在《詩論》中談到過中國古典詩人和西方古典詩人的差別,大意是說中國古典詩人對現實世界的描述足夠,但對理想世界的描述是差強人意的。當時讀到這句話特別有感觸。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樣的?我們未必回答得好這個問題。去年在寫長篇《四季錄》的過程中,有個朋友問我,寫的是個什么故事?我想了想,回答:寫的是一個關于生活的正當性的故事。我小說里的主人公認為生活的正當性非常重要,生活得正當才能生活得好,這算不算是一個光亮性的東西?
黃詠梅:我一直以為,詩性是物質黑洞的那一線光亮。很多時候,我感到自己像一只飛蛾,被黏稠的日常生活所困,但是翅膀卻在掙扎著扇動。這扇動的翅膀,力量微弱,卻會扇出風、旋律、光影。這掙扎本身就是一種美。這種美的舞蹈,就是日常生活里的詩性展現。日常生活由合法化逐漸邁向審美化,詩性是這個過程的靈魂,無此,這個轉變無法完成,或者說毫無意義。只有這樣,即使寫作者塑造的失敗者縱身一躍而下,也能使他人讀到靈魂的高蹈,是飛升的。詩性拯救了陷入日常泥沼中的沉重的肉身。這是文學趨光屬性的一個永恒不變之途。
楊怡芬:“買買買”,這三個字,已經成為很多女人的生活常態,包括我。不要說“物質”,單說這種購買的欲望,冷靜想想,也蠻嚇人的。但是,個體的精神生活在這樣被物質遮蔽的形態下依然存在,渴望了解自己,渴望知道前路何在,渴望知道自己生存于此的意義,這樣的精神活動不會比任何一個時代更單薄,日常生活的“詩性”依然存在,甚至,因為物質相對豐富之后,精神追求也相對豐富。單純地割裂、對立物質和精神,會走向某種虛妄。被物質占有的現代人,要克服對物質占有的罪惡感,在豐富的基礎上,培養自律和知足,好過在貧乏之時的壓抑。——在物質面前做到“自適”,不被物質所物化,也許是每個現代人都得學會的命題。以上,我說的是生活。
至于小說里被物化的人,我覺得我們寫得還很不夠,我們小說中的日常性與現代性的結合,似乎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但怎么去撥開物質的面紗直擊“被遮蔽之后的個體精神生活”呢?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誠實地以小說的樣貌呈現曾震動過我心靈的現實(無論是他人的故事還是自己的親歷),是我唯一能做的;至于藝術和現代性悖論,允許我掉書包吧。波德萊爾說過:“現代性是短暫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藝術的一半,藝術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的”。他又說過:“那些到古代去尋求純藝術、邏輯和一般方法之外的人是可悲的,他深深地一頭扎進去,而無視現在,他棄絕情勢所給予的各種價值和權力:因為我們所有的創造性都來自時代加于我們情感的印記。”
郭 艷:中國人對于城市的想象乃至于在城市中實際的生存經驗迥異于歐美社會,具有新舊雜糅的復雜特征。現代日常性敘事中呈現出一個有別于苦難和殘酷人生經歷的中國敘事。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中,數以億計進城的淘金者可以匯聚成一個巨大的奔跑的人。這個從鄉土出走的巨人漂在中國的大中城市,吸引他們的是現代城市和城市生存方式:個體的、自我的、封閉的,冷漠的,又各自相安的私人化生活。貧富差依舊觸目驚心,然而卻被混跡于快餐店、超市、百貨公司甚至于公園景點的人流沖淡,且在無數的霓虹燈和廣告的暗示下,人人都覺得自己正在或將要擁有機遇與財富,成為城市的主人。無數個中國人都是這樣一個個擁堵在現代性時間維度上的淘金者。這些淘金者樂于擺脫鄉土倫理羈絆,迷戀現代都市,既是時代的主流人群又是當下主流社會的邊緣人。請談談您對主流人群與主流社會邊緣人的理解。
黃詠梅:這些人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至今依舊在為掌握自己的生存權而奮斗,至于話語權,他們無暇顧及,他們甚至認為只有精英分子才配擁有話語權。物質越繁華,內心越荒蕪。就是這種心理狀態,使他們一直感到邊緣。事實上,邊緣更多指向的是一種心理感受,失落、漂泊、看似擁有很多實則什么都沒有;在城市回望故鄉哼出的卻是一首首挽歌,而在城市仰望星空,每每心里又在醞釀一個個烏托邦式的“逃跑計劃”。這些主流的邊緣人成為我們現在筆下最重要的主角,他們以邊緣的姿態和心態,代表了我們身處這個轉型時期的惶惑感。
喬 葉:我第一次發現主流人群和主流社會不畫等號。如果沒有物質和精神的有力倚仗,主流人群就不能進入主流社會,這很殘酷。但就文學意義而言,就是這些人,最是充滿了生機勃勃的可能性,他們有欲望,有夢想,有煎熬,有掙扎,有痛苦。這些都是文學的沃土。身為一個寫作者,一個進城工作將近二十年的鄉下女子,我特別理解他們,也特別心疼他們。雖然我對他們愛莫能助。而在對他們進行整體觀照之后,我的愛,最終只能也必須通過文字落實到人身上。而人,是一個,一個,又一個的。是具體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誰和誰都不一樣。
艾 瑪:我們目前的城鄉差別還是很大的,人們離開鄉村不一定是為了擺脫鄉土倫理羈絆,更多的應該是為了追尋更好的生活。鄉村傳統禮治秩序崩潰后,現代法治秩序未能建立,這使鄉村陷入茫然無序的狀態,鄉土已無法滿足年輕人的生存和心理需求。如果中國鄉村的文明程度能達到歐美鄉村那樣的程度,那么農民到城市去不過就是職業的轉換,他們由農民變成了建筑工人、職員、家政工作者,他們的生活處境只會跟他們在城市的個人發展狀況有關,會呈現出豐富性,你也就無法再用一個“農民工”來簡單概括他們了,當然也就不好把他們看成是“一個巨大的奔跑的人”。我對所謂主流人群或是邊緣人群缺少考察,也沒有刻意去寫一個主流人或是邊緣人的經驗。有個感覺,如果群體性的特征太突出,個體就會缺少豐富性;為避免類型化,離奇而充滿偶然性的故事可能就會成為寫作的最佳選擇。
楊怡芬:什么是時代的“主流人群”呢?單從人口出生年份說,據說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年出生的,是中國的主流人群;這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二三十歲的時候,為城市化進程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也就是那個“巨大的奔跑的人”。若從能不能主導社會來定義,那么擁有話語權和決策權的,才是“主流人群”——主流社會;從這個角度說,這個“巨大的奔跑的人”便是主流社會的邊緣人。我也在以年齡劃分的主流人群里,我也是這個“巨大的奔跑的人”的一分子,對從農村到城市的經驗,感同身受。在我所處的沿海發達地區,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城市擴張,農村萎縮;從面上看,城鄉差別在縮小,但貧富差距依然在那里。所以,即便在我們這樣的小城市,也還有從鄉下來的“淘金者”的,現在走在城市街頭,隨處可見他們的蹤影。年長的,我們還可以從形體和衣著上來區別;年輕的,那真的是和城市人口一樣,甚至最新潮的裝束和發型都是屬于他們的。小城本地人,反倒顯得保守和拘謹。一些事情在起變化,年輕的淘金者和前輩不一樣。
郭 艷:中國廣大鄉土依然作為現代性未完成的事實廣泛存在,人身心搖動不安,情感混亂迷惑,靈魂下沉掙扎。農民進城和大學生在城市的屈辱遭際一樣成為新的問題小說,這些和社會同步的寫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雙向解構了對于“現代文明”的認知。——所謂的“進步”依然是一個必須被不斷質疑和重新估量的詞語。請談談您對問題小說與審美現代性之間關系的理解。
艾 瑪:回答這個問題前我搜索了“問題小說”,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釋,“明確地接觸每一社會現實或人生現象,有意識地提出問題,甚至試圖解答問題的小說”就是問題小說。但是我對問題小說有另一層理解,那就是如果寫作的焦點太過集中在“問題”上,難免會有千篇一律之感。當代歐美作家大多寫日常,他們的作品呈現出了豐富多彩的個人存在;而我們的現實問題太突出,也太容易被分類和被概括。至于問題小說和審美現代性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的理論性太強。有個感覺,從歷史上來看我們沒有經歷過西方社會經歷過的啟蒙運動和激進的現代化、工業化,以及先前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后來的憲政運動;所以我們的“問題”和別人的也應該不一樣,審美現代性是不是也有新的內涵?或者我們談審美現代性是不是早了一點?就我個人的寫作來說,我先前的小說,好像有問題小說的一些特點,但近年來我逐漸把自己的關注點從問題回落到人,具體的個人。我的一點淺見是,只要把人寫好了,對問題的反思、批判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鳴。
黃詠梅:我們當然需要與社會同步的文學。如我們所知,問題小說大多反映時代之變,塑造時代之變中的人。可是,大量的問題小說沒寫好,是因為這些小說沒能安靜、耐心地去反映人之常。如同巨輪翻起海面一時的風浪,歸于平靜后,無人再想起那些曾經的風浪。處理好時代變革中的人之常,能很好地打通問題小說與審美現代性之間的關系。這真的很不容易,時代命運的伏線與人的命運的呼吸節奏共同彈奏出復調之音,這是經典對文學的要求,我對這樣的小文學肅然起敬。
楊怡芬:我覺得,二十世紀初的作家,比我們更具現代性的自覺,在審美的現代性方面,比我們中的大多數走得更遠,因為他們有比我們更為寬闊的世界觀,還有更雄厚的知識儲備。記得在魯院“群山合唱”筆會上,有人說到“七〇后”部分作家是在自覺接續五四傳統,我覺得挺有道理的。趙樹理也把自己的小說叫作“問題小說”,他說:“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碰到的問題。”至于“傷痕小說”,那自然也是問題小說吧。在每一個時代轉型的節點,只要寫作者對人生對社會有思考,他就會自覺不自覺地用現代性的審美來關照此時此刻;希望現實有改變,希望將來更美好。我也是自覺地用“問題小說”的思維寫,我的《金地》,是說房價一路飆高的,我的《兒孫滿堂》,是反思我們海島“大島建,小島遷”;但是,還往往會停留在“問題”層面,沒有上升到“人性”或“國民性”的高度。也就是說,還是缺乏審美現代性的關照,這就是我對問題小說與審美現代性的理解吧,后者能帶領前者走出“問題”,或者能找到療救的藥方。
喬 葉:所有的小說都是寫問題的,哪怕是最抒情的那種。至于“中國廣大鄉土依然作為現代性未完成的事實廣泛存在”,我懷疑真正的完成——尤其是精神上的、骨髓里的完成,是任何學者或者研究機構都無法分析和預測的。這種完成的過程一定會非常漫長和遙遠,同時也會跌宕起伏迤邐有致。而這個過程中盛放的那些文學之花,也必定沾染著現代性審美的顏色,攜帶著現代性審美的氣息,包括我自己的小說。至于現代性的成分和質地到底如何,我很期待你們這些優秀的評析者能夠給出精彩的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