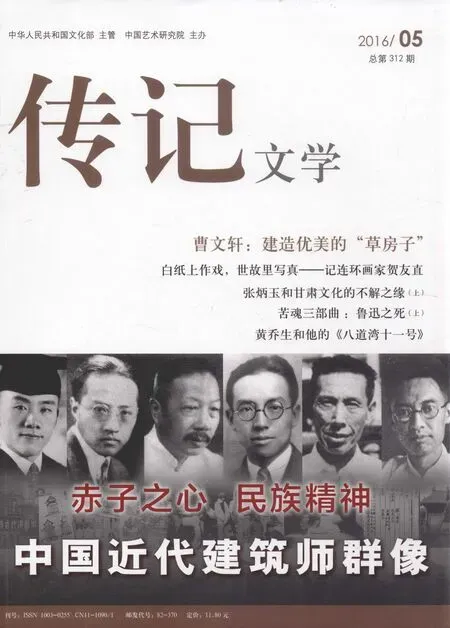張炳玉和甘肅文化的不解之緣(上)
文 常金生
張炳玉和甘肅文化的不解之緣(上)
文常金生

重回文化廳
1991年年初,也許是甘肅省委覺得張炳玉完成了在省委領導機關的鍛煉提高,決定派他回到文化廳主持工作。
主持文化廳工作以后,張炳玉把主要精力放在藝術工作方面。他的思路是,先把從1949年后到自己上任前的情況做一個全面了解,對全省文化工作的現狀做個調查研究,特別是對省直8個專業劇團進行剖析式調研,發現問題嚴重:一些劇團處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有人把這些劇團歸納為“四無”劇團,即無演員、無編劇、無導演、無音樂。張炳玉進到一些劇團的大門,有一種凄涼的感覺。本來應當是藝術之園,但他看到的卻是荒蕪之地。有的劇團甚至擺出一副“散伙”的架勢。目睹劇場與劇團的現狀,張炳玉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顯然不能就事論事,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必須從長計議,統攬全局,找到問題的“抓手”。
經過較長時間的思考謀劃,張炳玉終于確定了主抓創作的基本思路。到了年底,他主持召開了全省藝術創作會議,在會上提出了“以敦煌為源流,以絲綢之路為背景,以多民族為色彩”的總體思路,后來文化系統簡稱“敦煌·絲路·多民族”。這個思路既是對過去甘肅藝術創作的一個總結,也是對今后藝術創作的一個目標追求。從張炳玉上任文化廳廳長,主持文化廳工作的十年期間,始終遵循這樣一個基本思路,推出了一大批具有甘肅特色的藝術成果,同時也推出了一批有相當影響的藝術俊才。比如《大夢敦煌》,就是“敦煌·絲路·多民族”的實踐成果。第四屆中國藝術節推出的八臺大戲也是這個思路。在這十年里,有相當一批劇目先后獲得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最高獎項,同樣是沿著這個思路。
今天看來,張炳玉當時確立的藝術創作思路和方向是符合甘肅實際,也能夠調動甘肅文藝工作者積極性的。
就在“敦煌·絲路·多民族”這個思路出臺之際,文化部在北京酒仙橋飯店召開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代部長賀敬之在講話中談到了1992年春季在云南昆明舉辦第三屆中國藝術節劇目入選情況:幾乎全國各省、市(區)都有一臺劇目被選定,唯獨甘肅沒有。張炳玉很吃驚,他到文化廳后,也沒人告訴他有藝術節這個概念。當時的現實狀況是,8個藝術院團中只有隴劇團在排練一臺叫《天下第一鼓》的劇目。甘肅能否補報?張炳玉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賀敬之的秘書趙鐵信。趙秘書要張炳玉寫個書面的材料。
對文化人出身的領導和同事,張炳玉一向都有一種特殊的敬重。對詩人出身的賀敬之,張炳玉更是如此。他記得1990年秋季的一天,賀敬之在銀川出席一個會議后,取道寧夏固原和甘肅莊浪,考察秦安大地灣史前遺址與天水麥積山石窟、伏羲廟。時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張炳玉與相關部門的人員在甘寧交界的六盤山迎候賀敬之一行,中午在莊浪午餐,平涼地委一位負責同志得知身邊坐的是賀敬之時,激動地握住他的手,背誦起中學課本中那首耳熟能詳的《回延安》來。這一舉動,一掃賓主、上下級之間的生疏與隔膜,現場的氣氛也在一瞬間融洽起來。說來也巧,結束考察時,張炳玉在天水火車站為賀敬之送行,年輕的車站站長疾步上前問候賀敬之,說:“我們這一代人,是伴隨著你的詩歌成長起來的。”說話間,再次背誦起那首《回延安》。
賀敬之這次考察給張炳玉留下深刻印象的還不止這些。他對大地灣古遺址、麥積山石窟的評價及提出的意見,在張炳玉看來,至今仍有很強的針對性。時隔數月后的1991年元月,遵賀敬之囑托,秘書趙鐵信給張炳玉轉來臧克家給賀敬之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青島大學兩位教授研究臧克家的作品,編寫了一本叫《臧克家研究資料》的叢書資料,但遭遇出版困難。臧克家希望此書能在甘肅出版,他請賀敬之在甘肅給這本書一個出版的機會。張炳玉收到信后,深感自己的責任和這本書的分量,當即與甘肅人民出版社取得聯系。出版社也很痛快,他們表示,一定要讓這本極具學術價值的書稿出版發行。就這樣,一本85萬字的《臧克家研究資料》在甘肅出版問世……
有了這層關系,張炳玉就大膽給賀敬之寫了封信。信很快得到批復,同意甘肅補報《天下第一鼓》為第三屆中國藝術節入圍劇目。消息傳到隴劇團,演員們也非常振奮。隴劇自《楓洛池》開創性搬上舞臺后,30多年來,再沒有在國家層面露過臉。終于有了機會,大家都表示,一定要努力,下決心把這個劇目以隴劇的全新的形象推向全國。
隴劇團在原有基礎上,對《天下第一鼓》反復修改打磨多達半年。1992年春節后,他們把該劇帶到春城昆明,參加第三屆中國藝術節演出。
在昆明的日子里,張炳玉帶上請柬、名片,一一拜見各大媒體記者、劇評家,傾聽他們對隴劇的意見。關肅霜是京劇界的大師級人物,又是云南京劇團的團長,作為東道主,已經被許多事務搞得焦頭爛額。她是否有時間和精力觀看甘肅的隴劇,張炳玉內心沒有太多把握。也許是被張炳玉的真誠約請所打動,首場演出,關肅霜就放下手頭急辦的事,趕來劇場觀看。她說:“甘肅是我很向往的地方,這個隴劇我一定要看。”在看戲的過程中,關肅霜全身心投入,看得入神,看得著迷,也看得動情。當演出結束,大幕還未落下,她便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直奔后臺,對演員們說:“好戲,好戲!難得的好戲!”在次日的評戲座談會上,關肅霜不吝溢美之詞,對《天下第一鼓》大加贊揚。她說:“你們打出了中華民族的志氣,真乃天下第一鼓!”說著,她突然起身離座,朝編劇、導演和主要演員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關肅霜的“三鞠躬”傳遍春城,成為藝術節期間海內外文藝界、新聞界熱炒的“花邊新聞”。

參加首屆中國京劇藝術節留影
《天下第一鼓》在春城昆明第三屆中國藝術節的演出大獲成功。甘肅特有的蘭州太平鼓,堪稱天下一絕。甘肅隴劇團本著傳承、改革、創新的原則,把原本屬于農民自娛自樂的地攤文化,大膽搬上戲劇舞臺,讓太平鼓的黃河奔流氣概、雷霆大作之威風盡現舞臺,強烈地震撼和感染了專家和觀眾。接下來,該劇又順利獲得文化部的文華獎。這是甘肅戲劇作品首次獲得國家級最高獎項。張炳玉欣慰的是,他那關于“敦煌·絲路·多民族”的創作思路,終于結出了初步的碩果。
甘肅省藝術院團每一部作品的成功、每一位人才的推出,應該說都是張炳玉付出辛勤勞動的,也是他和他的同事、下屬共同用心血澆灌的結果。后來,張炳玉曾經寫過一篇《苦路與鋪路》的文章對此進行過總結。
甘肅文化廳在張炳玉接任廳長之前,已經有過驕人的成就。那些年,宣傳文化系統領導和干部經常在嘴邊提到的是“文革”前的話劇《康布爾草原》、電影《紅河激浪》和改革開放之初的話劇《西安事變》、舞劇《絲路花雨》,應該說那些年甘肅的戲劇在全國還算小有名氣,全國文藝界也常有“甘肅的戲劇、陜西的小說、青海的散文、新疆的詩歌”這樣的說法。但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屆中國藝術節以來,甘肅似乎再未出現有較大影響的作品,也沒有推出好演員。尤其是1983年為戲劇演員專門設立的梅花獎以來,甘肅一直沒有推出梅花獎演員。張炳玉到文化廳后,他才從媒體上獲知甘肅連續8年都是空白。這時的張炳玉感覺到壓力,但似乎短時間也無力改變現狀。雖然當時的竇鳳琴也有了一定的影響,作為全省青年演員大獎賽的優秀演員,從慶陽秦劇團調入省秦劇團。但由于沒有好作品,也沒辦法往上推。
為了出作品,1992年,張炳玉極力爭取拿到了第四屆中國藝術節的主辦權。他核心的動機就是想借助舉辦藝術節的東風,推出一批好作品和藝術人才。后來的實踐證明,這個目的的確達到了。從藝術節舉辦之后的1995年,也就是從第十二屆梅花獎開始,直至2015年,甘肅不間斷地推出梅花獎演員,總人數達13人,其中京劇演員陳霖蒼、話劇演員朱衡獲“二度梅”。
張炳玉與這些藝術人才中的絕大多數,都發生過一段段直接或間接的故事。
打造“明星”
京劇《夏王悲歌》的作者康志勇,已經在此前創作過歌劇《陰山下》。他最擅長的也許就是寫那氣貫長虹的悲劇情節、表現情緒。好在時代又前行了幾年,悲劇也不再那么敏感。康志勇原本在嘉峪關工作,由于寫小說在全省有一定名氣,被文化廳調入省歌劇團擔任專業編劇。本子是他繼《陰山下》后的又一力作,早在藝術節之前就寫出來了,張炳玉看后,就琢磨這個劇本怎么用。中間九易其稿,直到1992年夏天,文化廳承辦全國戲劇小品大賽。有一批專家來蘭州擔任評委。張炳玉覺得這正好是個機會,他安排讓把本子分送給專家審看。多數人由于忙于評比大賽的參賽節目,無暇顧及這個本子。但其中的著名戲劇評論家曲六乙回到北京后認真看了本子。他專門給張炳玉寫信,表示支持《夏王悲歌》作為藝術節劇目投入排練。

甘肅省首屆戲劇“梅花獎”大賽期間與武威歌舞劇團演職人員一起合影
經過認真討論,文化廳正式確定排演《夏王悲歌》。首先是確定導演,鑒于甘肅導演極缺的現實,他們外請了導演過當時著名京劇《高高的煉塔》的吉林省京劇團著名導演藝術家李學忠擔任導演。《高高的煉塔》張炳玉以前曾看過,印象很深。
李學忠也看好《夏王悲歌》的本子,爽快地答應了甘肅方面的邀請。但他來蘭州進入排練過程后,跟京劇團負責人多次發生矛盾、摩擦,最后不辭而別。這個難題擺在了張炳玉的面前。情急之中,他想到正在話劇團排練話劇《極光》的中國鐵路文工團資深導演、導過歌劇《張騫》的陳平。
1993年年初,張炳玉在北京參加文化部文華獎頒獎大會期間曾請來陳平擔任話劇《極光》的導演。對她在頒獎大會上關于《張騫》的導演闡述的一段話表示非常佩服。
張炳玉在話劇團排練場找到陳平,問她能否救場,接手《夏王悲歌》的導演。陳平聽了張炳玉的話后,好久沒有吭聲。張炳玉猜測,她是否在擔心讓她既導話劇,又導京劇,導砸了怎么辦?于是,就試探著對她說:“藝術的感覺是相通的,以你這樣藝術閱歷豐富,藝術實踐多多,對別的劇種嘗試嘗試有何不可呢!”他還對她說:“這兩個劇團相距很近,便于你來回串場,交錯排練,整體齊頭并進,也算是一舉兩得的事。”
陳平也想了想,說:“也只能如此了!”這也是陳平的導演生涯中,第一次碰到同時導演兩部不同劇種、而且兩部作品都是參加重要節會的情況。最后的結果是兩臺戲都取得了成功。
《夏王悲歌》成為第四屆中國藝術節叫得最響、觀眾反映最強烈的一臺戲。有人甚至認為,該劇不論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上看,也不論從史學價值,還是藝術價值看,都具有史詩般的意義。時任主管領導,也是藝術節主要領導的省委副書記孫英,對該劇也有特殊的偏愛。這位歷史專業的領導還專門安排相關人員為《夏王悲歌》撰寫劇評文章,為該劇叫好。
考慮到李瑞環同志喜歡京劇,對京劇也有很深的研究,文化廳便通過組委會安排李瑞環提前觀看《夏王悲歌》。藝術節開幕前一天,也就是8月17日,李瑞環抵達蘭州。當天,他連賓館都沒進,在機場略作休息后,就直接到達黃河劇場。李瑞環看過后,對甘肅能夠拿出這樣一臺高水平的京劇,也非常高興。該劇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京劇味,又巧妙地吸納了地域文化的元素,有了鮮明的地方特色。此后,人們把《夏王悲歌》視為西部京劇的經典之作。1995年,《夏王悲歌》獲文化部文華獎。1996年,主演陳霖蒼獲第十二屆中國戲劇梅花獎,這也是甘肅第一位獲梅花獎的演員,為甘肅戲劇實現了梅花獎評獎零的突破。
陳霖蒼后來講,有三件事讓自己對張炳玉印象深刻:
一是1989年京劇《原野》赴京演出前,張炳玉代表宣傳部到車站送行時說:“你們這個團的走向和發展、生存和失敗,在此一舉,只能成功,不能失敗。”這些話有激勵作用,加上劇目本身過硬,這次進京演出,獲得了新劇目獎、優秀表演獎。
二是1994年12月,《夏王悲歌》赴北京參加梅蘭芳、周信芳誕辰100周年展演,在臨行前,張炳玉講:“這次我們也是遇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希望你們去后,務必作到一舉三得:拿下文華獎、梅花獎和展演的成功!”在北京期間,京劇團果然如張炳玉為他們送行時所說,取得了一舉三得的效果。在北京展演時,反映強烈,謝幕時,有觀眾喊著導演和編劇的名字,強烈要求出來謝幕。在《夏王悲歌》赴京演出的同時,張炳玉立即安排有關處室申報陳霖蒼參賽第十二屆戲劇梅花獎。因為這個時候已經到12月底,離申報截止時間還有兩天。申報梅花獎的演員有45歲的年齡界限,假如過了年底,陳霖蒼就46歲,再也不能申報,將永遠失去申報梅花獎的機會。
三是1996年,《夏王悲歌》與《原野》赴臺灣演出前,張炳玉在送行時講:“你們這次去,不僅是團里的榮譽,也是甘肅的驕傲。甘肅這樣一個邊遠省份的京劇團,能夠帶上兩臺大戲,很了不起。希望你們到臺灣后,把中國京劇發展的新成果展示給臺灣同胞,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出力。”該劇應邀到臺灣演出期間,引起極大轟動,海峽兩岸的學者還就《夏王悲歌》的演出,成功舉辦了專門的學術研討會。
獲第十四屆梅花獎的秦劇演員竇鳳琴在上推初期,文化廳準備上報她主演的劇目《白花曲》。按規定,要把戲帶到北京,由中國文聯、中國戲劇家協會組織演出,由專家評審。張炳玉當時考慮,怎么找個讓劇團上北京的機會呢?這時候,剛好遇到一個情況:文化部要在西安舉辦全國的梆子戲調演。甘肅文化廳當初報的是蘭州市的一臺戲。但這臺戲沒有通過文化部的審查。張炳玉得知這個情況后,也是為了不缺席梆子戲調演,就給文化部藝術局的姚欣副局長打電話,請求能否補報省秦劇團的《白花曲》參加西安的梆子戲調演。張炳玉當時考慮的是:梆子戲調演雖然是文化部主辦,但評委中多數都同是梅花獎的評委,如果他們能夠在西安提前看到竇鳳琴的演出,更有利于為劇目上北京演出打下一個好的基礎。姚局長表態他個人同意,但需要第二天由文化部藝術局正式答復。
第二天上班后,文化部藝術局正式給甘肅省文化廳答復,同意《白花曲》參加在西安舉辦的梆子戲調演。為了在西安演出成功并協調與有關方面的關系,張炳玉親自帶領秦劇團赴西安參加調演。后來他才知道,這是秦劇團組建以來的第一次出省,而且是在秦腔的老家參加全國性調演。省秦劇團全團上下自然是精神振奮,興高采烈。

藝術節前與文化部部長助理高運甲(左二),文化部藝術司司長曲潤海(左一)、副司長姚欣(右一)合影
實際上,張炳玉去西安的主要目的,除鼓勵演員外,主要還是想拜訪各位評委,請他們關注甘肅省參加調演的劇目。當時,雖然是來到了秦腔的老窩子,但張炳玉自己還是有充分的自信。參加調演的演員中,恰好也有竇鳳琴的強勢挑戰者、陜西戲劇研究院秦劇團的李梅。李梅當時參加的劇目是陜西省自己創作的新編歷史劇《蔡倫》,李梅扮演蔡倫夫人。張炳玉特別關注竇鳳琴和李梅的對比,他分析認為:單就表演看,竇鳳琴絕不亞于李梅。從搜集到的反映看,陜西的戲迷們都為竇鳳琴叫好,說:想不到,甘肅還出了這樣的好演員。戲劇專家也對竇鳳琴的演出給了較高的評價。
最后評獎時,《白花曲》囊括了表演、劇本創作、作曲、舞美設計等方面的獎項,也給陜西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調演期間,為了便于直接赴北京參加梅花獎評審演出,張炳玉要求把《白花曲》的演出安排在了后期。調演結束后,借著演出成功和高漲士氣,直接把劇團帶到了北京。因為有西安的成功演出,北京的演出也就順風順水。最終,竇鳳琴獲得了第十四屆中國戲劇梅花獎。
另一位梅花獎得主雷通霞,原是定西地區秦劇團演員。張炳玉在定西下鄉時,看過她的折子戲《打神告廟》,覺得這個演員條件好,有潛力,也有一定實力。這個時候,省隴劇團也看中了她。這樣,文化廳就決定把她調到省隴劇團,給她一個更大的平臺和施展才華的機會。
文化廳對這個演員的培養目標也是梅花獎的獲得者。她在地區一直演的是傳統劇目。要獲獎,必須為她打造一部新的劇目。這個時候,正好又有了一個機會。文化部在天津舉辦首屆中國京劇節。在參加京劇節期間,山東京劇團演出了京劇《石龍灣》,張炳玉和文化廳藝術處處長在看戲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念頭:這個戲能否移植過來讓甘肅省隴劇團演。文化部當時也在提倡移植劇目。張炳玉讓藝術處處長找到山東京劇團,先把劇本拿到了手。
從天津返回蘭州后,文化廳就與隴劇團商議,最后決定移植京劇《石龍灣》。排練后,大家反映雷通霞把劇中人演得光彩照人,她的唱功震撼了觀眾,不少戲迷認為雷通霞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這時候,中國現代戲研究會要開年會,隴劇團是現代戲研究會的團體會員,按規定,研究會的年會由團體會員輪流坐莊承辦。研究會提出這屆年會由甘肅主辦。隴劇團團長為此事來找張炳玉,希望文化廳支持他們承辦年會。
現代戲研究會的年會在蘭州舉辦得很成功,省隴劇團的演出,尤其是雷通霞的演出,得到了專家們的高度評價。當時,張炳玉還在年會期間,在《甘肅日報》上刊發他自己撰寫的文章《一個明星的發現與培養》。張炳玉把當天的報紙送到與會專家學者手中,他們跟張炳玉開玩笑:“廳長親自出馬推人才了!”這件事,在客觀上也的確為雷通霞獲獎起到了很好的鋪墊作用。
1997年,雷通霞終于通過移植的隴劇《石龍灣》獲得了第十六屆中國戲劇梅花獎。
《敦煌古樂》的誕生
敦煌遺書是世界公認的歷史遺存和文化瑰寶,遺書中有一部分珍貴的古代樂譜。但長期以來,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用今天的記譜方式還原它的真實面目。曾經的著名音樂人,如今的網絡脫口秀紅人高曉松談論過一個話題,叫“漢人無音樂都怪老祖宗”。所以怪老祖宗,并指“漢人無音樂”,恐怕既有文化傳統、思維習慣的問題,甚至封建專制制度本身的問題,但恐怕更有記譜方式的問題。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音樂形式,人們在今天所能看到的也只有那些曲牌和后人根據自己理解譜寫的曲譜了。盡管已經有不少人試圖還原古人常用的記譜方式,但對敦煌遺書中的古樂譜的還原并取得成效,原甘肅省歌舞團的演奏員席臻貫,是第一人。
《絲路話雨》問世后,幾乎演遍世界。有一次在法國演出時,作為演奏員的席臻貫利用演出間隙,曾到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抄錄被掠奪到法國的敦煌古樂譜,后來他還利用各種機會收集流失在各地的敦煌古樂譜。張炳玉在拜訪席臻貫時聽了他的介紹后,為他的這種努力很受感動。在與席臻貫的交談中,張炳玉聽了他對破譯敦煌古樂譜意義的看法以及他個人在破譯工作中面臨的困難。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在經費上已經寸步難行,甚至連一頁稿紙都沒有,經常要把香煙盒用作稿紙開展研究破譯工作。張炳玉心里不是滋味,感覺對席臻貫認識得太晚。他當即表示,文化廳會竭盡全力幫助他把這件事做好。
回到機關后,張炳玉做了安排,讓歌舞團關心支持席臻貫的工作,并撥出經費用于古樂器的制作。席臻貫的古樂器設計,主要是根據古樂譜相關圖畫,并參照日本奈良正倉院收藏的古樂器圖譜設計而成。為了進一步促成敦煌古樂的研究復原工程,席臻貫提出歌舞團要重新組建領導班子。他也給省委主管副書記孫英做了匯報。后來,組織上采納了他的意見。這就給他創造了敦煌古樂研究的充分條件。敦煌古樂的研究從此得以順利進行。
1992年10月,敦煌文藝出版社與甘肅音像出版社聯合出版了席臻貫的《敦煌古樂》。敦煌古樂終于重現人間。1993年,江澤民總書記來甘肅視察時,欣賞了席臻貫破譯的25首敦煌古樂,在接見席臻貫的時候指出“可以考慮將其搬上舞臺”。1993年11月,已經更名為敦煌藝術劇院的原甘肅省歌舞團帶著《敦煌古樂》的舞臺藝術赴香港參加香港藝術節,給香港帶去了驚喜與興奮。
1994年,正當《敦煌古樂》進一步完善,進入第四屆中國藝術節排演的緊張過程中,席臻貫患膀胱癌住進了醫院。在病重期間,他忍著劇烈的疼痛,還是念念不忘《敦煌古樂》的排練,用各種方式指導排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讓《敦煌古樂》能夠亮相第四屆中國藝術節。
離藝術節的開幕越來越近,席臻貫的病情也越來越嚴重。好不容易,終于等來了《敦煌古樂》作為甘肅入圍節目在黃河劇場上演,席臻貫強烈要求到劇場觀看,他要親眼見證自己凝聚心血和生命的成果。經請示省委領導和醫院的特別許可,席臻貫坐著輪椅進入劇場。那天晚上,李瑞環觀看《敦煌古樂》,演出結束后,席臻貫在輪椅上與所有演職人員一起受到了李瑞環同志的接見。李瑞環高度評價了演出,也充分肯定了席臻貫的這種工作精神。
1994年10月6日,在第四屆中國藝術節結束的半個月后,席臻貫帶著對敦煌古樂的眷戀與世長辭。
張炳玉對席臻貫的看重和惋惜,還寫成題為《走進“天門”揭破“天機”——記敦煌樂譜破譯者席臻貫》的紀念文章,1995年1月在《中國文化報》上發表。其中的三個小標題就足以說明他對席臻貫一生努力的敬重:“耗十年心血破譯千古之謎”、“奔走江南終使唐代樂器復生”、“他在輪椅上含淚聽著敦煌古樂”。

第四屆中國藝術節開幕式現場
文化之基層
張炳玉到文化廳工作后,對民間文藝和群眾文化也同樣重視,他作為體制內主抓所謂高雅藝術的官員,對那些通俗和流行的文化現象也采取了非常寬容的態度,并主張雅俗共賞。當時,在文化和文藝的理論界,曾一度掀起一場關于高雅文藝與通俗文藝之辯的爭論。有人對流行文化現象對正統文藝形式的沖擊憂心忡忡,有人甚至上綱上線。但張炳玉認為,包括通俗歌曲在內的通俗文藝形式,既然能夠在中國普遍流行,就有它能夠流行的道理,一些人的少見多怪會逐漸變為見怪不怪,甚至多見不怪。即使是被體制推崇的戲劇,也有個從民間走向廟堂、從通俗走向高雅的過程。他后來還認為,中國歷史上關于雅俗背向的歷史偏見實在是走向了一種誤區,對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構成了長期和深遠的畸形影響,也誤導了中國人的審美傾向。
群眾文化,也即今天所說的社會文化,它所關注和管理的是社會上或者說民間的非文化系統直屬的各類群眾性文化和文藝活動與現象。張炳玉基于對中外語言文學和藝術現象的深刻理解,也是從長期從事文化管理工作的經驗和感受出發,覺得體制內文化工作固然重要,固然擔負著主導文化發展方向,引領主旋律的作用,但社會上和民間的文化現象和文藝創作、某種文藝形式的流行,也更加發揮著一個民族文化傳承的真實作用。他在主持文化廳工作的10年中,甘肅的群眾文化也開展得有聲有色。
為了加強群眾文化工作,特別是農村文化工作,需要從基層選調干部充實廳機關的群眾文化處。這個時候,他想到了過去在基層下鄉督察群眾文化工作時認識的兩個人,一個是慶陽地區文化處群文科的干部李文華,一個是隴南群眾藝術館的干部曹銳。
張炳玉在慶陽下鄉時見過李文華兩次,印象是熟悉基層文化工作,文字功底不錯,很適合做機關工作。李文華調上來后,又發現她在文學創作方面也很有潛力。有一天,李文華給他送來一大摞文稿,戰戰兢兢地對他說:“廳長,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也不知道水平到底咋樣?您能否幫我看看?”張炳玉讓她留下了書稿。她走后,張炳玉就想:我們的干部本職工作雖然不是搞文學創作,但她能夠利用業余時間寫出了這樣的東西,我作為她的領導,應當支持。
隨后,他大概看了這部叫《重婚》的長篇小說底稿后,就給當時省文聯副主席、作家協會主席王家達打電話,介紹了情況,希望讓王家達先給把把脈,審讀一下,看能否達到出版要求。王家達接到書稿后,認真地看了一遍后,對張炳玉說:“稿子不錯,完全可以出版。”有了這個權威的說法,張炳玉就與出版社聯系,大概書名在那個時代就有沖擊力,加上書稿的創作又有著扎實的生活基礎,出版社也看上了這部長篇小說,并決定出版。書出版后,果然在當時出版發行冷清的環境下引發了不小震動,成為當時的暢銷書,甚至還出現了盜版情況。李文華本人也因此成為當時甘肅中唯一靠版稅致富的作家。當然,當時文藝界的一些人士,并不認同這部作品,主要是對它的內容不屑一顧。但著名評論家陳荒煤對這部作品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不過,這些都沒有影響《重婚》在市場上的暢銷。時隔20年之后,敦煌文藝出版社有一個再版長篇小說的計劃目錄,其中就有這部叫《重婚》的作品。
張炳玉對曹銳的認識要更早一些。1990年,他當時還在省委宣傳部任副部長,分管文藝工作,當時的省文化廳廳長因病去世,新的廳長還未配上。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推動全省農村文化工作,省委宣傳部決定與省文化廳聯合舉辦一次農村文藝調演。這次調演活動在慶陽開幕、在平涼閉幕。在慶陽調演期間,張炳玉看了隴南的《鶯鶯拷紅》,覺得這部傳統題材的小戲帶有荒誕的情節,很有新意,讓人眼前一亮。當時他就想見見編劇。這是張炳玉第一次見到在隴南群眾藝術館工作的曹銳。
張炳玉到文化廳后,對曹銳有了更多了解,所以就想到了把曹銳調來文化廳工作。曹銳調來以后,表現出了很好的專業水平。在做好群眾文化工作的同時,也時常被一些單位、企業請去編排輔導文藝節目,逐漸在社會上有了影響。在第四屆中國藝術節期間,作為東道主,除了上推入圍的8臺專業劇團演出的大戲外,還要上一臺群眾文藝節目的組臺演出。曹銳作為主力之一參與了工作。這臺群眾性演出節目在藝術節演出中,同樣受到觀眾的贊賞。
曹銳在工作之余,時不時寫一些散文和小戲曲,從中也看得出其文字功底。第四屆中國藝術節之后的一天,曹銳給張炳玉送來了最新創作的作品,表現以白馬人生活習俗為題材的舞劇腳本《白羽歌》。張炳玉當時吃不準,便利用在北京開會的機會把這個本子帶到北京,想請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長、著名舞蹈表演藝術家、舞蹈理論家資華筠把脈鑒定。資華筠當時正在住院,中午,張炳玉利用休息時間去看望她,并把《白羽歌》的本子帶給了她。張炳玉是資華筠為了編撰《中國舞蹈志》在蘭州出差時認識的,后來,因為欣賞她的文采,多有往來,也算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資華筠聽了張炳玉的介紹后,就在病床上看完了本子。看完后,她很激動,說:“這是個好題材,甘肅出了《絲路花雨》,如果再搞敦煌題材的舞劇,人們很自然地要和《絲路花雨》比照,這就要慎重。不妨另辟蹊徑,比如白馬人這個題材就很好。當然,這個本子還是初稿,顯得粗糙一些,需要進一步修改完善。”回到蘭州后,他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曹銳,并開始琢磨如何改這個本子。
為了把劇本改好,就想再吸收省內的一些藝術家,參與本子的修改。文學方面,吸收了省話劇團團長、著名劇作家姚運煥;舞蹈方面吸收了舞蹈編劇牟瑜、晏建中、陳泓。為了不受干擾,張炳玉把他們集中到位于郊區的地質研究所招待所,關起門來進行創作。一個星期之后,稿子改了出來,大家覺得比當初的稿子有了大的改進。稿子送相關范圍征求意見后再作了修改。反復多次后,方方面面都覺得比較完善了。唯一沒有確定的是舞劇的名字。大家都在想,該給即將出生的這個“孩子”起什么名。
這個時候,張炳玉也在考慮省內導演拿下這個舞劇有一定困難,就想在外省找一個導演。幾經周折,也走了不少彎路后,最后找到了大家都很滿意的沈陽軍區前進歌舞團編導、著名導演藝術家門文元。
排練過程中,張炳玉多次到排練現場看望演職人員。他對門文元既愛護演員又嚴格要求演員的扎實作風留下了深刻印象。排練過程中,他也想到了舞劇的名字:《悠悠雪羽河》。最后這個名字得到了門文元和其他編導的一致贊同。
舞劇排練成后,他們又請北京的舞蹈大家們來蘭州指導,包括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賈作光,中國舞蹈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長資華筠,總政歌舞團著名舞蹈家趙國政。專家們看后非常滿意,賈作光還即興賦詩一首。
歷經數載和省內外藝術家的共同努力,大型民族舞劇《悠悠雪羽河》終于正式立于舞臺。1999年國慶50周年大慶之日,繼20年前《絲路花雨》赴京參加國慶30周年獻禮演出后,《悠悠雪羽河》再次赴京,參加國慶50周年獻禮演出。后來,這個舞劇參加第六屆中國藝術節,并榮獲文華新劇目獎。
繼《悠悠雪羽河》之后,曹銳又陸續創作推出了隴劇劇本《官鵝情歌》《苦樂村官》、秦腔劇本《百合花開》《麥積圣歌》《西峽頌》等劇作,而且多數劇目都獲得國家大獎,曹銳也因此列入全國著名劇作家行列。
與《悠悠雪羽河》劇本創作過程相似,張炳玉對另一秦腔劇目《白花曲》也作了同樣的支持與推動工作。
《白花曲》作者包紅梅原來是隴南地區西和縣秦劇團的一個演員,創作《白花曲》的時候在縣地方志辦公室工作,劇本初稿完成后,幾經修改,最后在《甘肅戲苑》雜志發表,劇本發表后先后獲得全省劇本評獎二等獎,1991年獲全國少數民族題材劇本銅獎。這引起張炳玉的興趣。1994,文化廳決定把這個劇本搬上舞臺,并參加第四屆中國藝術節。這期間,劇作家包紅梅本人在中國戲曲學院進修學習,張炳玉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機會專程去看望了她并轉達了文化廳的意圖。
由于原劇本與第四屆中國藝術節對入圍劇目的要求還有距離,張炳玉就安排原省文化藝術研究所所長、劇協主席金行健和劇協副主席李遲共同參與加工修改。劇本修改后,張炳玉堅持修改者不署名,只作文學顧問。他的觀點是:我們的著名劇作家幫助基層劇作家修改本子也是對基層藝術工作的輔導、扶持。他這樣做,也許對金行健、李遲有不公的地方,但張炳玉惟有在內心希望他們能夠理解自己那個時候的初衷。
在后來的工作中,包紅梅還陸續創作了《魏孝文帝》《柳笛怨》《山妹子》等多部劇作。
(待續)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