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十字鎮:灰色與明亮的完美結合
胡艷麗
施奈德有著“庖丁解牛”般的技法,對牛的身體構造了如指掌,信手拈來的剝皮技巧令人毛骨悚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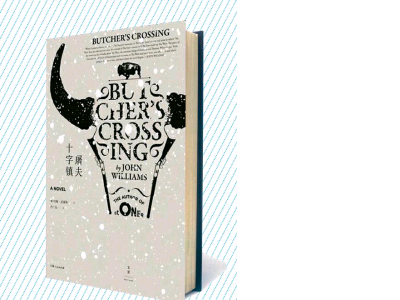
《屠夫十字鎮》講述的是一個渴望自由的年青人放棄學業,來到西部荒野探險,一路與打獵小組為伍,歷經身體與心靈的雙重磨礪,尋找自我、發現自我的故事。該書的魅力在于它有無數的棱面,從個人的自我發現角度,它是一個認知自我的故事;從生態角度,這是一首悲哀中孕育希望的歌謠;從市場角度,這是一部泡沫破碎回歸理性的警世通言;而若從社會發展角度,則是文明發展過程的一段血色插曲,偶然中存在著必然。
該書整體給人以干凈透明的印象,但這種印象卻不是一步成形的,而是要歷經思維的復盤,慢慢品味,才能在混亂、無序、殘忍、貪婪、癲狂、善良、欲望等一系列復雜的印象中慢慢浮現,變得百味雜陳后,形成我們對該書唯一的印象。
這本書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暗沉。小說的開篇便營造了一個灰色蕭條的氛圍,悶熱的天氣,有氣無力的馬車,看上去殘敗破落的小鎮,以及和小鎮的蕭條相匹配的面貌蕭條的人物。主人公安德魯斯,是書中的第一抹亮色,他帶著月光一般的心靈底色,來到了這個遠近聞名,卻又名不符實的屠夫十字鎮,期待與西部荒野的一次親密接觸。然而這番出行,卻令他五味雜陳,一方面他完成了此行的目的,進行了遠足,參予了打獵,經歷了各種困難,獲得了期望的經歷;另一方面,他的內心卻在一次一次的磨礪中長出了一層一層的繭子,理性中多了份沉重,也因沉重而多了一份糾偏后的堅定。
對該書的第二重印象是殘忍。這是書中的“高潮”部分,四人打獵小組在歷經艱難后,終于找到了“傳說”中的牛群。米勒打獵的技術爐火純青,“擒賊先擒王”的心理戰術也令他成功控制了整個牛群,從威風凜凜的成年公牛,到初生待哺的童稚小牛,任其獵殺。而施奈德有著“庖丁解牛”般的技法,對牛的身體構造了如指掌,信手拈來的剝皮技巧令人毛骨悚然。不知多少牛的死亡成就了這一對“黑白雙煞”。當數百只、上千只野牛相繼倒下時,米勒嗜血的一面越發突顯,人性消減,獸性勃發,殺成了唯一的目的。欲望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形變,但相同的是,缺乏理性的約束、靈性的指引,人會變成魔鬼,成為屠戮生命的機器。
與書的開篇相呼應的是書的后半部分,比書的開篇更蕭條。剝皮人施奈德不幸死亡,一車牛皮付之東流,曾經的冷血殺手米勒回到屠夫十字鎮后,無法面對牛皮市場崩潰的現實,精神隨之崩潰,不可一世的牛皮商人麥克唐納傾家蕩產,積攢了一冬的牛皮被瘋子米勒付之一炬。一場鬧劇的結束,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在大自然沒來得及報復這些獵殺狂人之前,市場已經事先啟動了修復程序,一切虛妄終歸消散。
對該書的第三重印象才是明媚與干凈。在故事戛然而止時,再去回味書中行云流水般的結構,體味安德魯斯的精神成長之旅程,一切才清晰浮現。安德魯斯的冷靜、堅忍與尊嚴,是在與老一輩獵人的對比中展現的,他的欲望在節制中有理性,他的教養與智識,令它對眼前發生的一切有了較為清醒的認知。他對精神的追求遠遠高于米勒等人對人之初欲望簡單的滿足。如果說米勒所有的人生經驗,全部服務于獵殺野牛,那么安德魯斯的激情與智慧,則用于成就生命的夢想。
在書中,西部荒野只是一個意象,它象征的是人們對自由與野性的向往,是美國夢的一部分,指引著年青人去探險,放逐生命,挑戰生命的潛能。然而,這種憧憬和希望又是粗糙非理性的,是青年人理性未開,懵懂時期的一種遙遠召喚,這恰如當時的美國夢一般,需要冷靜下來,去思索發展的意義,思索人與自然、社會、環境、市場的終極關系。該書余韻的明亮干凈,在于它令我們在復雜的人性中透見了精神的光,留下了希望,盡管這種希望以沉重為代價,以生命為代價。復雜之后再見單純,殘忍之后復見良善,絕望之后再見希望,總能給人以震撼,而之前的灰色與血色,亦隨之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