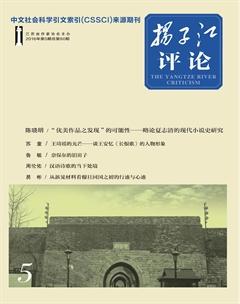從新見材料看穆旦回國之初的行跡與心跡
對跨越現當代階段的作家研究而言,如何更為廣泛地獲取文獻資料,已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各類文獻之中,檔案又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十余年前,我開始著手撰寫《穆旦年譜》的時候,即曾感到非常之困惑,因為除了少量書信、日記外,坊間極少穆旦的自述類材料。穆旦生平之中的若干重要轉折點,幾乎都是模糊不清的。最終破解這種狀況的,是穆旦個人檔案以及南開大學當年的相關檔案。它們不僅厘清了穆旦的諸多生平疑點,也比較深入地凸顯了穆旦與新中國文化語境之間的內在關聯a。
近期,孔夫子舊書網的拍賣平臺出現了兩批穆旦(以及其夫人周與良)留學歸來之初的材料。本文所述及的是1953年1月至4月間的多種回國留學生登記材料,以及政府部門(廣東省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人事部等機構)的相關函件。這些材料原本是應歸入相關檔案卷宗的,不知何故流散書肆之間b。它們與原有檔案略有重疊,更多的則是新見材料,有助于更為精細地呈現穆旦回國之初的行跡和心跡。網絡交易平臺之于材料發掘的意義、新材料之于作家研究的特殊效應,于此都可見一斑。
一、 廣東,新起點
此前,穆旦回國之初的行跡出自妻子周與良的回憶:1953年初,經香港、九龍、深圳、廣州、上海,抵達北京。當時,國內親戚替夫婦兩人辦了從香港入境的手續,但香港只允許回大陸的旅客過境。當郵輪到達香港附近,他們就被中國旅行社用小船送到九龍火車站附近。上岸后,又被香港警察押送到九龍車站——
在車站檢查很嚴,然后關在車站的一間小屋里,門口有警察,不準出屋,停留了幾個小時,由香港警察押送上火車。火車開了一小段,又都下車,因這段車軌不相連,走了一小段,再上火車,在深圳停留了一天,等待審查。然后去廣州,住在留學人員招待所,填寫了各種表格,住了一周審查完畢,才離開廣州。c
新近材料充實了在廣州時期的信息。穆旦夫婦于1953年1月14日抵達廣州,所見最早的材料則是1月15日妻子周與良填寫的《回國留學生登記表》和1月16日穆旦本人填寫的《回國留學生登記表》 (按:所有的材料,都是用本名“查良錚”)。兩份表格的版式內容是相同的,如下為穆旦表格的主要內容:
國內學歷及專長學科: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專長于詩的創作及批評,在國內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主編)印有詩集一冊。
國外學歷及專長學科(中外文):芝加哥大學英文系碩士,專攻英詩,戲劇,創作方法,及俄文。
國內工作經歷: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助教。緬印遠征軍翻譯官及英文秘書。中國航空公司職員。沈陽新報編輯(此報后被蔣政府查×d)。聯合國糧農組織編譯。
國外工作經歷(中外文):聯合國糧農組織駐東南亞分處(設在泰國)編譯。美國函授學校英文教員。
工作志愿:教書或編著工作。
國內重要社會關系:巴金(“作家”、“友人,并曾代出版創作詩集”)、馮至(“教授及作家”、“師友,因為都寫詩,所以很熟”)、王佐良(“外國語學校教授”、“同學及好友”)、杜聿明(“國民黨反動派軍人”、“曾在他部下做翻譯及秘書”)。(說明:此處表格比較細,非原文完整照錄)
國外重要社會關系(中外文):陳時侃,同學,想回祖國卻一時回不來。
通訊處:離招待所后——北京北新橋小菊胡同4號;永久——天津桂林路20號轉。
在目前所見穆旦所填寫的類似表格之中,這一份算是最簡單的,僅一頁。表格內容也與日后的諸種表格有一些重要差別,比如社會關系一欄,區分為國內和國外,而不是“進步的社會關系”和“反動的社會關系”——日后,杜聿明即是一再地被填入“反動”一欄之中。至于“國外重要社會關系”一欄所填寫的陳時侃,日后未再出現在穆旦所填寫的各類表格之中。
填寫這兩份材料的時候,穆旦和妻子應該還在廣東。上述兩份登記表均蓋有“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公章,而且,新材料中,有1953年1月17日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函件兩封[(53)財留 內字第六號/第柒號 公元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七日e],函件為介紹函,送達機關不詳,穆旦和妻子為分別填寫,函件為同一款式,上面還印有文教廳廳長杜國庠和兩位副廳長蕭雋英、秦元邦的名字,以穆旦材料為例,函件正文為:
茲有回國留 美 學生 查良錚 攜家屬 人由廣州經上海赴天津 特介紹前來請予接見指導并簽發證明以便該生依法辦理居留手續為荷。
穆旦夫婦在廣州的更多信息,暫時已經無法獲得。稍后北歸途經上海時,穆旦與巴金夫婦、王勉等文化界人士有過碰面,但在廣州時期,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回憶記載。穆旦夫婦離開廣州一個月之后,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曾有信寄到北京,但原信未見,目前所見只有相關部門2月20日發出的一則短函——
查良錚、周與良同學:
茲將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給你們的信件一封轉去。因該信寄到時信封已破裂,故特加封寄去,希查收。
又你們前次離京時,事前未曾與我們聯系,不知你們的計劃如何?是否仍擬回北京?你們進行工作的計劃如何?希來信報告我們。
司章
二.廿
實際上,更確切地說,目前所見,是一份寫有“存底”字樣的函件。而“司章”也只是手寫體,而并非某司的公章。從此后的一些函件來看,這個“司”應該是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學校人事司。信封“破裂”自然是一個很微妙的說辭(或有信件檢查的行為),填寫各種表格、按照組織的要求“依法辦理”各種手續、及時向組織報告行程和未來計劃,這都是回到新中國的穆旦夫婦所不得不面對的新的現實。
二、開始填寫“認識”“動機”與“感想”
新見材料之中,接下來的是1953年2月21日的四份登記表。當日,穆旦填寫了《回國留學生登記表》 (回字第938號)、《回國留學生分配工作登記表》(回字第938號,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制),前者比較簡略,為A3紙大小的油印件(中縫對折),后者則是更為正式的打印件,且膠裝成冊,內頁共有5版。周與良亦填寫了兩份相同的表格(回字第939號)。
比照廣州時期,抵達共和國首都之后所填表格在內容版塊上有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具體填寫亦有變化。先看《回國留學生登記表》的主要內容:
專長:英詩;戲劇及小說的創作方法;俄文及文學。
工作志愿:文學研究工作或綜合性大學內的教書工作。
回國日期及經過情形:1952年12月返國。經過九個月的手續,請了律師和學校幫助,才得以和愛人一同返國。
詳細學歷及履歷(請注明年月):此次將1929年進入南開中學之后的主要經歷一一列出,具體從略。
著作:探險隊(詩集),旗(詩集),穆旦詩集(詩集),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內有自己的詩二首)。
社會關系(有什么至親好友?姓名、職業及政治面目):周叔弢、王佐良、江瑞熙、杜運燮、袁水拍、巴金、李廣田、梁再冰。(說明:此處內容較多,具體信息從略。)
參加過什么黨派或社會活動:西南聯大南荒文藝社,芝加哥中國同學學術討論會。
“回國日期及經過情形”“詳細學歷及履歷”“參加過什么黨派或社會活動”等版塊為新增,“專長”“工作志愿”“著作”“社會關系”等版塊的填寫則已有微妙的變化。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回國留學生分配工作登記表》雖是同一日所填寫,一些相同版塊的填寫卻也有差異。有的涉及史實,比如回國時間由1952年12月變為1953年1月——綜合各種材料來看,后者是準確的。而有的變化,綜合穆旦檔案中的各種表格來看,則可能是時勢使然f。
當然,更引人注意的是內容版塊上的變化。其中,“國內外社會關系”一欄,分“進步的”和“反動的”兩格,前者共填有9位,人員和《回國留學生登記表》相同,但順序有變化,依次為:王佐良、杜運燮、江瑞熙、巴金、袁水拍、楊剛、周叔弢、梁再冰、李廣田。后者所填則是4位國民黨員:查良鑑(臺灣偽司法行政部次長,堂兄)、查良釗(印度德里大學教書,堂兄)、杜聿明(反動軍人,已被俘;在他部下做英文編輯)、羅又倫(臺灣,教他英文,朋友)。
“在國內外參加過何種社會活動”、“國內外詳細學歷及經歷”兩欄,均增加了“證明人”版塊,所填“證明人”依序有:杜運燮,北京新華社工作;李志偉,北京國際經濟研究所;周玨良,外國語學校教授;王佐良,外國語學校教授;楊剛,政務院總理辦公室;徐露放,中國茶葉公司;李舜英,中國人民銀行;江瑞熙,北京新華社編輯;周華章,同行返國。
更大的變化是增加了“回國經歷情形”“在國外對新中國的認識及回國動機”“你在回國后有何感想”等版塊。“認識”“動機”與“感想”部分,均是預留了整版的篇幅,顯然不是兩三句話就能交代清楚的,而需要對自己進行深入的思想解剖——由此也可以說,“名為‘登記表,實際上就是一種交代材料,它要求個人交出自己的過去、現狀以及對于未來的想象,將自己的一切置于時代的掌控之下,再也不能為內心保留某種秘密。”g至于“回國經歷情形”一欄,預留的也有半頁篇幅,實際填寫時也涉及思想方面的內容。
需提及的是,坊間新見的這份《回國留學生分配工作登記表》,并非穆旦本人所填寫,而是一份抄件(因內容較多,后幾頁字跡較草,出自何人之手暫不可知)。南開大學檔案館現存有一份由穆旦本人本日所填寫的登記表(這也是此前所見穆旦回國之后最早的材料),兩者內容相同,可證明此份抄件的真實性h。先前在撰《穆旦年譜》時,因為一些因素的限制,檔案材料對思想認識部分的內容引述不夠,現一一摘錄如下(謄抄件在文字上略有出入,這里錄自南開大學檔案館所存由穆旦本人所填寫的材料):
回國經歷情形?
我和愛人同在美國讀書,她讀植物,我讀文學。我是要早些回來的,不過為了等愛人畢業,直到一九五二年三月她畢業了,才辦理返國手續。那是美帝已不準理工同學返國,這情形使我們焦慮萬分,不敢到移民局去聲請i,因為一旦被批駁,便有永遠不能離美的危險。和朋友們經常打聽消息和研究辦法的結果,決定了最好是繞道別國,假充到別國去居留。因此我便替愛人發了不下二三十封求職信到各國,如果她能找到事去,我便先行返國。但是歷經四五個月的求職,只有印度肯考慮,有希望,但終以路費問題而不果。此路既不通,我們便想第二個辦法,就是找人向移民局暗中疏通。好容易得知一位猶太律師,和他們很熟,通過他得知如有學校證明信,證明她所學的無實際用途而且美國不需要的,便有希望。以前教授是不肯寫這種信的,因為他根本不同情我們返國。以后看到我們歸意堅決,便寫了信。于是通過這信和律師的人情,我們便于十月初獲得移民局的準許返國。但香港過境,又有問題,必需有卅人以上才能團體押送過境,因是我們又由十月初等到十二月底,才得以搭船離美。這等待是令人焦急的,因為恐怕艾森豪威爾上臺后,辦法加緊,我們或許走不成的。
在國外對新中國的認識及回國動機?
在美國住了三年半,逐漸對它加深了認識,令人不能忍受的感覺與日俱增,終至于深惡而痛絕。所謂自由,平等,博愛,每天掛在說教人,報紙和廣播員的嘴上,流露在無恥的中產階級的自滿自足的意識里,可是實際上,就是他們在干著最不自由,最不平等,最不博愛的勾當。人們做著工資的奴隸,一般人用以品評人的標準,是看他賺錢多少,有多大努力,有多少辦法去壓榨人,去“損人利己”。上司(boss)的專制和蠻橫,已經是被認為自然間固定法則一般地被接受著,在上司下面工作的人們,便每天戰戰兢兢地過著日子。美國雜志報章上每講到別國人民時,總是用著輕蔑的開玩笑的口吻,像是大人講著不長進的頑童一樣;并且以黑當白,以白當黑,對于凡是好的事情(像民族獨立運動這么明顯的好事)都盡量予以侮辱。在美國國內,有多少民族,便分成多少被歧視的層次;做帝國主義最久的民族,便最受尊敬。美國的法律,更是扶強欺弱。土匪和騙子,已經成了可尊敬的法律制定者,并且做著各種負責的職務。就是這樣的一種社會(它的貧窮和多種腐化墮落的現象尚未列舉),給我呈現了資本主義社會極端發展的典型。而就是這種社會,美國人還要贊美它,說它是“西方文明”的堡壘,其所自炫的“文明”程度和“言論自由”,簡直令人作嘔。
我自己是學文學的,在文學上,更覺得所謂的“西方文明”是完全破產而且日趨沒落了。英美資產階級文學已由十九世紀末的沙龍和象牙塔走出,現在是走向墳墓,以歌頌“死”和神秘主義為唯一的題材了。文學作品中一切的人生問題,都要提到形而上的水平上討論,才能顯得“高深”,才“值得注意”。實際上已經只剩了幾個空洞僵死的名詞在那里耍來耍去;就是專門追求技巧的作家,他所自詡的技巧也因為沒有活的內容,而變成寒酸小巧的裝飾。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凡是不肯接受共產主義的“西方”作家,無論以前他有怎樣似乎是堅實的作品,現在都在腐化和沒落著,他的作品也隨著他的反動傾向日益黯淡和解體了。(如Auden, Spender, Steinbeck, ……j等)。
由于對于帝國主義世界完全厭絕,我對于和它完全相反的,一切都蓬勃合理向上的共產主義世界,便充滿了傾慕和渴望。我愛祖國,尤其是因為她在共產主義的世界里。從國內朋友的信中,從寄到的報紙雜志中,我覺得自己的理解和猜想完全得到了證實。在美時和中國同學談話,常常為了辯護及解釋祖國一切合理的設施,爭辯得面紅耳赤。以后覺得如此下去,自己會處于危險的地位,便自動少說。但因此,自己更難過日子,而對于白華學生和那欺騙蒙昧他們的教育以及他們反動的階級本質,也更加厭惡。在最后九個月中,我感覺無法再在美國呆下去,再呆下去,自己會瘋了的!
你在回國后有何感想?
回國以后,立刻感到祖國的溫暖和親切;她嶄新的光明的面貌使我歡快地激動。在個人具體的認識上,我覺得有如下幾方面的提高:
(一)回國以前,只抽象地理解了共產黨的領導是對的正確的,既然有共產黨領導,人民就應該跟隨,好像這跟隨是被動的,被拉著走的。回來以后,才深切感覺到群眾的自發自覺的力量。原來群眾一旦得到了主動力,就像大機器的輪子一旦轉動了起來,它就會推動自己的各部分轉動起來。可以這么大膽地說:好多事情,全是在群眾理解了黨的原則以后,自己推動自己做出來的,而領導人物也在其中卷進來跟著群眾學習和進展了。從這種性質的社會運行中,我才理解到我們民主精神的真諦,和黨的正確的領導的真諦。
(二)回國以前,知道“人吃人”的社會制度被打倒了,人再也不壓迫人,歧視人,彼此的羈絆都解除了。但是否人就按照“你不管我,我不管你”的個人主義態度活下去呢?回國以后,才發見原來人在被解放以后,并不就停在那里,而是要積極爭取人的友愛和溫暖。如果有所謂永恒人性的話,這爭取友愛的心才是正確人性的表現。我們的社會已成了一個非常融和親愛的大家庭。在這里,如果你還保持個人主義(這在以前我認為是文藝復興“解放人性”的正確人生觀),那便完全暴露了你的僵硬和殘暴的本質。由此我認識了,只有集體主義的人,才是“人性”的真正的表現。集體主義的好處,只能從我回國后的切身感受中獲知。這一點也證明了光是念死書,是獲得不了很多知識的。
(三)看到和接觸到一些人,對于他們的沉著踏實和不憚煩的工作和求知的態度,令我異常欽佩。這是在我們新社會中普遍建立起來的工作態度,是以前和國外所看不到的。我深切地感覺自己應該向他們學習。
這份材料有多處文字下劃有紅色波浪線(不見于抄件),除了上述材料明確標出的外,之前“有哪些進步的社會關系”部分,李廣田及相關說明信息(云南大學副校長,共產黨員,朋友)下劃有紅線,“有哪些反動的社會關系”部分,查良鑑、查良釗、杜聿明、羅又倫這四人名字下均劃有紅線,“國內外詳細學歷及經歷”部分,也多處劃有紅線。看起來,所劃記的都是比較重要的信息,應是出自材料審閱者之手k。
三、與妻子材料的對照
回國僅僅一個來月的穆旦,似乎已經比較熟諳新中國的話語方式。這種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話語方式,在穆旦日后的諸多登記表、交代材料中更是反復出現。今日讀者在面對這樣的材料時,往往會有該如何認識的疑惑。
綜合比照,就某些方面而言,材料中的表述還是有其現實依據的。穆旦在美國時期的思想狀況,日后在妻子周與良的回憶材料中有較多描述——
當我在辦理回祖國的手續時,許多好心的朋友勸我們:何必如此匆忙!你們夫妻二人都在美國,最好等一等,看一看,不是更好嗎?當時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萃集了許多中國優秀的人才,如學物理的李政道、楊振寧等人,學文科的如鄒讜、盧懿莊等,都是我們的好朋友。學理科的同學主要顧慮國內的實驗條件不夠好,怕無法繼續工作;學文科的同學更是顧慮重重。因此,許多同學都持觀望態度。當時良錚經常和同學們爭辯,發表一些熱情洋溢的談話,以至有些中國同學悄悄地問我,他是否共產黨員。我說他什么也不是,只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在抗戰時期他親身經歷過、親眼看到過中國勞苦大眾的艱難生活。l
穆旦所謂“在美時和中國同學談話,常常為了辯護及解釋祖國一切合理的設施,爭辯得面紅耳赤”,和妻子回憶中的“經常和同學們爭辯”一節,大致上應是相通的。而妻子提到的“觀望”的說法,穆旦因親身經歷舊中國“勞苦大眾的艱難生活”而“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說法,以及穆旦本人所謂從國內來信受到鼓舞的說法,亦可見于比穆旦夫婦稍早回國、曾在南開共事的巫寧坤后來的回憶錄m。同時,鑒于“回國”事實上是穆旦后半生具有轉折意味的行動,也有理由相信他對于新中國的認識(“她嶄新的光明的面貌使我歡快地激動”)在總體上亦是有其心理依據的。至于那些漫衍開來的“思想認識”,在《穆旦年譜》中,我曾經結合穆旦所填寫的《我的歷史問題的交代》 (1956年4月22日)中的一個細節給出過說法:
且不說文字中為自己所作的諸種曲意辯護,說一說當時所遺留下來的一個細節:在交代出國前的思想狀況時,穆旦寫下了這樣的對時局的認識:“我原已準備迎接解放,因為當時我認識到,共產黨來了之后,中國會很快富強起來,我個人應該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高興,他們翻了身,個人所感到的不自由(文化上,思想上)算不了什么,可以犧牲。”這段文字旁有四個字的批語:“純粹扯淡!”在我看來,它以一種粗鄙而又地道的語言涵括了那些深諳政治文化奧秘的審閱交代材料者對于穆旦的“思想認識”的基本看法。因此,在運用這類檔案材料時,筆者盡量只選取其中的事件線索,而剔去那些枝枝蔓蔓的“思想認識”。當然,即便沒有“純粹扯淡”一類批語,相信今天的讀者對于此類材料自會有明晰的判斷,不致迷失。n
同時,我在先前的《穆旦年譜》等書寫作時,未看到穆旦妻子周與良的同期材料,無法采信。現在看來,穆旦妻子周與良所填寫的相關表格亦是一種參照。周與良1953年1月15日所填《回國留學生登記表》的“國外重要社會關系”一欄,同樣也出現了陳時侃(“設法準備返國”)。《回國留學生分配工作登記表》 (回字第939號)的“國內外社會關系”一欄,僅填有“進步的社會關系”,“反動的社會關系”一欄為空白。其他的部分內容是:
回國經歷情形?
自1952年3月即開始辦理回國手續o,但美方移民局已有不準理工科的中國留學生回國的規定,故而自三月畢業后即向東南亞各國謀教書工作。寫了很多求職信,只有印度德里大學回信說有個職位可以考慮,但后又因路費問題而未成功。后來沒有辦法只好冒險向移民局申請,并且經過多方面的探詢,得以認識一位猶太律師,他是和芝城移民局人非常熟悉的,因此便請求這位律師幫助,并且要了學校的成績單和很費力才得到的主任教授的一封信,向移民局解釋我的所學是沒有實際用途,在美國也找不到適當工作的,經過這幾方面的努力,總算得到移民局的離境許可;但香港不發過境證,必須要等卅人的團體過境證,因此又由十月初等到十二月廿號才能成行。
在國外對新中國的認識及回國動機?
在國外對新中國的認識
(一)從國內親友們寄去的信,書報和雜志上,知道新中國的一切都走向合理和繁榮,以前那種人吃人的社會被打倒了,而代以自由和平等的社會制度。
(二)不過對于聽到的開會太多一事,不甚了解。學習會上不知學習些什么,對于科學研究工作,不知是否有妨礙,又考慮到自己在開會時無話可說。
回國動機
(一)自己是中國人,本來在出國前就想學成回國的。
(二)更加看到祖國在革命后一切都走向合理和繁榮,更愿意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
(三)在美時見到白種人歧視和迫害中國人和一切有色人種的現象,深加痛恨,從而更加強了自己對于祖國的熱愛。
你在回國后有何感想?
(一)入深圳后,立刻感覺到工作人員的態度和藹可親和認真,后來到了別的城市也有同感。
(二)在各方面見到的人們,無論是老人,家庭婦女和小孩,無論是那一種工作崗位的人都有很高的政治認識和興趣,并且都有向上學習的熱忱,這是和以前的情形大不相同的。
(三)對于祖國的建設進展,雖然尚未有機會親眼見到,但僅自傳聞和報章已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比照穆旦所填寫的內容,“回國經歷情形”版塊在細節敘述上略有出入,語言也更簡潔,但大體上還是相同的。“在國外對新中國的認識及回國動機”“你在回國后有何感想”兩大版塊,一些細節表述有其相通之處,看得出,兩人在填寫材料時應是有過溝通、協商,但總體上卻又可謂差別非常之明顯。理工科出身的周與良博士文字簡潔,沒有枝枝蔓蔓的“思想認識”,似乎可以說,她顯然還不熟悉新中國在思想認識表述方面的語體風格,也并未決心將自己交出去——實際上,關于“開會”(“學習會”)的一段,所暴露的正是對于未來的某種隱憂。
四、“我在答應此事時心中有矛盾”
表格已經填寫了不少,工作卻是還沒有著落。新的材料繼續提供了一些細節。
1953年2月21日穆旦夫婦所填寫的分配工作登記表上,“工作志愿”一欄,均只填有地區,而沒有具體的單位意向:穆旦填的是北京、華北區;周與良填的是華北區綜合性大學、北京科學院。看起來,新中國的首都北京(而不是南開大學)是其工作的首選。
“今后的職業問題”如何決定呢?妻子周與良日后的回憶并沒有敘及當初抉擇的情形。當時在北京新華社工作、曾被穆旦列入“進步的社會關系”的梁再冰,稍后在一份檢舉材料的說明或可參考:穆旦在北京等待工作期間,和她、杜運燮、江瑞熙等友人就此有過商量——
在談到他今后的職葉問題時,向我們表示,他不愿到學校去教書,或作機關工作,只想作一個“個人”職葉p文學翻譯,翻點東西拿稿費。同時,我們知道,他在美國時把俄文學得很好。當時我們都反對他搞“個人”翻譯,勸他到學校教書,以便更快地改造自己。q
若是,那就正如前述幾份表格的“工作志愿”所填寫的“文學研究工作或綜合性大學內的教書工作”,兩項內容之中穆旦原本是更傾向于前者。但實際上,如朋友們所勸誡的,“‘個人翻譯”已不合時宜,“改造自己”要緊;而且,文學研究工作看起來也不好找。穆旦本人稍后在交代材料中也曾敘及抵達北京之后的情形——
到北京后即向高教部報到,結果派我到南開大學英文系。我在答應此事時心中有矛盾。自覺寫作和研究最適合自己,而教書,過去十多年前教過,頗為不佳,現在口才及能力是否勝任,毫無把握。但不教書似又無他項工作,而且南開大學又可和愛人一起工作,因此便答應了。r
新見材料中,有1953年3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致中央人事部的函件一封,看起來,其時穆旦夫婦已經決定同去南開任教了——
事由:請調新從美國歸國之留學生查良錚與周與良去南開大學任教
發往機關:中央人事部
發文日期: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
函文: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
茲接南開大學二月二十一日(53)津南字第一四一號來文略稱:該校外國語文系英文組及生物系植物組均需增聘教師一名,尤以“植物病理”一課一直無人擔任。近悉新從美國留學歸來之查良錚與周與良二人能分擔以上兩門課程,請予洽調。等語。特轉請你部考慮調給,并希見覆。
新見材料中,還有1953年4月6日,關于穆旦夫婦的《回國留學生分配工作意見簽》(編號分別為133、132號)。這并非由穆旦夫婦本人所寫,而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第三局簽發的材料。其中,關于查良錚(穆旦)的處理意見有三條:
(一)1940.7.西南聯合大學(原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畢業后曾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任助教一年半……(說明:以下為具體經歷,從略)
(二)查的家庭關系較簡單,但社會關系很復雜,認識一些政府負責人及教授,如楊剛、袁水拍、周叔弢、李廣田等,亦認識一些極反動的偽國民黨匪幫,如其堂兄查良鑑(國民黨員),臺灣蔣匪司法行政部次長,堂兄查良釗(國民黨員),在印度德里大學教書;杜聿明(國民黨員),反動軍人,已被俘,查曾在他部下做英文編輯;羅又倫(國民黨員),現在臺灣,查曾任其個人教師達二年之久。
(三)中央高等教育部來文調查良錚及周與良去天津南開大學任教。本人亦同意去該校任教。當否,請示。
關于周與良的分配工作意見簽的“處理意見”部分亦是三條,行文也是個人經歷、家庭及社會關系、工作單位去向。兩份材料的審核人均為董××,其在穆旦材料上簽有:“此人關系經歷復雜,任教較為妥當”;在周與良的材料上則簽有:“此人系干部子女,雖其愛人關系經歷復雜,任教尚可。”局長批示欄,則僅有簽名和日期:“宋誠 4.17”。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的人員所簽發的處理意見,自然是基于穆旦夫婦本人所填寫的材料。在1953年初這個時間節點上,日后盛行的組織審查、群眾大會或個人檢舉的情形尚未出現。“進步的”或者“反動的”社會關系的界定與落實,首先源自本人的交代。以此來看,回國之初穆旦所填寫的這些材料,除了前述某種現實心態的印證外,也顯示了他對于新中國、新社會的單純看法:如實交代“歷史問題”,積極交出自己。當然,后續歷史事件充分表明,作為一種流行的政治意識,“社會關系”對于個人的影響顯然是非常深遠的,即便是家庭成員,也會陷入“不公正的”態度之中s。
大抵是因為人事部相關領導未及時簽署意見,穆旦夫婦的工作一時之間無法落實。新見材料中,還有1953年4月穆旦夫婦與人事部相關人士的往來函件。4月14日,查良錚、周與良夫婦致函人事部的“存德同志”,信函中文為:
約于兩星期前我們曾寄部一函,告知我們經考慮后已做的決定,請部中寄我們對南開大學的介紹工作函一封,惟迄今未得答覆。不知是否該信遺失,或有其他緣故,因特再函詢問,請予告知為感。
“存德同志”即上述關于穆旦夫婦的《回國留學生分配工作意見簽》的主辦人佟存德。4月18日,佟存德撰稿,并于4月22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第三局二科簽發文件(發文 乙字 2516號):
收文機關:周與良、查良錚同志
事由:函告已同意他倆去南開大學任教
函文:
關于你倆去南開大學任教事,已經批準。將我部的介紹信已送中央高等教育部,并已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轉南開大學,南開大學接此信后,即可通知你們上班。特此函覆。
此致
敬禮!
中央人事部 三局(公章)
四月廿二日
其實,在穆旦夫婦以私人名義向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的工作人員詢問情況的前后,南開大學與中央相關部門也在就穆旦夫婦工作事宜進行協商。查南開大學相關檔案,4月10日,南開大學收到高教部學校人事司函(高人發446號),內容為介紹查良錚、周與良到校工作,并附工作登記表2份。22日,人事科有記錄:“材料轉來,本人尚未到校,擬通知本人即來校工作。”23日,學校批示:“通知本人到校并通知外文與生物系速與本人安排工作。”25日,學校致函穆旦、周與良夫婦,對兩人的到來“至表歡迎,并已預為安排住處,特函奉達。讓我們攜起手來共同為祖國的教育建設事業而奮斗。”
1953年5月中旬,穆旦夫婦正式到南開大學工作,穆旦在外文系英文組任教,周與良被分配到生物系微生物教研室。之后的故事則是讀者比較熟悉的了,穆旦在南開過得頗不順心:1954年即卷入“外文系事件”;1955年在南開大學的肅反運動中,當年參加中國遠征軍的問題重新被提出,成為肅反對象;1958年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并被判處管制,逐出講堂,到南開大學圖書館監督勞動……
實際上,并不用說更遠時候的遭遇,就在1953年暑期,穆旦即曾因自覺“實在無教書才能”而感到“情緒消沉”——
1953年5月中到南大,這是我參加革命工作的開始。但上課一二次,即對自己的教書能力異常灰心,無英文口才。一星期后改換課程,為重點課,又無教學法,更無法應付。一月后即暑假,決意辭去教書職,屢與系領導表示,未獲準。領導責備我不努力,我則認為領導不理解我實在無教書才能,因此情緒消沉。在美國時的一腔熱情,回國后反而低落了。t
余論 “精讀過俄國文學”
按照穆旦本人的交代,從1953年1月回國到該年暑假,不過短短幾個月,原本“一腔熱情”的他卻可謂經歷了從積極投合到矛盾猶豫再到“情緒消沉”的過程。這番自述的可信度有多高,自是一個問題。穆旦的實際教學情況如何呢?友人回憶中有穆旦和學生交流不暢的記載u,妻子周與良回憶里說的卻是穆旦“課教的好”,“受學生歡迎”v。對此,一般讀者顯然也是難以準確辨明。不過另一點可以確認的是,自從1953年底出版第一部譯著到1958年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止,穆旦共約出版了譯著25種(包括出版改制之后新印的),“查良錚”的譯名給新中國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從翻譯的角度再回看這批新見材料,也還會有些細節可資進一步追索。比如說,有一個事實基本上未曾觸及,那就是“俄文”。在目前所見的穆旦回國之初所填寫的第一份表格《回國留學生登記表》(1月16日)中,“專長學科”部分最末一項填的是“俄文”。及到2月21日所填寫的《回國留學生登記表》《回國留學生分配工作登記表》的“專長”一欄,最末一項略有補充,填的是“俄文及文學”(后者的學習經歷部分,在芝加哥大學階段亦有“俄文及俄國文學”的內容)。但在4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第三局簽發的《回國留學生分配工作意見簽》之中,關于查良錚(穆旦)的處理意見之中,“所學科目”僅有“英詩,戲劇和小說創作方法”,“俄文”并沒有抄錄在列。以此來看,大致上可以說,回國之初的穆旦,并未將“俄文”置于更高的價值等級——看起來更像是附著于英文之后的一種點綴。而在官方的辦事人員眼中,懂“俄文”似乎也并非一項特別的才能,思想問題(“關系經歷復雜”)才是最緊要的。
但是到了1953年6月,穆旦所填寫的“高等學校教師調查表”(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且需報送教育部一份)之中,卻是有了非常重要的轉變,“俄文”頻頻出現——“俄文”被提到更醒目的位置,甚至有翻譯俄語文學理論教材方面的信息:
何種專長與技能:十余年前在大學讀書時,即專學俄文兩年。因此,除英國文學外,亦精讀過俄國文學。在國外時并以一年余在學時間攻讀蘇聯文學理論,等。
通曉何種外國文字,能否筆譯……:英文及俄文,可自由閱讀文學作品。英文有翻譯能力(中譯英)。中文——有創作經驗,曾出詩集數種,亦曾翻譯。(俄文英文翻成中文)。
曾從事何種研究工作,曾有何種著作、譯述:……蘇聯季摩菲耶夫教授所著大學文學理論教本《文學原理》,在譯出中,即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印出。按:本書已印出。
現從事何種研究工作?今后擬研究什么?對今后工作的志愿?:擬從事文學研究及介紹工作,其方面如下:(一)介紹俄國文學(二)研究英國美國文學,用馬列主義觀點予以重新譯定。(三)廣泛的文學理論問題。w
盡管穆旦妻子周與良的回憶早就指出,回國之初途經上海時,穆旦曾與早年好友、巴金夫人蕭珊談到學習俄文及翻譯俄國文學作品的打算,得到了蕭珊的積極鼓勵x;到達北京后,在教育部招待所學習并等待分配工作時,“基本上住在北京家中,日以繼夜翻譯季摩菲耶夫著的《文學原理》”y;但是,將這些行為置于上述穆旦回國之初的總體背景之下,也是別有效應:一方面,翻譯之于穆旦所具有的獨特的精神效應正在初步顯現,它陪伴穆旦度過了回國之初的矛盾猶豫乃至“情緒消沉”的時刻(日后情勢更為殘酷、嚴峻的歲月里,翻譯始終是穆旦的精神陪伴)。另一方面,它能更清晰地見出穆旦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精神世界的轉變——亦或可稱之為某種決斷,即確立了翻譯之于其工作乃至生命的意義。此后穆旦積極工作,大量譯著的順利出版,“自然得力于在平明出版社等出版機構任職的巴金、蕭珊等人的大力幫助”,也表明“穆旦的熱情并沒有虛擲,新的體制正在不斷構建途中的‘新中國以一種積極的姿態接納了他。”z于此,穆旦所謂“她(新中國)嶄新的光明的面貌使我歡快地激動”,也可謂有了非常切實的內涵。
2016年8月 長沙
【注釋】
a易彬:《穆旦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b兩批材料進入交易市場并完成拍賣的時間分別是2015年5月22日、2016年7月21日。坊間穆旦手稿、手跡類材料非常之少,故這兩批材料旋即引起了熱烈關注。
c參見周與良:《永恒的思念》,杜運燮等編,《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頁。
d此處有一字被所貼照片蓋住,疑為“封”。按:因本文所涉及的材料,多為手寫,凡字跡難以辨識的,均用“×”標記。
e周與良的材料,日期誤為“一九五一年”。另外,兩份材料,“財留”二字均不夠清晰。
f本文作者曾就多種表格之中的兩個細節予以說明:一個是“曾用名(筆名)”的填寫,即是否填入筆名“穆旦”;另一個是所列“證明人”、社會關系(進步的與反動的)或交往情況(“經常來往的朋友”)等部分的人員變化,認為其中都包含了“對于時代語境的感知”。參見易彬:《穆旦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15-416頁。
g參見易彬:《穆旦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頁。
h一般讀者顯然還不大能區分穆旦的字跡,若干材料之中,這份抄件以最高價(38900元)被拍走,反映了穆旦手跡在坊間受歡迎的程度。
i “聲請”當作“申請”。
j此處共用英文填寫了四位作者,最后一位字跡難辨認。
k在穆旦所填寫的其他材料上,如本文稍后提及的《高等學校教師調查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制定,1953年6月填寫),也有類似的紅色劃痕。
l周與良:《懷念良錚》,杜運燮等編,《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32頁。
m除了一些類似細節外,巫寧坤還寫道:“和大多數中國同學一樣,我是在國難和內戰的陰影下成長的,渴望出現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見《一滴淚》,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0-12頁。
n易彬:《穆旦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頁。
o周與良后來在回憶中說:回國申請1950年就已開始辦理,但美國移民局一直到1952年才批準,見周與良:《永恒的思念》,杜運燮等編,《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頁。
p本段兩處“職葉”當作“職業”。
q1955年11月26日,肅反期間,梁再冰寫了一份檢舉材料:《關于我所了解的查良錚的一部分歷史情況以及查良錚和杜運燮解放后來往的情況》。
r據穆旦檔案之《歷史思想自傳》(1955年10月)。
s周與良的大哥、著名的歷史學家周一良在穆旦逝世很多年之后曾有回憶:“我們家大多數人對他過去的情況都不夠了解,因此他每次到我們家來,當大家(兄弟姐妹十人中有六個黨員,兩個民主黨派)歡聚在父母身邊,興高采烈,高談闊論時,他常常是向隅而坐,落落寡歡。許多年中,我去天津,記得只上他家去過一次。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我們對他的態度是非常不公正的,感到非常內疚。”見周一良:《鉆石婚雜憶》,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26頁。
t據穆旦檔案之《歷史思想自傳》(1955年10月)。
u周良沛:《穆旦漫議》,《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第1期。
v周與良觀點,見李方:《穆旦(查良錚)年譜》,《穆旦詩文集(增訂版) 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頁。
w說明:本處幾處省略號為本文作者所加,為省去若干不直接相關的文字。
x周與良:《懷念良錚》,杜運燮等編,《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頁。
y周與良:《永恒思念》,杜運燮等編,《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頁。
z易彬:《穆旦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