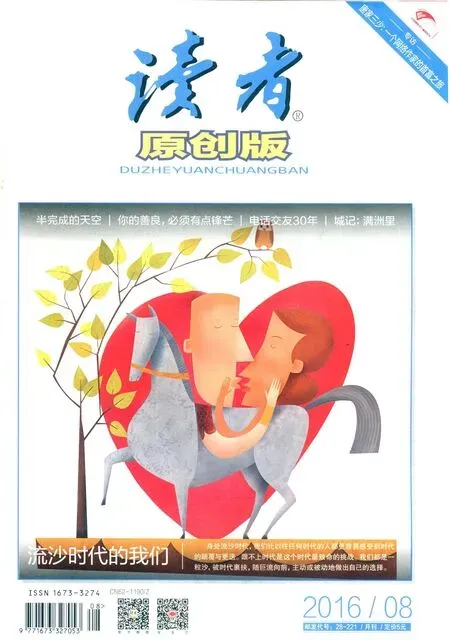逃學路上
文_盧十四
逃學路上
文_盧十四

每個人都有一段青春里的隱秘故事。我們在成長里獲得的所有真知灼見,都是在各種貌似不可告人的禁忌和秘密里無師自通。
“盧十四,你的作業呢?”
“忘帶了。”
“回家拿去。”
于是我垂頭喪氣地走出教室,到車棚取出自行車,騎出校門。然而,我并沒有往家的方向騎。
那一年我上初二,整個生活的核心、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學習。我的成績并不算太差,但無法令任何人滿意。我還有很多精力可以投入到學習上,但我就是不學。
對了,當時我差不多有3年沒看過電視了。每天回家吃完晚飯,我就必須回到自己的房間寫作業。“為什么每天學校的作業都要做到十一二點?”我爸問我,“你就不能早點兒做完?想給你安排點兒額外的學習任務都不行。”
如果早點兒做完作業的下場就是被安排更多的學習任務,我為什么要早點兒做完?難道我傻嗎?
所以,無論如何,我都要在房間里磨蹭到11點以后。我看閑書、發呆、口水流一桌子……像服刑一樣。
事實上,我連學校的作業都未必會完成。為了少做一點兒作業,我和我的同學們研究出許多辦法:想辦法瞞過課代表不交作業;算準哪些習題集老師不會細看,交“白卷”上去;早讀的時候借同學的作業來狂抄,有時候連抄都來不及了就胡編。有一次語文課上,老師說:“有些同學,寫作業很不認真,亂寫一氣。‘焚書坑儒’的名詞解釋,居然寫成‘燒書埋人’。”全班哄堂大笑,我笑得格外響亮,不知為何,老師狠狠瞪了我一眼。等作業發下來,我翻開自己的本子一看——白紙黑字,那個把“焚書坑儒”解釋成“燒書埋人”的居然就是我。
至于忘記帶作業,一開始是真的忘記了,老師就讓我回家去拿。很快我發現,當我沒做作業時,“忘帶”是很好的緩兵之計,一旦老師讓我回家去拿,我就趕緊跑到學校附近的江邊補作業。
作業其實也沒多少,10分鐘就補完了,但我不可能10分鐘就從學校到家走個來回。為了把謊扯圓,我得在江邊待夠20分鐘。我向后躺倒在石凳上,仰面朝天,看天上的云緩緩飄動……突然之間,我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放松。
一直以來,我的世界就是家和學校兩點一線。我要在固定的時間來到學校,在固定的位置上坐一整天;我要在固定的時間回到家里,然后在房間里坐到11點。我要靠瞞、騙、賴,去獲取一點兒喘息的機會。我可以在房間里趴在桌上睡覺,但不能出房間;我可以不寫作業,但不能被老師發現……這些喘息的機會如此有限,根本不能稱之為自由。
而此時此刻,周二上午9點,本應在教室里聽課的我,卻躺在江邊看云。雖然只有短短20分鐘,卻讓我從牢籠中暫時跳了出來。
20分鐘后我回到教室,心里多了一個支撐我活下去的秘密。
從那以后,我忘帶作業的頻率悄然提高了,而回家拿作業所耗費的時間也悄然增多了。很快我又發現,老師往往不會把“趕一個學生回家拿作業”這種課堂小插曲放在心上,他的注意力全在講課上,直到下課也沒注意到那個學生還沒回來。至于下節課的老師,多半也不會對班上出現一個空座位感興趣,無非是哪個學生請假了唄。
于是,我經常在上課時間出去游蕩一兩個小時。我明確地知道,這是在逃學。和那些強行和老師對著干的“暴力逃學”不同,我的逃學是“奉命行事”,因而極為隱秘。我深知這份隱秘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脆弱,如果我還想繼續擁有時不時逃一次學的自由,就要守護好這份隱秘,絕不能暴露。為此我要做好兩件事:一、逃學的頻率不能過高,否則勢必會引起老師的注意;二、這個逃學的方法只能我自己知道,連最好的朋友也不能與之分享。
既然不能分享,就只能一個人游蕩。我該去哪兒呢?我面臨著新的困惑。當然不能一直在江邊躺著。我的零花錢不多,對游戲廳也沒興趣,還有很多地方容易撞見熟人,都不能去。
最終,新華書店成了我的首選,鉆進去隨便找本書看,一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另一個好去處是小公園,那里有很多賣舊書的書攤,里面有很多新華書店里找不到的有趣的書,何況舊書很便宜,碰上自己喜歡的也買得起。
可是很快這兩個地方我都不太好意思去了,因為新華書店的店員、舊書攤的老板居然都認識我了。特別是舊書攤的老板,老遠看到我就打招呼:“小伙子,你又來啦!”這令我羞愧難當。我是一個正在逃學的中學生,我巴不得在人群中隱形。我不想被人注意、識破,在背后指指點點:“這個小孩也不知是誰家的,不學好,成天逃學。”
于是我只好回到江邊,繼續躺下看云。輕松愉快的感覺漸漸消退,我開始感到無聊、不安,甚至想早點兒回學校去。
初中生活已經開始兩年了,此刻迷惘無望的生活還看不到盡頭,偶爾回憶起無憂無慮的小學時光,感覺簡直像上輩子的事情。如此“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我望著天上的悠悠白云,不知該怎樣掙脫這一切,也并未意識到這就是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