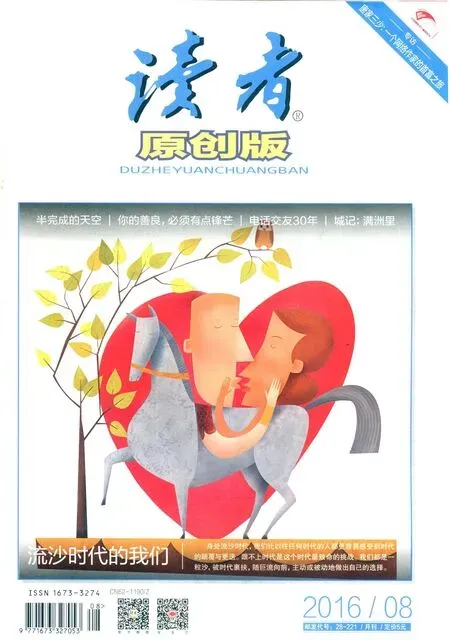最怕深夜“朋友圈”
文_一葦
最怕深夜“朋友圈”
文_一葦

我是一個正常的人,我的“朋友圈”是一個正常的“朋友圈”。和所有人一樣,大家看看新聞,曬曬春花秋月、美食旅游與娃,一切都在正常的范圍內。
可每天一過晚上11點,微信“朋友圈”里的人就都變了。
原本喜歡發工作內容的,曬出了電腦屏幕和手邊的一杯咖啡,給自己加油鼓勁,說天亮前一定能搞定方案;原本只是略微傷春悲秋的,在深夜紅酒的引誘下流露出了恨嫁的情緒,講自己單身20年好孤寂;原本喜歡參加各種講座、沙龍的,拍下了午夜時分閱讀的書頁內容,順道分享了自己對這段話的感想;原本喜歡拍朝陽(晨跑)與晚霞(夜跑)的健身達人,發布了跑步軟件的截圖——他今天又跑出了一個二環;而那些平素就喜歡曬甜點飲品的人曬出的午夜饕餮盛宴,更是要把人逼上絕路。
午夜,像記號筆,把每個人的特質又重重地涂抹了一遍。
犧牲午夜意味著犧牲睡眠,人們愿意為之付出睡眠的代價,以上的內容便從粗淺浮泛的“興趣”“愛好”“消遣”上升為了“生活方式”“理想”“情懷”。每個深夜,他們在獨處中認定了自己是怎樣的人。每一個深夜“朋友圈”里收獲的贊,又幫助他們進一步獲得了對自我的確認。
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著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書中提出了“擬劇論”的觀點。他認為,人性化的自我與社會化的自我存在差異。作為一個表演者,為了不讓觀眾們(不管是真實存在的還是假想的)失望,演員需要隱藏起真實的自我,表演出觀眾期待的角色。
角色也并不是完全統一的,正如莎士比亞在《皆大歡喜》中所說:“整個世界是一個舞臺,所有男女不過是這舞臺上的演員,他們各有自己的活動場所,一個人在其一生中要扮演很多角色。”例如,一個女人需要在丈夫面前扮演妻子,在公司里扮演職員,在兒女面前扮演母親。繼續細化,一個人需要在公益活動中扮演愛心人士,在高端晚會里扮演有修養的中產人士,在批發市場里扮演市井小民,在單位活動里扮演積極活潑、熱心助人的角色。
人們用心經營著自我形象,各類形象管理養活了不止一個產業:從書籍到媒體,到咨詢,到培訓。表演的動力有二:一是出于對“被社會排斥”的恐懼,一是源自對“理想自我”的追逐。這個世界里,似乎有不同的軌道通往每種形象的終點,一旦脫軌,往往不能再到達那個設定好的目標。人們對此很謹慎。
我是一個早睡早起的人,早上5:30自然醒,晚上10點已開始做夢。于是,無法成為觀眾,相較失眠的那些年,也少了很多焦慮。唯一的遺憾是不能及時給老板發的“朋友圈”點贊。
偶爾,我會在凌晨時段的“朋友圈”里發現一些憤世嫉俗的、消極厭世的言語。一會兒,這些內容又被作者刪除,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
還有一些人,會定期刪除早年發過的“朋友圈”內容,以及微博、博客、論壇發言,仿佛那個年輕的自己并未存在過。
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出于什么考慮,是保護隱私,還是角色調整。對,我也刪。我看著以前那個過度高瞻遠矚、憂國憂民的自己,有點兒厭煩。
深夜還是用來睡覺比較好。午夜的“朋友圈”,不一定是真實的“朋友圈”,也許是個夸張變形的“朋友圈”。
人有時生活在幻想里,并不比做夢更真實。以幻眼觀幻形,從哪里獲得真知?
圖_小黑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