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以不快樂
薛巍
英國社會學家威廉·戴維斯說,一些公司開始注重員工的幸福度,但這并不是一件好事。
快樂崇拜
一首新的神曲中唱道:“感覺身體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其實老板們早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英國社會學家威廉·戴維斯在《快樂工業》一書中說:“對資本主義最大的威脅要是缺乏熱情或活力呢?當代資本主義面對的也許不是暴力或明確的拒絕,而是工人的厭倦。沒有工人一定程度的獻身,生意就會遇到問題。近年來,這種擔心已經吸引了經理和政策制定者們的想象力。”
他介紹說,蓋洛普的研究發現,全球勞動力中只有13%的人上班時足夠賣力,在北美和歐洲卻有大約20%的員工“積極地閑散”。閑散表現為曠工、生病或只出勤不干活。加拿大一項研究提出,四分之一以上的曠工是由于筋疲力盡,而非生病。如今私人管理者不再需要跟工會談判,但他們面對著一個更加麻煩的挑戰,就是處理員工們缺乏動力以及持續的、輕度的精神健康問題。抵制工作不再表現為有組織的聲音或直接的拒絕,而是表現為缺乏興趣和慢性的健康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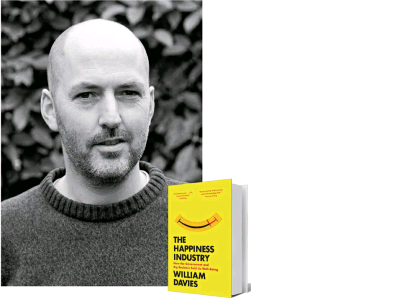
英國社會學家威廉·戴維斯與他的著作《快樂工業》
結果“快樂”這一概念從私人領域轉移到了公共領域。威廉·戴維斯說,越來越多的公司任命了首席幸福官,谷歌有人專門負責調動員工的情緒。兩年前,英國航空試驗了一種幸福毛毯,當乘客變得更放松時,毛毯的顏色會從紅色變成藍色,讓乘務員可以看到乘客滿意度的水平。
TED上有許多關于如何變得快樂的演說,如“想要更快樂嗎?活在當下”“東西越少越快樂”。全球幸福研究院院長尼爾·帕斯理查的演說《美妙生活的三個秘訣》已經被觀看了260多萬次。還有許多可以下載到手機上的情緒追蹤應用,如“快樂生活”“更快樂”“快樂化”,每一個都承諾它們將使用積極心理學和專注技術幫助人們擊退負面情緒,還說86%的客戶在使用兩個月后變得更快樂了。
快樂確實對工作很有利。一個快樂的工人的工作效率會高12%。所以關于人類情緒的科學是增長最快的操作型知識。快樂科學的先驅是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對于致力于把快樂最大化的機構來說,測量快樂是一個難題。邊沁提出了兩種克服這一困難的辦法。他認為快樂是一種復雜的愉悅的感受,他提出也許可以通過測量心率來把快樂量化。或者用金錢當作測量的標準:如果兩種不同的商品售價相同,那就可以假設它們能夠帶來相同數量的愉悅。邊沁更喜歡后一種方法。
積極心理學的倡導者理查德·萊亞德說:“快樂是終極目標,因為它是自明的善。如果有人問我們,為什么快樂很重要,我們給不出進一步的外在理由。它就是顯然很重要。”萊亞德這種觀點代表了當代思潮中一種很有影響的潮流。這種觀點認為,快樂或者滿足感是每個人都想要的。唯一的問題是如何得到它,對此積極心理學能夠給出方法。有了這種科學,政府就可以用以前做不到的方式來確保社會的幸福。
約翰·格雷說:“這是一種驚人粗糙的、頭腦簡單的思維方式。這么想的人不知道各種探索和質疑快樂的意義與價值的哲學著作。他們就像發明了這種思維方式的邊沁一樣。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就是自我實現,斯多葛派使幸福從屬于義務,歷史上許多思想家努力協調對幸福的追求與其他價值,而在邊沁看來,這些都是形而上的或者是虛構的。積極心理學的倡導者追隨現代功利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大部分倫理思考都已經過時或者無關緊要。”
快樂的社會維度
英國左翼哲學家特里·伊格爾頓在評論戴維斯這本書時寫道:“無疑每個人都希望得到快樂。唯一的問題是,快樂由什么組成,對于這一問題道德思想家們從未達成一致,可能永遠也不會達成一致。快樂是純粹的主觀感受,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測量?你可以毫無覺察地快樂著嗎?你只有在沒有覺察的情況下才能快樂嗎?會不會有人非常悲慘卻相信自己處于狂喜之中?在營銷研究人員和為公司服務的心理學家們看來,幸福就是感覺良好。但不公正和剝削的受害人不可能真的幸福,這是幸福技術專家們忽視的問題。所以亞里士多德談及幸福的科學時,稱之為政治學。”
伊格爾頓認為,用心理學來解釋工人們的不快樂是為了轉移人們對這一問題社會原因的注意。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就有一些心理學家說,問題不在銀行而在大腦。華爾街是受到了錯誤的神經化學物質的影響。交易員的睪丸素太高了。根據對交易員的腦部掃描開發的藥物能夠改善他們的決策。“在后資本主義的自戀世界,重要的不是你想什么、做什么,而是你感覺如何。而且人的感覺是無法爭辯的,這樣就很便利地隔絕了所有的辯論。人們四處走動時不停地自我監測,用應用程序跟蹤他們的情緒變化。資本主義老式的殘忍的、專橫的自我讓位給了更加溫柔的自我沉迷的自我。”
他說,戴維斯認識到,資本主義現在已經把對它的批判包括進來了。這一體系過去懷疑的東西如感情、友誼、創造性、道德責任,現在都為了利潤的最大化而被籠絡過去了。一位評論人士甚至提出免費發放商品,以便拉近與顧客的關系。有些雇主把漲工資當作送給員工的禮物,希望引發他們的感激之情,從而更努力地工作。好像沒有什么是不能被工具化的。但幸福的意義在于它本身是目的,而不是獲得權力、財富和地位的手段。對于從亞里士多德到阿奎那和黑格爾的倫理思想傳統來說,人的自我實現源于道德實踐,這完全是為了它自身的緣故。倫理學回答的是如何才能幸福。至于為什么要幸福,這不是它能解答的。
這一倫理傳統還拒絕把幸福跟它的物質環境分開。人們只有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才能全面發展。幸福跟我們的活動密切相關,它不是一種私人的精神狀態。我們是實踐主體,不是行走的意識狀態。一位經常被暴打的奴隸也許會說他很滿足,但這可能是因為他不知道別樣的境況。在這個意義上,幸福不是完全主觀的事態。有人也許以為自己很幸福,但其實那只是自我欺騙。
戴維斯說,不應該把個人的成長當作一種功利主義的目標。迪拜發誓要成為全世界最快樂的城市,還想出了無比精細的方式來收集幸福數據,有人提議用監控系統監視公共場所人們的面部表情。隨著科學日益精密,幸福指標以前被當作社會改革的基礎,挑戰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沉迷,現在卻被用作改變或者規訓個人的基礎。幸福成了個人的事業,每個人都要為之努力,就像去健身。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抑郁被視為一種認知或者神經上的缺陷,而不是環境造成的。這讓人覺得感受自己的感受成了每個人的責任,事情不對時就覺得自己失敗了。認為人們每天都應該特別快樂,這會使我們的日常生活成為病態。我們不能悲傷,不能心碎,也不能失望,不可以情緒低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