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教的圈子與成本
周琳曾親眼看到,老板教女教練要跪在地上抱住客戶大腿求買私教課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陳振華/北京報道
2003年初,吳承翰從臺北來到北京,成為北京青鳥健身中心私人教練部總監。
那時候,私人教練還是個新鮮詞。吳承翰到處講課,同一張PPT講了三年。如今,吳承翰成為北京浩沙健身俱樂部(以下簡稱浩沙)總經理,管理著對外稱“亞洲規模最大的連鎖健身機構”。
2005年,葉恩還在北京體育大學讀書。聽說私人教練很賺錢,為貼補家用,他就干了這行。而這一做,就是7年。
“像我這種做這么長時間私人教練的,很少很少。”葉恩告訴《瞭望東方周刊》。2014年,他創辦了北京子陽國際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簡稱V-lines健身私教工作室),現在北京已有5家連鎖店。
同一年,出于興趣愛好,謝奕煒放棄了職業經理人的工作,創辦了上海菁重健身有限公司(旗下為輕重健身工作室)。閑暇時,他還喜歡上知乎回答各種關于健身和私教的問題,他的簽名介紹是“魔都健身仁波切”,經營著上海的兩家店。
在體制內供職十幾年的周琳,觀察到了這股私教工作室創業的熱潮。2015年初,周琳決定下海,但他并沒有開辦私教工作室,而是辦了北京潤康體育發展有限公司,專注于運動康復。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說,“私教圈子太浮躁,而且私教工作室的經營模式并不理想,幾乎都在虧本。”
“十三金剛”來“傳教”
“中國的健身產業從1982年開始恢復發展。”中國健美協會秘書長古橋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彼時的健身,完全是個稀罕物。穿緊身衣,跳動作張揚的健身操,“人們觀望,又驚訝,又有點躍躍欲試”。

進入“后奧運時代”包括健身行業在內的體育產業迅速發展起來
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健身行業進入規范提升的階段。古橋介紹說,那時商業性的健身場所,還需要體育主管部門的前置審批,要對業務進行指導和監督。
“后來‘簡政放權,體育主管部門不再參與管理,健身機構的設立完全由工商部門按照一般商業機構的模式操作處理了。”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中心職業技能鑒定管理部主任羅軍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健身機構的確越來越多,但人們的參與熱情并未同步增長。2003年3月,吳承翰來到北京時,驚訝地發現人們幾乎不怎么運動。
“來北京沒多久,‘非典就暴發了,之后我才看到,大家買羽毛球拍,廣場上跳操的人也越來越多。”吳承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他看來,“非典”讓更多人“動了起來”。
也是從那時起,吳承翰開始宣傳私人教練。他從健美比賽中發掘了13名冠軍級選手,帶著他們到各地巡回比賽,還讓他們學跳舞跳操,接各種活動,向大家展示健身后的肌肉和身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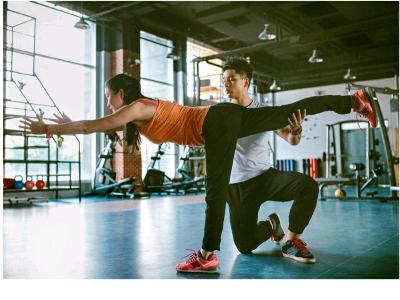
在北京V-lines健身私教工作室,客戶以女性居多,圖為私教為一名女學員上課
“當時知道的人太少,就采取‘健美先行的模式開展宣傳,告訴大家通過私人教練的幫助,也能把身材練得像他們一樣好。”吳承翰說。
最轟動的一次,是他帶領“十三金剛”上了2004年的央視春晚,表演了《陽光健身房》舞臺劇,一時間熱潮涌動。
古橋也觀察到,“非典”之后,全民體育的熱潮開始興起。只是對于健身行業而言,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還需要再等5年。
“2008年北京奧運,極大推動了體育運動發展。進入‘后奧運時代,國家也開始將推動體育產業發展并入到之前的推動競技體育和全民體育發展的規劃中來。”古橋說。
價格連續翻番
2008年,吳承翰跳槽來到北京浩沙健身俱樂部。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了巡場教練。
“以往健身房會有巡場教練,但并沒有很好地指導會員鍛煉。”吳承翰把巡場教練調教成了私人教練,力推私教業務。他也從私教課程中,發現了巨大的潛力。
“2000年初,私人教練每節課有可能到30元,十分低。2003年的時候提高到70元左右。我來到青鳥健身,直接將價格提升到150元,翻一番。”
逐漸地,吳承翰開始給從業人員講課,普及私教需要了解的運動、生理、營養等各方面的知識。他自己操作的私人教練試點項目,在2005年單店做到150萬元的營收,頗受業界認可。
那時候,私教開始火起來。葉恩也會在課余時間兼職私教,動力自然是收入,“做得好的甚至能月入上萬。”
2006年,吳承翰講課用的PPT終于“下崗”,因為私教的基本理念已經被大家接受。他觀察到,不管是大型連鎖健身房,還是小型私教工作室,都開始出現專門的私人教練業務。
10年之后,吳承翰已成為北京浩沙健身俱樂部總經理。如今浩沙健身在全國有88家店,30余萬名會員,以及800~1000名私人健身教練。
此時,每節私教課的價格又翻了一番,達到300~500元。
不過吳承翰也坦言,從一個大型連鎖健身俱樂部的角度而言,私教業務不應是利潤的主要來源。
“假如健身房掙100元,可能靠售賣會員卡掙80元,私教只占20元的比例。但話又說回來,如果一個健身俱樂部沒有了私教業務的利潤,它是不掙錢的。”吳承翰說。
“抱大腿”強賣課程
2015年國家體育總局職業技能鑒定指導中心發布的《2015中國健身教練職業發展報告》顯示,健身教練行業的職業信心指數是80.4分。
“這說明健身教練這一行當有很強的吸附能力,如今月薪過萬還是比較輕松的。”羅軍說。
但是,真正能啃下這塊硬骨頭的,并不多。
葉恩向本刊記者回憶,他剛當私教的2005年,一起做的年輕人有十幾個,一個月后,只剩下他還在堅持做。“這一行看起來賺錢輕松,但實際上壓力很大。”
壓力來源于私教背負的經營指標。盡管這在業內諱莫如深,但在行業里浸淫了十幾年的周琳對此看得很清楚,“一個新人,要背十萬八萬的課程銷售任務,他怎么完成得了?”
周琳還透露,一些健身機構在和教練簽合同的時候明確提出,若完不成任務,提成和獎金全部沒有。而健身教練的基本工資并不高,每月只有2000~3000元。于是,一些扛不了的年輕人試了個把月就會流失。
“私教很亂很浮躁,也體現在這里,大家都想賺快錢。甚至于在他們做內部培訓的時候,根本不是教技巧和專業知識,而是教怎樣不擇手段地兜售課程。”周琳就曾親眼看到,老板教女教練要跪在地上抱住客戶大腿求買私教課。
健身房里兜售私教課程,套路輪番上演,也成為消費者煩不勝煩的事情。有時候,一聽消費者推脫說沒錢,教練會按套路演一出先把錢墊上的戲碼。“最終目的就是讓你抹不開面子,買課程。”周琳說。
或許是飽受賣課之苦,葉恩自己成為老板后,并不要求私教賣課,而是更看重教練維護客戶的能力。
“我們會給新教練指派一批學員,一個月下來看續訂課程的有多少,把這個作為考核的主要指標。”葉恩介紹說,根據續訂和新開發客戶的數量,獎金會有所不同。當然,表現太差的教練依然會被炒掉。
致命成本
2014年創辦V-lines健身私教工作室時,葉恩拉著合伙人和親戚朋友,在北京朝外Soho開了家90平方米的小店,總共投入60萬元。
這算是很正規的起步了。周琳見過更簡陋的:“兩個架子,一套啞鈴,工作室就開始運作。”
同年在上海開辦輕重私教工作室的謝奕煒則發現,一二線城市里跟風開店的工作室越來越多,但質量良莠不齊。
“成立一個健身工作室的啟動資金,不同地區、不同大小、不同檔次,差異很大。民宅里開一個小面積的,可能只要三四萬元,而在商場里做一個1000平方米的豪華店,可能需要上千萬元。”謝奕煒說。
兩年間,葉恩已經在京廣橋、國貿、望京等核心商圈陸續開了5家店,V-lines逐漸成為一家中型連鎖私教機構。他更傾向于在核心商圈開私教工作室:“因為只有在這些地方,才有私教服務的高端人群市場。”
然而,這也帶來了更高的成本。
“餐飲業可承擔每天每平方米10元錢的租金,健身行業則只能承擔三四元錢。”吳承翰透露,浩沙選址有三個原則:有住戶、有商圈、租金便宜。
葉恩的店,每天每平方米的租金要5~6元,再加上器械、裝修等硬件設施的投入,成本壓力十分大。
這成為私教工作室的悖論:不開在好地段沒法攬來高端客戶,開在繁華商圈或高檔住宅區成本又太高。
同時,教練的人力成本也很高。
吳承翰告訴本刊記者,浩沙的私人教練工資水平每月在8000~10000元之間,在業內算是中上水平。
相較于傳統的售賣會員卡的盈利模式,私教的人工支出更多。
“這是因為,賣會員卡掙100元,除去銷售人員所得,健身房還能得到80元利潤,但是私教業務,機構要分40%~50%給教練,自身最多賺50元。”吳承翰解釋說。
與擁有較強議價能力的大型連鎖健身機構相比,私教工作室的壓力更大,因為它們基本上不賣純粹的會員卡而只賣私教課程。
“正是因為成本高企,逼得工作室向私人教練施壓,將教學服務演變成營銷售課,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周琳還透露,他估計80%的私人教練工作室都在虧錢。
這與吳承翰的判斷一致,他甚至覺得,私教工作室不是大型健身房的競爭對手,“前者在高成本下,沒有盈利模式”。
吳承翰坦言,私教業務不是浩沙的重點,就在于成本壓力過大。
私教的未來
據吳承翰介紹,在美國,私人教練工作室通常圍繞在大型健身房周邊,并且專業化程度高。
“因為大型健身房是比較基礎的設施,私人教練工作室提供更專業的設施和教練指導,要通過大型健身房引入客流,才可以實現盈利。”吳承翰判斷,未來私人教練會朝更細分、更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2013年起,他在北京一家健身房進行了這樣的專業化嘗試,專做節奏普拉提訓練,如今這家健身房私教業務占總營收的60%,超過了會籍業務。吳承翰認為這被驗證是可行的。
在葉恩看來,維護好客戶、做好質量,顯得更為關鍵。畢竟,如今能夠消費私教服務的,都是收入較高的人群。葉恩的經驗是,與他們成為朋友,不但能拿到更好的租金、管理方面的資源,甚至能直接從他們那獲得投資。
“我最初的60萬元啟動資金,就有客戶給我投了20萬元。我覺得做私教生意,現階段不應該強調賺錢,更重要的是與‘高管人群建立聯系,有高質量的口碑,才能做得下去。”葉恩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