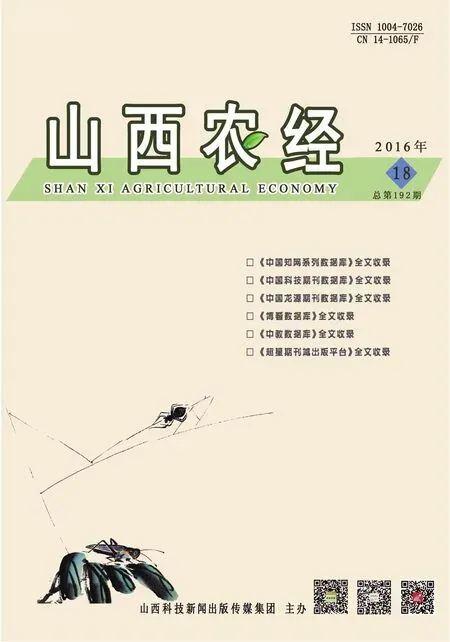山西票號業在時空變遷中沒落原因初探
□高洪山 王安菊
(臨汾市第一中心學校 山西 臨汾 041000)
山西票號業在時空變遷中沒落原因初探
□高洪山 王安菊
(臨汾市第一中心學校 山西 臨汾 041000)
本文以《山西票號史料》中山西票號的時空分布史料為核心,以票號業的時空演變過程來探討其空間結構特點,并分析其衰落的原因。這正是在歷史課程核心素養之歷史時空觀、史料實證、歷史理解、歷史解釋與歷史價值觀的指導下深挖歷史教材,契合高考素養立意要求而進行的研究。
票號;時空變遷
山西票號是中國近代金融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掀起了一個研究高潮,出版了大量相關著作,而史料方面集大成者即為《山西票號史料》[1],該書是目前出版的票號史料總收集最豐富的史料匯編。在人教版高中歷史必修二課本第三課《古代商業的發展》中僅在“歷史縱橫”有提及,這不足以讓學生對票號有充分理解。本文試圖以山西票號業的時空分布變遷為脈絡,探討其時空演變規律,進而揭示票號沒落的各種原因。
1 山西票號業在全國主要工商業城市的分布狀況
晉商票號的興起根植于今太谷、平遙、祁縣三縣地方活躍的民間商業活動。“自有明訖于清之中葉,商賈之跡幾遍行省。”[2]“足跡遍天下,執各大埠商界之牛耳。起家之數十萬者,尤為(太)谷人之特色。”[3]至同治后期光緒初期,票號業迅速風行于在外省經商的山西商人。
凡長江各埠之茶莊、典當、綢緞、絲布業及京津一帶營皮毛雜貨業之晉人,群起仿辦,往往于本號附設置票莊。[4]
這就使得票號業一開始就利用了山西商人的商業網絡迅速打開了局面,在五口通商口岸或其臨近地區,山西票號也如雨后春筍,迅速占領各個工商業城市和交通樞紐城市。據不完全統計(見下表)。

表一 同治光緒時期主要工商業城市票號設立表
這一時期在南方地區興盛的票號業因服務于國內大宗貿易而異常繁榮,在通商口岸更為發達。
上海與國內各地交易繁盛,每年已有億萬兩之巨額,而其轉送正貨所以極少者,賴有票號為之周轉,而彼此用相殺法也。[17]
票號代替了大宗貨幣的周轉流通,極大地提高了資本流通速度,在這些商業發達地區的繁榮自然可想而知。此外,太平天國和同治回亂時京杭運河和西北地區交通阻隔,票號也承擔了地方稅收和軍餉匯兌業務。
軍興以來,藏富于官,票號結交官場,是以存資日富。[18]
同治光緒時期,西北軍餉和京餉運輸也更多依賴西北地區的山西票號。
節次代解四川京餉、劃撥滇省軍餉,并由滇省匯兌。[19]
綜上可見,票號早在同治初年,便憑借晉商的商業地位和官方的倚重而迅速擴張。從地理上看,票號業已經形成了以山西為總部核心區,以京師、上海、漢口等為重點,輻射各個省會的空間結構,幾可稱其“匯通天下”。
營業區域極廣,不但在中國內地十八省,即使在蒙古新疆等邊遠地區,也有分號或來往商號。[20]
經過三十年的發展,票號的空間分布更加均衡。南方省會和交通樞紐也出現了票號業的分號,南下擴張明顯。而上海、漢口的票號業進一步發達,東南沿海通商口岸的票號空白區被填補,而且又擴散到經濟上較為落后的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整體上呈現出以京師、上海、漢口為核心而空間覆蓋更為均衡的地理特征。
從全國的視野來看,山西票號以京師、上海、漢口為最盛。
票號以北京開設為最伙[火]。各號均在北京設有分號。與前票號之往來,均以官家交易為主。北京為官吏之中心,不啻亦為票號營業之中心。各號存款、放賬以及匯劃事項,均以北京方面之交易額最巨。[21]
上海是全國第一大城市和外貿口岸,工商業發達自不必說,故有日人說:
上海與各地之交易,關系為最多,票號之數因是特盛。[22]
前所述中,福建山西票號本不多,在19世紀末,亦在廈門開設分號。
廈地生意向稱繁盛,(山)西幫票號有五六家之多。[23]
而曾經的天下繁華地——蘇州,山西票號勢力也十分強大。
票號皆為山西人所開設,…資本至厚,信用亦深。…票號可謂為大銀行…一店資本產業之總數,至少亦必在數十萬兩以上…[24]
以上史料都可見此時的山西票號如日中天的盛況。
2 山西票號衰敗的時空過程
在晚清票號名噪一時的同時,其衰敗的表現也逐漸顯露,從地理分布的角度來看,在一些重要的通商口岸,票號逐漸不敵當地和外國的金融機構,先前提及有數家票號的廈門票號在1895年后就展露疲態:
近數年來自臺割后,生意日漸頹敗,…,咸各收賬款歇業歸去者已有五家,刻只有”新泰亨[厚]”一家,可見商務之衰矣。[25]
而廈門票號業的衰落預示了全國范圍內票號業空間結構的崩潰。
此外,曾經分號數量僅次于北京的天津,票號雖仍較多,但大勢已去:

表二 各票號主要分號撤存一覽表[26]
“經光復之后,南方之山西票莊,倒閉凈盡,而天津之票莊,尚存留十余家。然營業范圍。均已縮小。又有本地錢莊與新式銀行競爭,故已成強弩之末。”[39]
先前票號業在長江流域的兩大重心上海和漢口,票號分號也急劇減少。而北京、天津雖然在分票數量上仍據前列,但也跌去一半。在殘存部分的空間結構來看,票號除了固守北方業務核心區京津以外,整體上被新興的銀行業向西北壓迫,票號業曾經的南方重鎮上海和漢口,其分號數已經下降到全盛時期省級中心的位置,在隨后幾年間被徹底逐出中國金融業的核心地區,而廣州等嶺南地區票號,更是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被一掃而光,這種自東南向西北的整體空間重心的位移,恰恰從地理上反映了票號業被新興銀行業所取代的歷史趨勢。
至1932年,全國保有票號之名的金融機構只剩兩家,基本宣告票號業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3 票號衰落的原因
自19世紀20年代,山西票號作為中國金融業的典型代表叱咤風云,一度執全國金融之牛耳,但入20世紀后,其發展江河日下,清亡后急劇衰落,個中原因值得深思。
3.1 票號牽涉政治過多,對官方與官員資金依賴很深,清亡受到極大沖擊
票號一面大量吸收清政府的利息很低的公款和官員的私款[40],甚至淪為官員儲蓄贓款的機構[41],另外又高利放貸,坐收巨利。其“認票不認人”的匯兌制度為“本票”淪為行賄工具[42]大開方便之門,這些都使得票號業與清政府牢牢捆綁在一起,無形間削弱了對政治風險的抵御能力,也使得票號在金融創新上畫地為牢,錯失了近代金融轉型的契機。如清朝滅亡,與官方關系最為密切的北京票號便應聲而落。
“(北京)官家款項,固已無染指,即私人交易,為數亦缺,尚不及爐房猶能在當地保其固有能力也。”[43]
3.2 票號業運營管理不力或依附于畸形產業,導致難以為繼
如西安票號就是運行混亂的代表:
“于金融業界最占勢力,唯資本雖厚,而組織不良,營業除匯兌外,濫放款項,漫無限制,以致光復后被累甚巨,難以繼續,宣告破產者不一而足。即存在者,亦以周轉不靈,停止營業著手清理。”[44]
廣西梧州票號則依附于煙土種植業,禁煙后業停則號亡:
“票號昔有百川通、新泰厚等四五家,專事云貴川各省匯兌。唯自煙禁以后,無業可營,均經收歇矣。”[45]
3.3 時局動蕩造成正常業務被迫停止,資金鏈發生斷裂
如河南票號的資金鏈斷裂就是此種情形:
“時值荒亂,紛紛提款,其零星小戶到號強迫,而外欠之款則收不回來者。此種情形,大抵本不虧空,特一時被擠,無可支持,如“日升昌”等號。大抵為三者之中,實以此種原因為最多數。”[46]
而山西總號在北方地區的困頓則是因地方形勢不穩,商業陷于停頓:
“辛亥以后,南中秩序不靖,銀根緊急,票號業因之縮減至最低度。…北方則活佛肆虐,白狼奔跳,內外蒙、甘、陜與直隸之張家口等處貿易全行歇絕。”[47]
3.4 其自身在金融業中的落后性注定了其要退出歷史舞臺,日人在這方面有著精辟的論述
“革命后成立共和政體,以上種種關系(指票號經辦清政府和官吏的款項)為之根絕。相反,中國、交通等銀行陸續成立,及外國銀行在北京設置分行,他們所經營的各地間之匯兌業務,準確而且敏捷,使票莊這一方面的業務全被奪去。而其從前利用各地銀兩之差異,乘機在匯兌手續費用上取得暴利。現在完全以銀元為匯兌金額,不僅不能如往昔的有利可圖,而其匯兌比新式銀行需要較多的時日,一般官民感到不便,存款也就因此減少。加以各票莊的南方分號放款收回不順利,來源更為涸竭。照他們目前的狀態,在金融上已到了不足道的地步。”[48]
注釋:
[1]中國人民銀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財經學院《山西票號史料》編寫組、黃鑒暉:《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
[2](民國)安恭己撰:《新修太谷縣志序》,《太谷縣志》,1931年,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第18頁;
[3](民國)仇曾佑:《新修太谷縣志序》,太谷縣志,1931年,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第18頁;
[4]王孝通:《中國商業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18-219,頁,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 19頁;
[5]“至于上海的票號,究以何家分設最早,今日已極難查考。”《上海通志館未刊稿》,丙“金融機關<一>”,第2-3頁,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8頁;
[6]據各年匯兌京協餉奏折,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9頁;
[7]據各年匯兌京協餉奏折,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9頁;
[8]“匯兌票局向只協同慶、新泰厚、蔚長厚鼎足而三”,《廈事匯登》,《申報》,1888年7月6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60頁;
[9]《上海通志館未刊稿》,丙“金融機關<一>”,第2-3頁,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8頁;
[10]既明:《漢口之錢業》,《銀行雜志》,第1卷第22號,1924年,第1頁,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62頁;
[11]葛元煦:《滬游雜記》卷四,《山西匯業》,光緒二年(1876年)刻本,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8頁;
[12]《申報》,1879年5月25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9頁;
[13]光緒七年九月《冠裳萃會》山西太汾兩府眾票號同立,《漢口山陜西會館志》,卷下,第14頁,這一數目尚未包括全部在漢山西票號,同年同月有“天地同流”匾額,還有另外數家票號,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64頁;
[14]“山西上海匯業公所碑文”,藏于上海博物院,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9頁;
[15]《答暨陽居士采訪滬市公司情形書》,《申報》,1884年1月12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8頁;
[16]《廈事匯登》,《申報》,1888年7月6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60頁;
[17]潘承鍔:《中國之金融》上冊,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第52頁,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9頁;
[18]《答暨陽居士采訪滬市公司情形書》,《申報》,1884年1月12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8頁;
[19]《山西巡撫英桂折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朱批》財政類,卷號34-40,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61頁;
[20]《北京金融談》,《東方雜志》第14卷第4期,第149—151頁,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318頁;
[21]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永瀧久吉明治三十九年(1907年)報告,見潘成鍔:《中國之金融》上冊,第52-53頁,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290頁,
[22]《中外近事福建票號收莊》,《大公報》,1903年5月17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316頁
[23]日本駐蘇州領事白須直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九月二十五日報告,轉引自潘成鍔:《中國之金融》下冊,第26-28頁,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321-322頁;
[24]《中外近事福建票號收莊》,《大公報》,1903年5月17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316頁;
[25]《北京金融談》,《東方雜志》第十四卷第四期,第149—151頁,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318頁;
[26]雙一:《中國各省錢業調查錄(續),《錢業月報》,第3卷第12號,1924年,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41頁;
[27]《漢中歸客之談話》,《大公報》,1915年12月21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41頁;
[28]《河南票商慘狀述聞》,《大公報》,1915年7月3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43頁;
[29]《汴省外縣商況志要》,《大公報》,1915年3月13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43頁;
[30]曲殿元《中國之金融與匯兌》,(上海)大東書局,1930年,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39頁;
[31]《訪問連成甫先生記錄》,1980年5月23日于武漢市,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40頁;
[32]《訪問武炳文先生記錄》,1980年5月24日于武漢市,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40-541頁;
[33]《訪問武炳文先生記錄》,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41頁;
[34]《北京金融談》,《東方雜志》,第14卷第4期,第149—151頁,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318頁;
[35]雙一:《中國各省錢業調查錄(續),《錢業月報》,第3卷第12號,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41頁;
[36]雙一:《中國各省錢業調查錄(續),《錢業月報》,第4卷第5號,第55頁,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46頁;
[37]《河南票商慘狀述聞》,《大公報》,1915年7月3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43頁;
[38]《山西之滄海桑田觀》,《大公報》,1915年3月26日,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44頁;
[39]《支那省別全志》,第18卷,第999-1001頁,轉引自《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536頁;
1004-7026(2016)18-0005-04
F832.9
A
DOI:10.16675/j.cnki.cn14-1065/f.2016.18.002
高洪山,男,1963年出生,山西省臨汾市人,中學高級教師,長期從事歷史教學研究工作。
王安菊,女,1965年出生,山西省堯都區人,中學高級歷史教師,長期從事歷史教學工作。